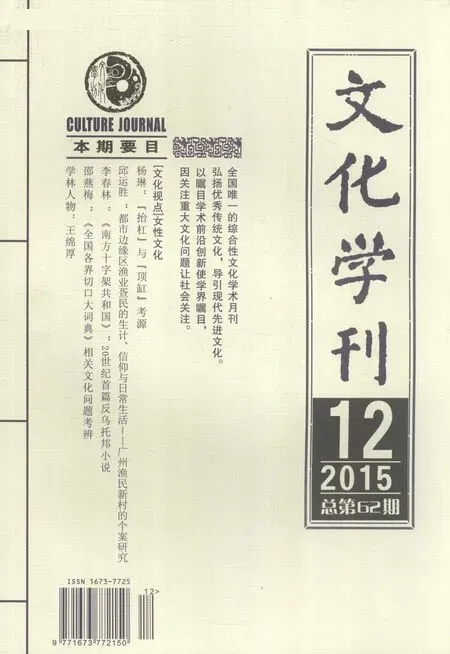《南方十字架共和國》:20 世紀首篇反烏托邦小說
李春林
(遼寧社會科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1)
談及反烏托邦小說,通常都會指出其代表作有俄羅斯作家葉甫蓋尼·扎米亞京的《我們》(1920),英國作家奧爾多斯·赫胥黎的《啊,神奇的新世界》(又譯為《美麗新世界》,1932)和同為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1984》(1949),美國作家列依·布雷德伯里的《華氏451 度》(1953)等。學界還認為,兩位英國作家的作品受有扎米亞京的《我們》之影響,甚至奧威爾都說赫胥黎的作品明顯受有《我們》之影響,盡管赫胥黎本人并不認同,然而,一個清楚的事實是在上述名單中,《我們》問世最早,因此被認為是20 世紀第一部反烏托邦小說,連俄羅斯文學史家符·維·阿格諾索夫主編的《20 世紀俄羅斯文學》亦持此種觀點:“扎米亞京早在1920 年完成的長篇小說《我們》,它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20 世紀第一部反烏托邦作品。”[1]
事實上并非如此:寫于1905 年的勃留索夫的《南方十字架共和國》,才是20 世紀第一部反烏托邦作品。
瓦列里·雅科夫列維奇·勃留索夫(Вале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Брюсов,1873-1924),俄羅斯著名詩人、小說家和文藝學家,俄羅斯白銀時代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作為俄國象征主義文學的一代宗師,其成就不獨表現在詩歌方面,在小說領域亦多有建樹。短篇小說《南方十字架共和國》即是其代表作之一。
作品寫于俄國1905 年革命之際。其主旨在于揭示烏托邦國家的荒謬性和潰敗的必然性。盡管作品最后也安設了一條光明的尾巴——國家還是被拯救,但顯然并非作品所要傳達的主旨。
在此作中,作家仍采用以“面具化”的敘事策略來敘述故事的創作方法,以一位記者的新聞報道形式來講述這個故事,借以增強其現實性和現場感。這個南方十字架共和國位于離南極地區不十分遙遠的南半球,與澳大利亞較近,給人的感覺似乎是新西蘭——新西蘭的國旗上即有南十字星座的圖案(其實與新西蘭風馬牛不相及)。作品重點描繪共和國的潰敗過程及場景,同時回敘了共和國的種種驚人之舉,其烏托邦的種種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諸多方面的設施和舉措。
在政治方面,“共和國的憲法仿佛是極端人民政體的體現”[2],但實際上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冶金工廠(當然是“國企”)的勞動者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從這些勞動者中通過全民投票的方式選出代表進入共和國立法院,它了解國家政治生活中所有問題,但無權改變國家的基本法律。國家的真正權力掌握在“原托拉斯創建人成員”(南方十字架共和國本是由坐落在南極地帶的鑄鋼廠托拉斯所組建)的手中,他們把自己人選任為工廠經理,由經理們組成委員會,領導整個國家。立法院只不過是委員會的意志的執行者。國家政治生活的運轉依憑著“無情規章制度”。“在自由的外表下面,對公民的生活進行了極嚴格的限定。”[3]委員會保持著龐大的密探編制及秘密警察。“工廠里到處都是委員會的爪牙”,“市面上由民衛隊維持秩序”[4],委員會也絕不放棄政治兇殺手段。這個國家事實上是以“民主的外貌”掩飾著的“純粹專制政權的暴政”[5]。
在經濟方面,勞動者不領取任何薪金。在工廠工作二十年的公民的家庭以及死亡的或工作期間喪失勞動能力的公民的家庭領取豐厚的養老金。經理們執掌著工廠的經濟命脈。數以幾十億的錢款流經他們之手。而其收支差額往往大大超出國家預算。經理委員會確定價格,而他們確定的價格制約著整個世界上幾百萬勞動者的工資。他們甚至可以使得一系列國家崩潰。
在文化方面,最突出的一點是極為嚴格的書報檢查制度。所有出版物都要接受嚴格的檢查,任何旨在反對委員會專制的文章不可能被放過,而且整個國家都確信這個專制有著良好的作用,排字工人自己就會拒絕排印批評委員會的文字。同時,這個國家又吸引著全世界的名人都把自己的才華帶到這里。這里上演過最優秀的歌劇,舉辦過最優秀的音樂會和展覽會。
在社會生活方面,國家為工廠勞動者的生活安排了所有可能的方便設施,甚至包括奢侈品。漂亮的房間、精致的桌子、教育機構、娛樂場所、圖書館、博物館、劇院、音樂會、體育場館,一應俱全。孩子的培養和教育、醫療與法律服務、舉行各種宗家儀式,均由國家負責。而首都星城的居民更是幸福,他們根本不用工作,是國家的“食利者”(若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則是“寄食者”)。他們從國家領到的錢使他們可以闊綽地生活。對于形形色色的生意人和企業主來說,這是一塊風水寶地。因之,星城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城市之一。
這個國家的社會生活的最大特色還是它的張揚共性、泯滅個性。所有建筑物的高度和外形都相同,而且墻上沒有窗戶(一律在內部用電照明)。提供給勞動者的所有住室的裝飾式樣高度同一。大家都在同一時間領取同樣食物。國家發放的衣服也是從無任何變化的同一式樣。每天在固定時間之后禁止外出。
以上種種令我們想起扎米亞京的反烏托邦小說《我們》。
讓人更加深長思之的是勃留索夫對南方十字架共和國潰敗的初始原因的剔挖:一種致命的流行性傳染病——“矛盾躁狂癥”。
此種“矛盾躁狂癥”初名“矛盾病”。但早在20 年前在共和國已有偶然的單發病例。其癥狀主要是病人們總是自己與自己的愿望相矛盾:想要一種東西,卻說著和做著另一樣東西;本想說“是的”,卻說出“不是”;本想往左轉,卻轉向了右邊。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美丑易位。對于矛盾和斗爭更是情有獨鐘,整個社會充滿了焦躁和暴戾情緒。隨著病情的發展,病人的話變得不可理解,其行為變得很是荒謬乃至殘忍暴虐。許多人自殺,兒童被任意虐待,在首都,市幼兒園兩個阿姨居然割斷了41 個孩子的喉嚨。兩個警察用榴彈炮向散步的人們射擊,死傷慘重。整個社會籠罩在一片對前所未有的巨大災難的不可遏止、不由自主的恐怖中。于是大逃亡開始了。高官和富人是始作俑者。后來,軍隊、警察、醫護人員等都參加了逃亡者大軍。“逃跑的企望成為一種狂癥。所有的人,只要能跑都跑了。”[6]很快,全體居民的三分之二都離開了。然而,城市仍是到處能看見“矛盾躁狂癥”患者,他們殺人、搶劫、縱火、強奸,無惡不作。城市食品、藥品、日用品等嚴重匱乏。在“矛盾躁狂癥”的控制下,火車司機本想避免翻車,卻總是將列車顛覆,結果導致交通斷絕。人們開始大批死亡。同時,還有一些人到賭窟、淫窟等處垂死狂歡,借以忘卻可怕的現實。世紀末情緒彌溢國中。隨著電站職工在“矛盾躁狂癥”發作時搗毀了機器,整個城市陷于黑暗。“隨著黑暗的降臨,城內殘存的紀律徹底崩潰了。恐怖與瘋狂完全控制了人們的靈魂。[7]”“所有的人身上極迅速地暴露出道德感情的淪喪。文化修養仿佛是幾千年長出來的薄皮,從人們身上脫落了。”人們不單殺人,而且吃人,“用孩子的肉來滿足自己身上蘇醒的吃人的本能”[8]。男女之間像畜生般淫亂,他們異化為“人狀生物”。整個首都潰敗了,并且迅疾波及到全國。
在這潰敗過程中,唯一的亮點就是首都星城市委員會主席奧拉斯·基維爾欲挽狂瀾于既倒而不得的最后斗爭。他也是整篇作品中唯一較為豐滿的人物形象。這個人物有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他堅定、果斷,牢牢地掌握著經過合法授受的權力,實行一系列非常舉措,對整個城市實行專制統治,將全市的資金、民警和企業均攬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便于與嚴重的無政府狀態進行斗爭。他恢復了已經中斷了三個世紀的死刑。他下令為了減輕“幾千人在最后的日子里的痛苦”,讓他們“在醫院里,在精心護理下死去”[9]。當伍埃金格建議殺死所有病人,認為在此之后傳染病將會停止流行,并且他及其支持者將此種主張付諸實踐,開始大開殺戒之際,基維爾則把自己的工作人員編成義勇隊,與之進行斗爭,盡管雙方死傷慘重,最后還是捉到了伍埃金格。
其次,在實行專制統治的同時,他又稟賦著一種濃烈的仁愛精神。正是由于他堅定地維護社會法紀,才使得幾十萬人獲救,從而得以安全地離開這個城市——他并不阻礙這些人們的離去,而是尊重他們的選擇。當食物嚴重短缺之際,他為留下來或者未來得及逃亡的人們建立了城市面包房和大眾食堂。交通斷絕之后,有2000 人擬步行出城,基維爾極力勸阻無果,于是,親自為他們提供衣食。基維爾雖說不能幫助所有的居民,但在市政局大樓里為所有仍保留著理性的人安置了棲身之地。在市政局閉門不出的人們中間也極少出現病人。這就是說,他試圖設置一塊沒有“矛盾躁狂癥”的理想鄉,并且得以短暫地實現。基維爾在自己的不大的團體里維持了紀律,直到最后一天。
第三,基維爾具有一位領導者高度的責任感和為大眾利益而英勇獻身的自覺的悲劇意識。他“關注一切,領導一切”,“不知道休息”。基維爾有先見之明,預見到城市早晚有一天會整個停電,提前準備了火把和燃料倉庫。誠然,他的所作所為并非絕無使人非議之處,例如他對幾千已經毫無救治希望的人實行“安樂死”,不知彼時南方十字架共和國是否有此種立法。然而他清醒地認識到自己不僅要對當下負責,也要對歷史負責。他對潰敗過程中的種種均記錄在案,以作為向歷史的交代。最后一次記錄寫于7 月20 日,這一天,瘋狂的人們開始向市政局猛攻。基維爾寫道:“春天之前等到援助是不可能的。春天之前靠現在處于我支配下的儲存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但我將盡職盡忠。”這是他最后的話。后來他英勇犧牲在自己的崗位上。其所昭示出來的不獨是一種韌性戰斗精神,更是一種自覺的悲劇意識和英雄情懷。
這篇作品給人以如下警示:
其一,烏托邦的理想雖然美妙,但真正地實踐起來卻問題多多。就以此作而言,那些高福利始終未能在全民中實行,僅在所謂國企中保有。另外,名實不符之處繁多,號稱工廠歸國家所有,其實廣大工人根本沒有參與管理的權利,經理們才是工廠的實際所有者。
其二,在烏托邦國家,所謂平等、民主等均是美好的詞匯,實際上往往倒是其反面。在作品中,高官們擁有種種特權,普通民眾卻只能俯首帖耳。民主徒具外貌,實質上是專制暴政。
其三,筆者以為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烏托邦社會對人的個性的壓抑,它將人異化為物和機器。而人總要有表現自己個性的強烈欲求,但又總不能得到滿足,于是必然會產生種種焦慮感,或曰如作品中所表現的“躁狂癥”。而被更具體地稱之為“矛盾躁狂癥”,這是由于這個國家到處是名實不符、言行不符的矛盾所養成。“小說中所幻想的那種‘矛盾嗜好病’,本來是人的意識受壓抑、心里受挫折而生成的一種生理病癥,它表現為那種喪失理智后的人身上一種驚人的偏執狂:一個勁地要破壞(既自我摧殘又摧殘他人)的欲望。”[10]人們的心理矛盾沖突與整個國家社會各方面的矛盾沖突事實上是一種同構關系。兩者互相發明、互為因果,最后演變成為國家潰敗的心理動因。
其四,烏托邦國家社會危機很難化解,即便出現了基維爾這樣的優秀政治家,也只能局部地、暫時地解決某些問題,無法改變國家潰敗的基本趨向。社會一旦開始潰敗,是很可怕的。《南方十字架共和國》由于是個短篇,容量有限,寫得比較簡略;其另一短篇《最后一批殉難者》側重寫社會變革中的暴力與恐怖,可視為《南方十字架共和國》的補充和姊妹篇。而在俄國白銀時代另一位代表性作家索洛古勃的《創造的傳奇》中則對社會潰敗過程有更為精詳的敘寫①參見拙作《索洛古勃:預言俄國革命的先知——以<創造的傳奇>為中心》,《文化學刊》2014 年第3 期。。
作品結尾開出的藥方仿佛是多個外國的幫助。這恐怕也很難奏效。我們必須避免建立烏托邦國家、烏托邦社會。烏托邦的某些理想雖然美妙,然而實際上它是反歷史的,其泯滅人的個性的作法是違背人性的。當統治者強使人們整齊劃一,將“我”都變成“我們”時,或許初始原因在于如是為之有利于社會穩定和便于統治,其實適得其反,為社會潰敗積蓄了勢能——人畢竟不是木頭,表現個性和追求自由乃是人的本質屬性。大規模的階級斗爭也好,群體事件也好,盡管是以“群”的形態,但其中每一個參與者往往并非僅僅由于從中可以獲取經濟的解放,也在于從中可以獲得久被壓抑的個性的釋放,哪怕是短暫的。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任何人類歷史的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11],因為人類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所以,烏托邦國家和社會是反歷史的,也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正確之途應是通過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社會,建立一個如馬克思所說的使得人的個性能夠充分得到發展的社會(至少應向這個方向努力),減少和逐漸消弭民間普遍存在的“躁狂癥”和暴戾氣,社會才會真正趨于穩定,才會從根本上避免潰敗。
作為20 世紀首篇反烏托邦小說的《南方十字架共和國》,在今日仍有著極為深刻的警示意義。
[1]符·維·阿格諾索夫.20 世紀俄羅斯文學[M].凌建侯,等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282.
[2][3][4][5][6][7][8][9]. 勃留索夫. 南方十字架共和國[A].劉塵譯.安德列·別雷,等.吻中皇后[M].劉塵,周啟超譯.哈爾濱:哈爾濱出版 社,1994. 207. 208. 209. 208. 212. 218.219.213.
[10]周啟超.白銀時代俄羅斯文學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76.
[11]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A].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