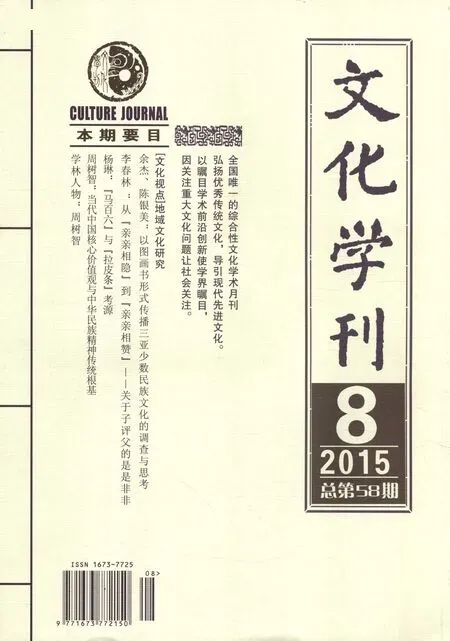當今社會民俗文化的價值和保護
——由斯文赫定于內蒙古民俗文化見聞談起
李夕璨 陶繼波
(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當今社會民俗文化的價值和保護
——由斯文赫定于內蒙古民俗文化見聞談起
李夕璨 陶繼波
(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民俗文化是反映最廣大人民群眾生活的文化,它代表人類群體生活的精神生產和活動,同時也因時代、地域、民族的不同顯示出獨特價值。全球化背景下,受經濟一體化和文化趨同化潮流的沖擊,民俗文化面臨流失的危險。面對我國多民族文化的國情,應當采取措施做好民俗文化的保護工作,使其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成為增強民族凝聚力、發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文化動力。
民俗文化;流失;保護;價值功能;保護原則
一、斯文赫定在內蒙古民俗文化見聞紀略
以瑞典地理學家斯文赫定為首的考察團于1927年至1935年為期8年的科學考察活動期間,沿途記錄了內蒙古地區所見的民俗文化。以下選取所記述的民俗文化進行介紹。
(一)搭建蒙古包的習俗
蒙古族搭建蒙古包的歷史已近千年,經過漫長的歷史演變,逐漸發展成多種搭建蒙古包的傳統習俗。1927年5月27日,考察團行至胡濟圖河時,斯文赫定記述了蒙古族搭建蒙古包的習俗。“考察團的帳篷在草地上排成了一長溜,拉爾生堅持讓我們遵照蒙古人的習慣,把帳篷的門向南開。”[1]蒙古民族一般會在蒙古包上設計和繪制一些圖案,使蒙古包更加美觀的同時也表達對生活的美好愿望。“……在帳篷長邊一側兩個稍矮些的角上,編著壽星的圖案,它代表著長壽,而在篷頂的中間,同樣的圖案又組成了一個有象征意味的圓圈。”[2]
(二)祭祀敖包活動
敖包在蒙古語中稱“鄂博”,多用石頭、沙土或樹枝堆積而成。考察團行至胡濟圖河時遇到“鄂博”,斯文赫定記述:“首領的代表告訴他們,可以做想做的一切事情,但就是不讓在土地上挖坑,因為這會傷害土地的靈氣。他們還特別要求不要觸動所有高起來的土坡,因為那上面都堆著鄂博。”[3]敖包在蒙古族居民生活中具有神圣地位,他們尊重敖包,認為那是神靈的象征,這不僅是對萬物有靈信仰的體現,還表達出蒙古族人民對安定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
(三)婚嫁習俗
蒙古族具有濃厚草原民族特色的婚嫁風俗。考察團行至西利烏蘇時,黃文弼記述道:“據云若育女子至長未嫁,而有孕生子,乃向蒙古包前馬樁上扣頭,意為與馬樁配婚。……婚前男先至女家,與女同回男家,拜馬樁,又拜來賓,即成婚姻。”[4]蒙古地區的婚嫁風俗是蒙古族社會生活和價值觀念的一個縮影,拜馬樁就鮮明顯示出這一點。
(四)喪葬風俗
蒙古族的喪葬習俗既蘊含著宗教信仰的內涵,又是社會民俗的具體體現。1927年5月19日,黃文弼記錄了蒙古族的喪葬風俗:“又聞此地喪禮甚薄,男子未成年者,以席卷之填于野。老人其棺木衣服,無論貧富,均不華麗。猶有蒙古之舊習也。”[5]由此可知,蒙古族“喪禮甚薄”的喪葬風俗與漢族有很大不同。對漢人來說,人生最重要的事莫過于“婚”“生”“死”,而蒙古族喪葬尚儉,不論貧富,亡者的棺木服飾都不推崇華麗。這種獨特的喪葬文化反映出蒙古族人們平淡自然的價值觀念,對現今社會厲行節約有借鑒意義。
(五)蒙古族的服飾
蒙古袍是蒙古族的主要服飾,具有濃郁的游牧民族特色。由于地域的差異,蒙古服飾在長袍的款式、婦女的佩戴首飾等方面存有不同。黃文弼在日記中記述了烏拉特與阿拉善兩地區之間婦女在穿著和裝扮上的差異。“據商人云,阿拉善女人裝飾與烏拉特不同。烏拉特女人發髻,珍珠珊瑚垂額;阿拉善女人發下垂,以網絡籠之,戴耳珠,以珊瑚夾銀華飾之,富者用真珊瑚,貧者以假貨充之。”[6]其作為鮮明的民族符號,成為展現蒙古族風貌的一個窗口。
二、民俗文化在當今社會的生存狀況
全球化背景下,我國民俗文化的發展面臨著巨大挑戰,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因其自身文化傳承的脆弱性,受到經濟一體化和社會生活現代化更強烈的撞擊。民俗文化在當今面臨著迅速變異和流失的危險。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民俗文化商業化現象
當前,文化產業作為新的消費熱點,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身為民族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民俗文化被廣泛商業化。一些開發商為追求短期經濟利益,不顧當地原有的文化形態,急功近利,將其過分包裝。如內蒙古祭祀敖包的民俗活動。在斯文赫定的記述中,敖包是蒙古族人對“萬物有靈”信仰崇拜的表現,祭祀敖包的活動神圣而莊嚴。隨著內蒙古旅游業的發展,一些敖包在商業利益的沖擊下,其本質開始扭曲。旅游開發者片面追求敖包外觀的宏偉,以達到賺人眼球的效果,但對其深刻的宗教信仰內涵卻漠視不顧。同時,許多游客也參與到祭祀中來,游客“祭祀的時候什么也不拿、不懂,就跟著牧民繞敖包三圈,嘴里喊著:呼來、呼來”。[7]游客并不真正理解敖包祭祀背后蘊藏的神圣意義,祭祀敖包這一傳統民俗文化無疑已在商業開發中變質。
(二)民俗文化的內部斷裂現象
經濟的快速發展推進社會生活現代化,許多民俗文化因不能滿足人們現代生活的需求而逐漸被遺棄,這種內部民俗文化的傳承斷裂現象在少數民族地區尤為嚴重。在內蒙古,牧民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巨大變化。許多牧民開始定居,擁有固定住房,蒙古包的數量銳減。
“現代牧民在自己承包的牧場上建造了磚瓦房,過上了定居生活,生活條件有了改善……牧民家有現代電器,多數牧戶有小四輪拖拉機和輔助機,有的家庭還購置了小汽車、摩托車。”[8]傳統的游牧民俗文化正在逐漸消失。斯文赫定在考察期間提及的蒙古包如今只能在一些草原旅游景點看到,作為具有觀賞性的民俗旅游消費吸引點出現,其蘊含的悠久深厚的民俗寓意已經消失。
(三)民族文化的同化現象
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各民族民俗文化同化現象日益突出,現代文明正以驚人的速度弱化民族的個性符號,民俗文化多樣性遭到嚴重破壞。
民俗文化的同化現象鮮明地表現在服飾和婚嫁習俗上。隨著文化交流日益增多,現在內蒙古地區的很多人已不再穿蒙古袍,不再佩戴自己的民族服飾。蒙古族的年輕人多數崇尚現代審美觀念,喜歡佩戴流行飾品,對蒙古衣服的做工及穿戴方法等逐漸陌生。現今的蒙古族年輕人婚嫁時,往往采取中西結合,甚至完全西式的結婚方式,很少沿用傳統當地婚俗儀式。蘊含傳統蒙古族文化的“以牛馬為聘禮”、舉辦“祭火儀式”等婚俗被棄之不用,使其失去了體驗民族自我認知感和存在感的一個重要途徑,這將導致民族意識的迷失。
三、民俗文化的獨特價值及保護的必要性
民俗文化作為一種精神資源,代表著中華各民族最具特色的東西,是一個民族存在的重要體現。它的獨特價值表現在文化、社會、教育、藝術等多個領域,極具發掘和保護的必要性。
(一)歷史文化價值
民俗文化是某一地區民族文明的傳承形式,它記錄了相應的歷史,反映某一時期的歷史畫面。“人是民俗的動物”。[9]人民群眾的社會歷史生活與民俗緊密相關。從斯文赫定記載蒙古族怕破壞土地的靈氣、祭祀敖包的習俗中,可以看出推崇“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對蒙古民族的深刻影響。由此體現出蒙古族的宗教信仰特征,再現蒙古民族在草原、溪流邊堆壘敖包進行祭祀活動的畫面,為學術的深入研究提供依據。
(二)社會調解功能
民俗文化作為一種無形的習俗慣制,對社會生活具有調節功能。民俗文化通過形成固定規范,起著穩定社會生活秩序,維系社會關系的作用。
據斯文赫定記載,“1929年夏召開的麥德爾節從蘇尼特右旗趕來的香客,就有2000人之多,據說從蘇尼特左旗也至少來了這么多人。人們騎著馬匹、駱駝,乘坐馬車、汽車紛紛趕來,只是為了一個目標——朝拜班禪喇嘛并接受其祝福。”[10]蒙古族集體參加麥德爾節這種習俗,反映出蒙古族共同的信仰基礎,它是民族團結的象征,是加強族內各地區之間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紐帶。
(三)現實教育價值
民俗文化蘊涵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對社會群體特別是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意義。有學者通過斯文赫定所記述的內蒙古地區民俗文化提出了開展民俗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即從民俗文化產生于民間、人們思想文化的載體、民俗文化的歷史地位等角度論述其開展教育的必要性。[11]并指出開展民俗文化教育的方式,包括學校教育、廣播、網絡電視風方式。[12]
民俗文化的教育功能獨具特色。一方面它與學校教育不同,不受時間地點、教師素質水平等條件限制,無時無處不在。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說:“個體生活歷史首先是適應由他的社區代代相傳下來的模式和標準。從他出生之時起,他生于其中的風俗就在塑造他的經驗和行動。[13]”另一方面,民俗文化教育大多不具有強制性,是潛移默化的,在不知不覺中影響人們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例如,每逢大規模祭祀敖包之后,蒙古族都會舉行摔跤、賽馬、射箭等娛樂活動,此民俗文化與蒙古族人粗獷豪放的游牧文明緊密相連,在無形中塑造、強化他們崇尚勇敢,尊敬武士的價值觀念。
(四)藝術審美價值
“民間藝術是人類文明古拙和精美的活化石。”[14]民俗文化是民間藝術的土壤,其本身所具有的審美價值不容忽視。作為審美的民俗文化有兩種形式。一是民俗物質文化,如黃文弼記錄不同蒙古地區婦女的裝飾物品,烏特拉婦女以“珍珠珊瑚垂額”,阿拉善婦女以“珊瑚夾銀華飾之”。它們是民俗習慣的產物,以其獨特的地域風格傳達美的理念;二是民俗活動。在民俗的動態展示中,也展現了特殊美感。蒙古族嫁娶儀式中,在馬頭琴悠揚伴奏下,新郎新娘盛裝華服,舉起銀碗向親朋歌唱敬酒,就傳達一種熱烈奔放的美。民俗文化豐富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滿足人們審美需求的重要作用。
四、保護民俗文化的原則
民俗文化對民族自身發展、文化多樣性的保持具有獨特價值。當今社會,隨著現代化進程不斷推進,民俗文化處于流失的邊緣境地,因此,亟需研究相關保護策略,但保護民俗文化應當堅持以下四個原則。
(一)整體性原則
從哲學角度來說,整體和部分不可分割,部分在整體中存在。保護民俗文化,必須堅持整體性原則,整體性原包含兩層內涵。首先,“中國民俗文化各種表現形式之間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聯系,彼此影響的一個整體,它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具有整體性”。[15]保護民俗文化就必須將靜態的物質文化與動態的精神活動相結合,將其作為一個整體,全面保護,不能顧此失彼。如,可在保護蒙古族傳統婚俗中同時推進民族服飾的保護。其次,整體性原則還要求將某區域的民俗文化融入到整個區域的文化發展中進行保護。例如,蒙古族崇拜萬物神靈,推崇摔跤、賽馬等習俗充實了內蒙古地區文化中善良淳樸、勇敢堅毅的精神內涵。深入挖掘蒙古族民俗文化對整個內蒙古地區文化的價值,對保護和促進多樣性的文化和諧發展有重要作用。
(二)教育性原則
教育性原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從宏觀上,要形成一套保護民俗文化的科學理論體系。例如,廣泛吸收國內外先進的民俗文化保護經驗,結合內蒙古地區草原遼闊、地域寬廣的特點,構建起具有游牧民族特色、適合游牧民族民俗文化發展的基本理論。在理論體系指導下,使蒙古族民俗文化與現代文明協調發展。從微觀上,利用民俗文化無時不在、潛移默化的特點,培養具有現代人文素養的文化主體。“文化的本質是人創造的。文化創造最重要的就是文化創造主體。”[16]加強對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少年的民俗文化教育,培養他們保護民俗文化的意識,避免民俗文化的內部鏈條斷裂,使民俗文化得以傳承發展。
(三)創新性原則
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指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提高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吸收再創新能力”。創新對民族經濟、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在游牧文明、農耕文明土壤中誕生的民俗文化正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發生劇變,要使民俗文化適應時代發展的潮流,就必須遵循創新性原則。創新能使民俗文化既能保持獨特的地域性,又能適應現代化潮流。例如,根據現代審美理念,將蒙古族傳統的民族服飾加入現代流行元素,創造民族特色品牌,進軍國內、國際市場。
(四)可持續性原則
1980年,國際自然保護同盟提出的《世界自然資源保護大綱》指出:“必須研究自然的、社會的、生態的、經濟的以及利用自然資源過程中的基本關系,以確保全球的可持續發展”。可見,可持續發展是一個綜合概念,它需要在生態文明、社會文明等協調作用下實現。民俗文化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部分,要獲得可持續發展,必須協調經濟、自然與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例如,在保護內蒙古民俗文化過程中,要保護好草原生態,遏制因過度放牧而造成草原面積萎縮、土地沙漠化。草原生態是蒙古族民俗文化產生的土壤,保護草原生態就是保護民俗文化的生長空間和發展背景。民俗文化的發展又能帶動民俗資源深入開發,促進經濟增長,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五、結語
斯文赫定在內蒙古考察期間記錄的民俗文化鮮明地體現了區域民族特征。全球化背景下,民俗文化的獨特個性是一個民族自我認同的重要標志,也是維系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紐帶。隨著人們生活現代化進程加快、文化趨同現象加劇,民俗文化正遭受著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大量民俗文化面臨內涵變質、傳承中斷等問題,處于流失邊緣。近代社會動蕩不安,缺乏安定,僅就內蒙古地區來說,土匪橫行無忌,嚴重干擾人們的生活,[17]社會動蕩不安、秩序紊亂。[18]這樣的環境自然會增加內蒙古地區民俗文化保護的難度,但這也側面說明民俗文化的保護具有必要性。
[1][2][3][10][瑞典]斯文赫定.亞洲腹地探險八年[M].徐十周,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22.24.26-27.325.
[4][5][6]黃文弼.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M].黃烈,整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7]張曙光.傳統的保持與再塑——關于白音敖包祭祀組織的觀察與思考[J].大連民族學院學報,2010,(7).
[8]蘇浩.草原傳統物質文化的變遷[J].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學報,2010,(9).
[9]鐘敬文.文藝理論的民俗學緯度[N].光明日報,2000-05-14.
[11]陶繼波,崔思朋等.從斯文·赫定的見聞紀略看開展內蒙古民俗文化教育的必要性[J].哈爾濱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4,(3).
[12]陶繼波,崔思朋等.斯文·赫定日記里的內蒙古民俗文化——兼論開展民俗文化教育的必要性與途徑[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4,(7).
[13][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2.
[14]張玉柱.齊魯民間藝術通覽[M].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98.1.
[15]王力尉.民俗文化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研究[D].成都:成都理工大學,2013.
[16]何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民俗文化可持續發展的思考[A].陳華文.民間世界:理論與存在——民俗民間文化保護開發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88.
[17]崔思朋,李夕璨等.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內蒙古西部土匪猖獗活動的原因分析——以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見聞為線索[J].黨史文苑,2015,(4).
[18]陶繼波,石巖飛等.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內蒙古地區政治與社會治安方面見聞紀略[J].哈爾濱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4,(5).
【責任編輯:王 崇】
K892
A
1673-7725(2015)08-0056-05
2015-06-05
陶繼波(1972-),男,內蒙古巴彥淖爾人,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內蒙古地區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