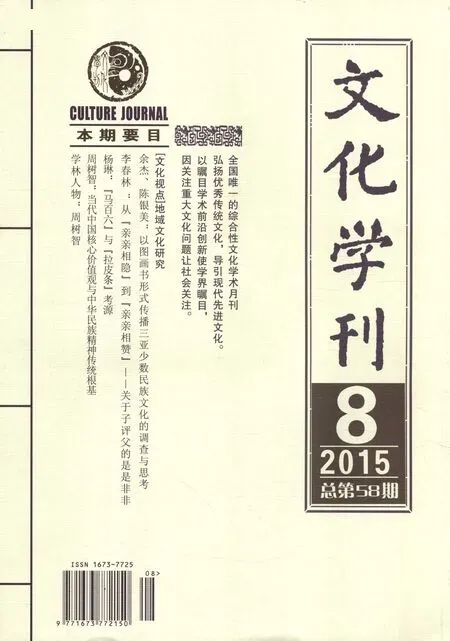荒原奇葩 空谷石楠
——艾米莉·勃朗特詩歌的倫理初探
逯 陽
(大連外國語大學,遼寧 大連 116044)
荒原奇葩 空谷石楠
——艾米莉·勃朗特詩歌的倫理初探
逯 陽
(大連外國語大學,遼寧 大連 116044)
艾米莉·勃朗特在英國文學史上可謂特立獨行,卓爾不群。除小說《呼嘯山莊》外,她的詩歌作品也備受學者關注。勃朗特的詩歌通過對主人公精神狀態的描述,刻畫了受男權社會壓抑的女性形象;同時她也賦予自然以人性,描繪工業社會對自然的破壞,表現女性與自然的天然同盟,具有生態女性倫理意識。
艾米莉·勃朗特;生態女性倫理;詩歌
一、引言
“生態女性主義”這一術語最早由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弗朗索瓦·德奧博納于1974年提出,用以指女性問題與生態問題的內在聯系。此后,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股強勁的文化思潮,影響日益擴大。[1]20世紀90年代,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形成,融合女性批評和生態批評諸多特征,從自然和女性視角出發,分析文學作品中自然與女性的聯系,揭示男性中心主義,挖掘女性作家的生態書寫,比較男女作家在生態寫作上的異同,并提倡一種女性的自然敘事,力求打破女性與自然在文學中的雙重失語。在當今生態危機日益嚴重,追求兩性平等、和諧的社會背景下,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呈現出勃勃生機。
生態女性主義是20世紀才發展起來的,但在它產生之前,一些思想前衛的女作家就已萌生這種倫理意識,英國詩壇奇葩艾米莉·勃朗特就是典型代表。在生態女性主義產生之前,勃朗特就在其詩歌中表現出生態女性倫理意識。這種超前意識的形成同她與自然緊密相連的人生經歷,她所處的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現實以及家庭影響等因素分不開。
二、作為詩人的艾米莉·勃朗特
艾米莉·勃朗特是19世紀英國文壇群星中最為獨特的一顆,她與勃朗寧夫人、克里斯蒂娜·羅塞蒂一同被尊為英國三大女詩人。其唯一一部小說《呼嘯山莊》奠定了她在英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從1847年小說出版,到現今已一百六十八年,而這部被稱作“斯芬克斯之謎”的作品像謎一樣持續吸引著全世界的讀者。也許是《呼嘯山莊》的光芒掩蓋了艾米莉的詩名,國內學界對艾米莉詩歌作品的研究少得可憐。其實,作為詩人的艾米莉同樣非凡超群。她的詩歌想象瑰麗、意象奇特,堪為英詩寶庫中的精華。可以這么說,就算是沒有《呼嘯山莊》,單憑其詩歌作品的藝術魅力,也足以讓艾米莉名垂青史。英國著名詩人兼文學評論家馬修·阿諾德,在其詩歌《霍渥斯陵園》中曾對艾米利·勃朗特的詩才欽佩不已,慨嘆道:“自拜倫逝后,殊世無雙”。[2]實際上,在創作《呼嘯山莊》之前,艾米莉用大約十年時間,創作193首詩歌。其中有敘事詩,也有抒情詩。這也為日后小說的創作做出充分準備和演練。這些詩歌風格、主題及藝術手法同小說《呼嘯山莊》如出一轍,甚至有的評論家說這些作品可以稱得上是詩歌版的《呼嘯山莊》;也有人說《呼嘯山莊》是從這些詩歌中衍生出來的,是一部裹著小說外衣的長篇敘事詩。可見,艾米莉的詩歌和小說創作一脈相承。研究這些詩歌作品,對于正確理解詩人的詩學思想,深入理解《呼嘯山莊》的藝術內涵,全面、準確地評價艾米莉·勃朗特在英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都具有重要意義。
艾米莉·勃朗特“當時聲名雖遠不及姐姐,但后世評論認為她無論是作為詩人還是小說家,天分都在勃朗特姐妹中居首位”,[3]她是勃朗特姐妹中最具詩才的一個。弗吉尼亞·伍爾芙也曾經評價說“《呼嘯山莊》是一本比《簡·愛》更難懂的書,因為艾米莉是一個比夏洛蒂更偉大的詩人”。[4]艾米莉的詩表達了對種種社會不公現象的批判。將自然比作母親的隱喻更具超越時代的積極意義。這種倫理意識與當代生態女性主義的理論不謀而合。
三、詩歌中生態女性倫理意識的形成與表現
(一)苦難的人生經歷令其向往自然
在艾米莉的詩歌創作中,自然具有不同尋常的地位。艾米莉三歲喪母,在童年的歲月里,母愛缺失的創傷難以撫平。家鄉霍渥斯偏僻閉塞,在這石楠叢生的荒原上,艾米莉度過苦悶的童年。從小在霍渥斯荒原長大的艾米莉深深眷戀著荒原的蒼勁之美。母愛的缺失令其投入自然的懷抱,大自然給了她母親般的愛撫和慰藉。她與自然親切對話,受自然的啟發和鼓舞,感悟自然的力量。也正因如此,在其詩歌中,艾米莉一直對荒原和石楠情有獨鐘。夏洛蒂曾經這樣說過:“我妹妹艾米莉喜歡荒原。她覺得即使是石楠叢生的荒地里最黑的部分,花開得都比玫瑰鮮艷,她的心能把灰白的山坡上最陰沉的洼地想象成伊甸園。”[5]荒原的風景不僅為她的小說提供自然背景,也為她詩歌提供生態題材。誦讀她的詩歌可以感受到一股撲面而來的濃郁的大自然氣息。
艾米莉是一位神秘的泛神論者。在其詩歌中,她常以擬人的手法書寫自然,賦予自然萬物以人的情感,讓自然與人密切交流。自然界的“晚風”“青草”“荒原”“石楠”和“野鳥”都給予她精神力量。在她詩歌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太陽落山了,那長長的草兒,在晚風中凄涼地搖曳。野鳥從那古老的灰巖上縱身飛起,去某個溫暖的角落找尋棲身的巢穴。我在四周孤寂的景色中央,看不到一絲光亮,聽不到一點聲響,只有這來自遠方的風,嘆息著掠過這一片長滿石楠的荒原。[6]
詩人張開想像的翅膀,為讀者描繪了一幅傍晚荒原的自然畫卷。景物在這里不只是詩歌的點綴,而是化作詩人賴以生存的空間。艾米莉一生只離開過荒原四次,加起來大約三年時間。而每次離家,她都表現出強烈的身體不適。可以說,在艾米莉短暫且磨難重重的一生中,自然扮演著母親的角色,給詩人生存的信心和希望,也給她戰勝困難的勇氣和力量。
痛苦女神走來,摘去了金色的花蕾,罪惡女神又捋走了那茂盛的枝葉;可是,在自然慈祥母親的胸懷里,永遠奔流著一股生生不息的潮汐。我很少為逝去的歡樂憂傷,也不為那空巢和沉寂的歌兒悲戚;希望女神就在那兒,為我一笑解憂愁,悄悄地說:“冬天很快就會過去。”看著吧,以十倍有加的恩澤,春天枝頭綴滿美麗的花朵;和風細雨及溫暖空氣撫愛著,來年五月又是個滿枝的輝煌。[7]
(二)女性的社會境遇令其求助自然
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是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相對而言,女性無論在經濟地位,還是在思想意識上都只是附庸。同許多維多利亞女作家一樣,艾米莉在作品中也反映出女性在男權社會尋求自我身份認知過程中所經受到的苦楚和無助。艾米莉的困境是當時女性現實生活的縮影。維多利亞時代,女性被稱為“家庭天使”“花園皇后”。社會普遍認為:“家庭領域是女人展示其杰出才能的最好場所。女性應該是溫順賢良、無懈可擊的,女人的任務就是取悅丈夫,優雅地去忍受男人的熱情和暴躁,了解和接受他的品味。”[8]“家庭天使”的形象是女人的典范,女人的生活重心和活動范圍是家庭,她們與社會無緣。家庭教師是女性所能得到的最好工作,而文學創作則被認為是男性的專屬。夏洛蒂曾寫信給當時的桂冠詩人羅伯特·騷塞,請教文學創作的問題。騷塞在回信中無情地指出:“文學不能也不應該是婦女的終身事業,婦女越是投入于她應盡的職責中,就越沒有閑暇來從事文學活動,哪怕只是把它作為一種消遣也罷。”[9]可見,19世紀女作家們很難得到展露才華的機會,她們體驗到的多是生活的艱辛與苦澀。于是,為避免非議,勃朗特姐妹最初出版作品時都使用男性署名。
艾米莉也曾嘗試與夏洛蒂一起外出求學并開辦學校。但這兩次外出謀生的經歷讓她更加深深地體會到社會對女性的偏見。于是,她不久就返回霍渥斯。她迷戀這個廣裹的荒原,荒原對她來說就是人間的樂土,快樂的源泉,靈魂的歸宿。面對女性悲慘的社會處境,艾米莉已萌生女性主義意識,并用寫作來抒發女性情懷,表述女性體驗,為女性自己而寫作。這種思想在《濃濃的暮色將我包圍》一詩中一覽無余。
濃濃的暮色將我包圍,狂風呼嘯而來;但有一種無形的魔咒鎖住我,讓我無法,無法離開。風中,大樹彎下了腰,白雪積壓在它們的枝頭,暴風雪突然襲來,可我卻無法離開。烏云在頭上翻滾,沙兒被狂風卷起;什么都無法將我動搖;我不愿,也不能離開。[10]
這里濃濃的暮色、呼嘯的狂風、大樹、暴風雪、烏云都是荒原上最常見的自然景物。這首詩意味深長地傳達出顛沛流離、備受壓迫的維多利亞女性對自己有權享受幸福的堅定追求。在這種壓抑陰森的環境背景和悲戚憂郁的思想情緒的激烈撞擊下,艾米莉的詩歌形成一種粗獷、剛勁的風格。面對惡劣的環境,詩人斬釘截鐵地宣告:“我不愿,也不能離開。”
(三)相似的“他者”地位令其結盟自然
艾米莉· 勃朗特不但關注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也同樣關注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維多利亞時代是一個鋼鐵煤炭取代田園牧歌的時代。工業革命給自然環境造成的破壞和對人性的異化也進入艾米莉的視野。在工業革命浪潮中,充滿生機的自然界遭受無情的破壞:工廠礦山林立,森林變成木材廠,濃煙遮暗原本秀麗的自然風光。霍渥斯也變成工業小鎮,擁有多家煤礦和紡織廠,環境受到嚴重影響。據史料記載,當地居民的飲用水受到嚴重污染,各種病菌滋生,傳染病連年不斷。1850年,霍渥斯六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高達41.6%,這一數字與倫敦城內衛生狀態最差的區域相同。[11]當時霍渥斯居民的平均壽命只有二十五歲,這也從一個側面解釋了勃朗特姐妹過早死亡的原因。女性在男權社會中的苦楚與自然在工業社會中的遭遇如出一轍。于是,詩人與自然一道發出哀鳴。
薄霧尚未散盡,貧瘠的山坡寸草不長;陽光和剛睡醒的早晨,未能增添多少金色的景象。[12]
在詩人眼中,土地在礦廠的開采中變得貧瘠,“寸草不長”這樣的自然背景使得朝陽與黎明也黯淡無光。詩人繼續寫道。
一切如同陰郁的黃昏,嘆息著訴說煩惱與憂傷……褐色的石楠還能在那兒生長嗎?它受盡折磨,低聲對我講:邪惡的石壁壓著她,去年夏天卻還曾花朵芬芳。[13]
在另外一首名為《星星》的詩歌中詩人又寫道。
整個夜晚,你燦爛的目光,都在往下凝視著我的雙目,以一聲由衷欣慰的感嘆,我謝謝你那神圣的關注!我靜靜吸飲著你的光輝,尤如它們就是生命的瓊漿,陶醉于那變幻無窮的夢鄉,就像海燕在海上乘風破浪。星星隨著星星,思緒接著思緒,穿梭于無邊無際的天地,忽遠忽近掠過一種美好的感覺,這就說明了你我的合一。[14]
可見,詩人在其作品中已萌生原始的生態女性主義倫理思想,這種樸素的意識讓女性與自然合二為一,共同追求打破“男性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二元對立模式,建立天人合一,男女和諧的理想社會。
四、結語
艾米莉·勃朗特的詩歌,以敏銳的女性主義視角,旗幟鮮明地表達出當時被男權社會所忽視、壓抑的女性話語,對女性的生活歷程作全新評判。同時,在其詩歌中,自然作為母親形象出現,成為女性汲取力量,反抗男權的源泉。盡管艾米莉并不是在有意識地進行生態女性主義寫作,但是她的作品卻充溢著現代生態女性主義倫理意識,充滿了對“男性中心論”“人類中心論”的不滿和對大自然母親的熱愛。可以說,艾米莉的詩在內容、主題及藝術手法上都具有超前性和創新性。作品中充滿對自由的渴望,蘊含著詩人對自然、社會、自我的深邃感悟。她的詩雖有一種沉郁、凄涼、哀惋和悲劇特征,但同時也具有自然真摯、慷慨悲壯、剛勁有力的風格。她筆下的荒原是自由、是生命、是希望。正如威塞克斯之于哈代,約克納帕塔法之于福克納,霍渥斯荒原賦予艾米莉詩歌罕見的文學魅力和藝術張力。艾米莉就是霍渥斯荒原上狂風中一株搖曳著的石楠,純真而高潔。
[1]吳琳.美國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與實踐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9.
[2]高萬隆.艾米莉·勃朗特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142.
[3]蔣承勇.英國小說發展史[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125.
[4]楊靜遠.勃朗特姐妹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189.
[5]蓋斯凱爾夫人.夏洛蒂·勃朗特傳[M].張淑榮,譯.北京:團結出版社,2000.145.
[6][10]逯陽.英美詩歌名篇賞析[M].大連: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2013.74.89.
[7][12][13][14]C.W.海埃菲爾德.埃米莉·簡·勃朗特詩歌全集[M].覃志峰,譯.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52.63.63.89.
[8]J.A.Oliver Banks.Feminism and Family Planning in Victorian England[M].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4.74.
[9]付玉群.與自然共舞,吟唱“自我”與“他者”——論生態女性主義視閾下的艾米莉·勃朗特自我詩歌[J].名作欣賞,2012,(3).
[11]Heather Glen.The Bront?s[M].Shang Hai:Shang 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2004.49.
【責任編輯:王 崇】
I561.072
A
1673-7725(2015)08-0161-04
2015-05-20
本文系遼寧省社科聯2015年度遼寧經濟社會發展立項課題(項目編號:2015lslktziwx-13)部分研究成果。
逯陽(1979-),男,滿遼寧沈陽人,副教授,主要從事英美詩歌詩論,中西詩學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