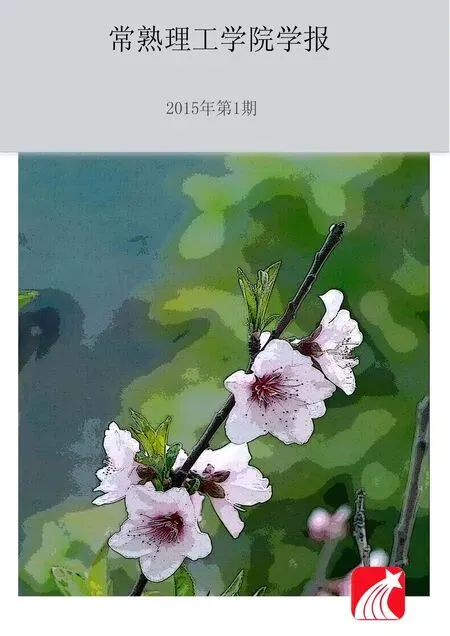論中國現(xiàn)代報告文學(xué)的敘事聚焦
郭志云
(福建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福州 350007)
論中國現(xiàn)代報告文學(xué)的敘事聚焦
郭志云
(福建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福州 350007)
零聚焦、限制聚焦與轉(zhuǎn)換聚焦,從敘事聚焦的層面上對中國現(xiàn)代報告文學(xué)進行了理論廓清。三種聚焦方式在線性歷史流變中呈現(xiàn)出的從單一而逐漸多元化的趨向,指認(rèn)了報告文學(xué)求新求變的文體生命力,更確證了報告文學(xué)對社會關(guān)注面的逐步擴大化及其介入現(xiàn)實的文體功能的不斷強化。而感知性聚焦之外的事實,則需要由認(rèn)知性聚焦進行有效補充,以發(fā)揮報告文學(xué)的文體使命。
報告文學(xué);敘事聚焦;轉(zhuǎn)換聚焦;聚焦對象;認(rèn)知性聚焦
由近代源起至今,中國報告文學(xué)走過了百余年發(fā)展歷程,誕生了《包身工》《哥德巴赫猜想》《天使在作戰(zhàn)》等諸多力作。然而,報告文學(xué)的理論研究卻與創(chuàng)作的豐碩極不相稱。就連簡單的文學(xué)性這一理論問題的廓清,幾代學(xué)人用力頗多,卻仍舊停留在了“結(jié)構(gòu)的奇巧、描寫的生動、文字的優(yōu)美、表達的流暢、以及可能的感染力等”[1]38閱讀的感性體驗上。感性閱讀的快慰當(dāng)然能顯示出中國報告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深入人心,但卻更加凸顯了報告文學(xué)理論研究存在的問題與缺陷——即學(xué)理性的匱乏。新聞事業(yè)不斷蓬勃發(fā)展的今天,報紙雜志上充斥著大量的新聞報道、通訊作品,它們在真實性的前提下同樣在描寫生動、文字優(yōu)美、表達流暢、藝術(shù)感染力等層面上用力頗多。如此一來,究竟用什么樣的標(biāo)尺將它們與報告文學(xué)進行區(qū)分成了報告文學(xué)理論研究首當(dāng)其沖要解決的問題。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報告文學(xué)所遭遇的時代尷尬正源于此。
作為一個彰顯社會性的敘述文體,報告文學(xué)的寫作主體有著強烈的主題意義的訴求。而聚焦方式作為傳遞主題意義有效且重要的工具,自然對報告文學(xué)敘事有著特殊的意義。基于這樣的認(rèn)定,選擇“聚焦”作為報告文學(xué)理論研究的角度順理成章。中國報告文學(xué)文體敘述的聚焦方式究竟呈現(xiàn)出了哪幾種主要的類型?在百余年的報告文學(xué)發(fā)展歷程中,這幾個類型又呈現(xiàn)出怎樣的線性流變?這種流變態(tài)勢的終極旨歸在哪里?而對于敘述過程中一些感知聚焦之外的事實,報告文學(xué)又該以怎樣的方式實現(xiàn)非虛構(gòu)性的聚焦?這些問題都要依靠中國報告文學(xué)敘事聚焦研究的展開與深入才能夠獲得妥帖的回答。
一
在小說敘述學(xué)中,熱奈特將敘述聚焦或者說“敘述情境”分為三個類型,即零聚焦敘事、內(nèi)聚焦敘事、外聚焦敘事。雖然,任何聚焦理論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但在當(dāng)下的敘述學(xué)界,熱奈特聚焦理論的輻射面與適應(yīng)性顯然是其他相近敘述理論所難以比擬的。因此,在探究中國報告文學(xué)敘述聚焦的基本類型時,我依然以熱奈特的聚焦分類作為理論基礎(chǔ),暫且將其分成外聚焦敘事、零聚焦敘事和內(nèi)聚焦敘事。
敘述者嚴(yán)格地從外部呈現(xiàn)每一件事,只提供人物的行動、外表及客觀環(huán)境,而不告訴人物的動機、目的、思維和情感,稱之為外聚焦。單純從非虛構(gòu)的文體屬性來看,外聚焦應(yīng)該是最適合報告文學(xué)的。如《包身工》的開頭部分提供的,幾乎就是類似劇本的客觀場景,既有人物語言,也有行為動作:
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點的“豬玀”身上踢了幾腳,回轉(zhuǎn)身來站在不滿二尺闊的樓梯上面,向著樓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來?懶蟲!等太陽上山嗎?”
蓬頭、赤腳,一邊扣著紐扣,幾個睡眼惺忪的“懶蟲”從樓上沖下來了。自來水龍頭邊擠滿了人,用手捧些水來澆在臉上。[2]265
敘述者在冷眼旁觀中展示了包身工晨起時的具體情狀。“就像許多其他現(xiàn)代作家一樣,他自我隱退,放棄了直接介入的特權(quán),退到舞臺的側(cè)翼,讓他的人物在舞臺上去決定自己的命運。”[3]9距離感的存在強化了所呈現(xiàn)事件的客觀性,也給讀者以身臨其境的在場感。敘述者沒有在最開始就站出來對工頭、資本家予以無情批判,而是先匿影藏形,一步步抽絲剝繭。
這種外聚焦敘事排斥提供人物內(nèi)心思想等信息,可使人物顯示一定的神秘或朦朧。但僅僅是畫面攝入?yún)s不進行解釋說明,這對于報告文學(xué)敘事而言是極大的缺陷,因為客觀真實與必要的敘事干預(yù)較之于情節(jié)模糊的吸引力更重要。“報告文學(xué)的最大力點,是在事實的報告。但是,這絕不是和照相機攝取物象一樣地,機械地將現(xiàn)實用文字來表現(xiàn)。這,必然的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傾向。”[4]因此,報告文學(xué)的外聚焦敘事在文本中只能是局部性出現(xiàn)。
零聚焦指稱的是傳統(tǒng)的、無所不知的視角類型。依舊以《包身工》為例:
還有一個,什么名字記不起了,她熬不住這種生活,用了許多工夫,在上午的十五分鐘休息時間里面,偷偷地托一個在補習(xí)學(xué)校念書的外頭工人寫了一封給她父母的家信,郵票大概是那同情她的女工捐助的了。一個月沒有回信,她在焦灼,她在希望,也許,她的父親會到上海來接她回去,可是,回信是捏在老板手里了。散工回來的時候,老板和兩個打雜的站在門口,橫肉臉上在發(fā)火了,一把扭住她的頭發(fā),踢,打,擲,和爆發(fā)一般的聽不清的嚷罵……[2]276
這里,敘述者儼然上帝般知曉不同時間發(fā)生在不同人物身上的行為,并進入任何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為敘述接受者提供他們的所思所想。全知全能的敘事者并不需要將觀察角度固定,而可以從任何角度觀察被敘述故事,并能隨意從一個位置挪向另一個。他在講述故事時,沒有看不到或感受不到的,場景與場景、人物與人物的轉(zhuǎn)換隨心所欲。這樣的觀察方式,意味著報告文學(xué)的敘述者時而能夠俯瞰紛繁復(fù)雜的群體生活,時而能夠窺探人物內(nèi)心隱秘的意識活動。那些規(guī)模龐大、人物眾多的報告文學(xué),如《中國的西北角》《中國農(nóng)民調(diào)查》《黃河生態(tài)報告》等均需要全景式的鳥瞰,將各個人物的言行舉止、各類問題的來龍去脈、各種事件的起承轉(zhuǎn)合盡收眼底并進行權(quán)威的講述。
在零聚焦敘事中,報告文學(xué)的敘述者比文本中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詳盡的敘述能夠充分滿足敘述接受者的好奇心,卻也不免使他們產(chǎn)生接受的惰性。所以,即便是作為中國報告文學(xué)文體敘述的一種最基本的聚焦類型,因其自身的局限,敘述者對零聚焦的使用還是相對節(jié)制的。
每一件事情都嚴(yán)格按照一個或幾個人物的感受與意識進行呈現(xiàn)的聚焦方式,稱為內(nèi)聚焦。《哥德巴赫猜想》中,徐遲在展示陳景潤的不堪命運時,巧妙地使用了故事人物進行觀察與敘述:
李書記皺起了眉頭,咬牙切齒了。他心中想著:“唔,竟有這樣的事!在中關(guān)村,在科學(xué)院呢。糟蹋人呵,糟蹋科學(xué)!被糟蹋成了這個狀態(tài)。”一邊這樣想,一邊又指著羊尾巴似的窗紗問道,“你不用蚊帳?不怕蚊蟲咬?”[5]114
這段話充分敞開了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了人物內(nèi)心的思想斗爭與情緒變化。“糟蹋科學(xué)”時代里知識分子地位的低下與生存境況的艱難,由此可見一斑。雖然聚焦限制會妨礙作者對需要展示內(nèi)容的全面與精確把握,但它的使用明顯縮短了人物同讀者的距離,使讀者接受時獲得一定程度的親切感。
這種類型的報告文學(xué)敘述者,完全憑借一個或幾個人物去看、去聽,只轉(zhuǎn)述人物從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產(chǎn)生的內(nèi)心活動。而對其他人物則像旁觀者那樣,僅憑接觸去猜度、臆想。顯然,視野的限制使得內(nèi)聚焦敘事難以深入掌控整個事件。在很多情況下,它只能提供一部分甚至是相反的答案。不過,從全知全能、高高在上的位置上走下來的敘述者通過一個或者幾個有限的人物視角去看世界,卻能夠使接受者和敘述者處在一種相對平等的地位。而更多的空白與懸念的存在,對于接受者而言,也是更大的能動性賦予。考慮到報告文學(xué)敘事采取內(nèi)聚焦時人物一般較多,目的只為聚焦上的限制,因此,選擇用限制聚焦這個概念替換內(nèi)聚焦無疑是合適的。
以上劃分出來的報告文學(xué)的三種聚焦類型各有千秋,也分別在報告文學(xué)的文體敘述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但是,對比而言,外聚焦出現(xiàn)的頻率要明顯地少于其他兩個類型,它更多的只能被處理為報告文學(xué)寫作中的一種藝術(shù)技巧,無法同零聚焦、限制聚焦相對應(yīng)。考慮到越來越多的綜合性報告文學(xué)作品都不是單純的用一種聚焦類型貫穿始終,聚焦方式的交叉與轉(zhuǎn)換在報告文學(xué)敘事中隨處可見,導(dǎo)致文本中存在著多種聚焦類型。因此,在這里,我認(rèn)為報告文學(xué)敘事聚焦有其獨特的聚焦類型——轉(zhuǎn)換聚焦。這樣一來,報告文學(xué)的敘述聚焦類型就變成了相對平衡的三種——零聚焦敘事、限制聚焦敘事、轉(zhuǎn)換聚焦敘事。當(dāng)然,轉(zhuǎn)換聚焦的存在并不意味著聚焦方式可以進行隨意變動。聚焦方式的轉(zhuǎn)換往往是某種內(nèi)在原因驅(qū)使的結(jié)果。零聚焦、限制聚焦與外聚焦方式各自的優(yōu)缺點能夠在轉(zhuǎn)換中得到互補。因此,轉(zhuǎn)換聚焦,作為報告文學(xué)文本敘事中一種特殊的敘述方式,能夠最大限度地保障文體特性、發(fā)揮文體功能。
二
雖然中國現(xiàn)代報告文學(xué)的發(fā)展時間并不長,但時代、敘述者、接受者等方面清晰的差異,還是必然以聚焦方式的線性流變在文學(xué)性層面上予以表現(xiàn)。
零聚焦的全知敘事便于展現(xiàn)宏大廣闊的現(xiàn)實場景、自由剖析所敘人物的心理活動。因此,它一直都是中外傳統(tǒng)敘事文的首選。深受傳統(tǒng)濡染的中國報告文學(xué)在其萌生階段也較多采用這種聚焦方式。《戊戌政變記》《一周中北京公民大活動》《勤工儉學(xué)生在法最后之運命》等便是選擇了這種“上帝之眼”進行聚焦。然而,細致考察近代至20世紀(jì)30年代以前的中國報告文學(xué),另一番現(xiàn)象更應(yīng)重視——至少在表面上看,包括梁啟超的《新大陸游記》《歐游心影錄》、瞿秋白的《餓鄉(xiāng)紀(jì)程》《赤都心史》等數(shù)量頗多的報告文學(xué)采用的并非零聚焦敘事,而是第一人稱“我”或“我們”的限制聚焦:
余蓄志游美者既四年,己亥冬,舊金山之中國維新會初成,諸同志以電見招,即從日本首途。[6]1
民國八年雙十節(jié)之次日,我們從意大利經(jīng)過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7]1
《赤都心史》將記我個人心理上之經(jīng)過,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所聞所見所思所感。[8]92
“余”、“我們”、“我”是文中的主要人物,又是第一人稱限制聚焦者,文本呈現(xiàn)的社會現(xiàn)實基本都以他們?yōu)橛^察點。雖然通篇都是第一人稱聚焦,但視野并沒有受太多限制。以“我”為中心的聚焦方式,事實上只是零聚焦的一種變形,它與零聚焦的差別只在敘事人稱上。“現(xiàn)代讀者對無所不知的敘述者的敘述是否真實可信表示懷疑,逼得不少作家改用限制敘事。”[9]130畢竟,“如果聚焦者與人物重合,那么,這個人物將具有超越其他人物的技巧上的優(yōu)勢。讀者以這一人物的眼睛去觀察,原則上將會傾向于接受由這一人物所提供的視覺。”[10]119本著啟蒙新民目標(biāo)的報告文學(xué)創(chuàng)作,限制聚焦敘事無疑更能發(fā)揮其現(xiàn)實效用。
1930年至1949年,發(fā)展期的中國報告文學(xué)獲得了長足進步。本時期包括《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包身工》《流民圖》等在內(nèi)的報告文學(xué)明顯強過前一時期。但單就敘事聚焦看,沒有明顯變化。前一時期廣為采納的零聚焦敘事與以“我”為中心的限制聚焦敘事仍是報告文學(xué)的主要選擇。在《包身工》《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個別文本中,外聚焦雖然作為一種藝術(shù)技法內(nèi)化參與到了聚焦進程中,但它終究未能演化成中國報告文學(xué)一個主要的敘事聚焦類型。
本時期的報告文學(xué),很大一部分延續(xù)了前一階段的紀(jì)游體風(fēng)格。《莫斯科見聞錄》《萍蹤寄語》《萍蹤憶語》等均是類似的“在路上”模式。西方世界經(jīng)濟繁榮、政治民主的誘惑,經(jīng)由梁啟超、瞿秋白等人的啟發(fā),依舊在報告文學(xué)界廣受歡迎。這類報告文學(xué)的聚焦方式,選擇的也是梁瞿等較為固定的以“我”為中心的限制聚焦。相比于國外旅行的坦途,當(dāng)時國內(nèi)環(huán)境顯然動蕩許多。戰(zhàn)爭紛擾導(dǎo)致了民眾的顛沛流離,極具社會責(zé)任感的報告文學(xué)作家自然沒有理由將普通人的生活苦難拒斥在外。如蕭乾的《流民圖》以其強烈的使命感傳遞著民間疾苦:
我走近難民叢中,即刻成為他們無告的眼神的焦點了。一個中年婦人走近,跪在地上,哭啼著說:“大爺,我的號碼丟了!”她以為我是放賑的。一個蓬頭瘦削的老媼也向我叩頭,說她是個絕戶老媽,家里房塌了,要我給她找副薄木棺材。鐵軌旁一大簇人翹首等著火車。當(dāng)我走過時,雜亂的聲音中一個戴寬邊草帽的男子問我:“大爺,車啥時候來呀?”一個老翁伸出顫顫的手指對我說:“你可不準(zhǔn)把我們賣給洋人呀!”幾百只、幾千只失了光芒的眼睛向著鐵道那端時刻瞭望。他們的希望都寄托在那遼遠的鐵道盡頭,滿以為只要登車而去,一定就可以睡在房頂下了。[2]157
“我”表面看來是第一人稱敘述,但“我”卻能超過人物聚焦的限制,知曉其他人物的內(nèi)在心理;而且,“我”還時不時地站出來,對目之所見進行情感上的評判。這看似第一人稱限制聚焦,實為零聚焦敘事。這種處理方式無疑能夠更加強化天災(zāi)人禍的“直烙人心”,也更具藝術(shù)感染力。
不過,本時期最典型的報告文學(xué)《包身工》采用的卻并非類似的聚焦方式:
這是楊樹浦福臨路東洋紗廠的工房。長方形的,紅磚墻嚴(yán)密地封鎖著的工房區(qū)域,像一條水門汀的弄堂馬路劃成狹長的兩塊。像鴿子籠一般地分得均勻,每邊八排,每排五戶,一共八十戶一樓一底的房屋,每間工房的樓上樓下,平均住著三十二三個“懶蟲”和“豬玀”,所以,除了“帶工”老板、老板娘、他們的家族親戚和穿拷綢衣服的同一職務(wù)的打雜、請愿警之外,這工房區(qū)域的墻圈里面住著二千左右衣服襤褸而替別人制造衣料的“豬玀”。[2]266
《包身工》所展示的社會內(nèi)容,一度鮮為人知。夏衍采用零聚焦對包身工的生活情況予以步步為營的拆解,生活場景的形象描繪與豐富的背景資料有機結(jié)合。部分看似不動聲色的外聚焦,也都包含著豐富的潛臺詞。而敘述者在文末適時站出來的議論,則洋溢著呼號、悲痛與義憤。本時期包括《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xué)》《中國的一日》《上海的一日》等群眾性報告文學(xué)在內(nèi),大都采用零聚焦敘事。雖有外來報告文學(xué)理論的有效借鑒,但中國報告文學(xué)敘事聚焦的藝術(shù)革新并沒有很快到來。
特殊文體遇合特殊時代的特殊需求,必然會有特殊發(fā)展。談起20世紀(jì)50年代以后中國文學(xué)的政治文化制導(dǎo),報告文學(xué)無疑是最典型的樣本。因其敘事的社會性、新聞性,報告文學(xué)承擔(dān)了更多的時代政治使命。通過抗美援朝戰(zhàn)爭、社會主義生產(chǎn)建設(shè)等重大政治性題材來表達政治化的主題,是本時期報告文學(xué)政治化特征的最好佐證。政治規(guī)訓(xùn)下的很長一段時間,在包括結(jié)構(gòu)設(shè)計、話語選擇等方面,報告文學(xué)敘事依然延續(xù)著零聚焦的全知全能。然而,時代在選擇了報告文學(xué)之后,也給報告文學(xué)作家的創(chuàng)作提出了新的挑戰(zhàn)。很快地,預(yù)示著文體新變的轉(zhuǎn)換聚焦崛起。《誰是最可愛的人》《生活在英雄們的中間》《在橋梁工地上》等在聚焦方式上的突破,讓我們看到了轉(zhuǎn)換聚焦迅速成為與零聚焦、限制聚焦同一層級的聚焦方式選擇的文體必然。及至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受到西方文學(xué)創(chuàng)作技法又一次風(fēng)潮式的來襲,轉(zhuǎn)換聚焦還一度躍居聚焦方式選擇的主角。
通常情況下,轉(zhuǎn)換聚焦在報告文學(xué)文本中有著兩種表現(xiàn)形態(tài):一是在一個文本中有序地嵌入兩種聚焦方式,如“零聚焦→限制聚焦→零聚焦”,呈現(xiàn)為明顯的“雙聲話語”;二是聚焦的蒙太奇,即一個文本中聚焦方式的轉(zhuǎn)換呈現(xiàn)出相對的無序、跳躍,話語復(fù)調(diào)就成為其外在體現(xiàn)。尤其是第二種形態(tài)的出現(xiàn),標(biāo)示著中國報告文學(xué)敘事聚焦的全面、多元與生動日臻完美。從20世紀(jì)80年代中后期的集合式與全景式報告文學(xué)的興盛中,足見多聲部轉(zhuǎn)換聚焦的魅力。《唐山大地震》《西部在移民》《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等文本中聚焦方式的環(huán)繞,有力沖決了報告文學(xué)零聚焦敘事的壟斷。
轉(zhuǎn)換聚焦的出現(xiàn)與繁榮,扭轉(zhuǎn)了中國報告文學(xué)單一聚焦模式的獨調(diào),顯示出報告文學(xué)文體求新求變的生命力。同時期,在小說等敘述文體中的“實驗性”的聚焦方式革新,也深刻地影響了現(xiàn)實行走姿態(tài)的報告文學(xué),拓展了敘事的藝術(shù)表現(xiàn)空間。90年代以來,調(diào)整期的報告文學(xué)在聚焦方式的選擇上,零聚焦、限制聚焦、轉(zhuǎn)換聚焦所占比重大體持衡。
可見,中國報告文學(xué)聚焦模式的流變總體上呈現(xiàn)出由相對單一而逐漸走向多元化的趨向。原本線性而平面的敘事表達,在復(fù)調(diào)式的雙重與多重話語中變得多維而立體。零聚焦敘事的持久魅力,證明了零聚焦敘事與作為其變體的“限制聚焦”之于報告文學(xué)文體的貼合性。而多元格局的逐漸明晰,則彰顯了報告文學(xué)文體掘進過程中對傳統(tǒng)的有效繼承與對西方敘述技巧的能動采納。聚焦模式的多元化,指認(rèn)了報告文學(xué)自身的日臻完善和求新求變的文體生命力。
三
各個敘述聚焦類型所具有的功能優(yōu)勢,為報告文學(xué)作家提供了觀察和認(rèn)識社會現(xiàn)實的多種角度。敘述者根據(jù)所面對的不同聚焦對象,相應(yīng)采用適合的聚焦方式。選擇本身,就包含著相應(yīng)的敘事目的和情感傾向,盡管有時相對隱蔽。換言之,真正左右報告文學(xué)敘述主體聚焦方式選擇的,恰恰在于聚焦對象。因此,在歷時梳理的基礎(chǔ)上,有必要對中國報告文學(xué)繁多的敘述文本進行一個共時的分類。根據(jù)聚焦對象選擇的差異,可分為三類——事件型報告文學(xué)、人物型報告文學(xué)、綜合型報告文學(xué)。
事件型報告文學(xué)指文體敘述以單一事件為聚焦對象。“單一事件”一般都發(fā)生在較短的時域中,規(guī)模較小,但事件仍有明顯的時空變化。這一類型的報告文學(xué),基本上以事件變化為線索,包括萌生期的紀(jì)游與時事、發(fā)展期的戰(zhàn)事與災(zāi)難、探索期的戰(zhàn)爭與建設(shè)、調(diào)整期的時政報告等。梁啟超《新大陸游記》《歐游心影錄》《戊戌政變記》、周恩來《旅歐通信》、瞿秋白《餓鄉(xiāng)紀(jì)程》《赤都心史》、蕭乾《流民圖》、鄒韜奮《萍蹤寄語》《萍蹤憶語》、夏衍《包身工》、雷加《三門峽截流小記》、李若冰《在柴達木盆地》、徐剛《國難》等都是事件型報告文學(xué)在不同時期的范本。
在事件型報告文學(xué)中,為全面展示事件,作者往往采取居高臨下的俯視姿態(tài),隨意變換聚焦的角度,隨意進入文本中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隨意站出來進行個人發(fā)言。這些敘事目的的達到,都必須仰仗全知全能的零聚焦敘事。不管是適當(dāng)?shù)臍v史回溯,還是對人物所思所想的直接表達,零聚焦敘事都能夠滿足報告文學(xué)敘事的需要。對事件全知性的介紹,方便敘述者快速推進行文,并能夠隨時體現(xiàn)出自我的價值判斷。非虛構(gòu)的文本訴求與主觀寫作之間的矛盾,必須仰仗零聚焦敘事才能調(diào)和。
對于事件型報告文學(xué)的接受者,傳統(tǒng)閱讀習(xí)慣的延續(xù)使他們更樂于聆聽全知全能敘述者的娓娓道來。雖然思考空間的狹窄化不免造成接受惰性,但實際創(chuàng)作中作者有技巧、有限度的聚焦控制,還是維系了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
比較而言,在人物型報告文學(xué)中,限制聚焦的采納要普遍得多。人物型報告文學(xué)指報告文學(xué)敘述以人物為中心。人物可以是一個,也可以是多個,可以是社會知名人士,也可以是鄉(xiāng)野村夫。相比于事件報告文學(xué)在中國報告文學(xué)史的主體地位及延續(xù)性,專注于人物刻畫的人物型報告文學(xué)的出現(xiàn)晚了許多。一直到抗戰(zhàn)爆發(fā)后,才出現(xiàn)《國際友人白求恩》《續(xù)范亭先生》《工人的旗幟趙占魁》等寫先進人物的報告文學(xué),并影響了新中國成立后報告文學(xué)的走向。意識形態(tài)規(guī)約下的文學(xué)選擇,有著外在的確定性,但其切入的角度開始從“以事件為中心”轉(zhuǎn)向“以人物為中心”。《誰是最可愛的人》《生活在英雄們中間》《保衛(wèi)和平的人們》《在橋梁工地上》等都是這種轉(zhuǎn)向的直接產(chǎn)物。人物型報告文學(xué)的風(fēng)潮,尤其體現(xiàn)在新時期開端階段,如《哥德巴赫猜想》《生命之樹常綠》《亞洲大陸的新崛起》《船長》《祖國高于一切》《大雁情》……即便到了90年代后的調(diào)整期,依舊有像《沒有家園的靈魂》《敦煌之戀》《天使在作戰(zhàn)》《木棉花開》等依托于人物聚焦發(fā)揮報告文學(xué)敘事功能的文本誕生。各個不同階層的人物,均參與到了報告文學(xué)人物形象體系的建構(gòu)當(dāng)中。人物個性化的性格特征,包括語言、行為等都在非虛構(gòu)性的文本聚焦中得到了盡可能完好的呈現(xiàn)。
在人物型報告文學(xué)中,敘事進程基本由人物推進。限制聚焦能充分敞開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表現(xiàn)人物激烈的內(nèi)心沖突和漫無邊際的思緒。在敘述過程中,作家從一個或幾個人物的視角限制中去觀察并表現(xiàn),也可以展示聚焦對象的內(nèi)心世界。聚焦的限制無疑能夠造成更逼真的非虛構(gòu)感。而且,一定的死角與空白對于讀者介入文本、參與文本能起到很好的誘引。因此,限制聚焦是人物型報告文學(xué)比較合適的選擇。
不過,聚焦限制于報告文學(xué)文體追求而言又存在著矛盾。一個或者幾個人物的有限視野,顯然無法涵蓋文本全面展示的企圖,敘事模糊不可避免。因此,即便是人物型報告文學(xué),限制聚焦的采納也只作為基礎(chǔ)選擇,不能通篇采用。零聚焦敘事一定程度的參與,才能實現(xiàn)敘事的清晰與完整。所以,嚴(yán)格地說,人物型報告文學(xué)并不存在單一的聚焦方式,更多的是以零聚焦為背景的限制聚焦。只不過由于它距離轉(zhuǎn)換聚焦仍有較明顯的距離,我們這里依然采用限制聚焦與人物型報告文學(xué)進行總體上的遇合確證。
三種聚焦類型中最適合報告文學(xué)的是轉(zhuǎn)換聚焦。它既包括了聚焦方式之間的交叉與轉(zhuǎn)換,也包含了聚焦方式的變異。單一化的全知全能會傷害報告文學(xué)的文學(xué)性,也直接挫傷讀者的閱讀興趣;限制性的敘事朦朧,對報告文學(xué)敘事功能的發(fā)揮同樣是致命的;只有轉(zhuǎn)換聚焦,能很好地平衡報告文學(xué)非虛構(gòu)性與文學(xué)性之間的矛盾。這一點可以從綜合型報告文學(xué)的成功得到證明。
綜合型報告文學(xué)是一個寬泛的概念,所有非事件型、非人物型的報告文學(xué)都可以納入這一范疇。綜合型報告文學(xué)出現(xiàn)的時間,基本上就是轉(zhuǎn)換聚焦出現(xiàn)的時間。這一類型的報告文學(xué)關(guān)注重大的現(xiàn)象或問題,人物數(shù)量較多,文本篇幅比另兩個類型更長。新時期以來的問題報告文學(xué)、改革報告文學(xué)、反思報告文學(xué)、全景式報告文學(xué)等都屬于綜合型報告文學(xué)。喬邁關(guān)注現(xiàn)實焦點的《三門李軼聞》、李延國反映改革新氣象的《中國農(nóng)民大趨勢》、胡平、張勝友探討出國潮問題的《世界大串聯(lián)》、麥天樞聚焦國內(nèi)人口流動的《西部在移民》、陳桂棣、春桃底層關(guān)懷的《中國農(nóng)民調(diào)查》等通過對一個重大事件或社會問題宏觀全面的把握與細致入微的體察,將綜合型報告文學(xué)的文體輻射面與功能指涉進行了更進一步的拓展。
顯然,正是不同聚焦對象對文體敘述不一樣的要求導(dǎo)致了報告文學(xué)聚焦方式選擇的不斷豐富。而報告文學(xué)敘事聚焦選擇由單一而逐步多元化的背后,我們看到的是報告文學(xué)敘事對社會關(guān)注面的擴大化及其介入現(xiàn)實的文體功能的不斷強化。
四
聚焦方式的不同選擇凸顯了報告文學(xué)與其他紀(jì)實性作品間的差異性。然而,不管是哪一種聚焦方式,事實上都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盲區(qū)。很多沒有親見的細節(jié)、事件宏大的背景、人物的心理世界等就變得無法捕捉。人對世界的聚焦,既有感知性的,也有認(rèn)知性的,感知性聚焦指的就是由眼、耳、鼻等身體感覺器官進行觀察;而認(rèn)知性聚焦則意味著敘述者意識活動的參與,包括回憶、推測、評判等知覺活動。認(rèn)知性聚焦是作為感知性聚焦的補充而存在的:
他關(guān)上收音機,推開窗戶,又打開了門,任凜冽的寒風(fēng)吹進房間來。好像在跑野外時的極度勞累以后,他站上山頂,登高遠望,已查明了構(gòu)造線,看清楚了大地位移,感到無比的暢快。黑暗的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動亂的中國,頓時充滿了無限的希望,閃耀著未來的光明。[5]78
寫作《地質(zhì)之光》時,李四光早已參加過了1947年底在英國倫敦召開的第十八屆國際地質(zhì)學(xué)會大會。未在場的徐遲借推測、想象等完成了對李四光行為動作與內(nèi)心思緒的還原。這段文字顯然不是作家感官聚焦的結(jié)果,而是認(rèn)知性聚焦的產(chǎn)物。在以往的報告文學(xué)理論研究中,通常將這種認(rèn)知性的聚焦與想象直接劃等號。它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虛構(gòu)”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虛構(gòu)的最基本特征就是現(xiàn)實的必然缺席”,“想象并不是一種自我激活的現(xiàn)實力量,而是必須借助外在力量才能夠得以展現(xiàn),通過主體(柯勒律治)、意識(薩特),或是社會-歷史心理(卡斯特里阿蒂斯)——上述列舉并非窮盡了可能的動因——才能夠成為自己。”[11]251將認(rèn)知性聚焦予以藝術(shù)化的呈現(xiàn)對于文學(xué)十分必要。它不僅賦予了文本以審美的維度,也使人類的日常生活行為具有了審美意味,缺少了這一聚焦動作,報告文學(xué)作家“將決不能活畫出這個世界,使得讀者不但了解他而且和它一道生活。”[12]
在中國報告文學(xué)的發(fā)展流脈中,認(rèn)知性聚焦有著多種表現(xiàn)形態(tài)。其中,細節(jié)還原、氣氛營造、類比想象等是比較常見的:
一個滿臉胡楂的男知青在可怕的沉寂中呆立了幾秒鐘,然后猛地扔開山鋤,發(fā)瘋一般往山下狂奔。他的眼睛凸突,臉色鐵青,仿佛一個聽到判決的死囚。他不顧一切地向前奔跑,無論陡險的山路,湍急的澗流,還是幽暗恐怖的大森林,統(tǒng)統(tǒng)都不能阻擋他的腳步。當(dāng)他終于跌跌撞撞出現(xiàn)在衛(wèi)生所門口時,已經(jīng)傷痕遍體,頭上淌著鮮血,衣服被灌木和荊棘撕成碎片。[13]15
在報告文學(xué)中,細節(jié)刻畫是文學(xué)生動形象性很重要的憑借。對于“滿臉胡楂的男知青”在驚聞“女知青的死訊”時的倉惶行動,沒有任何聚焦者親眼目睹、全程追蹤。但是,這些細節(jié)對于凸顯其“還是不可原諒地來遲了一步”,有著特別重要的敘述價值。
氣氛營造,不論是對事件來龍去脈的梳理,還是對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有重要意義。所以,在狀寫細節(jié)以凸顯在場感時,報告文學(xué)作家也很注重對周邊情景與氣氛的渲染。《地質(zhì)之光》寫到了凌叔華給李四光打電話這一真實細節(jié),但是包括打電話的時間、通話時的情景與氣氛等卻都是作者認(rèn)知性的推想:
當(dāng)黎明來臨,他還睡著時,被一陣電話鈴聲驚醒,從倫敦打來了一個長途電話,他穿著睡衣接聽。對方一個女性的聲音問訊他。
“是我,”他說。又問:“你是哪一位?”“凌叔華。”
“你好!什么事?”[5]84
李四光與凌叔華的通話情狀,只能依托他在倫敦期間的活動進行合理推想。通話時具體的情景和氣氛,更是要憑借通話內(nèi)容進行藝術(shù)性的推測。這種思維活動,并非徐遲所理解的“有事實根據(jù)的虛構(gòu)”,而是感知性聚焦之外的認(rèn)知性聚焦。在掌握可靠資料的基礎(chǔ)上,根據(jù)人物性格和事件發(fā)展的必然趨勢進行合理的認(rèn)知聚焦,能夠增強報告文學(xué)敘事的感染力。
在談到一個不被人熟知或是抽象的事物時,我們常用類比進行更淺顯、生動的傳達。報告文學(xué)沒有脫離集體性的歸附。類比想象的采納,無疑能深化報告文學(xué)主題意義的傳達:
看著這種飼養(yǎng)小姑娘營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時候看到過的船戶養(yǎng)墨鴨捕魚的事了。和烏鴉很相像的那種怪樣子的墨鴨,整排地停在舷上,它們的腳是用繩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魚,起水的時候船戶就在它的頸子上輕輕地一擠!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鴨整天地捕魚,賣魚得錢的卻是養(yǎng)墨鴨的船戶。但是,從我們孩子的眼里看來,船戶對墨鴨并沒有怎樣虐待,而現(xiàn)在,將這種關(guān)系轉(zhuǎn)移到人和人的中間,便連這一點施與的溫情也已經(jīng)不存在了![2]209
孤立地看,這段話與“包身工”似乎沒有任何關(guān)系。但恰恰是這種“毫不相干”的類比想象,將墨鴨的生存際遇與包身工的生存現(xiàn)狀串聯(lián)起來。帶工老板的貪婪無道、包身工生活的酸辛痛苦,便以更加形象立體的方式呈現(xiàn)了出來。而文本對包身工罪惡制度進行批判的主題,也得到了強化。
當(dāng)然,報告文學(xué)的認(rèn)知性聚焦在文本中,多與感知性聚焦以不易察覺的方式交融在一起,不容易被識別、剝離。“如果作家以他直接間接得來的素材為根據(jù),輔以主觀的分析、解釋、乃至于加以想象的補充——這雖然不是直接描寫事實,但也不是脫離事實的虛構(gòu)——往往能使作品更加生動和豐富而避免平鋪直敘的呆板和枯燥。”[14]84感知性聚焦與認(rèn)知性聚焦在文本敘述過程中的渾然天成恰恰能夠使報告文學(xué)的文體使命得到最好的發(fā)揮。
可見在學(xué)理意義上,從敘事聚焦的角度去探究報告文學(xué),尤其是轉(zhuǎn)換聚焦的引入,更能夠從理論的層面上對現(xiàn)代報告文學(xué)的特質(zhì)進行廓清。零聚焦、限制聚焦與轉(zhuǎn)換聚焦三種聚焦方式在線性歷史流變中呈現(xiàn)出的單一而逐漸多元化的趨向,指認(rèn)了中國現(xiàn)代報告文學(xué)的日臻完善和不斷求新求變的文體生命力,更確證了報告文學(xué)對社會關(guān)注面的逐步擴大化及其介入現(xiàn)實的文體功能的不斷強化。而感知性聚焦之外的事實,則需要由認(rèn)知性聚焦進行有效的補充,以使報告文學(xué)的文體使命得到最好的發(fā)揮。
[1]周政保.非虛構(gòu)敘述形態(tài)——九十年代報告文學(xué)批評[M].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
[2]中國報告文學(xué)叢書編輯委員會.中國報告文學(xué)叢書:第一輯第一分冊[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81.
[3]韋恩·布斯.小說修辭學(xué)[M].華明,胡曉蘇,周憲,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7.
[4]川口浩.報告文學(xué)論[J].沈端先,譯.北斗,1932(1).
[5]中國報告文學(xué)叢書編輯委員會.中國報告文學(xué)叢書:第三輯第五分冊[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82.
[6]梁啟超.新大陸游記[M]//飲冰室合集(7).上海:中華書局,1989.
[7]梁啟超.歐游心影錄[M]//飲冰室合集(7).上海:中華書局,1989.
[8]瞿秋白.赤都心史·引言[M]//中國報告文學(xué)叢書編輯委員會.中國報告文學(xué)叢書:第一輯第二分冊.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81.
[9]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zhuǎn)變[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
[10]米克·巴爾.敘述學(xué):敘事理論導(dǎo)論[M].譚君強,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5.
[11]沃爾夫?qū)ひ辽獱?虛構(gòu)與想象——文學(xué)人類學(xué)疆界[M].陳定家,汪正龍,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12]T·巴克.基希及其報告文學(xué)[J].張元松,譯.國際文學(xué),1935(4).
[13]鄧賢.中國知青夢[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3.
[14]以群.論迅速反映現(xiàn)實的特寫[M]//周國華,陳進波.報告文學(xué)論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85.
A Study of Narrative Focus on Chinese Modern Reportage
GUO Zhi-yu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F(xiàn)ujian Normal University,F(xiàn)uzhou 350001,China)
A theoretical clearance is made of Chinese modern repor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zero focus,limitation focus,conversion focus,and the level of the narrative focus.The three kinds of focuses show the trend from a single form to a gradually diversified one in the linear rheology in history,identify the vitality of literary style and innovative ideas in reportage,and also confirm its gradual expansion of social concern and the constant strengthening of the involvement in the reality of the stylistic functions.However,the facts beyond perceptive focus need to be complemented by an effective cognitive focus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reportage style mission.
reportage;narrative focus;conversion focus;focus object;cognitive focus
I206.7
A
1008-2794(2015)01-0043-07
2014-10-09
郭志云(1985— ),男,福建永春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xiàn)代報告文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