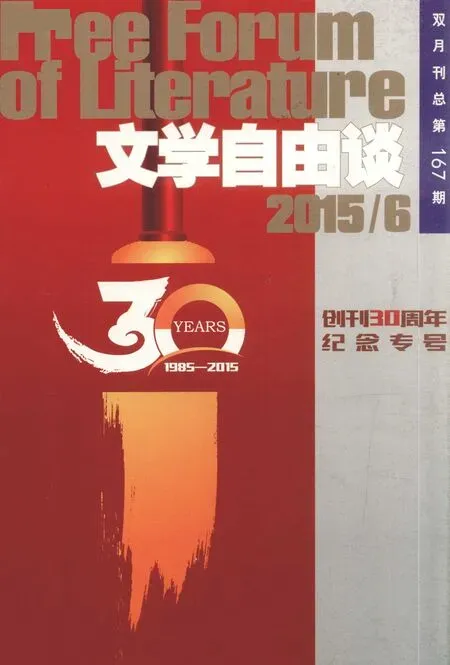自覺的批評與明顯的局限
牛學智
自覺的批評與明顯的局限
牛學智
蒙《文學自由談》任芙康先生和黃桂元先生不棄,當我的有些觀點和有些角度顯得好像比較扎眼而不能被其他刊物接受的時候,這份刊物給了我莫大鼓舞,我由衷地感謝這份刊物。兩位主編不但相繼刊發了我好幾篇小文,即便有些文章不被刊用,他們也總是以各種方式告知我不用的原因,而擔任溝通聯絡的通常是黃桂元老兄。他的話有時候說得很直接,比如他說得最多的一個詞是“長文呆論”;稍微柔軟一點的話,我至今還記著的,可能就是“再討論這話題似乎沒多大意義了”,或者“這話題已經有人寫了”之類。因為我和桂元兄是魯院同窗,想著他可能是念同窗之誼的緣故,用與不用才都一一回信,也就覺得心安理得了。后來,偶爾出外開會碰到也投稿給該刊的作者,寒暄之間,情況居然一樣,甚至透露有些回信大概有一整段的長度,說者情緒自然激動,聽得出來那意思當然是作為作者被格外尊重的感覺,并且是沒能受到尊重或頗感無奈無助的其他投稿經歷映襯的結果。這樣的事情遇到得多了,作為《文學自由談》的作者,不管曾經是還是現在是,冥冥當中,這份刊物似乎真就成了陌生人感情升溫的火苗,大家心里會油然地“哦”一聲,其他的來龍去脈仿佛完全不用多解釋——那還用說嗎,大家肯定是價值觀念的共同體了。
后來仔細琢磨,大家都是文學及其批評中人,投稿的刊物肯定不止一份《文學自由談》,然而,為什么唯獨《文學自由談》有這樣的吸力?或者說,人們認為觀點能被《文學自由談》接受,為什么就值得驕傲?我不揣冒昧,在這份刊物創刊三十周年紀念之際,試著說說這個話題,無論對于刊物還是對于作者,想來應該多少有點意思。
剛才我提到“價值觀念共同體”,需要一點解釋,不然很容易產生誤解。特別是圍繞在《文學自由談》周圍的價值共同體,或由《文學自由談》導向逐漸生成的價值共同體,更需要做一必要的界定。
省事的解釋,當然是“本刊選稿六不思路”了,那多清楚啊!然而,宗旨不等于實踐,這是常識。再說,類似我這樣有一搭沒一搭,甚至很多時候把科研選題之余,或直接說把不合“長文呆論”標準的“不得不說”、“不說都不行”的“思想火花”,寄往天津市和平區新華路237號《文學自由談》雜志編輯部的作者,肯定也不在少數。所以,三十年來,這份刊物所形成的基本穩定的文章風格特點,向來是由至少兩種人文價值訴求不斷滾動滲透,相互影響、相互改造的結果。一種是正兒八經的研究或創作,可能與“六不思路”并不太搭界,但長期的定向性研究或創作已經非常枯燥,憋了一肚子想說要說該說而其他刊物又不會輕易容納的話,正好適合于“自由談”;只是文風上要符合《文學自由談》,必須首先訓練好行文及語言措辭,最好是把“分裂”的痕跡打磨得圓潤一些。這樣,《文學自由談》上占一定比例的文章,總是顯得很凌厲很峻急,但觀點一般屬于對此時此刻文壇熱點的凝聚,從而造就了《文學自由談》總顯得富有“總結性”,其“牽一發而動全局”的急先鋒形象頓時被突出了。另一種是“很上手”的文章,讀打頭一段你就知道,該作者是“自由談”老手。與其說“六不思路”產生了這類文章,不如干脆說正是這類作者和文章,“六不思路”才被坐實了。六條否定性標準無形無蹤,不好拿捏,但讀這類文章并揣摩作者運思,其對應的肯定性標準便呼之欲出了。更重要的是,呼之欲出還遠遠不夠,肯定性標準正源源不斷自發地從后面推來,緊接著氣勢洶洶地向無盡的前方“殺”去,這才從稿源上確保了《文學自由談》批評價值基礎。
如此說來,圍繞這份刊物而形成的價值共同體,不妨說是一種自覺的批評意識形態。擇其要者來說,我個人以為這種批評價值共同體的主要訴求,大體有三點。
首先的一點是,文章絕對寫得有意思。不要小覷這個“有意思”。一個刊物中有那么幾篇寫得有意思,這是太正常不過的事了;但幾乎所有文章都讀起來很有意思,乃至于讀完一篇就想讀下一篇,讀不完整篇文章放不下,達到這個整體水平的文藝理論批評刊物,依我的閱讀視野,似乎不多。當然,這個“不多”我這里只限定為,議論什么暫時不去管,單就行文邏輯、話語選擇和捕捉當前人們基本趣味的說話語調口氣來論。否則,同樣小16K本的《讀書》《隨筆》也絕對有資格說是“有意思”的刊物。《文學自由談》的有意思,顯然首先是語言層面的。有時候它的欄目是“特約”“直言”“茶座”“思考”“視野”“閑話”“講壇”“人物”“反彈”“筆記”“序跋”,有時候有可能是“調查”“獨白”“來函”,或者“推薦”“行旅”“對談”“憶舊”“自省”,甚至“追思”“鉤沉”“解讀”“專題”“論壇”等等,但看得出,“特約”“直言”“茶座”“思考”“閑話”“人物”等是其主打欄目。讀每個欄目下的每篇文章,可以覺出作者和編者聯手,反復推敲語句、嘗試詞語準確度的過程,也能感受得到什么是面團越揉越筋道,什么是理越掰扯越透明的道理。它們或者目光如炬,不看出妖氣不收場;或者雅言勤勤,曲里拐彎不說服對方決不算完;或者刨根問底,不追究到祖墳不罷休;或者怒目逼視,非得把那么點神氣揭穿不可;或者氣淡神凝,非得把那么點裝勁打垮不可;或者手法嫻熟,非得把那么點遮羞布脫下不可;或者心細如發,非得把深藏于皺褶里的污垢一一翻曬不可……總之,無論議論的事情大還是小,話題莊重還是諧謔,涉及的人物位高還是底層,只要其不在理、不在行、不著邊際、不靠譜,便軟硬兼施、誘敵深入、關關設伏、層層剝筍地“自由談”,總能于短論中、片言中戳到軟肋上,打到七寸處。疲憊之余,焦慮之余,迷茫之余,或是被不確定性糾纏之余,捧讀《文學自由談》,哈哈一笑,那過不了的坎還是個坎嗎?那不愉快的事兒還是個愁事兒嗎?那不確定的事態還能把活人的兩條腿絆住嗎?
誠然,痛快歸痛快,作為一份談文藝文學或文化的刊物,最重要的乃是,讀者能從作者起承轉合的寫法中,真正明白板著面孔講道理是多么的不自在,正襟危坐論邏輯是多么的不入時,尤為可怕的是旁征博引最后的落腳點竟然是芝麻大點事,那該是多么的不值當?一個人的文章表現出如此語言面貌,絲毫不覺得稀罕,稀罕的是一份刊物的語言、修辭、表達方式居然也能表現得那么集中。往大里說,這不啻是一種批評方法論的張揚,抑或至少是批評語言論的示范。
其次是傳統文化倫理作為就事論事的價值標準。我關注并斷斷續續把《文學自由談》當作不得不讀的刊物始于2005年。這份刊物今年已經走過了三十年歷程,前面的三分之二光景我不甚了解,只就這后面三分之一來說,以我可能不準確的感知而論,這份刊物中的大小文章,有時你感覺蔓延得非常遠,幾近“散談”,但漸漸熟悉了之后,長短不一的文章,其實都不會離具體個體的道德倫理太遠。也就是說,有些投稿或許不這樣,但當投稿變成《文學自由談》中的鉛字,它有個萬變不離其宗的“宗”在那里堅硬地挺著。這個衡文論人的“宗”便是多少從中國傳統文化中轉化了一下的“溫、良、恭、儉、讓”。說到這一點,我必須申明一下,雖然身邊有好多《文學自由談》,但我不可能逐期細讀,即便細讀過某幾期,也不會是諸篇細讀。讀了誰的文章,完全取決于文章標題對我的吸引力,和我最想了解的話題。之所以說“轉化了一下”,也是我個人的一個感受。前面說過,這份刊物中的幾乎所有文章,從語言構建層面來說,寫得都很有意思。接著語言的有意思而來的,自然是論題論析得透不透徹的問題,而透徹程度,除了表述邏輯,還有價值觀。這一層看,該刊文章的“秋后算賬”風格,一定程度得益于它們都是沖著常識而去。面對常識被踐踏,面對常理被歪曲,面對基本經驗被誤識,中國傳統文化系統中的某些標準,才能派上用場。進一步說,在別的媒介,特別是理論批評刊物,為了什么而有意凸顯什么,以至于把“新”鼓蕩得神乎其神,把“奇”蠱惑得異常突出的時候,歷史感實際上早就斷檔了。此時《文學自由談》的作者——特別是穩定作者群,言事的道德成色,論文的倫理傾向,估人的人道主義情懷,恰好是對“歷史遺留”現象的莊嚴回眸。甚至不為名者諱,指名道姓;不繞著問題,拷問真相的質地,可謂刮骨療傷——驚出一身冷汗,換來醍醐灌頂的清醒。
李美皆筆下“總是很忙”、沒時間讀文本卻寫下了一篇篇大序的陳思和,百般支吾、矯情萬分的余秋雨,李銀河時代的王小波,等等,都堪稱這個價值支點下行文的典型性例子。讀此類文章,乃至于合上刊物,認為這些人或這些事,之所以該批,重要癥結,不就是不厚道、不誠實的問題嗎?如若非得說他們非如此不可的原因在別處,一定多么神氣,那就是成心與人抬杠了。而李美皆所用理論和評價尺度,當然也不高明,不就是下了比別人更大的文本細讀工夫,以基本的傳統倫理道德照出了平常心就能看出來,卻被平常心一再神化或異化了的真相嗎?
其他例子就不再多舉。總而言之,通過個別文章窺斑見豹,在大家都一窩蜂一樣一頭扎向“傳統文化”“國學”的當兒,《文學自由談》對作者有選擇地轉化并運用傳統倫理道德評價標準的持續支持,奠定了刊物的本土化理論基礎,夯實了作為優秀刊物應有的穩健價值基座。當然李美皆最近發表在該刊的文章,傳統道德倫理標準好像轉換成了所謂“女權主義”(或“女性主義”),又由“女權主義”異化成了私密化女性心靈遭遇,是典型的以女性怨懟心理宣泄為標準的衡文論人。暫時按下不表,后面再說。
再次,是格外突出了個人經驗的中軸作用,最低限度澄清了許多用高深理論越講越糊涂的道理。當然,這個“個人經驗”,不是泛泛而談的私密化心靈遭遇,更不是通常情況下排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語境,僅圍繞個人利益展開的自我本位主義。它是經過對論評對象全方位的占有、消化處理,再回爐吐出來的既有研究未曾發現、既有資料也不曾完全顯明的東西,故而這種個人經驗也可稱之為“主體感知性意見”,是良知、正義出發的必由之路。《文學自由談》對個人經驗的彰顯和眷顧,無需過多闡釋,僅本人的投稿體會,話就差不多能說一籮筐。2005年在魯院認識黃桂元兄以后,對這份刊物的畏懼心理有所消減,然而仍不敢投稿給它,主要原因是覺得人家是談全國性大問題,我當時還只在小范圍內“跪著”仰脖注視我的觀照對象;與之比較,單是我為文的姿態就驢唇不對馬嘴。黃桂元兄看出了我的猶豫和怯懦,鼓勵我說如有現成稿子可以給他先看看。記得那時候正好有篇寫西部文學精神的稿件,于是就給了他。過了一周左右,他約我說稿子的事,主要意思是,你從文學史分期說事,那么你的體驗是什么,這是其一;其二,你站在西部說西部文學如何是中國當代文學精神的高地,這有自我標榜的嫌疑,那么,這精神如果換成局外人來看,是否還是那個高地?不用說,這稿子肯定不能用。但我還不能馬上接受他這一套理論,我的理由似乎也很充足,執拗地認為文學批評就是要學科化、學術化甚至還要盡可能理論化。當時正流行“底層敘事”,我的主要觀點是西部文學大多數寫的是底層的艱辛和苦難,能否把這種寫實主義精神提升到理論的層面,然后推而廣之,矯正那種剛剛抬頭的“新新人類”價值觀對實際生活的遺忘式想象?拙文中所謂精神云者,其實是對亢奮的理想主義的批判和質疑。好了,這樣的一通雖未說出口卻眼神里早有的頂牛,好像激怒了桂元兄,他終于亮出了刊物殺手锏——長文呆論。這也是這個詞為什么我一直很敏感的幾乎全部原因。它像一個警鈴,鳴響于我的內心,盡管老毛病一下子改不掉,但每做文至一定長度,就會想起它。另外的例子還可順便再舉一個。比如某年某期我發的批評張頤武“架空性”寫作那篇,如果沒記錯的話,大概是迄今為止該刊所發文章中用了好幾個小標題的為數不多的幾篇之一了。但此文發表之前很是折磨人。先是去掉了繁瑣的注釋,再是把通行看法一一擠掉,最后要求我再從頭到尾潤色一遍……達到什么效果呢?達到完全是“我”的而不是“述”和“評”的簡單相加。可想而知,最終與讀者見面的文章,其實與前面的幾稿已經沒有半點關系了。說實話,于我而言,寫這類文章相當吃力,最難的還不是如何使用自己的語言的問題,而是如何使用自己的思想的問題。弄不好只有別人沒自己,或只有自己沒別人,更平庸的是用別人說自己,或用自己說別人,三不像。寫出點真正的個人經驗有多么難,我算是領教了。
至于該刊其他文章的個人經驗問題,相信它的忠實讀者一定有強烈的感性認識,毋庸多說。正是該刊冥冥中這樣的一個導向,從我個人體會說開去的話,個體感知性經驗至少有三點是為這個刊物的形象重塑加分的。一是為文壇新舊事留下了新觀點;二是為重新審視文學新舊理論留下了新經驗;三是為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的文壇是非留下了民意。
這便是個人經驗中最富精華的部分。當它發揮到飽和狀態而不過度,經它丈量過的文、人和事,最終顯示出了與通常的“史”“述”“論”和“評”有明顯區別的特色,“自由談”作為一種批評思潮的可能性也便昭然若揭了。它比中國古代印象妙悟式點評更理性更系統,比西方現代敘事學和敘述學研究方式,更靈動更主體化——也就更價值化一些。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刊物也有它的社會文化語境規定性,下面用少許篇幅說說《文學自由談》的局限性。為了更能說明問題,希望下面所舉例子不單是作者個人的,它理應是刊物趣味的具體化表征。對應于上面的三點,局限性我也試著提出三點,與編輯老師和讀者商榷。
第一,文章寫得有意思,與編選者的選擇有直接關系。文章普遍很有意思,這說明《文學自由談》的編輯具有伯樂眼光,也表明該刊編輯在用什么樣的稿子上具有絕對自主裁決權而不是相對自由的裁決權,更不是被動等待。另外,有意思的文章,說白了,語言表達之外,還必須得有有意思的價值追問,否則,有意思就會迅速變成漂亮的廢話、油滑的饒舌、順溜的行話。整體上說,《文學自由談》絕不在此列,但經常確有部分文章屬于此列,這在該刊常駐作者那里還是表現得比較突出的。比如《誰向誰投降》(陳沖,2010年第5期)一文,讀到最后掩卷而思,不就是借《人民文學》《收獲》發表郭敬明小說的事,想追問背后的市場原因嗎?然而這只是我的判斷,文章并沒有這樣做。文章繞來繞去繞到一個很小的角度——從兩個當年或現在的主編為何要發表郭氏小說的解釋開刀,中間分析不是“投降”而是“妥協”,最后又回到起點——“明白向糊涂投降”。轉了一大圈之后,最能觸及價值嘩變,從而也最能揭示主流知識分子或主流刊物集體性“轉向”的地方,始終沒有呼之欲出。可以想見,一直糾纏誰的解釋更理論更不被人抓住把柄,誰更不會掩飾自己隱藏自己,該是多么無聊啊!就是大膽談談社會機制和精神文化導向問題,又能怎么樣?當然,這一類文章也真不少,基本屬于只做文字表述功夫,并不想也不愿把問題引向深入。本來該指向普遍的文化現象,寫來寫去卻成了純個人趣味的取舍,或叫“妥協”。由此可推知,語言表達的有意思弄不好會蛻變成價值判斷上的“揉面團”和“打太極”。恕我直言,這一點正好暴露的是,吾國文人到了一定年齡,總喜歡儒、釋、道,是以所謂超脫眼光踐行“難得糊涂”人生哲學觀的體現。同理,一份刊物如果不加反思,先以有意思的文章為首要尺度,如此人生哲學觀就會如梗在喉,終將鑲嵌在它的成長始末,這就不是加分了。
第二,以傳統文化中具體的道德倫理方式方法為標準,以就事論事為疆界,好處是便于集中優勢兵力攻破頑敵,但痛快之余,犀利之余,長驅直入之時,是不是有意忽視了個體與集體、文學與社會、文化與政治、人性與時代之間比例的分配?換句話說,既然是談文學,以人性為中心、以情感倫理為重點肯定沒錯,只不過,有問題的是剔除使人性之所以是這樣不是那樣,剔除使情感倫理之所以是這樣不是那樣的普遍性文化氛圍和主流意識形態提倡的經濟主義價值導向,孤零零地談文學中的人性或虛構世界中的人事,是否可能?它的說服力在哪里?
比如《一個在校大學生該怎樣練習寫作》(韓石山,2015年第5期)一文頗能說明問題。如文章題目所示,中心就是為在校大學生開出一套或幾套有效的寫作“練習法”。可是讀著讀著味就不對了:你讓大學生屁股坐定,一門心思練習“平實敘事的本領”,還教學生如何警惕“不平實敘事”的影響——“《平凡的世界》文學品位不高,就是少了柔性,太正經了”。于純審美而言,作為過來人,可謂“箴言”。然而,當這樣的觀點不止一次出現的時候,當大學生一開始練習寫作,就學會玩趣味,甚至覺得趣味至上是文學的唯一要義之時,按照如此邏輯生產出來的文學,還會與作者前面批評的那些“智商不高的人”硬撐著“玩高智商游戲”的結果有根本不同嗎?那些“智商不高的人”玩“高智商的游戲”,“太正經”“少了柔性”,導致“好像越是上不了大學的,越是有文學的天賦,越是上不了大學的,越能寫出優秀的文學作品”,也就意味著中國當代文學整體水平不高。就中國當代史的特殊性來說,作家出身與文化程度錯位,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不能就此說明中國當代文學水平普遍偏低的原因就是語言表達上缺少柔性、太正經。價值問題和思想訴求算不算?有了足夠的柔性和不正經,就一定在自己的思想表達上高于西方文學嗎?這好像不是一個正比關系吧!
再回到在校大學生上來。錢理群窮極幾十年浸泡在高校,他對近年來高校學生價值取向的判斷是“精致的利己主義”。如果這個判斷是經驗的,那么韓文所主張的文學價值觀,正好反過來支持了錢理群的經驗,即是說,韓氏恰好是在“精致的利己主義”語境中談文學的,而不是跳出這個語境反思和批判的態度。錢理群和韓氏的思想分野,其實是現代性與傳統性的區別,前者對當今大學生集體性沉陷于利己主義導致的人文后果,充滿憂患意識;后者為當今大學生深得流行價值觀乃至走向小技術主義經濟工具,扶上馬送了一程。剛進入文學場,就尋求柔性十足和不太正經的,能是現代意義上健全的人格?如果把現代意義的人格簡單理解為運用自己的理性獨立判斷自己的社會現實和時代文化風氣的話,那么,這樣的大學生一經走向社會,假如成長成一個作家,還會像青年路遙那樣雖文字略顯粗糙但到底思考人的不自主一類問題,進而力所能及觸及政治嗎?答案是否定的。
說到人格事關重大,韓文所牽扯出的另一問題,抽象點說,是價值觀和世界觀問題。順著專業方向拼搏,精鉆一門技術,或許會成為一個不錯的專業技術人員,但手藝不錯的專業技術人員并不等于有擔當的公共知識分子,這恐怕才是我們的文學很難問鼎時代前沿思想問題的癥結所在,也是顧彬“垃圾說”的直接依據。
——這也不正是當代英國學者弗蘭克·富里迪《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對抗21世紀的庸人主義》一書批判的庸人主義嗎?我不敢武斷地說,韓文觀點就是庸人主義。然而韓文提倡的柔性十足的不太正經敘事,稍有不慎,很容易變成解構求真意志來迎合流行觀念的口實。一句話,這種四平八穩、安安詳詳、舒舒服服的文學觀念,其實是今天傳統文化熱中衍生出來的審美觀,它不同程度分布在社會各個行業,不單反映在文學上。即是說,大家都就事論事、練好討巧的技法、活命的技能,掃干凈自己門前雪得了,管那么寬干什么。
行文至此,我心里也十分不舒服,生怕有可能開罪于韓先生,于是停下來又翻了其他幾期刊有韓先生文章的該刊,另外的文章讀起來其實仍是一個味兒,這說明這種人生觀和世界觀,在韓先生那里,至少在《文學自由談》所刊發的韓先生大量文章中是經常存在的。
第三,關于個人經驗作為尺度的問題。我前面說,只要個人經驗的發揮沒有過度,在飽和而不漫溢的范圍,正好是個體感知性意見,即良知的表達。這種表達可以不用現成知識,因為現成知識沒法感知到正在變動的時代的問題。但是,一般情況下,個人經驗只是集體流行價值的復制,如果沒有社會學、政治經濟學視野支持,個人經驗充其量是個不具有學理合法性的個案,很難上升到普遍性高度。如此,始終以自信的個人經驗為標準,留下的只是個體僅為個人的內心絮叨。李美皆的《論周濤的反愛情主義》(2015年第5期)和《因為,你是朱蘇進》(2010年第5期),可以作為例子。
應該說,這兩文舉證都很翔實,是典型的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可是,材料還需要主體性照射才能被激活,否則,材料本身并不是自明的。這兩文都是個人經驗用過了頭的范例,前者指出周濤自述中的反愛情主義,按照所引材料看,似乎沒有什么不對。問題就出在作者總是以自己據說是“女權主義”的認知來打量周濤的愛情觀,弄得驢非驢馬非馬。周濤那一代人的歷史規定性、社會文化規定性幾乎被刪除殆盡,留下的只是作者——我可能產生了不必要的聯想:難道這是身邊某個待字閨中的中年婦女沒完沒了的祥林嫂式傾訴?作者反而成了中心,周濤自述不過是偶爾一用的例子。《因為,你是朱蘇進》一文企圖揭穿編劇朱蘇進與小說家朱蘇進在選擇失度后的墮落,但是也因過度使用個人經驗,一直絮絮叨叨說的是朱蘇進在兩者之間的表現,及表現如何滑稽可笑的事。追求更多的錢,本來放到誰身上都不是個單純的道德問題,但作者卻偏偏在單純道德問題上做文章,本來要談的主題——人文知識分子淪落的社會根源,終究因為深陷女性怨懟泥淖而從文章中隱遁了。
曾有批評家撰文,指出近幾年李美皆的批評文學發生了一個只羅列材料而很少價值判斷的刺目“轉變”。上述李氏這兩文,像是重新回到《文學自由談》的明顯標志,卻又給了我一個突出印象:從羅列材料到個人經驗泛濫,表明李美皆起碼的批評理性也失落了。當一個批評者很難平衡感性與理性的時候,不但無法穩定地辨析理性,而且自產自銷的感性也會變得極其不可靠,以至于成為無處不在的道德審判者和無時無刻不在絮叨的戀己狂。這也曲折地反映了中國女權主義盡管左沖右突,似乎處處樹敵、只要是男性都必然要警惕、只要利益分配不以自我為中心,就必然有問題,進而必須給以無情解構的泛批判和反理性傾向。然而,究其實質,當“男權為中心”的社會結構到了“經濟為中心”乃至“消費為中心”時,女權主義如果不能內在于經濟社會乃至消費社會,其實已經不再是這個社會的批判性思想了,而是經濟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寵兒,不大可能是現代社會機制的促進者和建構者。
《文學自由談》中這一類女性文本也著實不少,想來也不會與該刊的趣味沒有關系吧!
愿以此紀念這份我珍愛的刊物,并求教于編輯和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