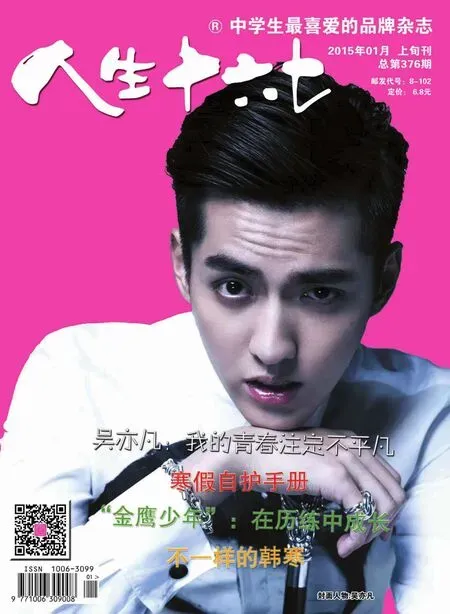遺失的寒冷
張亞凌
遺失的寒冷
張亞凌

搜索
張亞凌
作家名片:張亞凌,陜西省作協會員,所寫散文被《讀者》《青年文摘》《意林》等轉載,出版散文集《心似花開》《回眸?凝望》等。
三十年前,站在宿舍門口,看著萌發(fā)出新芽的柳枝映在斑駁的土墻上的影子,我一邊感慨著“春天來了”,一邊告訴自己,在以后所有的冬天,你再也不會有寒冷的感覺了。
也正是那年,十三歲的我,遺失了寒冷。一晃,三十年過去了,今天的我才嘗試著觸摸那段遺失寒冷的過程。
那年,我升入初中,必須在學校住宿。褥子被子一捆,和一大布袋子紅薯、糜面饃饃、玉米糕綁在一起,母親幫我拎起來搭在肩上。背上是褥子被子,胸前是一個大布袋子,后面重前面輕,我都有些把持不住自己的身子了。母親只是交代了句“不要貪吃好的,一頓蒸上兩個紅薯一個糜面饃或玉米糕就行了”,都不曾將我送到門口,就轉身忙活兒了。
走一走歇一歇,到了學校,喘了半天氣才緩過神來。宿舍是一面窄窄的空蕩蕩的窯洞,我們直接在地上鋪鋪蓋。
別人都是先在地上鋪一個厚厚的草墊子,上面再鋪個氈子毯子什么的,接下來才鋪上褥子,褥子上面還有個布單子,叫“護單”,怕將褥子弄臟了。我呢,只帶了褥子和被子,壓根就沒有其它東西鋪在地上。褥子顯然是不能直接鋪在地上的,我就找來了一些廢紙片鋪在地上,才開始鋪褥子。結果,我的床鋪比兩邊的同學低下來一截兒,她們都覺得我不應該夾在中間。于是,我就自覺地挪到了最邊上,門口的墻下。
我的褥子幾乎是直接挨著地面,很潮濕,挨地的那面經常濕漉漉的。只要有一丁點太陽的影子,我都會迫不及待地將褥子抱出去曬。我現在特別喜歡冬天的太陽,甚至會深情地看上半天,恐怕就源于那個寒冷的冬天我對太陽的感激吧。那時在別人眼里,我或許是個很可笑的女孩,跑到學校似乎就是為了等太陽出來曬褥子。
冬天天冷,夜又長,起夜的學生就多。門一拉一合,冷風就直吹過來。抗擊了半天寒冷好不容易才入睡的我,常常又被寒風刺醒。為了應對寒冷跟風的襲擊,我睡覺不再脫衣服且蒙住了頭。
我從來沒有給母親提及此事,母親看到我在家里睡覺的樣子便有些想不通,曾給父親說:“這娃書念的,成呆子了,炕中間燒得熱乎乎的,她咋老蒙著頭靠墻根睡?”
現在想來,那種奇怪的反應不會是寒冷留下的恐懼癥吧?是那夜夜寒風吹走了我的寒冷?
那年的冬天,下雪的日子經常有。我也清楚地記得當語文老師看著窗外紛飛的大雪吟誦“今冬麥蓋三層被,來年枕著饅頭睡”時,我的淚水悄然滑落。
對于我來說,下雪天是最難熬的日子,包括雪后的一段時間。不僅僅是褥子只能無奈地潮濕下去,更重要的是,我只有腳上一雙布鞋,不像別的孩子,還有一雙可以換著穿的鞋子或是能踩雨雪的黃膠鞋。教室、飯?zhí)谩苌蠋滋耍夹男拙蜐窳耍胩煜聛恚蜐裢噶恕N揖蜐M教室找別人扔的紙片,厚厚地鋪在鞋里。一兩節(jié)課下來,又濕透了,取出來扔掉,再找紙片再鋪進去,再應付一陣,如此反復。紙片也不是那么好找的,一個本子一毛錢,都是很節(jié)省用的。

雪后若有太陽,在別人吃飯的時候,我就留在教室里。餓是可以忍受的,入骨的冰涼卻難以抵御。等到教室里沒人了,我就將凳子搬到外面,將鞋子脫下來,底朝上曬曬。我則盤腿坐在凳子上,搓著冰涼如石塊的腳,讓它暖和些。再后來,我有些開竅了,找到塑料袋,撕開,鋪在鞋底,再鋪上紙,就好多了,也不用不停地換紙。有一句話我信,那就是“許多智慧來自于人們對貧窮的應對”。
更多的時候,是等著鞋子自己慢慢變干。我一度固執(zhí)地認為,是身體暖和了腳,腳再暖和著鞋子,直至吸干鞋里里外外所有的“水分”,鞋底才會變干。
每個周三下午有一個半鐘頭的活動時間,我常常趁機跑回八里外的家里取下半周吃的東西。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天下著大雪。
雪大風猛,我是抄小路往家里趕。有的地方雪沒過了我的膝蓋,很熟悉的小路也因大雪的覆蓋變得陌生,以致于我一腳踏下去摔進雪里。我把溝邊當成了小路,從雪里爬出來,繼續(xù)往回趕。我一推開房門,母親愣住了,一個勁地說:“照一下鏡子,看你成了啥樣了……”父親倒了一碗熱水讓我暖和。我伸手去接,明明接住了,碗卻掉在了地上。那一刻,我的手指凍僵了!我走到鏡子跟前,眼淚刷地流下來。被雪弄濕了的頭發(fā),在風的猛刮下,直直地向上豎著!
母親拿著梳子趕過來給我收拾頭發(fā),才驚叫道“你的頭發(fā)都結了冰”。我只說,趕緊給我裝吃的,我不想遲到。背起裝滿干糧的布袋子,我又趕往學校。風還是那么猛,雪更大了。
我也說不清為什么,至今想起那個下午,都會淚流不止,包括此刻。是那場大雪不客氣地凍掉我那脆弱的寒冷?我只知道:在三十年前,我,遺失了我的寒冷。
編輯/黃書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