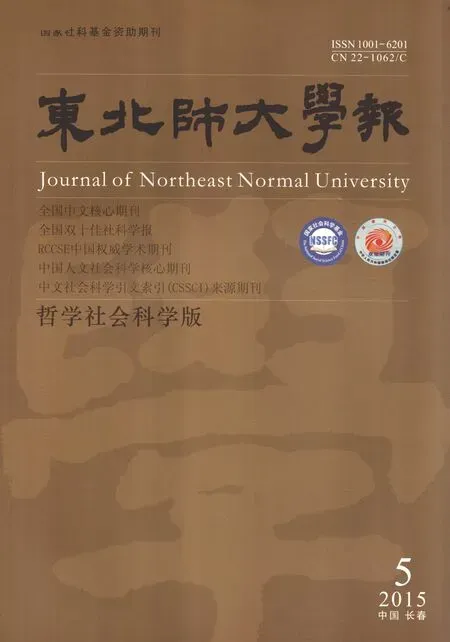孔子原創性美育觀理析
姜殿坤,王凌皓
(東北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吉林 長春130024)
美育起源于人類勞動創造美及其經驗的物化傳承。美育概念出現較晚,但其實踐已歷經數千年。美育概念古今不一,但其表現形態(自然美育、社會美育、藝術美育)同一,方式和內容有別。中國近代首倡美育的蔡元培先生把美育定義為“美育者,應用美學之理論于教育,以陶冶感情為目的者也”[1]。現當代,如有學者指出“美育,又稱審美教育或美感教育,是培養學生正確的審美觀點以及感受美、鑒賞美和創造美能力的教育”[2]。春秋戰國之際的美育是廣義的美育,也可以稱之為大美育,“廣義美育是指把美學原則滲透于對人的影響,從而形成人們高尚審美素養的影響活動,包括高尚思想道德教養、政治藝術美學以及陶冶人們美好心靈的文學藝術教育。”[3]它包含今日的德、智、體、美四育,其以人為本,期求人格素養的盡美盡善,即追求心靈美,在道德文化上期望與人為善。以孔子為代表的創始儒家所建構的美育學說的原創性及其在中華文明史上傳承至今,在春秋戰國的主要美育學說中,特立獨行、卓爾不群。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創始儒家“積極地探求和深化美育的方法、內容、規律的認識,建樹最大。”[4]其美育觀的主要內容包括:道、德、仁、藝全面發展的美好人格期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君子成人之美育人過程及基本路徑;興、觀、群、怨的詩教藝術美育社會功能。
一、道、德、仁、藝全面發展的美好人格期求
孔子從春秋末期賢人政治要求出發,將美育置于社會倫理架構上考量,提出了培養志士仁人、君子“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全面發展的美好人格期求。按照道、德、仁、藝四種素質,創新美育,改造、創新人性。
孔子所說的“志于道”,是指志士、君子、仁人以實行“道”為根本宗旨、人生志向和理想追求。孔子自稱“學而不厭”(《論語·述而》),他在編著《易傳·系辭下》中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講為人之道在三才之道,遵行天道陰陽、地道柔剛、人道仁義的對立統一規律,乃孔子宇宙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根本性、原創性。這種原創性認知指向,雖然未必揭示出天地人發展的客觀規律性,但他所強調者在于天地人三才之道“不可違”,尤其強調為政者必須實行“有道”之治,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榜樣。孔子以“里仁為美”(《論語·里仁》),他所重視首先在人道之崇仁貴義,而“孔子之學以仁為核心,孔子平生言論,一切都是為了人,但也應知道,孔子言人道的同時,也言及天道和地道。這是由于人和天地有密切關系,人生在天地間,一刻也離不開天地。”[5]當今世界與孔子之時變化之巨不僅古人難以想象,當下人們也未曾意料,但孔子有關以人道為主線,追求“成人之美”,兼行天道、地道、人道這個三才之道的原創性美育思維,卻歷久彌新,啟發人們深思。
“據于德”是指人們,尤其是執政者的言行舉止在任何場合都應以高尚的社會倫理道德準則為依據,時時自檢自律,自省自克。孔子所強調的“據于德”既包括外在禮制的道德約束,更主要的是自我意識的道德文化自覺、自我內在心理的自重自勵自警自律。孔子承認禮制的歷史變革和歷史借鑒,所以他認為“周鑒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在個體的美言美行上,要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雖然社會倫理道德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制度下有其特定的內容和要求,但“據于德”做人的人道基本要求卻是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制度下人們必須普遍遵守的。當今世界,價值多元,時尚多向,雖然見義勇為者多見,但物欲橫流,功利主義盛行。孔子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倡導的“據于德”、堅守道德精神家園的育人德行之論,在如今建構“把權力關在籠子里”的時代仍有其重要的行為導向的現實意義,因為無道德根基的種種制度之建制,難以進行法治國家建設,難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
“依于仁”是對“據于德”的德性本質的強調。二者具有同一性,但不具等同性。《論語》中記載孔子與其弟子和各諸侯國政要就“仁”進行對話有30余處。每次論“仁”都有特定的針對性。孔子與弟子的對話體現了他依據學生的個性特長所進行的因材施教,但其最基本的、最高的道德標準和信條主要有如下幾項:“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論語·雍也》);孔子將仁與智、勇并稱為君子的三大德性,指出:“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孔子強調克制自己,約束言行符合禮制就是仁了,“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樊遲向孔子請教“仁”的意旨,孔子答以仁者“愛人”(《論語·顏淵》)。孔子認為,仁在政治上應表現為仁政,仁政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惠民。他評價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論語·憲問》)。對于君子行仁政,孔子強調“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孔子期望成仁的最高境界是“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而終身奉行的行為底線,則須為仁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他又告誡弟子:作為仁者“君子矜而不爭”,但“當仁,不讓于師”……(《論語·衛靈公》)。“仁”既是孔子衡量人們行為正當性的基本尺度,又是孔子廣義美育觀的最高標準,也是孔子廣義美育觀的最終歸宿,是美與善的完美統一。
“游于藝”的“藝”在古代指農業技藝、田獵技藝、射御技藝、領導藝術、音樂舞蹈藝術等。孔子總結夏、商、西周三代技藝才藝的發展,在德才兼備、德藝雙馨原則導引下,概括為“六藝”、“四教”的廣義美育具體內容。“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四教”即文、行、忠、信。“六藝”、“四教”體現禮制、樂制的文化,如“八佾”歌詩、舞蹈于宮廷,是天子獨享的禮樂之制。諸侯國國君八佾舞于庭,是違反等級禮樂制度規定的,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因此,“游于藝”的藝也包括各種藝術表現形式的載歌載舞以及繪畫、雕塑、建筑工藝美術,但它作為廣義美育的一個器用內容,其范圍很廣,既有政治文化、道德精神方面的,也有軍事體能才藝以及自然科學知識和單純鑒賞性音樂、舞蹈美藝方面的。其范圍雖廣,但都圍繞一個中心——內心和人格氣質的完美,與道、德緊密相連,多元寓于一體。從審美情趣上分有雅俗之別,但雅俗都要符合政治、法律、倫理道德的禮數要求。這是如今狹義美育所缺失的,也是今天我們在如何發揮美育育人功能中需要深入思考的,美育在弘揚真善美的過程中應該起到正人心,揚正氣,美風俗的作用。
孔子總結自己和歷史上三代的育人經驗,原創性地提出了道、德、仁、藝全面發展美好人格的廣義美育思想理論,其本土民族性和在世界教育史上的開創性貢獻無與倫比,孔子構建了君子人格美修養的基本體系,有利于在更高視點上弘揚君子之德風,將美、文、藝的意蘊與天地人三才之道相呼應,啟迪人類智慧,創新發展政治美學、倫理美學、生態美學,將美育貫穿于德育、智育、體育之中,盡美又盡善,從而豐富美育內容,拓寬美育途徑,擴展美育功能,從總體上提升人們的文明道德水平[6]。
二、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成人之美的育人過程
孔子相信人在本性上向善,但也有可能在不良環境下失去善性而作惡,包括執政者對民眾有善舉,但也可能行殘民的惡政、苛政。基于人性兩個向度的可能,他不絕對地囿于性善論或性惡論,而是原創性地指出了“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的人性界定和后天揚善抑惡、改惡從善的施教定位,基于人類分具智商、情商,明確了人的知、情、意基本心理結構,系統地構造了他的“學而時習之”(《論語·學而》)、“溫故而知新”的治學方法論,提出了“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的育人過程主張。孔子“成人之美”的教育重點在君子,同時也希望對民眾“富而后教”,使人們具備各種美德美行,成為人格完美的高尚的人。
孔子何以將“興于詩”的詩教作為成人之美的首端?一因其知識性:《詩經》三百篇,既有鳥獸蟲魚、花鳥樹木等自然知識,又有社會習尚、風土人情之敘;更有政治倫理準則的故事典例,可以用于事君事父,甚至應對對外事務。二因其高雅性:風、雅、頌諸篇中,結集了盛行當時的“雅言”,學習“雅言”,有利于按禮制立德、立功、立言,形成寬廣的心胸和高雅的氣度,有利于在官場和社會上與人交往和情感交流,做一個合格君子。三因其趣味性:詩多口語式表達志趣情懷,其抒情表意內容易于了解,引人美感、動情、愉悅,吟詠配以手舞足蹈,宣示志意。學詩、吟詩、作詩,增強政治情懷,陶冶道德情操,加強學識才干。在詩的情理意境中,增益人格完美氣質、寬厚仁愛之心和各種美德。
孔子的美育觀以人為本,以立人為基礎,以立國為宗旨,以禮教為中心環節,將自立與外在制度化引領約束統一結合,培育理想的圣人君子。他要求弟子“立于禮”。禮源于祭祀,在現實上則有利于社會倫理關系制度化、規范化。禮的主要職責在于規定社會等級秩序,旨在建設等差有序的社會。禮中貫徹天地人三才之道和各種道德文化精神。因此,《樂記》也稱“禮者,理也。”禮之理是通過制度化、程序化和規范化形式表現表達。孔子說:“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君子尊禮、維禮、施禮,可為民眾表率,“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論語·子路》)。作為君子的成人之美,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對人們的“無禮”舉動疾惡如仇,他指出:“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論語·泰伯》)。為消除種種無禮、違禮的壞習氣,“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
在孔子期許的廣義美育中,禮具有什么樣的作用呢?禮是治國之大經,具有約束民眾的思想行為,規范社會秩序的功能。這種功能由外而內,由不自覺到自覺。一般而言,人們的情與禮是統一結合的,當然有時也有矛盾,循理有時不一定盡情,盡情有時可能悖理。禮教是調節、解決這種矛盾的功能機制。通過禮制的教化,孔子相信將禮內含的文理,對情感引領、約束、凈化、充盈、提高,將人的情感發而中節,達到致中和的境界。
孔子強調成人之美要立于禮,這不僅僅就育人過程將其置于中間、連上貫下的環節,而且從功能機制上說,起自詩之興,又有禮的外在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制約,可以使人們有禮有理地興、觀、群、怨。從孔子及其弟子相互對話乃至爭辯來看,離開了禮教,詩教就起不到它應有的作用。下面將要談的“成于樂”,與興于詩、立于禮統一結合,在體現情與理、個體與社會的統一結合,在成熟的人的美育中,同一與差異、強制與自覺、外在制約與內在自律的統一結合,人格美才顯示其光輝。因此,立于禮不能與興于詩、成于樂割裂開來,而是應該將三者一體化于立人——獨立完美人格的確立的整個過程之中。
“成于樂”表示孔子特別重視音樂在立人之美中的獨特作用,可以說無論是個人的政治、倫理道德情操修養,還是治國理政致力于達到“天下歸仁”理想境界的實現,都不能沒有樂教的參與。孔子成人之美于樂教的觀點和實踐開我國音樂教育的先河,其成人之美與樂教的原創觀點在世界教育史上顯示其卓爾不群的特征,表現對人的全面發展的深切關懷。
孔子有關樂教成人之美的思想觀點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而是繼承、發展了周初以來的傳統觀念和他自己因熟悉音樂而對音樂美育作用的深刻體悟。孔子對傳承于夏商兩代的西周禮制文化十分贊賞,對宮廷樂舞體制的堅守和贊賞無以復加,他據此以為,對于邦國治理來說,“行夏之時,承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與此同時,“放鄭聲,遠佞人”。因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公》)。孔子認為,君子修身,追求君子人格高尚、完美,絮絮叨叨的說教比不上扣人心弦的樂教,僅就各種藝術的美感教育作用而言,也比不上樂教的美感熏染撥動心弦的作用。孔子之意如今仍應引為深省,就教育對象的主體感受來說,知性的理性了解遠不如情性的不假思索的欲求;情感的欲求,遠不如情動于心、發自內心深處那樣由衷的喜悅。樂有聲樂、器樂并作,也常伴有歡舞,它易使人動情的特殊表達形式使人樂意自動領受。此外,還在于它的內容高于詩、勝于禮,追求著最崇高的、朝聞可以夕死的終極理想——天下歸仁、萬眾萬物和合的大道之行。顯然,孔子心目中的樂,非一般的樂,亦非俗樂,而是聽之令人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一類的雅樂。史載:“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論語·陽貨》)。孔子在等級禮制下指明君子和小人都可以因聞樂生美感而體悟道,共同取得對等級禮教的信仰,但因為所處地位尊卑有別:君子學道可以仁愛萬民,小人從道中可以認清自己應服從現有社會秩序約束,甘愿為統治者驅使,為社會、為國家效力。
可以這樣認為,孔子之所以特別重視樂教,在于他從君子人格修煉塑造出發,寓道與仁義于樂舞給人帶來的美感之中,從而形成了君子的成人之美。可以想象,人從樂舞所受美感帶來的愉悅之中,潛移默化,由情入理,不知不覺地達到最高的道德精神境界,胸懷仁愛之心,崇尚道——天地之道之意,使整個社會和諧有序。《論語》多處載記。孔子立人之期求在于“成于樂”,它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以人為本,追求民族、國家一體和諧、自強不息且有創新的思維方式使然,它是致遠的、也是現實的;是高度抽象的,也是有道之世期望般具體的,喜聞道而懷崇仁貴義之心,孔子之后兩千五百多年,代代傳承至今,雖經千回百轉、坎坷前進,終究不可中斷。向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那樣的治世,傳遞孔子先師之意而為后代百姓共同心聲。
三、興、觀、群、怨的詩教美育社會功能
孔子原創性美育觀沒有單純地囿于藝術領域的功能,而是著眼于育人,強調其興、觀、群、怨的詩教美育社會功能,包括其政治、倫理功能。
孔子的重要教育教學原則是學以致用,對詩教亦然。他對弟子們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可見,他注重詩之意境內涵,更強調詩之用,特別是詩教美育社會功能的發揮。他在同其弟子對話時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興(振奮精神)、觀(提高對事物觀察能力)、群(增強團結合作精神)、怨(學會諷刺批判方法),即使置于當下,也是具有現代社會思考、政治思維意蘊的。以孔子其時而言,他可謂中國古代提出如此創新意涵的美育育人社會功能基本向度的第一人。
“興”在甲骨文中作二人合力舉起重物之狀,其象形表意為古代鼓動合力協作舉起重物,常伴有歌唱、奏樂,激發情志,運用于詩歌創作和表現叫起興。詩之興以詩詠或奏樂激發情志、振奮精神,合力協作完成重大任務。孔子持此含義論詩的一種社會性功能,做出創新發揮,使“可以興”成為興發情意之意,引申為振奮精神。朱熹注解“可以興”為“感發志意”[7],大體符合孔子的本義,即吟詩、唱和詩,可以引發吟唱者的感情激動,從而進一步抒發情志情趣。從發生學上說,詩之“可以興”有助于形象思維的養成和發展,有助于振奮精神,推進發力,協同努力完成重任。
“可以觀”的“觀”意為人們通過詩歌表現的藝術形象可見其反映的思想內容、情趣情操、意境意向。觀作為觀察、思考活動,促發讀詩、誦詩、歌詩產生某種觀感,既有善惡得失之評價性觀感,更有美丑辨析性觀感。“可以觀”是孔子對西周初“陳詩以觀民風”之“觀”的政治肯定和贊許,更表達了孔子對“可以觀”的審美愛美的美感增加了豐富生動的內容和深入的認識。詩之可以觀的政治功能——從詩“以觀民風”,當代仍應繼承發揚,在育人美育上,運用古今詩歌“可以觀”的社會功能,應該是當代美育的應行可行之策。
“可以群”的“群”意指增強團體精神,在群策群力的意義上,古今見解沒有異議。孔子所言詩可以群,是說士君子們在交往集議中,以詩的語言為媒介,發表意見,交流情感,以促進彼此關系協調共進。對于用詩對話者來說,不論何種體式、何種含義的詩,只要賦詩以交流思想感情,密切關系,增進團結,就達到了“可以群”的目的。在孔子看來,從立言、可言個體主體性到吟詠詩歌“可以群”的群體性情感的外放并凝聚,是學詩的第一步,其深層含義則是通過學詩用詩,提高自己的道德素養、政治水平,以密切群體關系,團結積聚力量,從而己立而立人,己達而達人,去成就大事大業,實行“有道之世”的大道,這是“群”的崇高目的。可以說,群是通過詩歌之教達到君子完美人格塑造的總體要求、根本目的。孔子尊重當時不平等的等級地位的群體關系,但他更主張“君子尊賢而容眾”(《論語·子路》)。他追求師生之間如朋友一樣平等相處,表明他的學詩“可以群”有超越現實的更高追求。
“可以怨”的“怨”是為達到“群”的目的,在群體關系,主要是政治統治系統的群體關系中人的言行有所不滿,力求糾正其失誤、歪風而進行善意的諷刺和批評,不只是怨氣的宣泄。孔子的“可以怨”以執中持正、和合為原則,用詩以怨,旨在調和矛盾,不激化矛盾,它是對殷商以來樂、歌只表現快樂情感的傳統美學觀念的修正,也是對春秋之際出現的音樂詩歌表現哀而不爭、怨而不怒情感的美感范疇的肯定,形成了孔子原創、范仲淹表達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民族美學傳統。它以民族命運為重,民族大意為旗幟,指明了歷代仁人志士應有的寬廣胸襟和重義情懷。這都是對當時、當代和未來的以育人為本的美育具有重大借鑒價值的。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學詩以興、觀、群、怨的觀點的四個向度都突出指向詩之用上,這是同春秋社會大變動的歷史條件,禮崩樂壞的制度衰微,以及春秋之際詩歌創作思想還未發展的情況分不開的。孔子以“述而不作”自詡,十分精通樂,但不作樂;他十分熟悉詩,但也不作詩。不僅他自己不作樂不作詩,也不贊成那時有閑人士作樂作詩。基于詩之用,孔子形成了獨一無二的詩論與詩教論,從而將當時分散的、簡單的、初步的有關詩、詩教的美育社會功能加以提高并系統化,創造性地提出了學詩用詩的四大社會功能。尤其其中的“群”、“怨”兩大社會功能,也應是當下詩歌創作和學詩用詩應加以借鑒的。
對孔子原創性美育觀的研究經歷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由淺入深的逐步發展,至今仍有待繼續發掘、繼承、發展這份珍貴的中國教育歷史遺產。本文只是作一粗淺簡約的嘗試,期望有關先秦史、中國教育史和教育學原理專家參與討論,以利以孔子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的文化建設中的“返本開新”。
[1] 金雅.蔡元培美學文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174.
[2] 楊兆山,姚俊.教育學原理[M].大連:遼寧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295.
[3] 王凌皓,高英彤.孔子廣義美育思想理論研究[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3):51.
[4] 于民.氣化諧和——中國古典審美意識的獨特發展[M].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106.
[5] 全景芳.知止老人論學[M].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160.
[6] 王凌皓,姜殿坤.論莊子原創美學及其美育期待[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5):210-214.
[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長沙:岳麓書院出版社,2008: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