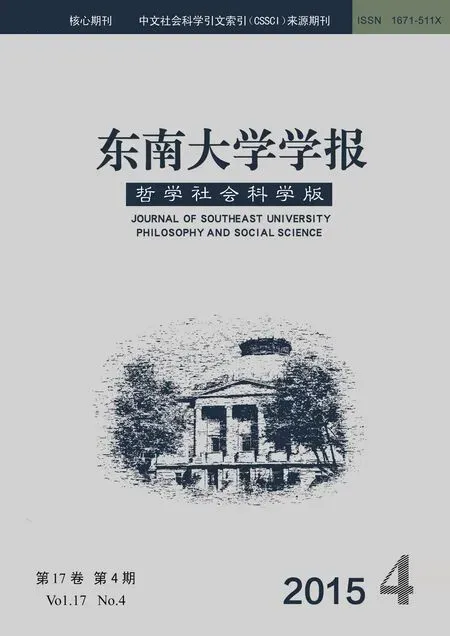政府、資本、社會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四個階段
呂乃基
(東南大學 人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6)
通常從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子系統及其關系來理解一個社會,經濟提供社會運行的物質基礎,如衣食住行,進而彼此交往和文化娛樂的設施等;政治規定社會運行的法律制度,經濟運行方式,如市場經濟及其范圍和比重,實施稅收、福利、選舉等制度,以及關于權力分配與制約的制度;文化倡導社會基本的價值取向,論證現行社會的合理與合法性等。在一個穩定完善的社會中,三大子系統處于相互耦合之中。計劃經濟年代以階級斗爭為綱,經濟停滯,社會陷入爭斗,三大子系統處于混亂之中。改革開放的一個口號就是,社會主義不是貧窮,此后GDP一路趕超到世界第二。然而社會主義也不只是富裕,生態危機,貧富懸殊,誠信缺失,表明政治與文化子系統及其與經濟耦合存在問題。這三大子系統如果都是在同一國家主體的掌控之下,何以往往發生偏差而失衡;抑或,如果它們不是由同一主體掌控,又分別歸屬于何種特定的主體?
近來多次看到另一個視角[1-2]:政府的權力、市場與資本,以及社會和個人①類似地,袁緒程認為,中國改革主要是改變國家和社會合一、“黨政經”合一的組織形態及其相應的制度規則,按照不同的功能定位,重建現代的政府組織,企業組織,NGO組織及其相應的規則和制度。政府組織逐漸退出一些公域和本屬私域的領域,擴大私權和私域,以利于市場組織和NGO組織的生長。但作者沒有進一步分析,這三種組織之間的關系與改革開放分期的相關性。[3];不僅在一個方面回答這一問題,而且有助于厘清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野等事例,以及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
一、資本、社會與政府
政府、資本以及社會②此處的“社會”為狹義,在理論上排除政府的權力和市場的資本。為論述方便,以下以“國家”指稱本來意義也就是廣義的社會,因而本文中,在不注明的情況下,“國家”一詞不含權力的意味。,三足鼎立,彼此支撐而又相互制約。
政府擁有權力,而且與權力高度合一。權力指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支配權,大致包括權力的作用者和承受者、權力的范圍和條件、權力本身受到的制約,以及權力的合法性等。雖然有的國家三權分立,有的大權獨攬,不過在一般情況下,政府擁有并實施權力,權力的承受者是全體國民。政府擁有全局時空上的信息優勢,高度組織化和迅速反應能力,通常越是集權,這種能力越強,不過這并不意味對于國家整體發展的效果也一定最優。政府通過法律和各種行政手段制定市場規則,調節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規范資本的行為,應對種種突發事件,維系政府的日常運行。政府通過法規和輿論調控社會和個人的行為,使之以適當的方式參與國家事務。政府按其執政理念審時度勢,通過制定法規等協調處理其與資本和個人的關系(如成品油降價和同時提高稅率),以維持其心目中的國家穩定和發展。
資本與市場息息相關,一方面資本受制于市場,只有在市場中才能發揮作用。資本必須在市場中選擇需投入的要素并組織生產,并使生產出來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轉化為商品進入市場,在商品交換中獲得資本的增殖,并以此維持或擴大再生產。另一方面,市場若沒有資本的運行,如同沒有演員的舞臺,也就沒有了生機。市場與資本,前者居于主導地位。在完善的市場中,資本主要扮演正面角色;而在扭曲、混亂的市場中,資本往往顯示惡的一面。當然,資本也會反作用于市場。
資本雖不具備關于全局的信息,但在供給與需求方面擁有更為精確細致的信息優勢,而且具有高度的流動性和杠桿效應,以及在各類商品之間充任交換的能力。人對各種商品,對自然、生態和環境的感受和喜怒哀樂等千差萬別,且因語境而異,甚至見異思遷,因而很難在彼此間加以比較和交換;在“價值通約主義”[1]的旗幟下,市場與資本將這些嵌入于特殊語境中豐富和個性化的感受,轉化為與語境無關而通兌一切非嵌入的單一的貨幣,于是交換發生,國家得以運行。資本以其擴張、增值和擺脫監管的欲望,由創新和擴展(全球化)驅動和改變現狀。資本無疑具有權力,但資本之權力的主體多元,外資、國資、民資,權力不一;同一種“資”也處于彼此競爭之中。資本權力的作用者更是多樣細碎。資本受到需求的制約與引導,彼此間還面臨競爭,消費者用腳和稀缺的“眼球”投票,促使資本不斷改進組織制度與功能,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務,并因此促進國家的發展。資本還以其市場意識制約政府及其權力,使政府(執政黨)的產生與更迭可以不再依靠暴力,而是經由民主(市場的)方式。資本通過市場將個人從以往單一的暴力權威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獲得勞動自由,并獲得影響社會的能力[1]。在人類歷史上,亞當·斯密所定義的市場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這之前是以血緣與宗法為基礎的傳統社會,而之后則是以擁有天賦人權和彼此間契約關系的個人為基礎的現代社會,政府的權力同樣在市場的基礎上建構起來。不過,由于各類資本主體之間經由漲落、競爭與合作等自組織過程尋求各自的生態位,視野較小,較關注眼前利益,因而在整體上的效率不如政府。然而從另一角度看,正是在市場自組織的過程中,各種生產力要素被整合進來,各方的訴求得到最大程度的磨合與耦合。
個人的集合組成了社會。個體占有信息少,三教九流背景各異,個人的訴求混雜松散甚至彼此相左,缺乏穩定有效的組織,因而在三足鼎立中,如果沒有工會等非政府組織的介入,社會通常處于弱勢,易于受到權力和資本的擠壓和分化。然而,社會中的個人既是政府權力的作用對象,也是政府權力的最終授予者;個人通過創新、就業和消費(政府當然也消費,不過說到底,消費的主體依然是個人)活動提升其需求層次,使資本的運行、循環和增值成為可能。社會以正義觀念抵御資本拓展經濟合理化的企圖,以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和新的知識提升資本和社會的運行水平,以新的需求引領資本,完善社會和國家。個人雖因其分散而弱勢,然而也因此不會形成相對一致的利益集團,從而可能以其對自由和更高境界的追求,經由自組織的途徑均衡政府權力和資本與市場。個人是一切發展的動力和出發點,也是一切發展的目的和歸宿。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創造和承載知識的人成為一切發展最重要和最強大的源泉,在三足鼎立中,社會的地位也就越發重要。
經濟、政治、文化主要是從功能的視角著眼,考察在一個作為整體的國家內三個功能子系統之間的耦合;而政府、資本、社會三者皆為實體,每一方都會站在自身的角度,同時關注政治、經濟和文化。相對而言,政府雖然關注GDP,乃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關注國民的價值體系,但重中之重無疑是政治,是執政的地位和權力分配。資本對政治環境極其敏感,也關注消費者的消費欲望,最終是落腳到收益和利潤。個人關注收入和物價,關注社會的公平與公正,希望實現理想,感受幸福。政府、資本和個人雖處于同一國家之內,卻都有自身的利益擔當和訴求,都自覺不自覺遵循經濟人假設,力圖以最小投入獲得最大效益,并且傾向于自我擴張。制定美國1787年憲法的核心人物麥迪遜說:“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政府、資本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合作與博弈,匯成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個功能子系統。這正是一個國家自身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是否耦合的根本原因。
政府權力過大,越俎代庖,干預、替代市場和資本,壟斷資源如土地和能源,市場被扭曲,失去配置資源的功能,資本或者失去生產力要素的選擇權,或者投靠權力,權錢合一,共同盤剝社會與個人。政府的公權力全面侵犯個人的私權,也就剝奪個人的選擇權,導致專制型與盲從型人格,表現為官本位和公務員熱,或者蝸居于“小時代”,社會失去活力而停滯。反過來,若是政府權力太小,也無力處置市場和資本與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系。福山曾經在他的著名的《歷史的終結》中認為,西方民主會取代和終結所有其他的“專制”政體,成為統治世界的唯一政體,歷史終結于西方民主。然而通過近年來對中國崛起等事例的思考和對西方民主的深入反思,福山意識到一個強大政府對于三足鼎立必不可少。美國的“制衡效率太高”,導致聯邦政府的施政能力低下。它在某種程度上能防止“壞皇帝”,也可能會束縛“好皇帝”,使他做不成好事[4],已經從原先的精英民主走向庸俗民主。在野黨為了能上臺執政,攻擊政府的每一項政策,讓國事停擺、經濟空轉;甚至造成社會分裂與人民對立[5]。
市場和資本的勢力過大,會排斥、逃避政府和社會的監管,唯利是圖,不擇手段,破壞生態,盤剝民眾,走向壟斷,泯滅向上的動力,推高基尼系數,造成兩極分化,以及腐蝕政府和社會,把權力和人間一切或美好或丑陋之事物折合成貨幣,標價出售。資本的每一個毛孔都滴著鮮血,唯獨不是“道德的血液”。“任何能夠想象出來的人類行為方式,只要在經濟上成為可能,就成為道德上可允許的,成為‘有價值的’,只要付錢,任何事情都行得通”[6],甚至包括在價值判斷上互相對立的事物,造成價值觀的模糊與混亂。資本的所作所為不僅在道德層面,而且會訴諸暴力(如中國眼下的拆遷,乃至艾滋病拆遷)。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揭示,資本收入增長總體上高于經濟增長,金融危機更是凸現了資本大到不能死的事實。此外,任由“看不見的手”一意孤行還會一再墮入危機之中。反過來,原社會主義陣營已經見證了摒棄資本與市場的后果。
社會過強,社會運動頻發,并且往往以道德自居,以民主名義走向政治激進化,非要自己贏了才算數,任意破壞法律,實際上是反民主。或者陷入彼此間的紛爭之中,難以凝聚到一個方向,致使政府和資本難有作為(如南美、泰國);或者爭自己的權利而無視自己的責任,加大企業成本,增加公共財政的負擔和政府債務(如歐豬四國)。反之,社會與個人的羸弱會扭曲政府的運行(例如,中國的老百姓“太好了”云云,于是政府和資本得以過度膨脹),以及讓資本的增值最終成為泡影;由此可見,正因為社會的弱勢,需要政府和資本時時記在心間,予以精心呵護和培育,尤其是培育NGO和作為社會之中堅的中產階層。
資本具有無限增值和擴張的欲望,組成社會的個人力圖沿需求層次提升;相對而言,政府較為保守。如果不是為了更好地管理和控制,如果沒有來自內部資本和社會的壓力,沒有來自國際競爭的壓力,政府往往會選擇維持現狀。
政府、資本與社會,各自作為實體發揮其功能,由合作與博弈匯集起來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在功能上的耦合與否,又反過來規范和改變政府、資本與社會各方的權重及其行為,三方之間處于長期的磨合之中。在政府調控下,社會和諧向上與經濟穩定發展,二者之間的長期和解,在大部分情況下并不是現實,而是作為一種理想來衡量和引導現實。
二、案例分析
1.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站在這一視角看,在亞當·斯密時代,政府和社會尚未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生成,資本基本上沒有受到來自政府和社會的制約,處于完全“自由”的狀態,加之資本稀缺和勞動力過剩,物以稀為貴,致使資本的力量過強,以至“每一個毛孔都滴著鮮血”。這是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是資本的“黃金時期”,資本的天堂也就是社會的“悲慘世界”。
兩次工業革命期間與此后,工人階級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社會抗議運動。人既不是工業革命中的機器,不是《摩登時代》里的卓別林;也不可以折算為或等同于市場中的貨幣,并不只是“經濟人”,工人的自我意識覺醒。在工業化先行一步的英格蘭,個人和團體都參與有組織、有計劃的救助工人、窮人和弱者。在1819年英國槍殺示威工人的“彼得盧”事件后,政府迅速妥協,促進立法,改進刑法,成立社團,教會也參加進來,傳教士則在布道之余從事社會福利工作,從而免于革命。很多作家也有形象的描述和深刻的批判,例如雨果、狄更斯,以筆墨喚起良知。馬克思進而揭示資本的本性和利潤的來源。與此同時,工人的情況也在改變。隨著工業化的深入,培育了具有特殊技能的工人,能獲得較高的工資,逐步進入中產階級,工人代表進入議會,“參政議政”。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逐步提煉出來并成為社會的榜樣。在某種程度上,現代社會的自組織過程也就是中產階級的自我塑造過程。新的社會秩序就是這樣“涌現”出來[7]11,119。巴爾贊認為,就社會觀而言,19世紀堪稱“愛的世紀”[8]479。隨著社會涌現成為相對獨立的力量,資本與政府讓步。此前,政府是資本的代理人(馬克思)。工人階級運動促成了政府和資本的相對分離。政府逐漸看清放縱、投靠資本的危害,制定一系列法規制度,明確對資本的限定,以及政府和資本各自對社會的責任。經過數百年的發展,逐步建立起三方之間的相對均衡,其典型或許是北歐的福利資本主義。這一歷史過程可以歸結為資本主義由初級階段到高級階段。值得注意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自我完善過程與科技的發展同步,前者為科技發展提供通衢,后者促使國家權力不再偏向資本一方。
目睹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罪惡,在不發達國家,無產階級革命造就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模式,走上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道路,也就是消滅資本和市場經濟,試圖通過公有制讓社會控制經濟。這么來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野,就在于在資本和社會二者之間政府的站位。資本主義也就是政府與資本站在同一條戰壕,或者完全仰承資本之鼻息,一起壓榨社會,故稱“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則是政府完全為了社會,政府和社會一起棄絕資本。為了把資本趕盡殺絕,必然要徹底根除哪怕“資本主義的尾巴”,加上“靈魂深處鬧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社會最終也就淹沒于國家的汪洋大海之中。這是人類歷史上一次重大的試驗,在早期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就,成為落后國家趕上發達國家的主要路徑。然而失去資本的擾動和市場的自組織,泯滅社會由下而上的原創和動力,這些國家先后在不同程度上走向“貧窮社會主義”[2],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紛紛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引入資本與市場,走上各具特色的改革之路。
在一國內部也可以做類似的分析,例如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美國的共和、民主兩黨就分別偏向資本與社會,卡梅倫則要求英國人在經濟發展和混亂二者之間,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在資本和社會之間做出選擇。
2.全球化中的資本、社會與政府
二戰之后,西方國家基本上確立了對資本的規制體系。全球化意味著資本沒有了國界,資本掙脫主權國家的規制,跨出國門,在海外,特別是在渴求資本而又缺乏對資本監管的不發達國家,找到了“自由”發展的空間。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不發達國家爭先恐后給予種種優惠來“招商引資”,譬如中國。
“外資”所到之處,便與當時當地的政府相結合,制造一個又一個貌似初級階段的資本主義。不受制約的外資將求“資”若渴的當地政府拖下水,一起對付社會,掠奪當地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以及欺凌民資;如若政府不從,則隨時撤資。一旦當地資本日益充沛,加上社會的訴求日盛,政府便取消優惠,制約和規范外資。
在資本流出的發達國家,資本因此變得稀缺,從而加大在資本、社會和政府三者博弈中的權重,延長工作時間、推遲退休年齡,以及降薪和降低福利待遇,等等,壓榨社會的地盤。發達國家工薪階層上街游行抗議,其緣由正在于全球化改變了資本與社會博弈的格局。資本家說,你罷工我就到東歐去,東歐也罷工我就到中國去……。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類似的意義上,資本只有遍及全世界,才會回過頭來接受監管,才會理解資本真正的自由必須與人的全面發展相一致。政府如過于偏向社會,資本難以為繼,經濟衰退,到頭來難以滿足社會的訴求;政府如倒向資本,便失去來自社會的選票而下臺。希臘左翼反對派在2015年大選中獲勝,隨即發生希臘國內社會與歐元區資本之間的博弈。此處的復雜性還在于,“社會”在希臘,而“資本”在歐盟,二者分屬不同主權的主體。
數月前發生在臺灣的“太陽花運動”,在某種意義上也與資本的特殊流動和運作有關。2010年,兩岸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其濃厚的特色就是大陸讓利,“太陽花運動”的直接誘因《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也是如此。大陸的資本以某種特殊方式流向臺灣,多與企業商賈打交道,也就是在資本上做文章,相對而言較少與社會公眾交往互動,主要獲利的是臺商等擁有資本的階層,進而指望與臺灣本土的資本聯手影響臺灣事務。社會則以“太陽花運動”的反彈,昭示自身的存在,進而在選舉中致使國民黨失利。誠然,臺灣終究還是要發展經濟,社會也繞不過資本,不過,大陸也可以從中汲取經驗教訓,在處理海峽兩岸關系中,資本并非萬能。馬英九的老師熊玠認為[9],大陸需要轉變對臺思路,不能盲目讓利,切不能讓民進黨認為可以通過反大陸得到更多好處。最近“習朱會”的一大變化就是,更重視青年和基層。
香港“占中”的起因與“太陽花運動”及而后的事態有相似之處,香港社會的一部分叫板特區政府。由于大陸對香港的影響遠大于對臺灣的影響,香港社會的力量又遠弱于臺灣社會,因而“占中”的結果在一開始就已經注定。撇開這些特殊影響不論,從資本、社會和政府三方的博弈著眼分析“占中”的前前后后,依然會使人饒有興味。在“占中”過程中,特區政府的主要策略是,以商鋪、出租車司機、旅游業等經濟損失,高級白領上班出行不便,以及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動搖為由,也就是聯絡資本來壓社會;資方在情感上可能同情占中,但在利益上難以割舍,因而會默認或支持特區政府所為。特區政府的另一張牌是以另一部分社會,也就是給市民生活的不便來反制“占中”行動。特區政府依法治港,最終控制了局面。雖然“占中”已然落幕或告一段落,但大陸依然有必要從中汲取與臺灣選情類似的經驗教訓。
隨著“一帶一路”緊鑼密鼓的推行,隨著中國成為資本凈輸出國,上述經驗教訓值得記取。單純的經濟考量,有意無意之間對政府和資本的偏重,往往會疏離個人與社會,一旦有關國家因選情而發生政府更迭,最終事與愿違。無論來到哪個民族什么國家,說到底,個人與社會才是一切發展的源泉,也是一切發展的最終目的。
3.科技創新的影響
科技的發展無疑在總體上提升政府及其權力、市場與資本,以及個人與社會的運行水平,譬如互聯網,譬如高鐵,這一點已有共識,不再贅述。
有必要指出的是,科技對政府及其權力、市場與資本,以及個人與社會的影響并非是“1+1+1”或“三一三十一”。一般而言,科技發展對這三方的影響某種意義上呈“等差”甚至“等比”的關系。政府以其擁有的權力和高度的組織性,往往可以在科技的發展中獲得更大的“收益”,以至眾多西方的研究者把科技劃為政府實行統治的“工具”。例如,在已經或正在到來的大數據時代,由于政府具有信息優勢,可以在更大范圍內而又更為精準及時地監控市場與資本,俯視社會與個人;譬如只有政府看得見而個人不能看的不動產。牧羊人和羊的隱喻被一再提及。資本居其次,也可以在稍小的范圍內監控公司的員工和消費者。在引入ERP(企業資源計劃)之后,楊元慶不無得意地表示,現在聯想集團的運作變得透明,如同看著金魚缸里游動著的金魚,而他本人則在魚缸之外。最后是個人。雖然科技提供個人更多選擇權,個人由此獲得更大自由,可以脫離組織和“單位”自我擴張,但個人畢竟勢單力薄,只能用腳或眼球投票制約政府和資本。
即使這樣的均衡也一再被科技創新所打破。幾乎每一項科技創新,或者將新的要素投入市場,或者重新配置各項資源的關系,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改變原有生產力各項要素在市場中的權重和價格;導致以個人與社會一方,與資本為另一方關系的此消彼長。在科技的發展中,先是體力勞動貶值,隨后是單調重復的勞動貶值,接下來可能會輪到從事簡單邏輯思維的腦力勞動。個人唯有以其有價值的創新和社會的自組織抗衡市場與資本。
科技創新也改變政府權力與市場資本的博弈關系。一旦新的產業產生,政府、資本和個人三方之間的游戲規則有待在博弈中重新商定,政府需要時間審視資本與社會的新的關系,重置自身在資本與社會之間的立場,使資本不至于擺脫監管,社會既得到發展,又不至于無序和弱化。于是,資本便會有一段自由期,在新拓展的疆域獲取超額利潤。當下,互聯網所到之處正是這樣的“空白地帶”。傳統金融不敵互聯網金融,電商位列2014年度中國最吸金行業之首,在相當程度上即因為此。
互聯網也賦予個人以前所未有的話語權,由此所匯成的社會輿情,其漲落的頻率更高,幅度更大,范圍更廣,更易激起蝴蝶效應;然而更難追溯和追責,更難管理。在某種意義上,分散的個人破天荒第一次獲得與政府和資本叫板的地位。不過雖然如此,由于新媒體的破碎和短平快等特點而缺乏理性和必要的深度,充滿情感和非理性色彩,往往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眼下的一個典型就是醫生自拍事件中,從一個極端到了一個極端的輿情。
隨著科技的發展,隨著三方博弈關系的演進,資本由商業和產業資本發展到金融資本,覆蓋的范圍更廣,具有全球影響,跨越的時間更久,含有對未來的預期甚至某種信念,如保險、股票和期貨等,同時流動性更強,杠桿的倍數更大,還有諸如抵押、租賃和借貸等,因而所對應信用等的文化內涵更高更豐富。一端要求法制環境更加公正透明,要求國家乃至世界局勢相對穩定,可以預見;另一端則是不確定性加大,擊鼓傳花,傳遞并放大風險。由此可見,資本升級的同時也要求政府權力和個人與社會的遞進。科技創新大潮所到之處,政府、資本與社會三者關系重構,政治、經濟和文化也就于新的平臺上重新調整彼此間的功能耦合。
在科技創新的推動下,生產力要素中的核心因素或“序參量”由土地、資源、資本一路攀升,知識,特別是創造知識的能力和源泉正在并已經成為核心因素,成為制約或促進資本繼續增值的短板。科技在風投等資本的激勵下,一步步由低向高驅趕作為勞動者的個人,把他們由體力推到精神和知識,由重復勞動推向創新的高度。知識社會中的人力資本,這一特殊的“資本”與其所有者不可須臾分離,卻與傳統意義的資本相分離。在這樣的高度,再加上金融資本本身的要求,歷來處于弱勢的個人和社會獲得了未曾有過的權重。
不過不同于政府的權力,可以由立法、司法和執法行使權力;也不同于資本,可以頤指氣使,有錢能使鬼推磨;甚至也不在于政府和資本三顧茅廬,求賢若渴;創新動機、能力和人才并非如諸葛亮那樣就明“擺”在那里,等政府和資本去“顧”,乃至拔苗助長;個人與社會的權力在于,若是無視個人的合法權益,未能提供自由發展的空間和前景,其結果一方面是創新停滯,一切發展的源泉或者面臨枯竭,或者步入歧途,或者亂象叢生,陷入紛爭與混亂;另一方面是一切發展失去最終的目標,變得空洞、蒼白和虛幻。
三、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
或許更有意義的是,以這一視角來研讀中國改革開放至今的三十余年,回顧由計劃經濟年代一路走來的路徑,展望未來的發展。
1.分期
權威的《中國改革開放史》[10]把1978年至本世紀初的改革開放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8至1982年,歷史轉折、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起步。第二階段從中共十二大到鄧小平南方談話前,改革開放全面展開,同時也遇到波折并加以克服。第三階段是南方談話開始到上世紀末,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加快發展。21世紀開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現代化建設的新發展階段。袁緒程在2008年把改革開放的歷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為第一階段;8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為第二階段;從胡溫新政開始至今為第三階段[3]。這些研究成果在發表之時無疑有其價值。現在距權威著作的出版已有十余年,距袁文也已過去6年,在這些年,特別是2012年來,中國發生了太大太多的變化,沒有理由不把2012年作為改革開放新的里程碑。此外,以1980年代末或南方談話,以及以新世紀或胡溫新政作為劃分各階段的依據,尚有待揭示其背后深刻的內涵。
在某種意義上,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所面臨的正是如何重建在計劃經濟年代被政府權力消弭于無的資本與市場,以及個人與社會,與此同時改造政府權力,構建三足鼎立的均衡局面①類似地,袁緒程[3]認為,中國改革主要是改變國家和社會合一、“黨政經”合一的組織形態及其相應的制度規則,按照不同的功能定位,重建現代的政府組織,企業組織,NGO組織及其相應的規則和制度。政府組織逐漸退出一些公域和本屬私域的領域,擴大私權和私域,以利于市場組織和NGO組織的生長。但作者沒有進一步分析,這三種組織之間的關系與改革開放分期的相關性。。正是三方之間在這一過程中此起彼伏的復雜關系,成為劃分改革開放各個階段的依據。
改革開放之初,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念茲在茲的“球籍”,成為舉國上下,特別是政府工作的中心,落到實處就是GDP,目標宏偉,然而單一;當時的出發點是既無資本與市場,也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個人與社會;一頭是經濟上趕超的狹隘目標,另一頭是有缺陷的出發點,二者之間存在巨大落差和扭曲,這就注定改革開放必然會經歷曲折的路徑。之后,一方面中國的GDP高歌猛進;另一方面,在1992年資本與市場浮現后發生權與錢的種種不正當關系,并且引發嚴重后果,本世紀來一再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和維穩難以奏效,則意味著繼資本和市場之后,個人和社會在新形勢下再次登場。在種種曲折和復雜狀態的背后,正是權力、資本和社會三者關系的跛足、扭曲和傾斜。在此意義上,可以把至今的改革開放歷程劃分為4個階段:第一階段由1978至1992年,第二階段由1992至2001年,第三階段自2001到2012年,2012年開啟改革開放的新階段。雖然在時間的劃分上與上述成果有重合之處,但背后的依據不同。
2.1980年代:社會在資本與市場缺位的情況下曇花一現
在計劃經濟年代,中國的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同時也付出了沉痛的代價。一方面消滅市場,剝奪資本及其擴張的沖動。先是農村的土地改革與合作化運動,城市的工商業改造,直至“割資本主義尾巴”;另一方面,隨著“七八年再來一次”的運動和“靈魂深處鬧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扭曲社會和個人沿需求層次的提升。只有國家權力,沒有市場,沒有社會;國家統攝一切經濟政治和文化活動,管理民眾,事無巨細,從出生到進墳墓。一端是高度集權,另一端則是盲從。走到極致,統轄一切的政府及其權力也就走到了盡頭。
1978年中國的國情,不是一足獨大,另兩足過弱,而是根本沒有另外的什么“足”,只有政府權力“一足”。站在這一角度看,改革開放之初,是將這一足的立足點由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一足”通吃的根本局面并未改觀。雖然農村由人民公社、合作化回到包產到戶,但農民并沒有投資擴大再生產的資本意識,城市依然實行計劃經濟,雖然“放權讓利”,雖然“政企分開”,此時的“企”只是國企。改革的標志是“喬廠長上任”。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通過,隨即誕生了大量民營公司,該年因此被稱為中國現代公司元年。不過總體而言,當時資本弱小,市場也極其有限。
1980年代的主要特征是思想解放和啟蒙,為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是“激情燃燒的歲月”。隨著民主化呼聲日盛,個人自主意識逐步增強,社會浮現,這就構成與政府權力之間的直接沖突。由于思想解放本身的理論深度有限,個人與社會并未接受如18、19世紀西歐那樣的經濟啟蒙,尤其是缺少市場與資本的參與,個人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政府權力也沒有受到來自市場與資本的挑戰,結果是政府權力壓倒沒有經濟基礎的社會。個人與社會的萌生在資本與市場缺位的情況下注定只會是曇花一現。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上,雖然個人可以在沒有滿足低層需求的情況下直接追求高層需求;但是如果社會的相當部分甚至整個社會都陷入這樣的境地,必然給民族和國家帶來混亂甚至災難。然而,重新掌控大局的政府一時忙于治理整頓,改革開放前景迷茫,思想解放的戛然而止也留下了后遺癥。
3.1992年至世紀之交:資本與市場重現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的南方談話顯示出劃時代意義。1992年轉向市場經濟,這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資本在1950年代被從中國大地上鏟除后于世紀末再次萌芽,繼而迅速壯大,既喚醒并實現國人的致富夢,進而以第一桶金——帶有形形色色或多或少原罪——作為資本,匯成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為隨后社會的再度萌生奠定經濟基礎;也在原先單一的權力金字塔的一側,構建起資本與市場的營地,對中國此后走向的影響越來越大。在此意義上,政府與企業、權力與資本的關系,既是改革的基礎,又是改革的對象,還是改革的結果。甚至可以說,一部改革史,就是政府在找尋與探求自己權力邊界的歷史[11]——當然,不僅是政府與資本的邊界,而且是政府與社會的邊界。
然而,在1950年代初消滅了市場和資本的政府及其權力對此沒有準備,既不可能一步到位全盤引入發達國家成熟的市場規則,也來不及制定此時此景下中國特色的市場規則,即使摸著石頭過河,且行且建,也是執行乏力。政府逐步發現,在原有的權力之外出現了由看不見的手支配的市場和相對獨立的資本。權力對資本愛恨交加: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但這個錢不是自己的,不是權力可以呼來喚去,有時還要在資本的面前低聲下氣招商引資。市場與資本的強勢一時到達全民經商的地步,“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跑單幫”就是當時的寫照。權力,進而人間一切或美好或丑陋之事物統統折合成貨幣,標價出售。政府過強,官本位,一切折合成官,社會拜倒在官的膝下;而今,資本過強,錢本位,一切折合為貨幣,與官本位一樣荒謬。更危險的是,錢還會腐蝕權,權錢交易。在各類資本中,初來咋到的外資,或者說“高級階段”的資本,還帶著源于本國的法治底線、宗教情懷,以及對社會的敬畏之心;然而民資,除了少數還有歷史淵源(榮毅仁、王光英等)外,可以說就是“初級階段”的資本,既深諳經濟人假設而又無所顧忌,更清楚知道,與權力的勾結,可以以更少成本和更小風險更快更大獲取利益,這就是形成利益集團或權貴階層(吳敬璉)的淵源。
資本對權力的“敬重”一本萬利,換來了權力對資本的姑息和放縱。無論什么“資”,要地、要廉價勞動力、要原材料,所向披靡;不要監管、不要環保,肆意妄為。民資,不管怎么說還是在自家院子里,政府尚可越權而為;外資更不聽管教,來去自由,背后還有各自國家權力的靠山。有經濟學家聲稱,中國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加“自由”,中國都沒有與資方博弈的工會。由于沒有權力與資本的契約,沒有明確雙方的邊界和相互制約關系,一旦權力介入市場,企業的行為就會扭曲,因為它們首先要討好的不是消費者,而是官員,是控制資源和隨意制定規則的人。而資本介入權力,代表公益形象的政府就可能蛻化成利益集團,導致社會不公,社會結構崩潰。
4.21世紀初:個人與社會再度萌生
轉向市場經濟之際,也就是個人與社會再度萌生之時。不過這次主要不是在精神領域爭政治權利,而是謀求經濟利益。那些1980年代的精英發現,放下其思想解放的沖動,在經濟領域有廣闊的發展天地。1990年代登上舞臺的主流群體實際上換了一批人,本無政治權利訴求,于是民間致富的動機在相當程度上與政府的GDP目標相吻合。無論是自然界的資源和生態還是國家層面,都還有較大的空間,供個人與社會在馬斯洛需求層次的低層次發展和提升。因而在這一時期不會,實際上也沒有發生如第一階段那樣與政府直接正面的沖突。在1990年代,可以說政府與資本都未曾覺察到個人與社會作為與之相均衡的一方的存在,對于漸次生成的社會沒有準備。社會也沒有萌生自我意識。
不過,隨著資本與市場的不斷擴張,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成為世界工廠之后,社會以對政府權力和資本與市場越來越明確的抗衡昭示自身的存在。
加入WTO之后,中國充分發揮資源稟賦優勢融入全球產業鏈,在解決就業之時也引入了先進技術和管理,經濟迅速發展。然而在政府權力的溺愛和慫恿下,資本從各個方面不斷擠壓社會的空間,這是迫使社會沿生存權和發展權萌生的原因之一。各地競相壓低要求討好外資,熟門熟路的外資也摸透了中國政府和社會的底細,在中國特色的游戲規則中游刃有余。政府負責三通一平,取消稅收,盤剝農民工,消耗本國資源,污染青山綠水。只要世界工廠開足馬力為發達國家提供廉價商品,科學發展觀實際上只能是一句空話。即使做出如此讓步和犧牲,依然在全球產業鏈中處于微笑曲線的谷底,還要面臨種種挑剔和反傾銷。初級階段的資本對外受制于高級階段的資本,對內利用缺乏監管的空白肆意而為,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滴著中國人的血;假冒偽劣、食品和藥物安全,以及房地產等質量問題大部分均出于此。資本肆意妄為,致使生態惡化,十面“霾”伏。“社會主義不是貧窮”。始于解決馬斯洛底層生存需求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驀然發現,竟然依然面對生存需求,甚至是呼吸和飲水。危房、豆腐渣工程、沿街攤販,以及一再引發血案的拆遷,都屬于這樣的類型。21世紀初,在特殊條件下和某種程度上再現初級階段資本主義的罪惡,只是染上了中國特色。
此處的中國特色,在于資本與政府聯手形成利益集團或權貴階層,上述惡果因此被進一步放大。這些問題在面上看來是以個人與社會為一方,資本為另一方之間的沖突,然而在背后都少不了政府及其權力的騰挪。購房者說,明明是我們跟房地產商的沖突,為何政府都要擋在前面?在“艾滋病拆遷隊”的背后,政府的身影隱約可見。發改委價格司的貪官收受巨額賄金,動用公權力讓藥品價格驟然提高十倍、百倍、甚至千倍,多少百姓因治病而陷入絕境、多少生命因無錢而貧病夭亡。政府加上資本,與正在蘇醒沿馬斯洛需求層次底層向上攀登的個人與社會構成直接沖突。
原因之二,上世紀末后市場無限擴展,進入不該完全市場化的領域。市場和資本在中國擴張的過程中遭到了龐大的國有企業(譬如國資委及其麾下的“兩桶油”)強有力的抵制。但在房地產乃至包括教育、醫療等社會領域則長驅直入,造成“新三座大山”。政府罔顧民生,把自己分內之事完全推向市場。結果,應當高度市場化的經濟領域沒有足夠的市場化;不應當市場化的社會領域則高度市場化。實行了分稅制之后的地方政府,儼然成為最大的地產商。其結果,其一是敗壞了教育和醫療領域原有的風氣,逼良為娼,讓本應在相當程度上由財政承擔的部門自謀生路,這是教育腐敗和醫患矛盾的主要根源;其二,在教育和醫療本應體現社會公平的領域,按錢區分三六九等,制造社會矛盾。
原因之三,社會不公。只要身在政府部門、央企國企和金融機構等,即可近水樓臺先得月。財政部長樓繼偉透露,現在央企利潤實際超過1萬億,最后上繳只有約1千億[12]。變本加厲者進而巧取豪奪,其極致就是新四人幫,甚至新四大家族。哪怕只要與之有一絲一縷的瓜葛,便可至少分一杯羹。社會不公還包括對外資、國資和民資的不公。外資桀驁不馴,背后還有國家支持;民資會拖人下水;于是國資被撫養成“共和國的長子”。這下錢就在自己口袋里,想用就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還可以隨時撤換掌門人,以保證權錢合一。國資優先,外資隨后,民資墊底。柳傳志的多次談話和隨后的反響道出了民資的不平與無奈。國進民退,央企兇猛。國企央企攜巨資進入市場化領域,所向披靡。民企對自身地位的抗爭也匯入社會抗爭的潮流,共同把社會的訴求由經濟層面推向政治領域。社會不公還體現在風險的分配上。一方是鐵飯碗加養老保險,另一方是面對不確定的市場,風險自負。由民生到民主的呼聲,不能僅以翻兩番來應對。
政府官員為何多為資本背書而不為社會站臺?在日常生活中同樣是消費者,為何沒有如普通消費者那樣感同身受,在食品安全等侵犯消費者權益上沒有切膚之痛?就在于他們在相當程度上沒有發生如普通消費者那樣的消費。其一,三公消費覆蓋了政府官員作為普通個人相當部分的消費,如餐飲、旅游,包括出國;還有各類程度不一的“特供”。其二,送禮,各式權錢交易。一句“工資基本不用”就說明了問題。前者意味官員不屬于通常意義的社會,后者影響政府在資本與社會二者間的站位。至于違法拆遷等公權力侵犯私權利的事例,對于本在體制內的官員來說,即使不是絕無,也屬罕見。
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社會的萌生同樣處在“初級階段”,表現為相對弱小,其訴求的內容和方式處于生存和經濟領域的較低層次,大致有四種類型。
其一,個人行為,農民工開胸驗肺是其中的典型。更極端的是多起拆遷中的自焚。弱小的個人在走投無路之際,以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向政府和資本作最后的抗爭。遺憾的是,如此以生命為代價的抗爭并沒有如群體性事件那樣的影響和受到關注,這只能歸咎于政府只要不鬧大就沒關系的管理模式,以及包括媒體在內社會對個人生命的漠視。二代農民工的訴求已經不僅是工資和待遇,其極端是富士康的十幾連跳,以不同于其父輩的方式,提醒政府和資本關注這一群體的存在。
其二,已成為普遍社會現象的群體性事件。絕大多數參與者生活在中國社會底層,其訴求主要是為了生存,并不是要推翻國家政權和現行社會制度,大多數情況沒有計劃和組織,與個人行為相差不遠,屬人民內部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激化之故[13]。所謂“人民內部矛盾”,十有八九就在于資本和政府以種種方式侵犯個人經濟利益甚至生存權,在于政府在資本和社會之間“譜系”上的站位偏向資本一方。
其三,社會與資本和政府博弈方式的中國特色,那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社會不公對個人最大也是最惡劣的影響是扭曲個人的價值觀。對策一是同流合污。個人不是與社會不公對抗以改變社會不公,而是順從,進而想方設法也進入權貴階層。“寧可在寶馬車上哭”和“死也要死在體制內”的宣示清楚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對策二,躲進小樓成一統。沒有文革經歷作為反思的參照系,不一樣的80、90后頻繁跳槽、做宅男宅女,蝸居于“小時代”,管它春夏與秋冬!對策三,政府每出臺一項政策,即使缺乏法律依據,即使侵權,也不據理力爭,而是照單全收,回過頭來再尋找政府政策的破綻,譬如假離婚之類。中國人不是不會創新,而是把創新都用到發現規則的漏洞上。其結果是政府沒有公信力,社會沒有正義感,且越發狡詐。對策四,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破壞了市場規則,對司法的干預更是摧毀了公正的底線。大量的個案處理和下不為例將重復博弈變為一次性博弈,培育無視規則和背叛,化市場經濟之神奇(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為腐朽。既然大家都不講規則,那就破罐子破摔,劣幣驅逐良幣,全民誠信缺失。世風日下,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或是求助于傳統文化,然而孔子像的一遷再遷即可見傳統倫理道德在21世紀的尷尬處境;或是評選各類人物:感動、最美……;或是“八榮八恥”。民不畏“恥”,奈何以“恥”懼之?
或許最令人擔憂的是第四種類型,把當下的種種弊病都歸咎于改革,聲稱要對改革進行再改革,回到“姓社”“姓資”的年代[14]。計劃經濟年代,把市場與資本、社會與個人消弭于無,其惡果難道還不嚴重,教訓難道還不深刻?在這一思潮的背后,毛澤東的巨大身影清晰可見,而中華民族為文革付出的慘烈代價卻已然淡忘。
面對社會的萌生,資本或是逃避政府與公眾監管,或是躲在政府的巨大身影之中;政府的措施是信訪加城管,統一在維穩的旗幟下。如果不揭示群體性事件等背后的緣由,單純維穩會止于現象層面,治標不治本。至于倒退,更是在理論上錯誤,實踐上行不通。
5.2012年:走向政府、資本與社會均衡
凡此種種表明,政府缺乏法治意識。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府會禁不住越界踏入市場和資本的領域,往往傾向于靠近資本一方,弱化、放松對資本的監管,迎合資本不合理的要求而較少考慮社會與個人的訴求,甚至侵犯社會與個人的權益。金融危機后4萬億救市等措施依然指望投資拉動,在資本與社會兩端依然偏向資本。面對政府和資本的一再侵權,社會缺乏維權意識,更缺乏公民意識。資本面對社會任意而為,缺乏法治意識,面對政府或曲意逢迎或退避三舍,缺乏維權意識和公民意識。1980年代思想解放戛然而止的代價逐漸顯示出來,中國呼喚新的啟蒙。
由上述改革開放的歷程,便可以理解新一屆中央的戰略,尤其是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
通常都認為新一屆黨中央的一系列舉措意味著改革重啟,言下之意是由之前的停滯不前到這一屆的起步與加速。由上分析可知,除了上世紀80年代末短暫的治理整頓,改革開放的步伐從未停止,執政黨一直在摸著石頭尋求解決方案,只是沒有隨著資本和社會的萌生而相應地調整政府的思路和行為;從根本上說,也就是沒有劃清政府權力與資本和市場的邊界,沒有劃清政府權力與社會的邊界。
中共十八大之后的糾風與反腐,在于清算上兩個階段發生的權錢交易和所形成的利益集團,切斷政府與資本之間的不正當關系,從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決定性作用。強化對資本的監管,如生態和食品安全等。史上最嚴的新《環保法》從2015年1月1日開始施行。法治,是處理政府與各類資本關系的準繩。
在與社會關系的一側,強調內需拉動、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教育醫療養老改革、關注民生,以及扶持非政府組織和社區建設等,表明政府正在調整自己的坐標,由偏向資本轉向社會。內蒙呼格案糾錯和賠款昭示糾正政府對社會的侵占,厘清公權力與私權的邊界。上述舉措,讓新一屆中央得到來自資本和社會的廣泛支持。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順理成章提出依法治國。劃定政府與資本的邊界:提供市場充分和透明的信息,制定市場規則,以及監督資本的所作所為。政府出臺政策,發揮金融杠桿作用,引導資本進入國家戰略領域,進入有助于社會發展的領域。政府劃定與社會的邊界,扶持社會成長,以核心價值觀引導社會自我完善。
資本面對政府強化維權意識,遵守市場規則,規范自身行為,提升對于社會的責任感。社會面對政府和資本都需要強化維權意識,培育公民意識,沿馬斯洛需求層次提升自我,積累自身的人力資本。資本與社會結合開展社會創新,由民間力量自發創辦社會企業,促進解決社會問題,“運用商業手段,實現社會目的”。由扶貧、教育、環保等傳統領域拓展到醫療、養老、社區服務、特殊人群關懷。公益基金會秘書長沈東曙認為,2014年是中國社會創新的市場建構元年[15]。由這句話可以聯想到在西歐,19世紀被稱為“愛的世紀”。在依法治國的基礎上,在核心價值觀的引導下,中國傳統文化也將推進社會的自我管理和完善,共同構建國家治理體系。資本與社會同樣不能以錢和人情逾越法的底線。
由此可見,依法治國,是對改革開放特別是轉向市場經濟以來所積壓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政府與資本和社會關系的總清算。推進“依法治國”不僅有利于公平、公正地解決因征地、腐敗和污染等引起的社會矛盾,而且意味著在憲法的基礎上構建政府、資本與社會三者均衡。改革開放三十余年,在河中甚至深水區摸石頭的相對不確定的社會轉型,從此將進入相對有序清晰的發展軌道,進入改革開放的新常態;這是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等各領域“新常態”的核心。
相對而言,東西部、城鄉、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在依法治國的實施上會有相當大的差別。東部、城市、發達地區,資本較為充裕,個人有較強的維權意識,政府需要做的主要是沿著依法治國的軌道,完善市場運行的制度和環境,讓資本和社會的積極性充分涌現,鼓勵創新和培育品牌意識。西部、農村、欠發達地區,因其相對滯后而有更強烈的趕超意愿或任務,需要或涌現出“有魄力”的能人、強人,因對資本的渴求而削弱對資本的監管,外資和來自東部的資本也會尋找“自由”而來到西部,而西部的社會與個人則較為軟弱,缺乏維權意識。在這些因素的綜合影響下,官員會情不自禁掙脫乃至無視牢籠對其權力的制約。在此意義上,落后地區更需要依法治國。
然而,這并不意味依法治國會束縛落后地區的發展,而是對所謂“魄力”要有新的理解,不能以趕超為由逾越法治的底線。對于落后地區的發展來說,魄力,首先在于對依法治國的深刻理解和堅定不移的實施,其次在于對自身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的深刻理解,以及對目標的確切定位和發展路徑的獨特設計,最后是對資本和社會的細致解釋、說明、動員和規約。顯然,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相對落后地區,依法治國都對官員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謀求發展或跨越之時,需均衡而又動態積極地處理政府、資本和社會的關系。
政府、資本和社會三足之間的均衡,將克服改革開放以來的路徑所存在的弊病,進一步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巨大優勢。以往的弊病集中體現在以下方面:其一,權力過大,往往因失去監督和制約走向集權甚至極權,或者發生腐敗。權力干預市場,造成不公平競爭,權力壓制社會,泯滅社會的自組織能力。依法治國,就是要把這樣的權力關進牢籠,理順權力、資本和社會的關系,互相制衡,各就其位。其二,官本位久治不愈,甚至愈演愈烈。公務員熱,死也要死在體制內的宣示就是明證。一鳥入林百鳥噤聲。資本和社會紛紛選擇與權力保持一致,中國的發展失去由下而上的動力和各方之間必要的張力。其三,難以保證政府的決策萬無一失。改革開放以來,各級政府長官意志隨意決策,違背經濟規律的錯誤可謂比比皆是,層出不窮。依法治國將依法追責,也就是在有限規則的基礎上重復博弈。這些弊病,有望在依法治國的框架內得以從根本上消除,從而在黨的領導下進一步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依法治國,中國的社會轉型進入新常態,雖然還會有不確定因素,但整體而言會較為有序,中國的發展因而將更加健康,中華民族也將對自己的道路更為自信。一旦權力不再越界,一旦資本得到規約,社會將在法的底線之上自主自立。法無禁止即可為。在憲法的基礎上,在核心價值觀的引導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來自社會的創新動力將噴薄而出。媒體常言,中國是某某大國,卻不是某某強國。如今政府依法治國,市場完善而規范,以及由自立自強的個體構成的富有活力的社會,中國,由此從大國邁向強國。
19世紀末,李鴻章驚呼“三千年變局”開始了,黃仁宇稱之為200年“大革命”至今也已有160年的歷史。期間雖經多次戰爭與革命,但中國仍處于皇權專制解體的“千年變局”之中,三十余年的改革開放依然是百年震蕩和變革的延續[3]。而今,在這個千年變局的百年震蕩中,中國通過改革開放,通過政府、資本和社會三方的互動與均衡,正在走出傳統循環的周期律,迎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1]謝嘉幸.論不可交換價值[D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1035bc010007zb.html.
[2]鄭永年.“笨蛋 這是資本”[DB/OL].http://www.80sd.org/pl/2014/10/14/66779.html.
[3]袁緒程.中國改革開放30年回望與前瞻——歷史進程、經驗和走向[J].中國改革,2008(5).
[4]福山.說中國集權的人是不懂中國歷史[DB/OL].http://news.ifeng.com/a/20150423/43618947_0.shtml.
[5]沈裕尼.強大政府與民主制衡[DB/OL].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talk/story20150203-442674.
[6][美]馬歇爾·伯曼著.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現代性體驗[M].徐大建譯.轉引自 何亞娟.生態危機根源的經濟哲學透析[J].現代經濟探討,2013(1).
[7]呂乃基.科學與文化的足跡[M].北京:中國科學文化出版社,2007.
[8]雅克·巴爾贊.從黎明到衰落[M].林華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9]馬英九老師:大陸應問臺灣到底要武統還是和統[DB/OL].http://news.ifeng.com/a/20150113/42922598_0.shtml.
[1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編.中國改革開放史[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2.
[11]雪珥.熔爐與叢林:三十年來中國政商關系[DB/OL].http://finance.qq.com/a/20150103/002240.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12]養老改革,國務院在全國人大釋放了什么信號?[DB/OL].http://news.sina.com.cn/c/zg/slt/2014-12-30/1634504.html.
[13]百度百科條目.“群體性事件”[DB/OL].http://www.baidu.com/link?url=uYQG39yweLv_Zx7CpyYLjgKkzzyijLFe7euyQh1fj5A2Vp-Tx8RB7ezeP3fgrXXXxD3J_Gs5oq0Bazf1FV3nr0q&wd=%E7%BE%A4%E4%BD%93%E6%80%A7%E4%BA%8B%E4%BB%B6&issp=1&f=3&ie=utf-8&tn=baiduhome_pg&rsp=1.
[14]《人民日報》發重大信號[DB/OL].http://www.mzfxw.com/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4&id=31027.
[15]陳實.2014年是中國社會創新的市場建構元年[N].南方周末2014-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