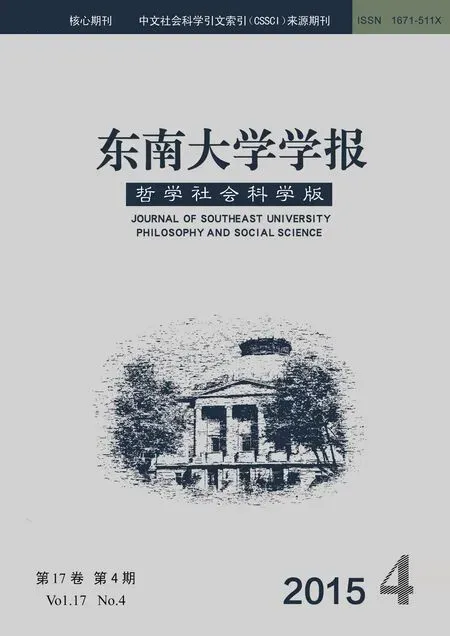德勒茲電影理論與后結構微觀政治學
田兆耀
(東南大學 人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6)
德勒茲(Gilles Deleuze,1925-1995)的電影理論集中在《電影1:運動—影像》(1983),《電影2:時間—影像》(1985),《哲學與權力的談判——德勒茲訪談錄》(1990)等著作中。王志敏曾指出,電影理論界還基本不太知道如何來面對這些有分量的著作,“這確實是對電影理論工作者的智慧的一個嚴重的挑戰”![1]87近六年來學界對德勒茲的研究出現迅猛發展的勢頭,除了編撰文選、譯介《感覺的邏輯》《千高原》等重要著作外,對其哲學思想、游牧思想、政治哲學、文藝思想等已展開深入研究。對其電影理論的研究也有所改觀,大致分為三類:一,從柏格森綿延學說、尼采的超人哲學以及皮爾士的符號學等角度探索其學術資源、挖掘其電影哲學思想。二,電影理論解讀,闡釋其關鍵詞、梳理電影理論內涵。第三,跨學科研究,從哲學的角度不必待言,有的學者還從教育學、類型學等視角闡發其價值。徐輝、聶欣如、黃文達、以及北海道大學的應雄等學者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徐輝的成就最為顯著。對德勒茲電影理論進行跨學科研究富有啟發意義,本文以會通其學理邏輯為軸心,從哲學思維方法入手闡明其電影理論的基礎、要義和蘊含的微觀政治學思想。
一、哲學劇場或曰“阿里阿德涅的線”
作為哲學家,德勒茲把自己的哲學思維方法帶入了電影理論領域,這是理解德勒茲電影理論的鑰匙。他首先在畫面與概念,電影與哲學之間尋找理論支撐,他指出:“概念本身之中即有一種與畫面的關系,在畫面本身之中即有一種與概念的關系。”[2]75電影本身是影像和符號的新實踐,哲學應該把它變成概念實踐的理論。所以他說,“我們不應該再問‘什么是電影’而是應該問‘什么是哲學’”。在德勒茲看來,哲學的建構主義有兩層意思:創造概念和構擬平面。二者就像翅膀和腳蹼,成雙成對,互為補充但性質不同。內在性平面“是思維為了顯示什么是思維行為,如何使用思維以及在思維中確定方向等而給自己規定的一幅圖景”。[3]250它不是方法、知識、定見。哲學基于內在性平面,形成、發明、組合概念,“嚴格地說,哲學是一門創造概念的學科。”[3]205
德勒茲批判西方傳統哲學觀念,拒斥穩定的同一性,反對普遍化的秩序,否定僵死的轄域化,而肯定差異、生成、欲望機器、流動、混沌、游牧、多元性,對概念的理解有別于傳統。在他看來,傳統的形而上學是一種“縱向性”的思維方式,按照不同等級安排事物,確定它們的位置。逃避形而上學的最好的思維方法就是承認差異,差異哲學是“橫向性”思維方式。差異和重復是聯系在一起的,兩者是不斷再生的運動。“真正的哲學起點,即差異,本身已經就是重復了。”[4]30在橫向連接中出現的一種新的綜合哲學,是介入世界的方式,而不是用僵化的形而上的概念、理性束縛生活,凌駕于生活之上。在傳統哲學中,比如柏拉圖哲學往往認為概念表達事物的本質,是用來推論訓練的。德勒茲卻認為概念不表達本質或事物,而表達事件,是一個實體,按照自己的方式對事件加以剪裁和重新剪裁,都有被視為自身的組成部分的交匯點,或者說凝聚點,擁有依其創造時的條件而定的確真性。“概念屬于異質生成,也就是說,屬于按照組成成分之間相鄰地帶作出的一種賦序。”[3]227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概念的地位具有:“一種多重性,絕對的面積或體積,自我所指物,一組內涵變式的復合體——這些變式因遵從某種相鄰關系的次序而不可剝離,而且被一個處于飛掠狀態中的端點所巡視。”[3]244他列出了哲學概念的顯著標志:特異性(事件)、創新性(生成),以及重要性(其結果所具有的生命力),“概念,無法與情狀相分離,我所說的情狀意指它們對我們的生命所產生的強烈效應;無法與感應相分離,也就是說,它們在我們身上所激發的新的看與感知的方式。”[5]13概念不是抽象的,它們是為活生生的生命而存在的。
福柯認為德勒茲采取的是一種哲學劇場的思維方法,這里有眾多的哲學家帶著自己的概念出場。哲學家用內在性平面切入世界,但人們從來就不在同一個平面上對話。概念的多義性僅僅取決于相鄰地帶(一個概念可以有數個相鄰地帶)。“概念只以內部和外部的相鄰地帶為規則。它的相鄰地帶或內堅實度取決于各個組成成分之間在模糊地帶里的銜接關系”。[3]327每一個概念的組成成分跟另一個之間都有局部的重疊,在概念內外模糊的相鄰地帶生成新的思想。“這是生殖性的思想,熱烈的思想,肯定性的思想,非范疇的思想:其中的每一種思想都有一張不可識別的面孔,都佩戴了一副我們從未見過的面具;這些差異,從未被預見到,但仍然促使我們回到它們那里,這些差異是柏拉圖、司各特、斯賓諾莎、萊布尼茨、康德和所有哲學家的面具的面具,這種哲學不是思想的哲學,而是作為劇場的哲學:一個上演啞劇的劇場,這部啞劇有許多轉瞬即逝的場次,在這些戲劇中,打著盲目的手勢。就是在這個劇場中,在蘇格拉底的面具下,突然爆發出智者的笑聲”。[6]210創造概念是純粹的漸變,一個哲學家總是會不斷地修正甚至改變自己的概念。盡管概念有時間性,有署名人,但概念是不斷變化、變異的,其更新賦予哲學一部歷史。在概念相鄰地帶的這根牢固的線,福柯把它比喻為引導忒修斯走出米諾斯迷宮的阿里阿德涅的線。
德勒茲認為將語言學運用于電影學的努力是災難性的,他發現電影評論遇到雙重障礙:一方面避免單純描述影片,另一方面又要使用外來的概念。“評論界的任務是提出一些概念,這些概念既非‘產生’于電影又只適用于電影,適用于某一類影片,適用于某一些影片。”[2]68鏡頭、景深等技術性概念服務特定的目標意義不大。電影的概念只能從哲學的角度生成。重復與差異、“阿里阿德涅的線”在電影哲學領域是一種富有生成意義的思維方法。比如使用“和(ET)”:“它引出了一切關系;有多少個ET(和),就有多少關系;ET(和)不僅使一切關系搖擺不定,也使êTRE(是、存在)、使動詞搖擺不定。ET(和),‘ET(和)…ET(和)…ET(和)……’,這完全是一種創造性的結巴,是一種語言的奇特用法,與建筑在動詞êTRE(是、存在)基礎上的規則的、占統治地位的用法相對立。當然,ET(和)意味著多種多樣性,意味著對同一的摧毀。”[2]51創造新概念,生產帶連接符號等方式的新概念,比如:運動—影像,時間—影像,感知—影像,動情—影像,夢幻—影像等,在概念間的細微差異、相鄰地帶中生成新思想,構成了德勒茲電影理論的顯著特征。
二、分類研究:運動—影像與時間—影像
德勒茲繼承了尼采、柏格森(尤其是《材料和記憶》)等非理性主義哲學,還吸收了皮爾士符號學的三分法(圖像、指示、象征),在電影著作中發展了早年《差異與重復》對傳統形而上學思想/影像二分法的批判,開創性地對電影進行分類研究。他認為心像和影像的相遇無可阻擋,哲學概念以“內在性平面”把握活生生的世界,電影以視聽形象表現生活,均給世界帶來新的思維圖景,他雄心勃勃地在哲學和電影的相鄰地帶革新電影的研究范式。在宏觀上他將電影分為兩類:運動—影像和時間—影像,在時間上與經典電影、現代電影的劃分基本一致,但是在思維基礎和內涵上差異懸殊。
所謂運動—影像表現為一種空間運動,是物質的,可見的,“運動并非某種匿身于影像后的事物,而相反地是影像與運動的絕對同一性,正是這影像與運動的同一性,使得我們立即地歸結出運動—影像和物質的同一性”,[7]121運動—影像和物質—流動表述同樣的意義。運動—影像是作為相異構成的客體,傾向于將時間空間化,時間是運動—影像有機構成的間接對象。在以運動—影像為主的經典電影中,全體被視為早就存在的先行者。如愛森斯坦的理性電影中,“所謂‘全體’”,就是以自身組成物之間不斷對立和超越而呈現的有機總體,(它)以辯證法的法則像一個巨大螺旋那樣進行自我建構。”[8]607其實是先驗的有機概念哲學在電影中的表現。在美國格里菲斯的敘事蒙太奇中,是向遭受威脅的有機體集合,是一種有機—活力蒙太奇[7]73-108。愛森斯坦的對立蒙太奇賦予辯證法一種純屬電影的意義,“作為任意當刻的區間變成擁有瞬間強大力量的質性躍升”,是有機—辨證蒙太奇。戰前法國的先鋒派構筑運動—影像的巨型機械式構成,致使某個世界同另一個世界形成對立。正是根據可公度性聯系,在空間中進行操作的力及因子才得以決定出最大運動量,體現的是一種數學精神,是一種類似康德的數理上的崇高,是同有機決斷的心靈—計量蒙太奇,比如岡斯的《車輪》。德國表現主義構思著一種精神世界的全體,是一種能動式崇高,將一非有機生命連接到一種非心理學式生命的精神—緊張化蒙太奇,比如茂瑙的《浮士德》。可變當刻可以變成區間、質性躍升、數位單元和緊張度,而全體則可以變為有機全體、辯證式總體、數理式崇高的巨大總體以及能動式崇高的緊張性總體。運動—影像有著兩種面貌,其一朝向整體集合及其組成部分,另一則朝向全體及其變化。這四種運動—影像構成的有機、辨證、外延、緊張等構想而發展出來的蒙太奇形態并無軒輊之分。“當我們將運動—影像聯系到某個不確定核心(聯系到一特殊影像時),它們就分化為這三種影像:感知—影像、動作—影像和動情—影像。”[7]130他還提出固態、法國學派擅長的液態和氣態三種感知模式,不同的感知模式提供異質性的運動情境。美國的西部片表現了一種大形式(SAS,情境—動作—情境,情境在動作反映中延伸),卓別林的喜劇片集中體現了小形式(ASA,動作在情境中發展)。戰后早期新影像有五個明顯的特點:“離散的情境、疏離的關系、游走的形式、俗套剪影的意識控制與共謀的揭發。”[7]341這一切預示了動作—影像、美國夢的危機,在運動—影像的危機中誕生了時間—影像。
經典電影的感知—運動情境被現代電影的純視聽情境取代,后者是由一些脫節的、空蕩的純視聽符號構成,物品和環境具有了自身的價值,情境和動作之間缺乏邏輯聯系,動作在情境中漂移而不是控制情境。如:《溫別爾托.D》中早上年輕女仆走進廚房,完成一系列無精打采的機械動作:打掃房間,用水驅走螞蟻,取出咖啡機,用腳尖關門,目光掠過自己懷孕的肚子。運動—影像側重“下一個影像上會看到什么”,時間—影像側重“影像上有什么值得看”。希區柯克的預感已兌現,一種攝影機—意識由它能夠進入的心理關系來界定,使人們獲得了對主體和現實的深層認識。
時間—影像是時間的直接呈現。在運動與時間的關系上,時間不再從屬于運動,不再從運動畫面的組合(蒙太奇)中推斷出來,而是相反,運動從時間中推斷出來,運動隸屬視覺。“當運動—影像及其感知—運動符號只與一種時間間接影像(隸屬于剪輯)發生關系時,純視聽影像,即純視聽符號和聽覺符號,便直接與一種隸屬于運動的時間—影像發生關系。這種顛倒現象不再把時間變成運動的尺度,而是把運動變為時間的視角,建構了一種時間電影,具有全新概念和嶄新的剪輯形式(威爾斯、雷乃)。”[9]34時間不再由運動來衡量,而是自身成為運動的數量或尺度(形而上學的表現)。這種時間類似音樂中的純粹時間,指時間的整體性,宇宙中最大的運動,也就是柏格森說的“綿延”。一些著名的電影理論家認為電影表現的仿佛是在某時某地正在進行的動作,如馬爾丹說電影畫面“始終是現在時的”。[10]3朗格指出電影類似夢,“夢的方式,則是一個沒有盡頭的現在”。[11]483德勒茲說,“運動—影像以經驗形式構建時間,即時間的過程:按照以前和以后的外在關系排列的連續的現在,過去就像是一個從前的現在,而將來是一個將至的現在。一種不完全的考慮斷定電影影像必須是現在時的。”[9]431這種結論是草率的、不全面的,對電影理解是毀滅性的。德勒茲以綿延說、生成論為基礎,指出現代電影時間有三種晶體形態:現在尖點、過去時面和未來時面,時間—影像重視生成的同時性,生成不允許把以前與以后或過去與將來分離或區分開來,“其全部特點就是將來與過去、主動與被動、原因與結果、較多與較少、太多與不足、已經與尚未之間的顛倒。這種可以無限分化的事件總是都在同時進行。”[4]218日本導演寺山修司的《死在田園》中就在同一畫面中表現中年的“我”與少年的“我”并坐對話的場景。德勒茲對時間—影像的認識糾正了學界對影像時間單一而錯誤的認識。
運動—影像重視有理—剪輯,時間—影像重視無理剪輯,德勒茲說,“一個是可稱為有機的流動狀態,此為畫面—運動的狀態,這種流動狀態源于有理剪切和銜接,它本身投射出一種真實的模式(真即一切……)。另一種是晶體狀態,此為畫面—時間的狀態,這種狀態源于無理剪切,只有一些重復的銜接,并以作為生成的假的潛能代替了真的模式。”[2]78兩種狀態代表兩種電影。時間—影像傾向于消解統一性。影像的各種元素進入一種內在的關系中,可視性和可讀性兼備。畫面變成了思想,變成了能夠抓住思想的機制。在聲畫關系上,“戰后的有聲電影則傾向于一種聲響的獨立,傾向于一種聲響與視覺的無理分割。”[2]74畫面與自己的光與音響成分保持著新的聯系。比如馬格麗特.杜拉斯的《印度之歌》(1975)、《她的威尼斯姓氏在荒涼的加爾各達》(1976)共用一條聲帶,音響相對獨立。“當眼睛具有某種預見功能的同時,影像的各種元素,不僅視覺的,還有聽覺的,便進入一些內在關系之中,使整個影像不僅可看,而且可‘讀’,可讀性與可視性兼備。”[9]34比如小津安二郎電影中的靜物。
三、電影理論蘊含的微觀政治學
德勒茲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的種種變化表明電影走在政治哲學的前面。“戰后歐洲的變化,美國化的日本的變化,68年以后法國的變化:電影不是脫離了政治,只是以另一種方式完全變成了政治。”[9]30在政治理論與策略方面,德勒茲及其合作者加塔利(Guattari,中文音譯也有不同)不喜歡“宏大革命”的模式,認為顛覆性奪權變得不再可能,相反,他們探討“局部的”可理解性原則,允許依據其克分子和分子傾向來評價具體的社會事態。總的說來其政治哲學帶有微觀政治學色彩。“微觀政治關注日常生活實踐,主張在生活風格、話語、軀體、性、交往等方面進行革命,以此為新社會提供先決條件,并將個人從社會壓迫和統治下解放出來。”[12]483德勒茲認為精神分析與資本主義的聯系體現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操縱了人的欲望,直接參與了資本主義的壓制,從而提出欲望的新理解:欲望不能僅視為一種基本的匱乏,它還有生產的側面。[13]25其本質上是積極性的生產性的機器。
在德勒茲看來,運動—影像的動作邏輯支撐一種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概念,在歷史和本質上與一統思想、戰爭結構、國家宣傳聯系在一起。經典電影中,整體的模式,敞開的整體性的模式,意味著在畫面之間,在畫面本身當中,在畫面與整體之間,有一些可比較的關系或一些合理的剪切。戰后電影與這個模式隔裂,興起了各種各樣的畫面無理剪切和不可比較的關系,無理剪切、時間—畫面是主流。“由運動而產生的敞開的整體性的模式便不再有價值:不再有整體化,不再有整體的內在化,也不再有整體的外在表現。不再有通過有理剪切的畫面連接,只有基于無理剪切的再連接(雷乃、戈達爾)。”[2]74從德勒茲的著作來看,他常把有理剪切,運動—影像和法西斯主義、斯大林主義相提并論,把時間—影像和解構主義抵制統一性等話語連為一體。“從一開始,運動—影像就在歷史和本質上與戰爭結構、國家宣傳以及法西斯主義聯系在一起了。”[9]260比如好萊塢商業電影帶著俗文化的印記控制著觀眾,愛森斯坦的理性(智性)蒙太奇強制觀眾朝一定的方向思索,帶有美學上的暴力傾向。運動—影像的登峰造極者是里芬斯塔爾,應該從電影內部入手,起訴作為電影家的希特勒,在電影意義上戰勝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在《時間—影像》中德勒茲分析了影像與思維的三種關系,力主時間—影像替代運動—影像:從影像到思維,從思維到影像,影像與思維的同一,認為電影是一種“精神自動裝置”,對它能產生正面的思考或者新思維的必然性提出質疑,電影可以激發思維也可以抑制思維,“應該擯棄運動—影像,就是說擯棄電影從一開始輸入的運動和影像的關系,以釋放仍從屬于它和沒有機會發揮自身功效的其他力量,如投射、透明度。”[9]420他結合《卡夫卡:走向弱勢民族文學》的觀點,研究了時間—影像帶來的變化,集中探討了少數族裔電影與第三世界電影的政治特性。
在德勒茲看來弱勢群體并不是量上統計學的少數,而代表一種變化的力量,它也可能是人數最多的群體。“藝術或哲學所呼喚的種族不會自命血液純正,而一定是受壓制的、混血的、地位低下的、無政府主義的、游牧型和無可救藥的次等的種族”。[3]356弱勢文學不是用某種次要語言寫成的文學,而是一個少數族裔在一種主要語言內部締造的文學。“小并不標志某種方言在量上或質上的邊緣性,而標志著語言和文學中固有的變化力量(符號的、語義的、文體的、語用的力等等),尤其是促進同義之橫向聯合的改造的力。”[6]302弱勢(小)文學是一種不遵守戒律的、富有創新的、敢于質疑的文學。“弱勢族群與強勢族群并不僅僅是以一種量的方式而彼此對立的。……不存在生成—強勢,強勢絕不是一種生成。只有弱勢性的生成。”[5]144強勢是一個同質的和恒定的系統,代表一種常量,作為一種它借以被評估的度量標準。弱勢群代表一種創造性的、潛在的、異質生成的可能。
在德勒茲看來現代政治電影的基礎是人民的缺席。電影作為大眾藝術的理念可以成為標準的革命藝術,或者民主藝術,讓大眾成為真正的主體。經典電影,曾對此確信不疑,如愛森斯坦的電影,其主角主要是人民。“一些因素危害著這種信仰,希特勒的出現,讓電影不再是讓大眾成為主體的藝術,而變為被奴役的大眾;斯大林主義,用一黨專制取代了人民的團結意識;美國人民的瓦解,不再相信過去人民所相信的熔爐,也不再相信通向未來的希望(哪怕新西部片也首先展現了這種瓦解)。總之,如果有一種現代政治電影,那其基礎就是:人民不再存在,或者還不存在……人民缺席”,[8]619“給意識覺醒敲響喪鐘的,恰恰是‘沒有人民’的這個意識的覺醒,只有許多人民,只有一種需要聯合起來的不同人民的無限性,或者(他們)由于問題變化而不需要聯合。”[8]621這就是人民缺席的原因。現代西方重要的政治導演雷乃、斯特勞布等懂得展現人民的不在場。“缺席的人民是一種生成,它在貧民窟、集中營或少數人聚居區自我生成,在新的條件下,一種必然政治化的藝術投身于此。”[8]620人民的缺席并不是一種對政治的放棄,正相反,這正是政治電影在少數族裔和第三世界國家建立起來的新基礎[14]。現代電影獻給新創生的人民。
經典電影不停地控制標明政治與私人相關性的邊界,從一個政治立場過渡到另一個政治立場;在少數族裔和第三世界的現代政治電影中,私人事務與社會—當下和政治混合在一起,私人事務直接就是政治的,牽動著生死裁決。“它的狹窄空間使得每一件個人私事都馬上跟政治掛上了鉤。”[3]35現代電影讓私人事務進入政治,讓政治事務進入私人生活。如果人民缺席,如果人民分化為少數族裔,那么“我”首先是人民,這里蘊含一種奇特的力量,“讓內部與外部、人民事務與私人事務、缺席的人民與缺席的自我之間發生直接關聯,是一層薄膜,一種雙重生成。卡夫卡曾談及弱小民族的記憶所具有的強力:‘一個弱小民族的記憶并不比一個強大民族的記憶短暫,因此它對現有素材的研究更深入。’它在深度和遠度上彌補了其在廣度上的不足。”[8]622個人經歷與集體記憶直接關聯。有評論者指責,“這些電影以及角色過于被動和消極,有時俗氣不堪,有時神經質或脫離社會,用一種‘模糊’視角替代改變行為。”[9]29現代電影建立在卡夫卡式的不可能性——難以忍受——之上。現代電影新的對象、狀態是陷入痛苦。“痛苦,或陷入痛苦就是一種轉變、一種過渡,或者一種生成:痛苦通過殖民者的意識形態、被殖民者的神話和知識分子的話語,讓言說行動變成可能。為對創造他的人民有所幫助,作者會讓一些組成部分陷入痛苦以讓人民創生,唯有人民才能建構整體。”[8]623人物不斷跨過私人事務與政治事務的邊界,讓個人陳述制造出集體陳述,私人事務從而變成政治事務。
少數族裔、第三世界政治電影的基礎是分裂和碎片。比如美國黑人電影中種類和形象的多元化,尤瑟夫.夏因的電影里多條線索糾結纏繞的多元性。戈達爾等新浪潮電影拒絕沿用傳統的剪輯原則,經常采用“跳接”,即“在不變換場景的情況下,把一個連貫運動中的兩個不連貫部分剪輯在一起。影片從一個場景驟然跳到另一個場景,事先幾乎沒有任何暗示”。[15]431影像不再符合動作邏輯連接,而是在純粹的影音的表達可能性中,符合于感情和沖動的破碎狀態,為深入表達西方現代人紊亂的意識領域提供了便利。亨利.朗格盧瓦高度評價了這一手法,認為電影有“戈達爾之前的電影與戈達爾之后”兩大時期。[16]4德勒茲在深廣的思想領域闡發“跳接”的哲學意義、政治意義、美學價值:“ET(和)既非成分也非總體,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我認為那是戈達爾的力量,生活和思想的力量,以嶄新方式表現ET(和)的力量,使ET(和)積極行動的力量。”[2]52弱勢文學的一大特點是:“一切都帶上了群體的價值”。[3]34在少數族裔的影像中,“一種我與世界之間的溝通,在碎塊的世界里和折斷的自我之間溝通,仿佛世界的全部記憶落在每個被壓迫的人民身上,而自我的全部記憶則游弋于一種有機的危機中。”[8]622現代電影的最新特色是通過自身聚合了集體的條件。由于人民的缺席,作者置于一種生產集體陳述的氛圍中,這些陳述就像即將登場人民的萌芽,其政治作用是直接且無法回避的。“作者更好地表達潛在力量,讓作者在孤獨中成為真正的集體代理人,一個集體的酵母,一種催化劑。”德勒茲認為,作者向其人物邁進一步,人物也會向其作者邁進一步:這就是雙重生成。這種杜撰是言說行動。針對少數族裔和第三世界面臨的雙重殖民(被外來的歷史所殖民和自身神話所殖民),德勒茲認為電影不應該敘述族裔神話或是虛構私人故事,為擺脫人種學、虛構的命運,電影應當化為言說行動式電影。人物通過它能不斷跨過私人事務與政治事務的邊界,并自行制造出集體陳述來。
四、結 語
關于運動—影像與時間—影像,德勒茲并沒有分出高下優劣,在《電影2》結尾說,“我們也不能確定哪個比哪個更有價值,更美或更深刻”[9],但是在《電影1》的前言中曾說:“關于運動—影像以及更為深刻的時間—影像的發現……”[7],字里行間又流露出對時間—影像的贊美與期望,因為它代表自己的差異哲學、生產理論和弱勢文藝思想。時間—影像傾向于無理剪切,和感知、情感、思維更復雜地聯在一起,有能力開發電影新形式,使思想重新變得可能。其電影理論發展了《柏格森主義》《重復與差異》《意義的邏輯》《千高原》等著作中的時間觀、非理性主義傾向、反對“一切規范化認同”的思想觀,體現了封筆之作《什么是哲學》中的哲學觀,豐富了人們對電影本質的理解。兩部電影巨著圍繞電影類型的轉化,重視間隙、裂縫、多元性,倡導去除一切形式的“能指之暴政”,重視弱勢文化的生成性,充分體現了他的解轄域化、游牧政治思想,讓電影理論研究和微觀政治哲學思潮緊緊相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們是作者繼《反俄狄浦斯》《千高原》《卡夫卡——為弱勢文學而作》之后關鍵性的政治學著作,是歐洲知識分子在“宏大革命”模式終結后獨辟蹊徑的范例,體現了后結構主義重視邊緣、消解中心的理論策略。在對弱勢族群、現代政治電影的評述中,提出時間—影像過渡到政治行為的途徑,似乎局限于文藝領域,要以此促使被壓迫者的抵抗變得卓有成效難免帶有烏托邦色彩。
[1]王志敏.德勒茲走向了自己的反面[J].藝術評論,2009(12).
[2][法]德勒茲.哲學與權力的談判——德勒茲訪談錄[M].劉漢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3][法]德勒茲,迦塔利.什么是哲學?[M].張祖建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7.
[4][法]德勒茲.哲學的客體[M].陳永國,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5][法]德勒茲,加塔利.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2):千高原[M].姜宇輝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
[6]汪民安.生產第五輯:德勒茲機器[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7][法]德勒茲.電影1:運動—影像[M].黃建宏譯,臺北: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8]楊遠嬰.電影理論讀本[C].北京:世紀圖書出版社,2012.
[9][法]德勒茲.電影2:時間—影像[M].謝強,等譯,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
[10][法]馬爾丹.電影語言[M].何振淦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
[11][美]朗格.情感與形式[M].劉大基,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12][美]凱爾納,貝斯特.后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M].張志斌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13]Gilles Deleuze,Félix Guattari.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
[14]呂國忱.社會動力的哲學反思[J].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4(1).
[15][英]賴茲,米勒.電影剪輯技巧[M].方國偉,等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5.
[16][法]薩杜爾.世界電影史[M].徐昭,胡承偉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