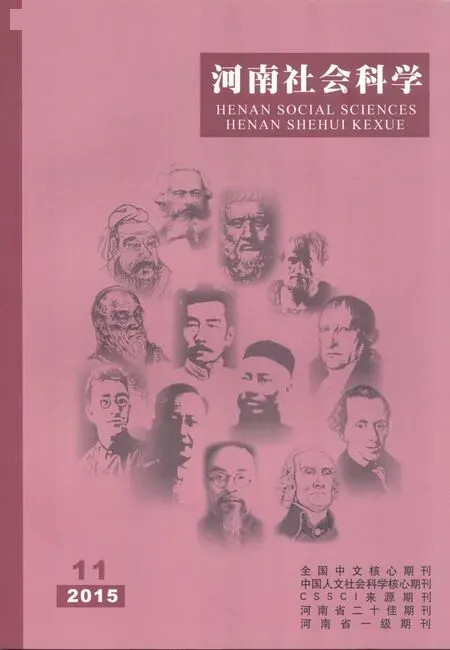構罪即捕現象的解析及應對
韓東
(中國政法大學,北京100088)
構罪即捕現象的解析及應對
韓東
(中國政法大學,北京100088)
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已經明確為法治的追求理想。然而時至今日,中國的刑事司法制度都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尷尬的局面:絕大部分的被追訴人在審前都處于被羈押的狀態。毫無疑問,這與程序合法性的價值訴求存在著較大差距。在2012年的《刑事訴訟法》修改中,通過完善程序機制力圖減少羈押措施的意圖,其實是非常明顯的。通過筆者的定性觀察來看,短期內根本性逆轉羈押比率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從思想層面上,構罪即捕觀念仍縈繞在大部分司法辦案人員的內心深處。審查逮捕是中國檢察機關行使法律監督權力的一種重要形式,也是被追訴人在刑事訴訟中走向何種命運的關鍵節點①。而構罪即捕觀念的存在,意味著犯罪嫌疑人只要符合刑法的罪狀描述,即可被羈押舉措加諸其身,而不論其他條件是否達標。如此一來,看守所內的羈押人數焉有不水漲船高之道理?
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后,在審查逮捕環節增加了訊問犯罪嫌疑人的環節,以突出該程序的訴訟性,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進而提升逮捕質量。但是在現實操作中,一些辦案人員卻發現,審查逮捕中的訊問環節似乎誘發了犯罪嫌疑人翻供的熱情。翻供現象的頻頻出現,在給承擔此項職責的檢察官帶來意外的同時,也造成了其心理上的困惑和不安。個別地區的基層檢察院已經著手開展調研,試圖尋找其誘發原因,并試圖采取措施加以遏制。事實上,立法機關增加訊問環節的初衷,恰恰就是為了通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辯解驗證各項逮捕指標,同時監督、遏制偵查中的種種不法行為。可以說,犯罪嫌疑人的“翻供”是逮捕訊問發揮其效用的正面反映,更何況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基本原則已然寫入了《刑事訴訟法》,避之不及的態度多少有些不合時宜。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可以解讀為:在辦案人員的心目中,實體上準確定性才是審查逮捕工作的第一要務。對于偵查機關提請逮捕的要求,如果審查逮捕部門不能給予積極的配合、應對,就會造成整個刑事訴訟程序難以為繼。既然準確定罪是審查逮捕部門完成本職工作的核心,作為“證據之王”的口供出現偏差自然是難以容忍的。“在刑事偵查中,通過獲取口供查明案情是一條捷徑,加上口供本身作為主觀證據也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據”②。由此,審查逮捕部門對翻供的抵觸就不難理解了,而透過這種現象也足見構罪即捕觀念的根深蒂固。那么,構罪即捕的形成原因究竟是什么,難道僅僅歸咎于思想觀念的守舊嗎?這其中是否存在制度層面的結構性矛盾,而解決方案又該如何規劃呢?
一、構罪即捕的基本成因
任何現象的產生都不是孤立、單一的,而是諸多現實因素交互作用的客觀結果。探尋構罪即捕的原因,恐怕也需要我們超越現象本身,去挖掘制度運行過程中所產生的那些帶有“隱性”特征的規則。
(一)錯捕賠償的影響
為了維系論證方法的科學性,筆者曾經就構罪即捕的形成原因,以定性研究的方式,征求部分辦案人員的意見,得到的回復大多與畏懼“錯捕”有關。按照這種說辭,審查逮捕工作一旦定性不準、把關不嚴,將不符合構罪條件的犯罪嫌疑人予以羈押,日后潛在的撤銷案件、不起訴或者判決宣告無罪等決定都會使之成為錯捕,引發國家賠償訴訟,相應的責任人也會受到處分。上述壓力迫使其把審查逮捕中的實體標準人為上升至與起訴、判決對等的地位,從而使審查逮捕異化成起訴、審判的提前“預演”。然而,結合國家賠償的有關規定仔細審視這一理由,就會發現這似乎是答非所問。盡管《國家賠償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的確將不起訴、無罪等訴訟結果作為錯捕的原因,但顯然不是以所有被追訴人都要處于羈押狀態為前提的。我國的刑事強制措施并非僅有逮捕一種,還存在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替代羈押措施。當犯罪嫌疑人的涉案情節難以滿足逮捕的罪行要件、證據要件或者羈押必要性要件時,適用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本就是順理成章的安排。從比例原則的角度出發,強制措施的多元化和層次性完全符合不同犯罪嫌疑人個別化的罪狀特征。“為了落實不可預測性,法律只能以類型化或者公式化的方式大致規定的權利義務狀態,靈活的裁量是必要的。”③更何況適用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之類的非羈押措施,根本不會導致國家賠償的后果,對于“錯捕”的擔憂也自然不能作為構罪即捕產生的實質癥結。
在筆者看來,構罪即捕所引發的對逮捕措施的過分依賴,反倒大大增加了“錯捕”的風險概率。因為只要適用逮捕措施,就會面臨被追究“錯捕”責任的潛在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構罪即捕相當于審查逮捕部門的一種自我施壓行為,是“錯捕”的因由,而非其后果。故而,“錯捕”導致構罪即捕的說法其實是本末倒置的,陷入了后此謬誤的窠臼。不僅如此,在隨后的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擁有裁量權的檢察官和法官也不得不考慮逮捕與否的事實,謹慎分析自己的裁決會給審查逮捕部門所帶來的消極后果。基于此,我們便能發現一些證據鏈條不甚牢固的案件也能起訴到法院,而一些本可不處以實刑的被告人還是得到了有期徒刑的最終裁斷。究其原因,不能不說是對逮捕決定給予遷就的影響。從這個層面看,構罪即捕實質上從起點上就限制了審查起訴與審判階段的裁量彈性,甚至一定程度“綁架”了刑事訴訟的整體進度。當然,這也同時加大了冤假錯案產生的風險蓋然性。
(二)歷史傳統的影響
那么,構罪即捕是傳統思維定式的產物嗎?這種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或許是成立的。在1979年2月23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逮捕拘留條例》中,明確規定了當時逮捕被追訴人的三大條件:“第一,主要犯罪事實已經查清,這就要求在逮捕人犯之前,必須做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對主要罪行取得證據,體現了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對待犯罪分子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的原則精神……”④這段立法機關的表態說明了逮捕制度在我國的建立原點,是具有顯著構罪即捕驅動的。盡管當時的逮捕條件也涵蓋了“有逮捕必要的”這一羈押必要性條件⑤,但是表述得較為籠統,加之歷經若干次“嚴打”活動,也便有名無實了。而對于罪行條件的苛求便打上了深深的歷史烙印,即便《刑事訴訟法》的兩次修改竭力清理有罪推定的舊殘余,其依然在實踐中保有旺盛的生命力。然而,盡管筆者承認這種傳統思維的存在是構罪即捕現象的產生因素之一,卻不能認同其為主要成分的結論,更不敢茍同將其作為唯一成因的推斷。畢竟,我國司法辦案人員的思想觀念不可能始終停滯不前,而全國大部分檢察機關都已經普遍實現了更新換代,經歷過構罪即捕階段的老辦案人基本所剩無幾,20世紀70年代、80年代后出生的“新一代”已然成為辦案主力軍,并不會背負太多歷史包袱。筆者通過同負責審查逮捕的一些辦案檢察官接觸,也發現他們對于逮捕措施的屬性是具有清晰認知的,并不認同將其作為一種懲罰手段置于刑事司法環境中,同時也希望非羈押措施能夠得到廣泛適用。然而,現實中出現與其上述希冀相悖的趨向,很大程度上卻帶有些無可奈何的意味。為何立法預期在殘酷的司法現實面前會舉步維艱,這種“無可奈何”又是因何產生的呢?還是需要從訴訟結構整體以及訴訟主體間的關系入手,尋找構罪即捕形成的主因。
(三)訴訟結構的影響
正如波斯納所言:“經濟學是一門關于我們這個世界的理性選擇的科學——在這個世界,資源對于人類欲望是有限的。……人在其生活目的、滿足方面是一個理性最大化者——我們將稱他為自利的。”⑥在訴訟中的各個主體其實也概莫能外。那么,我們不妨循著如下的邏輯進行推衍:構罪即捕導致逮捕的大量適用,而這樣的結果對哪些訴訟主體是最有利的,又是誰最樂于見到的呢?逮捕作為一種羈押措施,決定權與執行權被分置給了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兩個不同的公權力機關,已形成相互之間的監督、制約,避免被追訴人的人身權利受到無故剝奪。一旦檢察機關否定了公安機關的逮捕申請,后者只能退而適用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等替代性羈押措施。
對于公安機關而言,采取羈押手段無疑是風險最小而受益最大的路徑。所謂“風險最小”,取保候審意味著犯罪嫌疑人將處于人身自由狀態,管理、約束起來十分不便,潛逃風險也是客觀存在的。尤其是人口流動性增強的社會現實,使得公安機關寧肯犧牲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利益,也不敢冒風險適用取保。監視居住的強制程度盡管高于取保候審,尤其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實際上是一種近于逮捕的準羈押措施,但在公安機關看來,適用這種強制措施要耗費的人力和財力要遠勝于逮捕。我們姑且不論上述判斷的實證概率,但這確實阻礙了公安機關對替代性羈押措施的執行熱情。所謂“收益最大”,逮捕意味著犯罪嫌疑人將長期在看守所中生活,這就給隸屬體制上占據優勢的公安機關以各種便利條件。此外,看守所內充盈的犯罪線索也是公安機關繼續擴大戰果的一柄“利器”。考慮到大多數未決在押人員最終都將被認定有罪的現實,這中間必定夾雜著不少的犯罪信息或線索,尤其是一些累犯、慣犯人員,極可能自己存在尚未被偵破的罪行,還可能掌握著同伙或者其他人的犯罪信息。顯然,從這些在押人員身上去挖掘這些信息,對于偵查機關來說,是一條“低投入、高產出”的捷徑⑦。總而言之,逮捕顯然是公安機關最能欣然接受的一種強制措施,也是構罪即捕的最大受益方。
然而,逮捕的決定權畢竟掌握在檢察機關的手中,而不是作為執行者的公安機關。決定逮捕的直接受益者并不是檢察機關,不予逮捕的決定也不會給其帶來直接沖擊。換言之,構罪即捕是作為逮捕決定主體的檢察機關為執行主體之利益加以權衡的結果。為了保證執行機關的“高枕無憂”,決定主體寧愿增加自己身后的風險亦在所不惜。那對于審查逮捕部門而言,這樣處理的意圖又是什么呢?這就需要從訴訟結構的角度,審視我國獨有的訴訟主體關系。
我國的刑事司法程序在構造形式上主要突出其縱向性,以時空為單位,區分為三大階段,分屬于三個不同的專門機關。這是一種類似于線型流水作業的模式,刑事案件如同產品一般依次進入偵查、起訴、審判等三個“車間”,在經過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人民法院依各自職權“加工”處理后,再宣告終結。為了保障訴訟產品在“生產”上的順利,憲法為公檢法三方設定了“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基本關系模式。其中,“分工負責”是前提,“互相配合”是基礎,“互相制約”是核心⑧。為了避免“殘次品”的產生,三方會互相制約,而辯護人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同理。正是在上述思路的引導下,形成了我國訴訟構造的大體格局。訴訟構造的基本特點奠定了各訴訟主體之間在訴訟活動中的行為模式,尤其促使公檢法三機關在一些問題上的妥協與平衡。
以逮捕決定為例,檢察機關的審查逮捕部門當然有權否定公安機關的申請,并敦促其適用取保等非羈押措施。但是,這會給公安機關的執行帶來較大壓力,影響恐怕會波及案件“產品”順利轉入下一個階段,而該流程恰恰是檢察機關所主導的起訴階段。審查逮捕部門的“鐵面無私”換來的也許就是公訴部門的“舉步維艱”了,案件的基本證據要由公安機關提供給公訴部門,而取保候審在剩余階段的執行也有賴其保障。這樣復雜的利益格局下,互相之間達成必要的諒解與妥協,無疑有助于訴訟程序向前推進的整體大局。而起訴、審判等階段莫不受此種關系模式的影響。由此,構罪即捕的產生基礎也就不難理解了。固然檢察機關不是直接利益方,但是間接上也會受到自己決定的影響,而運轉平臺就是訴訟主體關系模式。為保障訴訟的順暢,需要不同機關之間的相互默契,這樣的關系基調恰恰是成就構罪即捕的主因。
二、構罪即捕的消極后果
我們究竟應當對構罪即捕持何種態度呢?筆者在與一些辦案人員交流的過程中,得到的反饋是認為構罪即捕并無不妥,可以準確把握案件,利于犯罪嫌疑人得到公正處理,并為隨后起訴、審判程序鋪平道路。那么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在這里,筆者有必要對羈押的基本功能做出簡單闡釋,以便衡量構罪即捕的學理價值。
(一)羈押措施的功能失效
從現有的研究以及實踐來看,羈押的目的大致可以解釋為以下幾個方面:保證被追訴人在訴訟程序中能始終到場;保全證據存在與真實;確保刑罰能夠順利執行;確保社會安全。世界各國幾乎無一例外地在刑事立法中,以上述要素作為法官裁量的依據。例如在比利時,1990年的《審前羈押法案》就為偵查法官設定了一系列的條件,作為簽發拘留令狀的參考因素:公共安全的必要性;涉案刑期一年以上;假如其涉案刑期沒有超過15年徒刑,那么令狀只能在較嚴重風險存在的前提下才被簽發,例如嫌疑人可能會再度實施嚴重犯罪或者潛逃,抑或毀滅證據,又或者與他人串通⑨。可見,除去構罪條件,羈押必要性起到的作用是絕對不容忽視的。而我國此次的《刑事訴訟法》修改,針對羈押決定權失控的現實,也特意細化了羈押的必要性條件,意圖增加該條件在批準逮捕過程中的權重⑩。此外,羈押必要性審查機制的創設,也是出于同樣之目的。這表明立法機關對于羈押的功能定位是趨向于普世價值的,而并未服從于其實際走向。因此,從羈押的功能設置角度出發,構罪即捕所產生的過度羈押后果是無法被接受的。羈押的大量產生固然增加了刑事司法質量把關的環節,但也扭曲了其本源屬性,而受犧牲的更是被追訴人個體的利益?。盡管我國的刑事訴訟結構以三階段的分工為基點,公檢法三機關作為主導力量,但并不意味著被追訴人就理所當然地處于客體地位。所謂訴訟程序之最終“產品”,指向的是案件本身,而非任何個人,被追訴人并不是這條“生產線”上的某個零部件,其具有主動參與之權利,人格亦應得到尊重和保障。
(二)刑事程序的運轉失靈
對于構罪即捕的否定并不僅僅可以從價值觀的角度入手,在現實層面所帶來的影響也絕非是積極的。檢察機關一直以“捕得準”“訴得出”“判得下”來掌握逮捕標準,但筆者在司法實務中卻經常聽到“硬訴”“硬判”等詞語,所隱藏的內涵多有些迫不得已的苦楚。以“硬訴”為例,一些案件在負責審查起訴的辦案人員看來,證據鏈體系并不是那么牢靠,案件定性或存在些許疑點。本來適合做出不起訴決定的案件,也會勉為其難地強行起訴到法院。究其原因,犯罪嫌疑人已經被逮捕,如果做出不起訴決定,審查逮捕部門之前的裁決無疑就是“錯捕”,檢察機關就需要承擔相應責任。而案件一旦訴至法院,鑒于無罪處理會給公訴部門帶來不良的后果,非監禁處理亦會導致國家賠償,法院在處置時也會充分諒解檢察機關的難處,當然前提是自己尚有從權之余地。當然,筆者并不否認構罪即捕在一些情況下對于案件質量把關的積極作用,但是訴訟進程中對于案件事實的認知本應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步深化。審查起訴的任務就是核實、完善偵查階段的證據材料,使之符合法庭審判的要求。而在此之前的逮捕環節很難起到等值效果,畢竟偵查活動尚未完成,過高的認定標準難免擠占起訴、審判環節的裁量空間,更容易扼殺公安機關完善證據體系的積極性。可以說,構罪即捕的存在對于整個訴訟進程都會產生破壞效應,造成起訴、審判環節遷就被追訴人的羈押狀態。
在現有司法環境下,由于逮捕對于偵查、起訴、審判三階段的重要意義,使其地位儼然如獨立的訴訟階段一般,而并非僅僅作為某個程序性環節。尤其對于偵查機關而言,申請批捕的過程就如同案件送交法院審判,而審查逮捕也可視作書面形式的小型審判。難怪有的辦案人員戲稱,“批捕是別人求自己,起訴是自己求別人”。這種說法十分形象地闡釋了公檢法三大訴訟主體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基本關系模式,再次驗證了我國特有訴訟構造下的扭曲狀態。故而,構罪即捕絕不是刑事司法某個環節所存在的弊端,而是整體性結構失調的一種表象,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影響能力。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在其形成的決定中提及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架構,正是決策者采取的針對性舉措。
(三)被追訴人的權利失范
在現代各國,單就等候審訊或審判的強制措施而言,剝奪人身自由只是一種例外,即使是已經被逮捕的嫌疑人也往往能夠附條件地被釋放,在基本自由的狀態下等候審判和準備辯護?。然而,我國的未決羈押人數呈現井噴之勢卻早就成為各方共識,毫無爭議。構罪即捕觀念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正是逮捕標準的人為調整進一步惡化了犯罪嫌疑人的處遇,使得未決羈押衍生為刑罰預支。顯然,這僭越了正當程序原則為每一位未決犯設定的權利邊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就曾指出:“審前羈押應是一種例外,并盡可能短暫。”?這樣的現實無疑會嚴重影響我國的司法形象,同時也造成司法資源的一種無謂浪費,消耗了太多人力、物力、財力等。但最為關鍵的,是逮捕措施的普遍化適用把多數未經定罪的公民置于險惡的環境之中,面臨身體、心理、名譽、家庭、經濟等多個維度的權利減損。在這樣的環境下,訴訟地位的失衡狀態進一步加劇,又如何能指望犯罪嫌疑人充分行使辯護權利呢?控辯平等是刑事司法程序運行的基本原則之一,考慮辯護一方處于守勢的客觀現實,長期的羈押勢必會進一步削弱被追訴人的對抗能力。不僅舉證活動會因人身受限而多有不便,在心理狀態上也會由此陷入更加消極悲觀的惡性循環。“對于一個在押人員來說,進入看守所意味著其將面臨著糟糕的近況,他必須接受與外界物理隔絕的現實,居住在自己不太適應的空間內。在警戒森嚴的監室中,他心里可能會充斥著焦慮、不安、傷感等不佳的情緒。更不幸的是,他可能已經失去了工作,對家庭的建設也難以有所作為了。他的社會生活業已破碎,在心理的重壓之下,他們日夜苦盼著得到司法官員的回應和處理。”?盡管近年,有關部門為了提升羈押場所內的人權保障水平做出了很多努力,顯現了不俗的成效。但在批捕率依然維持較高基數的前提下,很難奢望被追訴人的境遇能有本質上的改變,而構罪即捕的主導思想在其中所發揮的功能是不容低估的。
三、構罪即捕的解決對策
既然構罪即捕的消極價值已然十分明顯,那么究竟該如何破解這一司法領域的實際難題呢?筆者并不認為單純依靠立法就能解決這一頑疾,也不敢奢望觀念上的進步會迅即帶來積極的變化,改革還需要從矛盾的實質入手,即訴訟主體之間的關系。同時,進一步強化替代性羈押措施的實際利用率,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司法機關對于羈押手段的過分依賴問題。
(一)應堅持檢察機關作為審查逮捕主體的法律定位
“個別強制處分究竟應由機動性較高的偵查機關決定抑或由保障性較高的法官決定,涉及追訴權能與人權保障之間的權衡。”?因此,一些學者將構罪即捕作為反對檢察機關執掌審查逮捕權限的論據,主張將該項權能移交法院,實現西方式的司法審查機制?。的確,以國際公約設定的標準來審視我國的逮捕決定體制,法院似乎較檢察機關更符合中立第三者的角色。然而,探討中國的審查逮捕問題離不開其司法結構設定的獨特場域。中國的刑事訴訟構造下形成的主體關系不同于西方國家訴訟模式下的控辯審關系,前者突出縱向延伸,而后者著眼橫向制約。故而,單純更換審查逮捕的決定主體,只是一張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藥方”,恐怕難以標本兼治。我們不妨試想一下,倘若法院掌管逮捕決定權,是否可以真的能夠做到超然中立。法官在審查逮捕的過程中是否能夠對偵查辦案機關的傾向性訴求毫不理會呢?畢竟訴訟主體之間的關系不會因逮捕決定權的轉移而有所變化,案件若要順利進入審判階段,依然離不開公安機關的配合。在這樣的基本訴訟構造下,任何一方掌握逮捕權力都不會給刑事司法現狀帶來本質上的“化學反應”。讓法院越過檢察機關直接和公安機關產生聯系,不見得會帶來積極的響應。因而,筆者并不看好這種“變更主體”的提議。同時,對于構罪即捕問題的思考與解決,很難擺脫時下已然定型的訴訟關系模式。
憲法為公檢法機關設定的“配合制約”行為模式,是基于國家機構權力合理配置的考量,與我國的政治體制所需求的公權力布局密不可分,由此產生的訴訟構造本無可厚非?。筆者從不認為憲法的規定有失理性,其宏觀設想是具有進步性的,這一司法權力運行機制也得到了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認可,今后的訴訟模式必然不會脫離“配合制約”框架。我們需要檢討的是,在刑事訴訟這一具體部門法領域,是否缺乏對“配合制約”原則的必要解讀和細化,導致實踐中其固有瑕疵被意外放大,直至引發惡性后果。客觀地說,在當前,這樣的訴訟構造以及由此產生的關系模型既不存在調整的現實可能性,也無“傷筋動骨”的實際必要。脫離國情仿照西方國家的經驗的司法改造,只能帶來司法環境的錯亂和裂變。而破解構罪即捕難題,需要在訴訟主體關系中尋找適宜的切入點,通過某個基點的倒逼激活全局性的良性變化。
(二)進一步擴大羈押替代措施的適用范疇
其實,無論是學術界抑或實務領域,很多人都寄希望于擴大替代羈押措施的適用范疇,特別是激活取保候審,以化解逮捕率畸高所引發的一系列危機?。然而,單從立法條文的字面解釋出發,取保候審的操作空間似乎從來就不應面臨狹窄的窘境。那么,司法實踐中之所以會成為次要選擇,就只能從辦案人員的主觀裁量層面尋找原因了。就筆者了解,司法辦案人員尤其是主導偵查活動的公安機關,對于取保候審總是擔憂大過信任。強制措施的目標在于確保犯罪嫌疑人始終處于可控制的范疇內,或松或緊,而取保候審與逮捕恰好處在這兩個極端上。取保候審雖然給予了犯罪嫌疑人最大的人身自由限度,卻也蘊藏著脫離管控的風險,而這又是辦案人員所竭力避免發生的現象。從自身的便利角度出發,與其提升取保候審的適用效果,倒不如通過逮捕措施將被追訴人始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徹底消滅阻礙訴訟進行的脫逃蓋然性。
然而,適用非羈押措施是否真的會給公安機關帶來如此多的不便呢?這是一個需要認真核定的命題。筆者倒是覺得,在看守所的羈押是一種更為耗費人力和財力的強制措施。大量在押人員使公安監管部門殫精竭慮,生怕自己轄區內發生責任事故,只能依靠資源的大量投入去降低監管風險?。這樣的人力物力投入對于公安機關而言,難道就一定會低于取保候審等非羈押措施的投入嗎?難道就不如后者帶來的麻煩更多嗎?
因而,關鍵是針對非羈押措施的具體執行方式,公安機關尚未意識到技術進步會帶來的巨大便捷,依然顧忌犯罪嫌疑人的潛逃風險,不得不倚重人力。新《刑事訴訟法》提出了電子監控這一監督手段,但顯然公安機關并未給予必要的重視。西方法治國家在保釋制度的應用過程中,廣泛采用電子腕帶等技術措施以監督恢復自由身的犯罪嫌疑人及時應訴?。一旦犯罪嫌疑人逾越了設定的地理范圍,電子腕帶就會及時報警。同時,犯罪嫌疑人亦被定位,無法脫離監控系統的追查,私自拆除腕帶更不存在技術可能性。筆者相信此類技術的開發對我國而言,并非難于“上青天”。實際上,目前一些地區的看守所已經出現了這類電子腕帶。與其投入巨資開發看守所的安保系統,倒不如用心于替代羈押措施的技術攻關,或可收獲更大的“成本—收益”比值。總之,逮捕措施的執行效益優于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非羈押措施,是一個需要糾正的偽命題。
當然,青睞未決羈押的另一個心理誘因往往是以捕代偵,更是一種扭曲的錯誤傾向?。但無論如何,公安機關對于逮捕措施具有較強的依賴性,是不爭的事實。要消除構罪即捕帶來的陰影,就必須從打破這種依賴性開端。當公安機關喪失了惰性,重新認識了逮捕措施的價值,檢察機關審查逮捕也就不必為其“埋單”了。當然,筆者認為這需要一種強勢干預。而時下適宜的干預手段,無疑是考核指標的科學化調整。眾所周知,其對司法機關日常辦案具有“指揮棒”效應。因此,可以考慮通過由中立成員組成的考評委員會,根據各地案件類型分布,設定本地每年適用逮捕措施的上限,以硬性指標的形式控制羈押總數。以檢察機關工作機制的完善倒逼公安機關的執法規范化,為使前者適應新的考核體系,就必須達成默契,借助技術進步廣泛采取替代羈押措施降低羈押量。相信這一變化會誘發新一輪的“蝴蝶效應”,打破逮捕對審查起訴、審判活動的原有束縛,刺激刑事程序整體性回歸應然狀態,消除構罪即捕的生存因子。當然,這種設想需要以充分實證調研為前提,也離不開各地司法機關對自身羈押必要性趨向有更清晰的判斷。
(三)加快審查逮捕訴訟化改造的步伐
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為逮捕的審查活動增設了訊問這一必要環節,同時為辯護律師提供意見創設了渠道,在相當程度上推進了逮捕程序的準司法化改造?。從屬性上分析,逮捕決定應當近似于司法裁斷權。因而,上述新增內容有助于決定批捕之檢察官傾聽各方意見,從而做出更為中立的決定。但是,這種程序設計并不等同于以“等腰三角形”為特征的司法構造,現有的批準逮捕仍舊帶有顯著的行政化特征?。換言之,現有的訴訟化因素尚難以徹底扭轉辦案人員內心的構罪即捕傾向。與犯罪嫌疑人及辯護律師相比,公安機關顯然與檢察機關有著更為緊密的關系。置于中立、無偏私的地位,才能確保不因訴訟主體之間的特殊關聯而有所遷就。否則,即便在形式上實現了訴訟化改造,依然可能徒有其表,令辯護方的抗辯權能無從發揮。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盡管審查逮捕的程序機制構建正朝著司法化趨勢發展,卻仍不免停留在“紙上談兵”的尷尬境地,而并沒有充分展現出具有實質價值的個體互動。為此,只有進一步提升逮捕程序的訴訟化成分,以聽證的形式削弱構罪即捕的心理偏差。如果在這樣一個本應體現互動對抗的訴訟格局中,缺失了辯護人、被害人的有效參與,而檢察機關又怠于引導的話,正當程序價值的實現便難脫“空中樓閣”之命數。當辯護律師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權利,充分運用證據材料、法律知識與公安機關代表進行現場對抗時,逮捕決定的秘密性特征就將被打破,羈押必要性條件也會取代夠罪指標成為主導變量。此外,人民監督員的必要介入,也能有效阻止檢察官導向偵控一方,而堅守住自己的中立底線。如此一來,不同的訴訟機制之間就能形成有效的“串并聯”,引發訴訟全局的良性循環。當然,從行政化的審查逮捕機制轉型至司法化程序不可能一蹴而就,檢察官自身首先要適應從控訴者向裁決者的心理角色轉換?。當辦案檢察官在審查批捕之時,能夠更多地聽取辯護人一方的意見,就表明訴訟平等原則已然在審前階段日趨強化的勢頭。同時,構罪即捕觀念的消極影響就會受到有力的遏制,未決羈押真正地開始步入“備而不用”的理性狀態,而不再成為訴訟進程中的必經階段。
總之,構罪即捕現象的產生,在中國的語境下具有深刻的歷史及社會淵源,并且經過長期的浸淫化入檢察機關的辦案習慣。從應然角度出發,任何人都不可否定這一現象的非合理性。然而,徹底改觀構罪即捕的思維程式也絕非一件輕松的任務。單靠立法文本的循序改善,尚不足以產生立竿見影之成效,必定有賴于司法環節的日臻進化。而對其形成根源的想當然,不僅難以促成羈押控制的預期實現,倒容易造就適得其反的窘迫結局。真正有效的紓困路徑,必然建立于針對構罪即捕的理性認知之上,從而打造出符合中國實際及正義價值的羈押裁決機制。
注釋:
①謝佑平:《刑事程序法哲學》,中國檢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頁。
②吳瑋:《確保捕得準訴得出判得下》,《檢察日報》2010年7月30日。
③漢斯.J.沃爾夫等:《行政法》(第1卷),高家偉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360—361頁。
④趙蒼璧關于修改《逮捕拘留條例》的說明,載法學教材編輯部:《法學概論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582頁。
⑤對于這一條件,立法機關當時解釋:“如果介于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也不應逮捕,這是我國多年來實踐證明的一條好經驗”。趙蒼璧關于修改《逮捕拘留條例》的說明,載法學教材編輯部:《法學概論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582頁。
⑥[美]理查德.A.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蔣兆康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3年版,第3頁。
⑦李衛平、胡建華:《加強認識改進措施,做好看守所深挖犯罪工作》,《公安研究》2003年第3期。
⑧韓大元主編:《中國檢察制度憲法基礎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5頁。
⑨ED Cape,TaruSpronken,Jacqueline Hodgson,Ties Prakken,Suspects in Europe,Procedural Rights at the Investigative Stage of the Criminal Process in the European Union,Intersentia Antwerpen Oxford,2007,pp36,159.
⑩陳衛東主編:《2012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頁。
?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頁。
?孫長永:《偵查程序與人權:比較法考察》,中國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5頁。
?陳光中、[加]丹尼爾·普瑞方廷:《聯合國刑事司法準則與中國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頁。
? Patricia Wald,Pretrial Detention and Ultimate Freedom:A Statistical Study,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ume 39,1964.
?林鈺雄:《刑事法理論與實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頁。
?陳衛東主編:《刑事審前程序與人權保障》,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頁。
?韓大元:《憲法學基礎理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16頁。
?王貞會:《羈押替代性措施改革與完善》,中國人民公安大學2013年版,第9頁。
?例如,“躲貓貓”事件發生后僅一年,全國就有26個省級公安機關與財政部門重新核定了看守所在押人員伙食金額標準,月人均伙食費標準平均提高了35元;全國看守所新增警力8052名,新增文職雇員2421名,254個看守所提升了機構職級;1028個看守所新增或升級改造了監控,330個看守所增加了囚車,94個看守所增加了電網,104個看守所增加了信息系統。孫皓:《看守所規范化研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2013年博士畢業論文。
? NogaShalev,Mary Ann Chiasson,Jay F.Dobkin,Gunjeong Lee,Characterizing Medical Providers for Jail Inmates in New York State.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April 2001Vol.101,No4.
?孫謙:《逮捕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頁。
?張軍主編:《刑事訴訟法新制度講義》,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07頁。
?陳瑞華:《問題與主義之間——刑事訴訟基本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頁。
?卞建林:《刑訴法學如何回應法治時代新需求》,《檢察日報》2011年12月29日,第3版。
2015-08-10
韓東,男,河北安新人,中國政法大學證據科學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天津市河北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