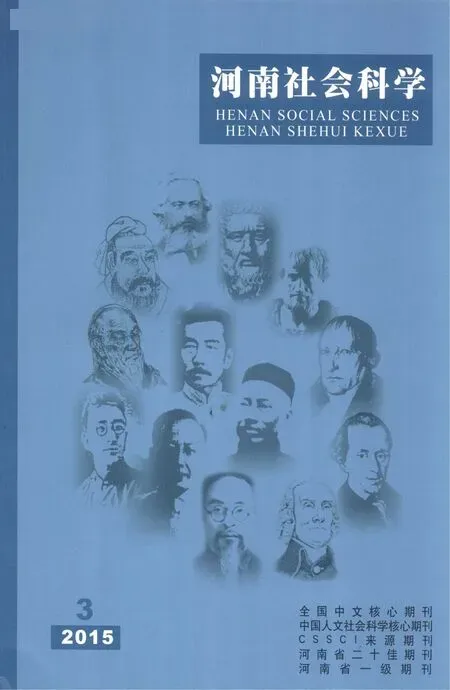盲人摸象與反本質論美學——認知美學的盲人摸象
張玉能,張 弓
(1.華中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2.華東政法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 201620)
盲人摸象的寓言昭示我們,人們的認識不能離開對對象的本質和整體的把握,也不能僅僅依靠感性認識。認知美學的反本質論,否認美的本質問題,實質上就是在盲人摸象。認知美學所把握的美的對象,離開了美的本質和美的整體,產生了種種錯覺。認知美學把美的生成看作“知覺模式”的結果,實質上就是在沒有美的本質和美的整體的情況下,把美(美的對象)當作了美學盲人的感覺的復合,是一種典型的唯心主義經驗論美學,無法還原美的本體。
一、盲人摸象的啟示
盲人摸象,又稱瞎子摸象,源于印度佛教的一個寓言故事。《大涅槃經》(卷三十二)載:“有王告大臣,汝牽一象來示盲者時,眾盲各以手觸。大王喚眾盲問之:汝見象類何物?觸其牙者言:象形如蘆菔根;觸其耳者言如箕;觸其腳者言如臼;觸其脊者言如床;觸其腹者言如甕;觸其尾者言如繩。……王喻如來正偏知,臣喻方等涅槃經,又象喻佛性,盲者喻一切眾生無明也。”《長阿含經·卷十九·龍鳥品》《百喻經》《菩薩處胎經》亦載有這個故事:印度古代有一個國王,叫一位大臣牽來一頭大象,讓幾個盲人用手摸。國王把幾個盲人招來問他們:你們見到的大象像什么東西?摸到了大象牙齒的盲人說:“大象就像一根大蘿卜。”摸到大象耳朵的盲人說:“大象像一個簸箕。”摸到大象腿的盲人說:“大象像一個杵臼。”摸到大象脊背的盲人說:“大象就像一張床。”摸到大象腹部的盲人說:“大象就像一口大壇子。”摸到大象尾巴的盲人說:“大象只不過是一根草繩。”六個盲人爭吵不休,都說自己摸到的才是真正大象的樣子。而實際上呢?他們一個也沒說對[1]。在這個寓言中,國王比喻如來佛糾正片面的知識,大臣比喻《大涅槃經》或者佛性,幾個盲人比喻所有的沒有正確知識的蕓蕓眾生。
盲人摸象的寓言昭示我們,人們的認識不能離開對對象的本質和整體的把握,也不能僅僅依靠感性認識。也就是說,一個人要把握對象、獲得真知,就必須從整體上把握對象,不能只把握對象的某一部分就得出結論,以偏概全。同時,人們也不能僅僅相信自己感覺器官的感知,還必須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運用思維,透過現象把握對象的本質;如果人們對于對象的本質沒有最起碼的了解和理解,就不可能把握對象的真實面目,不可能獲得全面的、整體的、本真的知識。
人們之所以要把感性認識在實踐中發展成為知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就是因為感性認識是一種片面的、不完整的認識,盲人摸象中每一個盲人所得到的認識就是感性認識,而且是一種單憑觸覺得來的認識。因此,人們的感性認識是人們通過感覺器官獲得的關于對象事物的個別的、外在的、直接印象的認識。人們的知性認識是由感性認識抽象、概括出來的,是對對象事物的本質的抽象和概括;它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所謂的“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的認識或者知識,反映了對象事物的內在的、固有的、區別于其他事物的性質。人們的理性認識則是感性認識與知性認識的統一,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所謂的“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2],對對象事物的全面的、完整的、辯證的認識或者知識。因此,關于事物的本質的研究是一種知性認識的抽象過程,往往表現為關于事物的概念、判斷、推理的形式。那么,在人的認識過程中,知性認識往往可能以一些概念、判斷、推理的形式,范導和規范著人的感性認識,二者的結合才可能得出真正的、全面的、具體的、完整的理性認識或者知識。盲人摸象中的那些盲人,之所以把大象判定為大蘿卜、簸箕、大床、壇子、繩子等,就是因為他們的意識之中只有一些具體的感性認識,而沒有比較抽象的知性認識,也就是沒有關于大象的“本質”的認識或者知識,所以他們就僅僅停留在感性認識的階段上,做出了錯誤的判斷。如果他們能夠通過書本或者他人傳授而獲得一定的關于大象的知性認識或者知識,比如,“大象是一種大型動物”或者“大象是一種大型哺乳動物”之類的認識或者知識,他們的判斷就不會錯得那樣離譜。所以,在認識過程中,知性認識或者知識對于認識或者知識的形成是具有范導和規范作用的。因此,人們對于某一事物對象的本質了解得越多、越準確,那么他們對這個事物對象的認識也就會越明確、越全面、越完整、越具體,也就可能得到比較正確的理性認識或者知識。
另一方面,人的認識不能僅僅靠感覺器官,還必須經過思維的知性認識和理性認識,才可能獲得完全的、全面的、本質的、內在聯系的認識或者知識。在這個從感性認識經過知性認識達到理性認識的過程中,人們已有的知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對于感性認識具有范導和規范作用;在實踐過程中,人們的感性認識在已有的知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范導和規范下,才能獲得新的知性認識和理性認識;新的知性認識或者知識就是對對象事物的概念、判斷、推理,它是抽象的、本質的、內在的聯系的認識或者知識,然而,仍然具有某些片面性,需要進一步在實踐中達到全面的、整體的、具體的新的理性認識或者知識,這樣才算完成了一次真正的、完全的認識過程,當然還得接受實踐的檢驗。因此,如果那幾個盲人,能夠在一定的知性認識的啟示或者提示下,再結合自己的感性認識,并且能夠綜合大家的感性認識,也許就可以得出一個比較接近對象事物的認識,比如,大象是長著大蘿卜似的牙齒、簸箕似的耳朵、壇子似的肚子、大床似的脊背、杵臼似的腿、繩子似的尾巴的動物或者哺乳動物。所以,關于對象事物的本質的知性認識或者知識,在一次比較完全的認識過程中,是具有決定性的范導和規定作用的,因而是任何認識活動所不可或缺的。缺乏了關于對對象事物的本質的知性認識或者知識的范導和規定作用,就必然會導致盲人摸象的結果。認知美學就是如此。
過去,我們的哲學認識論和認知心理學,僅僅把人的認識過程及其階段劃分為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兩部分,而且把人的認識過程視為一個單純的現在進行時和主體在場的活動過程,忽略了人們的潛意識和無意識中積淀的感性認識和知性認識的知識。比如,同樣是盲人摸象,一個盲人摸到象牙說是“大蘿卜”,另一個盲人說是“棒子”;同樣是摸到象耳,一個說是“簸箕”,另一個說是“蒲扇”;同樣是摸到象腿,一個說是“杵臼”,另一個說是“柱子”;同樣是摸到象肚,一個說是“壇子”,另一個說是“墻壁”;同樣是摸到象的脊背,一個說是“大床”,另一個說是“氈子”;同樣是摸到象尾,一個說是“繩子”,另一個說是“蛇”,諸如此類的不同感知和判斷,在“盲人摸象”的不同版本中都顯現出來了。這些都說明,人的認識,既不是單純的感性認識,也不是單純的知性認識,還必須形成結合感性認識和知性認識的理性認識。只有在關于對象事物的本質的知性認識的范導和規范下,人們的感性認識才可能接近于對象事物本身,也才可能進一步在實踐中結合感性認識和知性認識而達到理性認識,從而形成關于對象事物的完整的、具體的、全面的認識和知識。也就是說,我們既不能像盲人摸象那樣得出片面的、以偏概全的感性認識,也不能僅僅獲得大象的抽象本質的概念、判斷、推理之類的知性知識,而應該在這種關于大象本質的知性知識的范導和規范作用下,獲得大象的全面的、整體的、本質的、完整的、具體的認識或者知識。這種三分法的認識論,在德國古典哲學中已經形成,而在馬克思的實踐唯物主義哲學中已經廣泛應用到政治經濟學、哲學、美學、科學社會主義的研究之中,然而,我們的哲學認識論至今還沒有接受。在美學中,認知美學還在普及這樣片面的認識論。
認知美學的代表人物李志宏先生指出:“我們須借此機會普及一下認識論的知識:在科學認識論中,認識分為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兩大階段;感性認識是認識的初始階段,是對事物表面現象和外部聯系的反映;理性認識是認識的高級階段,是對事物本質和內在聯系的把握;人的認識總是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因此,說人對世界的感性體驗早于理性的活動,是非常正確的;但是,感性體驗也是認識的一種形式、一種表現、一個階段。人類的發展進步正表現在由對世界的感性體驗上升到對世界的理性認識;絕不能以為,只有理性認識才是認識,感性認識及直覺體驗就在認識活動之外。同時,審美判斷中也可以包含深刻的理性認識,不能以為審美都是淺薄的、非理性的自我感覺。”[3]李先生以這種簡化版的“科學認識論”來研究美和審美及其藝術,就必然會重蹈盲人摸象的覆轍。
二、認知美學的反本質論
認知美學的反本質論,否認美的本質問題,實質上就是盲人摸象。認知美學所把握的美的對象,離開了美的本質和美的整體,產生了種種錯覺。
席勒在《論美書簡》第一封信中開宗明義地指明:“對美學任何部分幾乎都不可缺少的美進行研究,會把我引向非常廣闊的領域,那里有我還完全陌生的領域。但是,為了作出某種令人滿意的結論,我必須把握住整體。客觀地提出美的概念并從理性的本性出發完全先驗地證明它——以致經驗雖然證實著它,但是它完全不需要經驗對它的有效性的這種證實——這種困難幾乎是不可克服的。老實說,我曾經試圖用演繹法來推論我的美的概念,但是沒有經驗的證明,它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樣的困難也始終存在:我的解釋之所以被接受,只是由于人們發現,它與審美趣味的單個判斷相一致,而(大概在認識終究必定是來自客觀原則的情況下)人們之所以認為自己對經驗中個別美的事物的判斷是正確的,卻不是因為這個判斷同我的解釋相符合。你會說,這樣論述意味著要求過多的東西;但是,當我們還達不到這一點時,審美趣味就永遠——康德還認為這是必然的——仍然是經驗的。然而,我還不能深信不疑地認為,這種經驗的審美趣味是必然的,而為審美趣味尋找客觀原則是不可能的。”[4]席勒在這里所說的研究美的概念和美的本質問題,確實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關系到整個美學研究的問題,可以說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是一個不能僅僅依靠感性經驗來證實的問題。因此,席勒強調:“為了作出某種令人滿意的結論,我必須把握住整體。客觀地提出美的概念并從理性的本性出發完全先驗地證明它。”[4]
其實,美學中的一切重大問題都必然歸源到美的概念或美的本質這個核心問題。任何一個美學體系都必須首先大致確定美的概念或美的本質,在此基礎上才可能逐一解決其他的所有重大美學問題。像席勒的人性美學體系認為美是客觀的屬性,“美是現象中的自由”“美是活的形象”;那么,美感就是對美的主觀反映、主觀接受、主觀創造;藝術就是對客觀現實中的事物的“摹仿”,是一種“外觀”,外觀形式的創造、外觀形象的顯現。像康德的先驗唯心主義美學體系認為美是主觀的屬性,“美是形式的主觀合目的性”“美是道德的象征”“美是知性與想象力的和諧心意狀態”;那么“審美判斷”(美感)就是無功利的愉快感、無概念的普遍有效的和必然的愉快感、無目的的合目的的快感;崇高就更加是“無形式的主觀感受”或者“感性的壓抑所提升的理性”,崇高感就是知性借助于想象力的飛翔;藝術就是“自由的游戲”“藝術是天才的自我表現”“天才的獨特創造”“天才為自然所定的法則”。像馬克思的實踐唯物主義美學體系認為美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那么美感就是“人在他所創造的對象實踐中直觀到自身”的愉悅,藝術就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一種審美精神生產、一種實踐—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由此可見,確定美的概念或者研究美的本質,不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不一定就必然導致形而上學的本質主義,關鍵在于,所謂形而上學的本質主義(本質論)是把美的概念或美的本質看作是一成不變的、先驗存在的、獨立自足的實體存在或者實體性質。反本質論的美學,否定任何探討美的本質問題的理論,實際上就是否定了人類知性認識的范導和規定作用,必然陷入盲人摸象的狀態之中。
分清對象的現象和本質,透過現象把握對象的本質,是人類理性的認知方式,也是人類不同于其他普通動物的根本標志之一。人類的認識過程必須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透過現象達到本質,因此人類認識的這種由現象達到本質的必然趨勢和結果,不是形而上學和本質主義,是美學研究的根本途徑。眾所周知,狗的嗅覺、鷹的視覺、兔的聽覺都遠遠超過人,然而,狗、鷹、兔在嗅覺、視覺、聽覺上的靈敏,都是自然本能的表現,它們并不知道事物的氣味、形狀、聲音等屬性與對象的內在聯系和本質關聯,它們不可能認識對象的本質和本質屬性。正因為如此,普通動物的敏銳感覺就只能停留在感性認識層面上,不可能上升為知性認識和理性認識,更不能升華為審美感受和藝術感受。它們就只能像先天的盲人那樣,只具有一些由本能的感覺得來的感性認識,而不可能把握對象世界的本質聯系、本質結構、本質表現,它們只是運用非理性的無條件反射的生物性活動獲得的感覺、知覺來滿足它們的功利性需要,保持它們自己的生存。人類就完全不同了,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既可以由感性認識經過知性認識達到理性認識,又可以在知性認識或者知識的范導和規范下更深刻地感知對象世界,把握對象世界和對象事物的整體。與此同時,人們還可以通過反反復復的社會實踐,把感覺器官轉化為審美器官,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在關于美和藝術的本質的知性認識或者知識的范導和規范下,更加深刻地感受美和藝術的對象,更加全面、整體、具體地掌握對象世界。因此,真正的美學研究必須研究美的概念或美的本質這個核心、關鍵、根本的問題,哪怕美的本質問題不可能一勞永逸、一錘定音地最終解決,也必須在總體上有一個大致明晰的美的概念、美的本質的觀點。比如,美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美是預存的還是生成的,美是實體存在還是關系存在,美是主觀意識還是客觀屬性等,否則,沒有美的概念、美的本質和美的整體觀念的美學研究就會成為空中樓閣或者水中浮萍,就只能是一種盲人摸象。席勒在1793年的美學研究中對此就有清醒認識,值得我們借鑒。我們絕對不能像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反本質主義和拒斥形而上學的美學研究那樣,抽掉了關于美的本質的知性認識或者知識,在那里重復盲人摸象。
三、認知美學在盲人摸象
認知美學的盲人摸象,首先表現在只承認美存在,而不承認“美的本質”的存在。認知美學者認為:“從科學的、邏輯的觀點看問題,如果世上存有美本身、美本質,那就應該是個實際的存在物,即美事物;‘美’字則是語言符號,是個概念,不是事物本身。事實是,美本質即美事物的存在只是意念中的,不能在實際生活中被證明;美概念的存在才是確實的。而以美概念的存在來表明美本質即美事物的存在又是沒有理由的。因為,美概念與美事物之間的對應聯系也是意念中的,不能在實際生活中構成能指和所指之間的對應關系。從審美實踐活動中的實際作用看,當人們在名詞的意義上使用美概念即‘美’字時,‘美’字實際上具有代名詞的功能。例如,當說‘創造美’、‘欣賞美’、‘生活中存有美’時,這里的‘美’字是在分別地指代美的事物、審美價值等等,‘美’字作為能指沒有獨自的所指物,因此不是合法的名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美’字或美概念是‘虛假的名詞’;并不是在語法的意義上將‘虛假的名詞’當做同‘一般名詞’、‘抽象名詞’、‘集合名詞’相并列的一個種類。”[5]認知美學家就像摸象的盲人一樣,只相信自己的感覺和知覺,凡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對于他們就是不存在的。對于他們來說,美本身、美本質就是一種“實際的存在物,即美事物”,把“美”“美的本質”看作一個實體存在才是一種真正的“形而上學”。只相信自己的感覺和知覺的認識論,是一種極端的片面經驗主義認識論,其典型的表現就是英國大主教貝克萊所謂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不能被感知的東西就是不存在的。所以,認知美學者就跟著西方傳統形而上學走到了片面經驗主義認識論的死胡同里。不僅如此,他還沿著這條路,比分析哲學的邏輯原子主義(羅素、早期維特根斯坦)和邏輯實證主義(卡爾納普)走得更遠,撈不到水中的月亮,就連月亮本身都否認了。早期的維特根斯坦秉承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和美學傳統以及摩爾的思路,對哲學問題進行“語言分析”,劃分出了所謂的“可言說的”和“不可以說的”,認為美學問題和倫理學問題或者“美”和“善”的問題,都是不可言說的、形而上學的、非科學的、神秘的問題,要求對此保持沉默。后來的一些絕對科學主義的分析哲學家和分析美學家就接過維特根斯坦的這種對“美”和“善”的懷疑,進一步擴大為所謂“反本質主義”,認為除了可以用經驗科學證實或者證偽的問題,一切形而上的“本質”“美的本質”問題,都是假問題,“事物的本質”和“美的本質”都是不存在的,“美是什么”就是偽命題。認知美學現在所說的和所做的,就是拾反本質主義之牙慧。可是,他們沒有想到,晚期維特根斯坦還是想關注“美是什么”之類的神秘問題、形而上的問題,提出了一個“家族相似”把西方傳統形而上學的“實體”本質論,轉換為“開放性”本質觀,于是分析美學家們,如比爾斯利等人仍然在探討“藝術是什么”之類的形而上問題;所以有人把早期維特根斯坦的美學思想叫作“解構的分析美學”,而把晚期維特根斯坦的美學思想叫作“建構的分析美學”[6]。認知美學代表人物李志宏先生把“解構的分析美學”奉為圭臬,置“建構的分析美學”于不顧,甚至批判“建構的分析美學”“不徹底”,而唯有他的認知美學才“徹底地”否認了美的本質問題,倒退到了西方近代認識論美學泥淖不能自拔,成為鴕鳥式的“盲人”,露出了認知美學的反本質論的“知覺模型”的丑陋之處。
認知美學把美的生成看作是知覺模型的結果,實質上就是在沒有美的本質和美的整體的情況下,把美(美的對象)當作了美學盲人的感覺的復合,是一種典型的唯心主義經驗論美學,無法還原美的本體。
單從李先生的論證過程來看,他就像“盲人摸象”那樣把事物割裂得七零八落,不成整體,而且把事物的“美”或者“美的事物”的形成歸原為人類的“形式”概念所形成的所謂“知覺模式”。他說:“事物與其外形在物理學的意義上是絕不可能分開的。事物是指事物本身,同事物內在的利害價值緊密相連;事物形式是指事物的外在表現。形式本不具有利害價值;但任何一個具有一定利害價值的自然物體,都有外在表現形式,外形就成為事物的信號,即成為事物內在利害價值的信號。于是,對事物外形的知覺就在知覺結構中刻畫出與具體外形和一定情緒相聯系的知覺模式。例如,人一看到野兔會感到興奮,一看到虎豹會感到恐懼。但早期人類只有初步的主客二分認識能力,雖然能把自己與外在事物區分開來,但還沒有‘形式’概念,不能把事物與其外形區分開來,也不能把自己的內在需求同知覺區分開來。這就使得人在對事物加以把握時,總是同自己的生存需要相關聯,情緒直接地被事物的利害價值所引發,事物外形是事物利害價值與功利需求之間相聯系的中介,不能獨立地、直接地引發情緒。”[3]稍有一點哲學史和美學史知識的人都知道,李先生的這種說法其實是重復了別人的話,一切主觀唯心主義者都是這樣看待事物的性質和狀態的生成。英國哲學家貝克萊說“存在就是被感知”,康德說“美是形式的主觀合目的性”,貝爾說“美是有意味的形式”,立普斯說“美是移情”,布洛說“美是距離”……把事物的美或者美的事物歸根到人的主觀意識或者主觀心理,就是一種以主觀意識或主觀心理來決定事物的存在及其性質狀態的主觀唯心主義美學,不論這種主觀意識或主觀心理是“知覺”還是“知覺模型”,或者是“形式感”,抑或是“感情”和“距離感”(無功利感),它們都沒有本質區別。李先生認為對象事物的美是由人的“主觀認識”決定的,但他卻還是要把審美客體的存在及其性質狀態與主觀意識或主觀心理中的過程魔幻地轉換到客體對象之上。他說:“事物與其外形的分離,只能在意識中得以實現。只有人類思維具備的抽象能力才可以把事物及其外形抽象地分離開來。抽象思維能力的發展是一個過程。在長期的實踐活動中,思維的抽象能力不斷提高,終于由不完全的抽象達到了完全的抽象,這時才可以將事物本身與其外形徹底地區分開來,形成‘內容’與‘形式’的概念。這時的主客二分,有了更深層次的表現,不僅是一般的主體與客體相對立,還實現了主體與客體各自的深層分化,即主體內在功利需要同客體功利價值相對立,主體知覺與客體形式相對立。只有達到這種深層的主客二分,人才能在沒有功利性需求的狀態下,超出客體實用功利價值而對事物形式加以相對獨立的知覺,并由形式知覺而形成愉悅快感,也就是美感。人類審美活動就是這樣發生的。”[7]這里的錯誤和混亂是十分明顯的。難道人們在審美過程中,首先要把對象事物的內容與形式抽象地分開嗎?事物的內容與形式的分開就是主體與客體的深層次的“二分”嗎?“主體內在功利需要同客體功利價值相對立,主體知覺與客體形式相對立”,這樣的“主客二分”就可以產生美嗎?就能把普通事物轉變成美的事物嗎?如果把普通事物“看成了美的事物”,它就是美的事物了嗎?這違背了常識、違背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哲學基本原理。
李先生堅持盲人摸象,最近他還說:“認知美學認為,所有‘美的事物’的共同性僅僅在于人們都能對這些事物產生美感,表現出的是人在感覺方面的共同性,而不是事物構成屬性方面的‘共相’。因此,決定事物美不美的關鍵因素在人的認知活動中,是人把普通事物看成‘美的事物’,事物的功利價值決定事物的審美價值。認知不是決定‘美的事物’作為事物的存在,而是決定已經存在的事物是不是美的。認知美學對審美認知活動內在機理的闡釋明白易懂;同時,這些論點是西方學者所不曾說過的,因此遠遠不是‘跟著西方分析哲學和美學亦步亦趨’。”[8]這種“明白易懂”的認知美學,否定了美感的客觀根據,實實在在就是一種主觀意識決定論。那么,為什么西湖是美的,而臭水坑卻不美而丑呢?用各個不同的“認知”來決定“美的事物”,其結果就只能是盲人摸象,每一個人摸到什么就算什么,不可能有什么“共相美”或者“共同美”。然而,共相美或者共同美卻是確實存在著的。如果說由于人的“知覺模式”的相同而決定了對象的美,那么為什么世界上的美又是那么多種多樣、形形色色、不可窮盡呢?因此,認知美學的反本質論美學,在本體論上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在認識論上是片面的先驗論的,在方法論上是形而上學的;從總體上來看,也就是跟著西方近代認識論美學中的主觀唯心主義美學亦步亦趨的。休謨說:美就是快感。李先生說:美感就是美。康德說:美是知性與想象力的和諧心意狀態。李先生說:美是人的認知活動決定的,是人把普通事物看成“美的事物”。可是,李先生又說:事物的功利價值決定事物的審美價值。那么“事物的功利價值”不是一種“關系屬性”嗎?然而,事物的美的屬性恰恰是在實踐中對“事物的功利價值”的超越,這已經是人們的共識和美學的基本常識。由此可見,李先生是盲人摸象中的固執的“盲人”。他先是跟著西方分析美學“亦步亦趨”否認美的本質問題,接著就倒退到西方近代認識論美學跟著主觀唯心主義美學“亦步亦趨”了。這個認知美學的“盲人”,沒有了自己的哲學根基,就只能跟著別人“亦步亦趨”,還完全不知自己的“明白易懂”的認知美學原來是拾人牙慧而已。
[1]楊任之,周行健.簡明典故辭典[Z].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
[2]中國作家協會,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3]李志宏,滕銳.難以否認的美學倒退走向——對實踐存在論美學自我辯解的評析[J].文藝爭鳴,2013,(9):22—26.
[4][德]席勒.席勒美學文集[M].張玉能,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5]李志宏,張紅梅.根源性美學歧誤匡正:“美”字不是“美”——兼向張玉能先生及實踐美學譜系請教[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5):42—48.
[6]劉悅迪.分析美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7]李志宏,劉洋.認識論和“主客二分”何錯之有?——兼論實踐存在論美學的倒退[J].文藝爭鳴,2013,(5):37—43.
[8]李志宏.在“美的事物”中尋找“美”如同水中撈月——與張玉能、張弓二先生商榷[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02-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