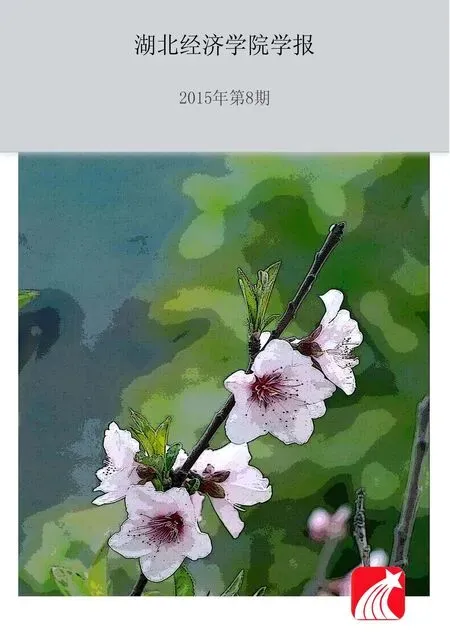我國農村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的優勢互補分析
中國共產黨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以“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為總題,提出“開展形式多樣的基層民主協商,推進基層協商制度化”。農村協商民主建設是基層協商制度化的一個重要工作,展開農村協商民主制度建設,不能忽視農村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如何協調與配合的問題。本文認為,農村選舉民主是存量民主,農村協商民主是增量民主,二者之間的共存不是零和博弈,二者之間需要協調配合,優勢互補,有機統一,形成合力,共同促進我國協商民主政治的建設。
一、當前我國農村選舉民主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1998年11月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村委會組織法》,規定村民自治要通過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來實現。從此以后,選舉民主成為村民自治的重要內容,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各省制定頒布的《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確立了普選原則、平等選舉權原則、直接選舉原則、差額選舉原則、競爭選舉原則和秘密投票原則。農村選舉民主使農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熱情高漲,廣大農民法治素質有了新的提高,“通過選舉,將那些群眾真正用擁護的思想好、作風正、有文化、有本領,真心實意為群眾辦事的人選進村委會班子,” [1]農村基層干部結構有了新的改善。然而,選舉民主也有許多無法兼顧的地方,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我國農村政治的發展路徑在當前遇到了嚴重的體制性和機制性瓶頸,這使我們必須正視農村選舉民主存在的一些問題。
(一)選舉過程賄選現象屢禁不絕
我國農村地區基層民主選舉中,賄選現象較為突出,而且賄選手段趨向隱蔽化,出現了“界定難、取證難、處理難”等問題。常見的現象是一些候選人利用親朋好友出面,選舉前先口頭協議賄賂方式和數額,待選舉成功后再實施兌現。這不僅影響到選舉的公正性、而且也影響到村委會日后開展各項工作的權威性。
(二)當選的村干部職務犯罪驚人
2013年,最高檢反貪污賄賂總局曾對2013年1~9月全國涉農案件進行統計,發現2013年以來涉案超千萬村干部案共12起,總額達22億,其中征地款成為村官貪腐的“重災區”。例如,深圳龍崗南聯村主任周偉思,坐擁20億資產,僅在當地舊城改造項目中就收受逾5000萬巨額賄賂;在沿海和內地發達地區一些富裕農村,村干部腐敗案件涉案金額更是驚人。上述村官腐敗案,讓人們震撼于村官強大的腐敗潛能。
(三)村兩委關系和鄉村關系的體制性難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
村兩委關系是指村民委員會和村黨支部之間存在的二元權力結構關系。村委會由村民選舉產生,村黨支部成員是由鄉鎮黨委任命。這種二元的鄉村政治框架設計容易造成自上而下的黨支部和自下而上的村委會間的二元權力結構沖突。兩種權力關系一旦處理不好,就會造成兩委之間的摩擦而無法正常開展工作。
(四)村干部在當選之后,自以為權力在握,作風專橫
一些村干部在選舉工作完成以后,自以為獲得了使用權力的合法性,為了快速見到成效,新官上任三把火,工作作風難免浮躁。“通不通,三分鐘,再不通,龍卷風”就是這種工作方式的真實寫照。更有的鄉村干部盲目的辦企業、上項目、跑銀行貸款,搞群眾集資,雖說也搞成了一些企業,但大多數還是連本帶利賠個精光,使村集體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群眾的集資款打了水漂。群眾為這類問題意見很大。想想這些作法,真是干部掏出好心卻得罪人,做了不少工作,卻被群眾上訪告狀。這種結果造成的原因在于,因為缺乏集思廣益的協商機制,難免導致了村干部的作風專橫。
農村選舉民主在實踐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根本的原因在于農民行使自己權利的形式僅僅局限在參加村委干部的民主選舉工作,而在選舉之后,農民基本沒有參與村莊政治的機會,而當選的村干部則認為自己可行毫無顧忌地行使管理權了,不再顧及民意和民情。與此同時,廣大農民成了鄉村政治的旁觀者,他們參與農村政治的渠道狹窄,不能充分地和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無法對村“兩委”工作行使監督權利。當前農村,迫切需要尋找一種鄉村政治機制,這種政治機制既能夠保障廣大農民自由表達訴求,充分行使監督權,也能夠促使村委會廣納群言,廣集民智,從而使村干部和村民之間共同商議村政,形成合力。于是在國家的推動和農民的積極參與下,農村協商民主應時而生。
二、農村協商民主的優越性
在十八大召開之前的一段時期,“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不斷發展,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得到進一步發揮,在我國基層興起了多種形式的協商民主實踐。” [2]如浙江溫嶺的“民主懇談會”、四川省成都市的“居民議事會”、貴州遵義市的“黨員與群眾的集中訴求會”,都取得了成功的經驗。另外,受溫州民主懇談會模式“參與式預算”協商模式的影響,無錫、哈爾濱、上海等地也開始了“參與式預算”民主協商實踐。上述基層協商民主實踐的經驗凸顯了社會主義農村協商民主的優越性,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總體說來,農村協商民主具有如下優越性:
(一)化解鄉村矛盾,更加充分地滿足村民政治訴求
在傳統鄉村政治框架下,選舉民主一枝獨秀,村民只享有選舉權,而沒有實際的參政和議政權,因此,在農村公共事務的民主管理、決策和監督過程中,村民沒有相應的參與和表達自己意見和建議的機會。這勢必打壓村民的民主參政意識和維權意識,進而引發社會矛盾和沖突。而農村協商民主則可以彌補上述選舉民主的不足,一方面,它強調鼓勵廣大的人民群眾通過相應的機制、程序安排,實現了參與權,知情權,另一方面,它讓村民能在參與的過程中表達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見。
(二)促進我國鄉村治理中政府與村民的互動
協商民主強調參與主體的平等性,為所有參與者提供公平的表達不同的意見機會,使各種利益訴求都得以自由表達。在協商的過程中,全體參與者通過對話、討論、商談、妥協和審議等協商方式最終達成一致,并且這種一致不僅出于多數人的意愿,而且是集體理性反思的結果;協商的本質目的是為了追求團體利益的最大化,在多元利益間達成妥協和平衡。 [3]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協商民主可以充分發揮溝通、協商的作用,促進共識。政府和村民通過協商可以找到匯合點,化解矛盾,實現共贏。
(三)協商民主有利于解決我國鄉村治理中的民主困境
當前,我國鄉村治理中出現“民主困境”,主要表現為村民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干群關系緊張。這種現象導致村民消極參與選舉民主,村民利益表達更是沒有一個制度化渠道,于是只有通過非制度化渠道表達,暴力事件頻繁發生,嚴重影響鄉村社會的穩定。而農村協商民主盡量保證每個村民平等參與,通過友好和理性的協商達成共識,這樣不僅可以提升選舉的公正性以及村民的政治認同感,同時也暢通了村民利益表達的制度渠道,從而促進了鄉村政治的和諧發展。
我國農村協商民主經過在不同區域的實踐,充分彰顯了自身的優勢,引起了廣泛的觀注,最終,協商民主并且和選舉民主一樣,得到決策層的認可,成為一個鄉村社會治理的重要機制。2012年11月,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報告首先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積極開展基層民主協商”,豐富和拓展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內涵。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又以“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為題,要求我國基層政權積極“開展形式多樣的基層民主協商,推進基層協商制度化”。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對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作出了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大大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進程,是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新經驗如“溫州模式”等基層協商民主理論創新的充分肯定。
三、農村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的優勢互補分析
農村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并存的格局,促使學術界和決策層開始思考二者如何協調配合的問題,例如國家政協主席賈慶林在2012年11月8日參加黨的十八大北京代表團討論時曾經指出,要深入研究和推進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的協調配合問題,使兩種民主形式更加優勢互補,形成合力。在我國農村,同樣存在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的協調與配合問題。總體看來,農村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之間存在著如下優勢和互補:
第一,各自獨特的優勢。首先,選舉民主是基礎性民主,是農村基層政治的基石,是現代民主制度的核心要素,決定了農村政治的根本格局;而協商民主是一個過程性民主,是一種村民民主理念提升的表現。其次,選舉民主是存量民主,而協商民主是增量民主。農村選舉民主是一個既成的“文本的”、“沉淀的”制度,是在憲法和法律規定范圍內的一項成熟和成型的民主制度;而農村協商民主則剛剛形成雛形,在全國各地的協商民主實踐中,表現形態各異。在憲法和法律框架內還沒有明確的規定,目前僅僅限于政策的確認與推動和保障。換言之,農村協商民主是一個正在成長和發育的民主胚胎,雖然生命力非常旺盛,但是沒有成熟和成型的理論機制,它還需要很大程度的完善和提升;再次,選舉民主是一項周期性民主,它是根據法律規定,在村委干部的任期將要結束時,必須開始的一項民主活動。例如,法律規定村委干部的任期是三年,那么選舉民主在三年任期期滿之前必須按時舉行,選舉新一屆的村委干部,周而復始,具有很強的周期性;而協商民主則是協商民主是隨機性民主,它沒有什么周期性,它不應僅僅被理解為自由選舉和票決的理論與實踐,它還應包括討論、交流、建議、咨詢、參與、協商、合作等多種行為的過程;最后,選舉民主的結果具有強制性,是一種法律意義上的權力授予,被選舉上的村委干部將會獲得一些管理和決策的權力,這些權力對所有村民都是有法定約束力的;而協商民主的結果則具有契約性,它是一種自由意志的表達和民間的理性共識,它的表達結果必須經過村委的決策后,才具有強制性,所以,農村協商民主更像是一種對村民民意的尊重。
第二,二者的優勢互補。首先,農村協商民主是農村選舉民主的對應和銜接。在農村協商民主的成功實踐中,協商與合作永遠占主要地位,這同時貫穿在選舉民主的全過程。選舉之前,協商民主要求對候選人的協商提名;投票之前,經過反復的討論,征求各方意見之后才形成票決的結果。經過選舉和票決之前的交流、討論、協商等行為,選舉和票決的結果于是真正反映大多數人的意志的;其次,二者在目標、宗旨、原則和功能上有很多共同之處。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都是健全民主制度,并最終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這一民主價值的形式與手段。從民主價值上說,二者都有助于避免社會暴力,保障全體村民公平進行政治參與,進行鄉村公共事務的科學管理,增強政治參與的合法性。從形式上講,對于農村選舉民主和農村協商民主來講,不是某一種民主形式天然優于另一種民主形式,并非要在二者之間作出單項選擇,二者具有互動作用,它們以相互結合、相互滲透、相互交織的方式融合在民主政治的現實操作之中。就是說,選舉中可以有協商,協商中也可以有選舉; [4]再次,二者是一種互動關系。選舉民主從制度上保證廣大村民選舉權,而協商民主則是在實踐中,鼓勵全體村民積極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管理,最終就決策形成共識。如果沒有選舉民主,協商就有可能被操控,或者被利用;而如果沒有協商民主,選舉民主就會流于形式,公共利益就會受到侵害和影響。
總之,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不是彼此對立的,也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關系,選舉民主中有協商,協商民主中有選舉,二者之間具有優勢互補關系。
通過上述農村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的優勢與互補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不是非此即彼的關
(下轉第1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