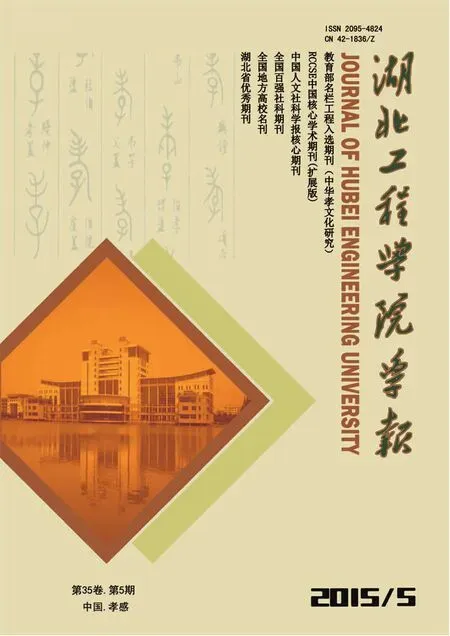論寺廟的民事主體地位
許小芳
(西南政法大學 民商法學院,重慶 401120)
論寺廟的民事主體地位
許小芳
(西南政法大學 民商法學院,重慶 401120)
當前民事立法規范對寺廟的民事主體地位定位模糊,而司法實踐對寺廟主體地位態度明確。結合我國傳統上寺廟的立法規范,評析了日本的宗教法人立法,提出我國寺廟的民事主體地位應為財團法人的觀點。同時囿于我國立法并無對財團法人之規范,呼吁未來民法典應完善財團法人制度,以切實明晰寺廟財團法人的權利義務。
寺廟;民事主體地位;寺廟法人化;財團法人;宗教法人
一、問題緣起與綜述:寺廟民事主體地位的研究現狀
1.問題的提出。寺廟或為分工高度明確、聯系日益緊密的現代社會裹挾,被迫走下神壇,或為跟隨時代發展,擴大自身影響力,維護自身權益而自愿融入社會,總是不可避免與世俗社會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尤其是近幾年來,中國四大佛教名山競相上市,佛、道教寺院宮觀被商業化侵襲,各地“借佛斂財”的種種怪現狀層出不窮。[1]寺廟作為概略上的民事主體,究竟應當在市民社會中扮演著何種角色,才能既避免淪落為工具性的存在,保持神圣性、純潔性,又能夠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維持自身的有序運作呢?
2.研究現狀述評。
1)國外研究現狀評述。外國學者多從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等憲法視角來研究以寺廟為代表的宗教組織的法律問題,從民法角度探討宗教組織的學者較少,其中井上惠行和山本雅道從大陸傳統民法學視角討論了日本《 宗教法人法》的基礎理論問題。 Lars Friendner探討了歐洲各國宗教組織私法上的法律人格問題,W.Cole Durham,Silvio Ferrari逐一研究了東歐劇變以后東歐各國的宗教組織法律地位問題,James A.Serritella,Thomas C.Berg等專門研究了美國宗教組織在私法上的法律地位問題。上述研究為本研究提供了理論借鑒和邏輯起點,但是其觀點只能參考而不能全盤接受,一是因為其不適合我國教派構成狀況以及宗教組織發展的階段和水平,二是因其與我國現行基本宗教政策相矛盾。[2]
2)國內研究現狀述評。國內學者對于寺廟的法律地位界定,或是將其納入非法人組織范疇予以考量,或是單獨討論寺廟財產權之歸屬以確定其法律地位,就筆者所搜集到的有限資料,只有莫紀紅、趙倩玉就宗教自身的法律地位問題予以探討,華熱多杰、仲崇玉則更進一步提出宗教人化的主張,足見我國法學界對以寺廟為代表的宗教民事主體法律地位問題仍不夠重視。
本文將通過對上述文獻資料的整合,以當前寺廟作為民事主體所遭受的尷尬困境為切入點,通過法律規范層面、司法實踐層面、法律傳統層面及域外立法層面等多方位考察、比對,尋求最適合我國寺廟的民事主體定位,以期能夠在民事活動中最大限度地維護宗教利益,保障宗教自由。
二、寺廟民事主體地位之困境:立法與實踐的沖突
1.現行法對于寺廟的民事地位界定。我國現行立法對于民事主體的劃分存在沖突:民事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采納了傳統民法的“二元結構”理論,將民事主體劃分為公民(自然人)和法人,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為代表的其他民事法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則以“三元結構”為標準,區分民事主體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三種。
遵循傳統民法的理論,寺廟似乎具備法人主體資格,但是根據《民法通則》第50條之規定,社會團體法人依法不需要辦理法人登記的,從成立之日起,具有法人資格;依法需要辦理法人登記的,經核準登記,取得法人資格。又根據2005年正式施行的《宗教事務條例》第15條之規定,宗教活動場所經批準籌備并建設完工后,應當向所在地的縣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申請登記。縣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30日內對該宗教活動場所的管理組織、規章制度建設等情況進行審核,對符合條件的予以登記,發給《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證》。可知寺廟依照《宗教事務條例》進行的登記是一種行政登記,并非《民法通則》所要求的法人登記,故寺廟不屬于《民法通則》所規定的社會團體法人。
隨著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各類社會組織大量涌現,為了解決類似寺廟這種既不屬于自然人,又不符合法人條件的社會組織在民事活動和糾紛中所面臨的尷尬處境,我國《合同法》第二條、《民事訴訟法》第三條賦予了這類社會組織以主體資格,并將其稱為“其他組織”。對此,有學者認為不能因現代民法承認其他組織的“主體資格”而等同于其具有民事主體地位。從實質考察,其他組織作為非法人團體,既不能自己享受權利,也不能承擔任何責任,應將其定義為不具有團體人格但具有“形式上的民事主體資格”的組織。[3]
因此,根據現行法律規范,寺廟是在民事活動中僅享有形式意義上的民事主體地位的組織,不能夠以自己的名義享有民事權利,或者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2.司法實踐對寺廟民事地位的態度。筆者通過“北大法寶”在民事糾紛范圍內,以“寺廟”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共找到197篇案例與裁判文書。通過對這些裁判文書的分析、總結,發現以寺廟為被告并且法院最終裁判由寺廟承擔相應責任的案件共有何樹碧與成都昭覺寺等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上訴案[參見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2008)成民終字第893號民事判決書]等10個。由此可見,雖然寺廟在民事立法中僅具有形式層面上的民事主體地位,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因為寺廟享有獨立財產,具備責任主體的標準之一——責任財產,而裁判由其承擔相應的責任,無形之中將寺廟法人化,在實質上賦予了其民事主體的責任能力,課以其民事責任的承擔。
三、寺廟民事主體地位之確定:財團法人
1.尋本溯源:歷史上寺廟的民事主體地位。我國歷史上關于廟產管理的法規肇始于民國時期,1913年6月20日袁世凱政府內務部頒布了《寺院管理暫行規則》,但該規則重點在于規制寺廟管理,維持寺廟的宗教用途,并未明確其法律地位。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教政雙方均呈請另行頒布寺廟管理條例。1929年1月25日國民政府頒布了《寺廟管理條例》,該條例明確寺廟財產之所有權屬于寺廟,第一次明確了寺廟享有物權法上的所有權,奠定了寺廟具備民事主體地位之基礎。后由于該條例飽受詬病,同年12月7日國民政府便明令廢止了《寺廟管理條例》,另行公布了《監督寺廟條例》。新條例第6條第一項規定“寺廟財產及法物為寺廟所有,由主持管理之”,第10條規定“寺廟應按其財產情形,興辦公益或慈善事業”[4],再次重申了寺廟獨立的財產地位。雖然新條例對于所有權的規定極為虛化,難以在實踐中操作,但該條例中寺廟對廟產享有所有權,并指定住持為其財產管理人的創造性規范,頗具傳統民法上財團法人的色彩,為寺廟民事主體地位之確定提供了歷史依據。
2.他山之石:以日本的宗教立法為視角。二戰之后,日本在國家民主化進程中逐步完善與宗教相關的法律法規,專門建立起《宗教法人法》用以管理其國內宗教事務。在宗教主體資格上,依據《宗教法人法》,宗教法人分為宗教場所法人和宗教團體法人兩個大類。前者是指有宗教場所為依托的宗教團體,而后者所指的是由前者所載團體所組成教派、宗派、教團、教會、修道會、司教區等宗教團體。在宗教法人的設立上,該法規定只要依據該法進行登記,宗教團體即可獲得宗教法人資格,依法對宗教團體的宗教設施和其他財產的維持運用、宗教目的的經營事業享有財產處分權利。但是宗教團體經法院認定有從事不符合宗教團體宗旨的活動等違法事項時,可以命令解散宗教團體,剝奪團體法人資格。[5]
日本的《宗教法人法》對于我國確立寺廟的民事主體地位具有啟發性的意義,賦予宗教以法人人格,厘清宗教的財產歸屬,對于宗教在從事商品活動中保有獨立地位具有重大意義。[6]但是日本對于宗教之定位,是在傳統民法之社團法人和財團法人劃分之外,創設性地將宗教自成一類宗教法人。出于維護法的安定性考量,此種宗教法人于我國是否有必要值得深思。
3.立足國情:寺廟財團法人化。通過對法律傳統之考察、域外立法之參照,結合目前我國司法實踐的具體情況,應當賦予寺廟財團法人的民事主體地位。
(1)寺廟法人化之意義。宗教組織法人化是現今社會宗教發展的趨勢,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是通過法人制度來管理宗教財產。法人制度是伴隨著經濟發展而興起的,法人作為一種獨立的主體形式在私法領域意義重大。[7]寺廟法人化不僅順應了時代的發展要求,而且具有如下幾點現實意義:
第一,寺廟法人化便于其參與民事社會活動。寺廟具備法人人格后,能夠以其名義獨立地進行民事活動,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履行民事義務,并且能夠獨立承擔因其行為所產生的法律后果。其法人化滿足了當今民事活動對于交易便捷快速的需求。
第二,寺廟法人化有利于其維護自身權益。寺廟法人化意味著寺廟的財產獨立,能夠名正言順地以自己的名義使用財產,例如以法人名義在銀行開設對公賬戶,有效防止目前頻發的寺廟公款流入私人腰包的現象。其次,寺廟法人化能夠獨立地承擔責任,可有效解決部分寺廟管理人為避免承擔責任而放任侵犯寺廟財產權利的現狀,比如“被占用”、“被上市”的寺廟能夠以自己的名義主張權利,切實維護自身權益。[8]
第三,寺廟法人化能夠充分踐履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的宗教政策。寺廟成為民法上的主體,將打破目前我國依靠行政管理宗教事務的格局[9],寺廟將依賴自身獨立地獲取經濟來源,自主進行人事安排,在財務、人事等方面取得一定自主權,充分自治,真正地實現獨立自主自辦宗教事務。
第四,寺廟法人化保障依法規制宗教活動。寺廟成為民事主體之后,其在從事相關民事活動、宗教活動時必須符合相應的法律規范,事先在立法上對寺廟的相關行為作出規定,既有利于引導宗教活動有序進行,同時也是執法者對其進行監督管理的依據,能夠保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目標在宗教領域實現。[10]
(2)寺廟財團法人化之選擇。綜上所述,寺廟必須實現法人化,然而寺廟屬于何種形式的法人,學術界卻多有爭議,主要分為宗教法人說和財團法人說兩種。
1)寺廟宗教法人說之評析。主張寺廟為宗教法人的學說主要從如下兩個觀點予以論證:從“人”的角度上看,寺廟中的“圣職者”是不可或缺的,其存在具有自身目的和歸宿,是宗教組織不可或缺的“社員”,且寺廟在現實社會中因自身自養的需要不斷創造自身財富,甚至已經形成了宗教產業,宗教組織和成員從中獲利和收益。從“財產”的角度看,由于寺廟接受世俗的贈與,事實上也就成為了捐贈人的代言人和財產的管理者、使用者和收益者。[11]所以就寺廟的定位上來看,應當充分考慮其兼具財團性和社團性兩個方面,宗教法人的民事主體地位更為切合寺廟的性質。較之于財團法人說,宗教法人說認為一方面寺廟不僅僅是財產的集合,更具有“人合性”,須仰賴寺廟的成員方可形成,另一方面我國寺廟的獨立財產中包含著除捐助資產以外的財產。[12]因這兩方面與一般財團法人大相徑庭,因此寺廟為兼具財團法人和社團法人性質的宗教法人。
首先,對于宗教法人說認為的寺廟具有社團法人屬性,即須有相當數量成員的觀點,筆者不予認同。俗語有云:“流水的和尚,鐵打的寺廟。”對于寺廟而言,其最大價值在于宗教信仰之依附所在,因此無論寺廟中僧眾多少,亦或是其所接納虔誠信教者多少,對于其存在并無影響。哪怕該寺廟只有一個信教者常年供奉,該寺廟在從事世俗活動中的地位也不會因此而削弱。相反地,認為寺廟必須由一定數量成員組成方可獲得民事主體地位的觀點,與我國憲法所倡導的宗教自由理念相悖。因此宜認定寺廟為財產的集合體。
其次,宗教法人認為寺廟財產中含有捐助資產以外的財產,因而與財團法人財產來源相異的觀點,曲解了財團法人的成立基礎。依王澤鑒先生所見,財團系以捐助財產為其基礎的法人(財產組織體),如私立學校,寺院等。財團法人為財產的集合體,其成立基礎在于財產。[13]財團法人系以財產為組織基礎,捐助財產為其成立之依據,也是其賴以生存的核心財產,但并非其只能以捐助財產為來源。故而財團法人可以擁有非捐助財產以外的其他財產來源,只是其他財產來源不能超越捐助財產而成為財團法人的核心財產。
再者,傳統民法按照法人成立的基礎劃分為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并無宗教法人這一分類的存在,因此為保持理論的邏輯周延性,不宜再創設新的法人類型。同時基于實證角度之考量,財團法人之理論完全能夠滿足我國實踐所需,亦無須創設新的法人類型。
2)寺廟財團法人說之評析。財團法人是指法律上對于為特定目的的財產集合賦予民事權利能力而形成的法人。[14]84寺廟之所以能夠成為財團法人,可從如下四點理由探求依據:
其一,寺廟的財產基礎源于各信徒或社會各界人士之捐助行為、遺贈行為,但自捐贈行為完成后,各捐贈人不參加宗教的管理,即與財產分離,寺廟成為財產的所有權人,只有這樣寺廟方具有成為財團法人之基礎——特定目的之財產集合。
其二,宗教財產獨立參加民事活動,形成了事實上的法人人格,能夠實現捐贈人之財產與寺廟財產管理人意志相分離。同時各寺院宮觀獨立核算,獨立的享受權利承擔義務,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具有事實上的法人人格。[15]111
其三,將宗教財產的所有權依法賦予宗教財團法人——財產獨立的寺院宮觀,既符合財產捐助人的主觀意愿,也符合我國各種宗教的教規教律。“財團應當具備相當之組織,其組織及管理方法,由捐助人以捐助章程定之。”[16]169現在我國各寺廟都有管理委員會,這些就給依法確認宗教財團法人財產所有權提供了現實條件。
其四,我國法律允許宗教財團法人享有財產所有權。《民法通則》第77條規定社會團體包括宗教團體應享有其財產權利。根據法學原理,具有獨立財產、獨立參與民事活動的寺院宮觀只能是財團法人。[14]84
由此可見,寺廟依財團法人之規定行使民事主體權利,有其根源層面、實踐層面、結構層面和法律層面的支撐。并且結合上述對我國法律傳統的例證,寺廟財產歸于寺廟財團法人所有,從觀念上也早已經為人們所接受,甚至可以說它是一種歷史的選擇。[7]
(3)寺廟財團法人之制度構建。對于寺廟的財團法人制度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構建。
第一,寺廟財團法人之設立。寺廟財團法人設立需滿足如下四個要件:
1)捐助行為。須有信徒或者社會各界的捐助行為或遺贈行為之存在,使得寺廟所受的捐贈財產得以成立;
2)經訂定章程。為規范財團法人對其財產的使用,信徒或者社會各界人士在進行捐助行為時須以文書事先訂立捐助章程,捐助章程應訂明財團之目的、所捐之財產及其組織并管理之方法,即成立寺廟財產運行的基礎規范;
3)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可。在我國,寺廟財團于登記前,應得宗教管理行政機關之許可;
4)設立登記。法人須向寺廟所在地之主管機構進行登記,除該機關以外的登記不具有成立法人之效果。[15]114
第二,寺廟財團法人章程之變更。因財團法人具有公益性質,且其并無社團法人總會之意思機關,故依法不得自行變更章程。相對地,為維護財團法人公益性之目的,應當允許主管機關或法院遵照法律之授權變更財團法人之章程。因此,寺廟的財團法人章程之變更可分為一般設立登記事項之變更與特別情形之變更:
一般登記事項,如寺廟捐助章程之變更中變更寺廟住所,或者單純變更寺廟名稱。因上述變更不涉及寺廟財團法人之公益性,因此寺廟對此類事項進行變更時,無須得到相關行政主管部門的批準,可徑行向主管機構辦理變更登記。
特別情形,如涉及寺廟之組織及其管理辦法事項之變更,因其對寺廟運行有重大影響,出于公益性之考量,應當由寺廟向有關機構申請批準,得到同意變更批示之后方可向主管機構辦理變更登記。[15]120
第三,捐助行為之變更。所謂捐助,系指以設立財團為目的,無償提供一定財產之行為。一般認為捐助行為為單方法律行為,捐助人一為意思表示即發生效力。因此只要捐助人作出捐助的意思表示,捐贈財產即屬寺廟所有,并無撤回余地。但在寺廟成立的不同階段下,捐助行為存在撤銷問題:
在寺廟法人設立登記完成之前,須有法定撤銷原因始得撤銷捐助行為,不得任意撤銷。在寺廟法人設立階段,雖然寺廟法人民事主體地位尚未形成,但撤銷捐助行為仍對于公共利益之維持有一定影響,因此除非有法定的撤銷原因,捐助人或者遺贈人的繼承人不得任意撤銷捐助行為,以保障公益,并尊重捐助人原意。
在寺廟法人設立登記完成后,不問任何原因,均不得撤銷捐助行為。寺廟財團法人的民事主體地位確立之后,寺廟財團法人之基礎乃捐助財產,其脫離于原捐助人而取得獨立之人格。故,為維護公共利益,捐助人或遺贈財產的遺囑執行人不可撤銷捐助行為。[16]172
四、結 語
當下宗教組織的神秘色彩已逐漸淡化,宗教世俗化傾向越來越明顯,宗教經濟膨脹,宗教財產變動頻繁,然而現行立法中對于宗教的規范卻不明晰,不能夠有效地解決宗教活動中所引發的民事糾紛。宗教無小事,倘若不能妥善解決與宗教相關的問題,將會直接影響宗教事業的發展,甚至危及社會的安定團結。為此,未來在制定民法典時必須明確以寺廟為代表的宗教組織的民事主體地位。
為切實維護宗教利益,保障宗教組織自主自辦的獨立性,在立法上應當將宗教組織法人化,賦予其獨立的民事主體地位。通過對法律傳統的溯源、他山之石的借鑒、司法實踐的實證等多方面考量,我國寺廟可以遵循傳統民法中財團法人的規范,以財產的集合體為基礎,獨立地行使權力,承擔責任。但由于我國現行法并未對財團法人這一分類予以確認,因此在未來民法典的制定中,應當全面構建財團法人制度,以切實規范寺廟作為民事主體的權利義務。
[1] 兩會提案:解決寺廟身份問題[EB/OL].(2013-03-09)[2014-12-30].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4011.
[2] 仲崇玉.宗教法人制度論綱[J].青島行政學院學報,2013(3):109-113.
[3] 尹田.論非法人團體的法律地位[J].現代法學,2003(5):15-16.
[4] 張建文.目的財產學說對我國宗教財產立法的影響和實踐[J].河北法學,2012(5):74-75.
[5] 陳世佳.論我國宗教財產的民事保護[D].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13.
[6] 田麗莉.論寺廟財產歸屬及其糾紛解決機制[D].成都:西南財經大學,2012.
[7] 張妍.論寺廟財產的所有權歸屬[D].成都:西南財經大學,2013.
[8] 仲崇玉.宗教法人制度研究[EB/OL].(2014-12-26)[2014-12-31].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5422.
[9] 趙倩玉.論宗教團體的法律地位[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3.
[10] 奚松偉.我國宗教財產法律制度探析[D].重慶:西南政法大學,2010.
[11] 王澤鑒.民法總則[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26.
[12] 葛云松.中國的財團法人制度展望[J].北大法律評論,2002(1):176.
[13] 梅仲協.民法要義[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76.
[14] 孫憲忠.財團法人財產所有權和宗教財產歸屬問題初探[J].中國法學.1990(8)
[15] 林誠二.財團法人捐助章程之變更[J].法學雜志,2004(4).
[16] 林誠二.論捐助行為之撤銷及捐助財產之處分[J].法學雜志,2000(8).
(責任編輯:胡先硯)
2015-09-01
許小芳(1992- ),女,福建惠安人,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DF51
A
2095-4824(2015)05-01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