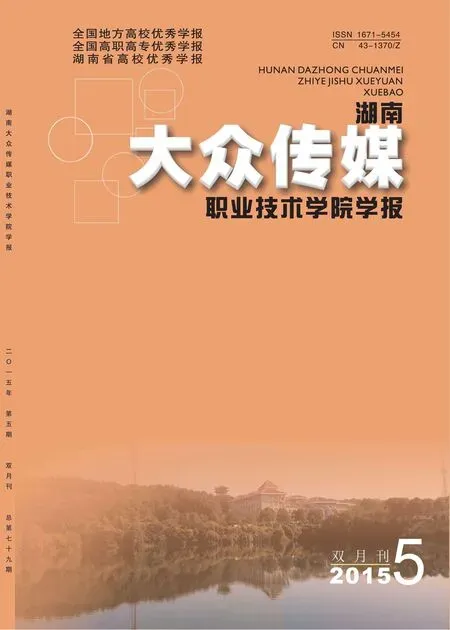許地山的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
黃林非
(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 國際傳播學院,湖南 長沙 410100)
?
許地山的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
黃林非
(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 國際傳播學院,湖南 長沙 410100)
[摘要]許地山具有學者和作家的雙重身份,其學術研究涉及宗教、文物、語言文字、歷史等領域。許地山的宗教研究尤其是道教研究和佛教研究對其文學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了解許地山的學術研究狀況和學術思想,有助于人們深入解讀其“復雜難懂”的文學作品并準確把握其“獨異”的藝術風格。
[關鍵詞]許地山;學術研究;文學創作
[DOI]10.16261/j.cnki.cn43-1370/z.2015.05.015
一
許地山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學術研究也卓有成就。其文學創作除了為人熟知的小說、散文外,還包括劇本、雜文、童話、詩歌等數十篇。在學術著作方面,有《道教史》(上冊)、《達衷集》、《印度文學》、《佛藏子目引得》、《國粹與國學》、《扶箕迷信底研究》等單行本面世;此外,尚有一些民俗學、宗教學及哲學論文未曾入集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許地山學術論著》匯集了許地山的學術著述約30萬字,但仍有一些篇目未被收錄,稍有遺珠之憾。許地山這位“飲過恒河圣水”的奇人以風格獨異的小說和散文名世,學界對其文學創作的研究已相當深入。不過,對許地山學術思想研究似乎至今仍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個冷門,這與許地山巨大的學術成就很不相稱。陳寅恪曾撰文專門論述許地山的學術研究:“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學,然于道教僅取以供史事之補證,于佛教亦止比較原文與諸譯本字句之異同,至其微言大義之所在,則未能言之也。后讀許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論文,關于教義本體俱有精深之評述。心服之余,彌用自愧,遂捐棄故技,不敢復談此事矣。”[1]放眼中國,能讓陳寅恪心悅誠服的學者能有幾個?許地山學術水平之高、學術成就之大,似可略見一斑。
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許地山就已是中國文壇的一員闖將,但是,如果簡略梳理其學術背景,即可知道他同時又是一位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學者。1920年,許地山在燕京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后來又進入該校宗教學院學習并于1922年畢業,獲神學學士學位,做過周作人等教授的助教。自1923年開始,許地山先后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國牛津大學學習,并赴印度瓦拉納西的印度教大學短期進修。在此期間,許地山獲碩士學位,系統地研習過宗教史、宗教哲學、民俗學、人類學、希臘文、梵文、印度哲學等課程。1927年后,任燕京大學副教授、教授,并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的兼職教師,擔任《燕京學報》第一至第十七期的編委。他在燕京大學講授文學和宗教學,在北京大學講授印度哲學,在清華大學、中山大學講授人類學。1935年,由胡適引薦,出任香港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從以上經歷可知,許地山并非只是一個作家,他受過正規的學術訓練,是一位學術視野開闊的有廣泛影響的學者。據筆者掌握的資料,許地山的學術研究主要包括宗教、文物、語言文字、歷史等四方面內容。
許地山在學術研究方面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當屬宗教研究,特別是對道教與佛教的研究。他所著的《道教源流考》、《道教思想與道教》、《道教史》、《佛藏子目引得》、《摩尼之二宗三際論》等篇,稱得上是中國宗教研究領域的開創性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許地山的思想雖受宗教的影響,但他的宗教研究建立在扎實的考證基礎上,采用的研究方法完全是科學的。茅盾曾評論過許地山的《扶箕迷信底研究》一書,認為許地山在宗教研究方面,其用心與研究扶箕的迷信是一樣的。在該書中,作者從扶箕的起源、箕仙及其降筆、扶箕的心靈學上的解釋等角度,對扶箕迷信作了全方位的考證研究,全書引述古代文獻中的扶箕故事多達132篇,并運用心理學、物理學、化學等科學理論加以闡釋。該書指出,占卜是不科學的,它的構成是由于原始的推理的錯誤。“原始人的推理力和孩童的一樣,每把幾件不相干的事物聯絡起來,構成對于某事物的一個概念,如打個噴嚏同時又聽見鴉啼,就把那兩件事來與明日的旅行聯絡起來,斷定在旅途中會遇見不吉利的事情。”因此,占卜也可以被看成交感巫術的一種。[2]131許地山最為人稱道的學術成果,應該是《道教史》。該書自1934年出版(商務印書館)至今已逾80年,但一直被學界重視,今天的相關研究者,幾乎沒有人能夠繞開它。這部著作是我國第一部道教專史,它系統地梳理了道教發生、演變的歷史,許地山因此被譽為現代中國道教研究的先驅者。
文物研究方面,頗能體現許地山學術興趣之廣泛。《香港考古述略》對香港附近發現的石器陶器、“廣東文物展覽會”所展示的一幅照片、新界的幾塊墓碑等進行考證,并加以推算、推斷,從而回答“香港人何時從何處來的”以及“最初來港的漢人姓什么”等問題。《禮俗與民生》區分了“風俗”、“禮儀”、“風化”、“禮俗”等概念,并從考察“生活的象征”、“行為的警告”、“危機的克服”三者的演進入手,來分析禮俗與民生的關系。《大中磬刻文時代管見》考證一件銅磬上所刻《心經》和《尊勝陀羅尼經》的刻文時代。《清代文考制度》依次考述“學校之設置”、“童生資格與入學”、“入學與入監”、“學校訓育原則及待遇”、“考試”等涉及清代文考制度的方方面面,并附有順治、康熙、雍正及乾隆年間所頒“訓士規條”。《貓乘》一篇,旁征博引,從神話、人事與自然三方面來談貓,文章爬梳使用了大量中西文獻,既嚴謹厚實,又很有意思。
語言文字方面,許地山有《國粹與國學》、《中國文字底命運》、《拼音字和象形字的比較》、《中國文字底將來》、《青年節對青年講話》等文章傳世。許地山反對當時學界的浮夸之風、迷古復古之風,他的一系列關于語言文字的文章,不僅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而且發人之所未發,有深刻獨到的見解。曹聚仁曾評論說,“三十年前,許地山先生在香港大學任文學院長,他病逝前的最后一篇文章,題名《國學與國粹》,刊在香港《大公報》上。我們對于讀古書的態度,可以說是完全相同。”曹文引述了許地山的一段文字:“中國學術不進步的原因,文字的障礙也是其中最大的一個。我提出這一點,許多‘國學’大師必定要伸出舌頭的。但,稍微用冷靜的頭腦去思考一下,便可以看出中國文字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到現在用的,還不是拼音文字,難學難記難速寫,想用它來表達思想,非用上幾十年工夫不可,讀三五年書,簡直等于沒讀過。繁難的文字束縛了思想,限制了讀書人的視線,所以中國文化最大的毒害,便是自己的文字。”曹聚仁在這段文字后面說:“這話說得平實極了。叫年青人讀古書,尤其是讀四書五經,便是要現代人用兩千五百年前的語言文字來表情達意,豈非自己開自己的玩笑?”[3]許地山看到了漢語言文字的改革方向,不僅在理論上做出了多方面研究,而且身體力行,在實踐中推動漢語言文字的改革。任職香港大學文學院院長之后,他曾大刀闊斧地改革原有的專業設置與課程設置,并力倡白話文,一舉打破了文言文在當時香港各校中文教學中的壟斷地位。
此外,許地山還在歷史研究方面下過功夫,且有重要的成果問世。比如他曾編撰服裝史,著有論文《近三百年來的中國女裝》。他的《達衷集(鴉片戰爭前中英交涉史料)》一書影響更大。該書是許地山留學英國時,受羅家倫之托,從牛津大學圖書館所藏的公文底稿以及舊函件等大量中國史料中摘抄整理而成。這本書被后世之史家反復引用,早已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珍貴史料。
二
許地山的學術研究涉及的范圍很廣,他善于整理歸納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能在此基礎上提出新的見解。正如任繼愈在《道教、因明及其他·序》中所說,“許先生在宗教學、社會學、新文學、考古學的開創之功是永遠存在的”。[4]許地山的文學創作深受宗教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影響,這與許地山多年從事宗教學的研究工作不無關系。不妨先看看許地山在道教研究和佛教研究方面的主要學術成果。
《道教史》是許地山最重要的學術專著。這部書的“緒說”開篇就直接談“道”這個概念,認為上至老莊思想,下至房中術,都可歸入“道”的名下。所以,“道”可分為思想方面的道與宗教方面的道,前者可稱為道家,后者即所謂道教。許地山顯然很看重道家思想,他指出:古初的道家是講道理,后來的道教是講迷信;道家思想可以看為中國民族偉大的產物,道家思想是國民思想的中心。在探討“道家”與“道教”的區分時,作者先后引用劉勰的《滅惑論》、阮孝緒的《七錄》、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以及張君房的《云笈七簽》,分別討論了劉氏的道家三品說(上品道、中品道與下品道),阮氏所謂方內道與方外道,馬氏的清靜說、煉養說、服食說和經典科教說,以及張氏將道教分為正真之教、反俗之教和訓世之教的觀點。許地山認為張君房的分法不盡如人意,訓世之教應屬儒教。不過,許地山將各種看法悉數羅列,有助于人們通過豐富的史料加深對“道家”與“道教”這兩個概念的認識。
事實上,許地山的學術興趣似乎更偏向“道家”,即“思想方面的道”,而非“道教”。《道教史》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宏大的歷史框架,并在這個框架中追溯老子、關尹子、楊子、列子、莊子等“道家”思想的緣起與演變,比較道家最初的靜虛派、法治派、陰謀派、全性派的相互關聯和不同主張,細致地呈現了“思想方面的道”的各個側面。除此之外,許地山充分考慮到道教思想淵源的復雜性和多元性。他稽考《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文獻,深入闡釋了道家的“養生”、“陰陽”、“五行”等概念范疇,并用兩章的篇幅,分別論述“神仙底信仰與追求”和“巫覡道與雜術”。在對道家的文化源頭和思想脈絡的考察過程中,許地山著墨最多、研究最為深入的,應該是莊子。《道教史》花了較大篇幅考證莊周的事跡、辨析《莊子》三十三篇的作者,更重要的是,許地山深入發掘、闡釋了莊子的思想,提出了許多深刻獨到的見解。
許地山說:“假若沒有莊子,道家思想也不能成其偉大。”[2]57許地山于諸種宗教文化中,鐘情于道家,于老莊楊列中,又注目于莊子。許氏論述莊子思想,頭緒較多,其中有三個值得特別關注的要點。一是他將莊子的齊物論概括為是非、物我和生死三個根本論點。他解釋說,是非之辨,沒有客觀的標準:天地萬物與我本屬一體,故萬象都包羅在里頭,無所謂是非真偽。如果依人間的知識去爭辯,那就把道丟失了。在物我的問題上,許地山指出,物我之見乃庸俗人所有。在這點上,莊周標出其真人的理想。所謂真人,便是不用心智去辨別一切的人。論及生死問題,許地山認為愛生惡死乃人之常情,而莊子以為現象界的一切所以現出生死變化,只是時間作怪,在空間上本屬一體,無所謂來去,無所謂生死。因此,“真人”不知“說生”,亦不知“惡死”。二是許地山提出了莊子的至人思想的內涵。他認為《齊物論》、《田子方》、《外物》等篇中的“至人”,與儒家的“圣人”有很大的區別,至人沒有政治意味,他有超越的心境,不以外物為思想的對象,離開民眾而注重個人內心的修養。三是他論析《天地》、《天道》、《天運》、《刻意》、《繕性》、《秋水》七篇,認為貫穿其中的一條思想脈絡,即是返回本性的道理。而《庚桑楚》、《徐無鬼》、《則陽》、《外物》、《駢拇》、《馬蹄》、《胠篋》諸篇,皆可作如是觀。許地山認為,莊子視人性的本源是從最初的無有無名發展而來的,所以人應當返回那個狀態,也就是返其性情而復其初。相比道教研究而言,許地山的佛教研究成果略少,但其學術影響不容忽視。他所主編的工具書《佛藏子目引得》旨在為學者研究佛教文獻提供方便。他的相關論文主要有三篇:一是1928年發表于《燕京學報》的《陳那以前中觀派和瑜伽派之因明》;二是1934年刊載于《大公報》的《觀音崇拜之由來》;三是收錄于商務印書館1946年出版的《國粹與國學》中的演講稿《宗教底婦女觀——以佛教底態度為主》。
因明學專家鄭偉宏曾評價過許地山的《陳那以前中觀派和瑜伽派之因明》一文,他認為許地山的論文“依次評介了龍樹、圣天(僅有生平)、彌勒、無著、世親其人其書,理清了陳那以前中觀、瑜伽派發展因明的線索,同時發掘了不少很有價值的史料,發表了一些新鮮見解”,并指證了許地山這篇論文的四個方面的主要貢獻。鄭文認為許地山的這篇文章非常重要,“是一篇長達六萬多字的因明史專論”。[5]許氏僅僅憑借這篇論文,即已在中國佛教因明學史上擁有一席之地。《觀音崇拜之由來》體現出許地山廣博的佛教知識和扎實的梵文功底,文章采納日本學者的學術成果并聯系自己印度之行的切身經歷,不僅揭示了“觀音”一詞的內涵,糾正了一些常見的誤解,而且指出了觀音崇拜的文化源頭和時間起點。文末還列舉了多達12種形象各異的觀音,其中既有中國的觀音,也有日本的觀音。作者涉獵之廣,搜羅之細,讓人嘆服。這篇文章篇幅雖小,但學術價值較高。《宗教底婦女觀——以佛教底態度為主》主要闡述佛教的女性觀,文章征引多部佛經中的相關材料,并參照基督教、印度婆羅門教的典籍,認為佛教對女子多持鄙薄的態度。許地山揭示了佛教給予女性的不平等地位,一方面考慮到男女的天然差別,另一方面又深究其社會根源。他客觀地分析看待宗教的婦女觀,認為“宗教沒了解女子,乃是在立教時社會沒了解女子所致”。他希望新的宗教不要再輕看女子,至少“也要當她做與男子一樣底人格,與男子平等和同工底人”。[2]262這篇文章并未對宗教的婦女觀提出過火的批判,態度公允,卻也可以看出許地山對女性的深切同情。
三
許地山的文學創作受到道家、佛家文化的深刻影響,這顯然與許地山多年從事宗教研究有關。他的第一篇小說《命命鳥》中,就留下了明顯的佛家文化印痕。“命命鳥”又叫共命鳥、生生鳥,出自佛經故事,《法華經》、《涅盤經》、《勝天王般若經》、《雜寶藏經》、《阿彌陀經》都有記載。在佛教傳說中,這種鳥兩頭一體,命運與共。用佛經故事中的詞語作為小說標題,既讓人倍覺神秘,又顯得新穎別致。小說女主人公有幾句祈禱,也是地地道道的“佛語”:“女弟子敏明,稽首三世諸佛:我自萬劫以來,迷失本來智性;因此墮入輪回,成女人身。現在得蒙大慈,示我三生因果。我今悔悟,誓不再戀天人,致受無量苦楚。愿我今夜得除一切障礙,轉生極樂國土。愿勇猛無畏阿彌陀,俯聽懇求,接引我。南無阿彌陀佛。”[6]99可以說,若不是許地山讀過大量的佛經,就不可能信手拈來用“命命鳥”作為作品的題目,也不可能寫出如此地道的一段佛弟子的禱告來。小說之所以籠罩著濃濃的異域情調和佛教氣氛,自然與作者年少時曾漂泊至緬甸仰光有關聯,更重要的原因,應當是作者多年研究佛教,已被佛家文化深深浸染。
《空山靈雨》里有一篇作品《香》,寫夫妻閑聊:“佛法么?一一色,一一聲,一一香,一一味,一一觸,一一造作,一一思維,都是佛法;惟有愛聞香底愛不是佛法。”“你又矛盾了!這是什么因明?”[7]13作品中,一詞一句,皆可見佛教經典的影子。再看《愿》里這幾句:“我愿你作無邊寶華蓋,能普蔭一切世間諸有情;愿你為如意凈明珠,能普照一切世間諸有情;愿你為降魔金剛杵,能破壞一切世間諸障礙;愿你為多寶盂蘭盆,能盛百味,滋養一切世間諸饑渴者;愿你有六手,十二手,百手,千萬手,無量數那由他如意手,能成全一切世間等等美善事。”[7]54這段話中,“寶華蓋”、“普蔭”、“世間”、“諸”、“有情”、“如意凈明珠”、“普照”、“金剛杵”、“障礙”、“盂蘭盆”、“無量數”、“那由他”等等,全是佛教典籍中出現頻率較高的詞匯。《七寶池上底鄉思》寫亡妻在西天極樂世界思念人間,思念丈夫。在這一作品中,幾個關鍵詞如“七寶池”、“彌陀”、“迦陵頻伽”等,都是佛經中的語匯,都是有來歷的。“彌陀”就是阿彌陀佛,“七寶池”、“迦陵頻伽”可見于《阿彌陀經》,前者指極樂國土,后者是極樂國土常出現的奇妙雜色之鳥。還可以看看作品中彌陀的幾句話:“善哉,迦陵!你乃能為她說這大因緣!縱然碎世界為微塵,這微塵中也住著無量有情。所以世界不盡,有情不盡;有情不盡,輪回不盡;輪回不盡,濟度不盡;濟度不盡,樂土乃能顯現不盡。”[6]54作品中很多詞匯出自佛典,字字句句散發佛光。這樣的作品,如若不是對佛學深有研究的人,是寫不出來的。
有意思的是,許地山談論創作時,也常常是滿口“佛語”。例如,《創作底三寶和鑒賞底四依》一文說:“寫出來底文字總要具有‘創作三寶’才能參得文壇底上禪”。他在解釋“三寶”時又說:“創作底三寶不是佛、法、僧,乃是與佛、法、僧同一范疇底智慧、人生和美麗。”解釋“四依”時,則引用佛教古德的話:“心如工畫師,善畫諸世間。”然后,他干脆借“佛家底四依”來談文學批評之道:“依義不依語;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7]297這是談論文學,還是談論佛學呢?在許地山這里,文學和佛學已然融為一體。
道家文化對許地山創作的影響可謂淪肌浹髓,已不止于語匯和意象的借用。許地山在道家思想研究方面的學術觀點與其文學創作密切相關,讀者如果明白了此中奧秘,對照許氏的學術思想去解析其諸多“復雜難懂”的作品,會有貼心潤肺般的到位之感。
如前所述,許地山對莊子的思想深有研究而且十分推崇,其文學創作也常常能體現他對莊子思想的理解和認同。例如,《暾將出兮東方》一文寫道:“本來,黑暗是不足詛咒,光明是毋須贊美的。光明不能增益你什么,黑暗不能妨害你什么,你以何因緣而生出差別心來?若說要贊美的話,在早晨就該贊美早晨;在日中就該贊美日中;在黃昏就該贊美黃昏;在長夜就該贊美長夜;在過去、現在、將來一切時間,就該贊美過去、現在、將來一切時間。說到詛咒,亦復如是。”[6]40文章消解了常人慣有的“差別心”,提倡以莊子式的眼光去看待世間的不齊,泯滅生活的差等。這段話簡直可以看作許地山對莊子齊物論的闡釋和評價。他認同莊子的看法,認為人可以通過齊生死、等是非、泯物我、一成毀,來獲得內心的愉悅自由,在不一樣的人生境遇中搭起一樣的逍遙殿堂。《愚婦人》借樵夫的歌唱說出了莊子“方生方死”的觀點,《山響》、《黃昏后》等作品則是對莊子生死觀的形象化表述:生不足喜,死不足懼,死亡不過是人順應自然、與時俱化的歸本歸真。
(責任編輯遠揚)
[參考文獻]
[1]陳寅恪. 論許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學:金明館叢稿二編[M]. 北京:三聯書店,2001: 316.
[2]許地山. 許地山學術論著[M].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
[3]曹聚仁. 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M]. 北京:三聯書店,2012: 261.
[4]許地山. 道教、因明及其他[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2.
[5]鄭偉宏. 佛家邏輯通論[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 169.
[6]許地山. 許地山選集[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7]許地山. 人生空山靈雨[M]. 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5.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454(2015)05-0058-05
[基金項目]本文為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資助科研課題“許地山的學術思想與文學創作”(編號:14YJ07)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黃林非(1972-),男,湖南湘陰人,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國際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收稿日期]2015-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