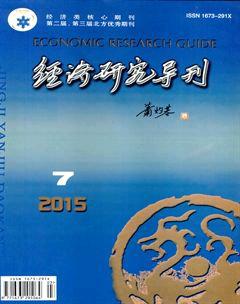淺論中國環境司法專門化與環境公益訴訟
謝 偉
(廣東財經大學法學院,廣州 510320)
環境司法專門化是指由于環境案件的特殊性,專門設立環保法庭,專門審理環境涉法案件。環境司法專門化的主要目的應是審理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但中國雖然有環境司法專門化,但審理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卻非常稀缺。
一、中國環境司法專門化與環境公益訴訟現狀
據不完全統計,自1998年以來,中國每年的環境污染糾紛以超過20%的速度增長,2005年后以每年30%的速度遞增,這些糾紛大多數都侵害環境公益。面對如此眾多的環境污染糾紛,司法作為解決糾紛的最終武器,理應在環境公益訴訟中占據主導地位,但是中國受制于傳統的起訴資格理論,多數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并沒有得到法院的受理。
環境司法專門化有助于解決環境訴訟案件司法標準不統一的問題,有助于提高全社會的環保意識。日益增加的環境案件,以及在環境案件審理中出現的一些法官不專業、環境案件因果關系難以確定、環境案件舉證難等問題的出現,促使中國一些地方率先開始設立環保法庭,環境司法專門化正式啟動。
2008年,無錫出臺《關于辦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的試行規定》規定:“本規定所指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為了遏制侵害環境公益的違法行為,保護環境公共利益,根據職能分工,通過辦理支持起訴、督促起訴、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等方式所實施的訴訟活動。”2009年,云南省高院通過《全省法院環境保護審判建設及環境保護案件審理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檢察院及在中國境內經依法設立登記的、以保護環境為目的的公益性社會團體,可作為原告向法院提起環境公益訴訟;公民個人可以向有關部門舉證反映,通過有關部門和組織來提起公益訴訟。”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務的若干意見》規定:“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環境保護行政部門代表國家提起的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糾紛案件”。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設立環境資源審判庭。
二、中國環境公益訴訟與環境司法專門化存在的問題和分析
(一)問題
1.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偏少。如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環境保護審判庭于2008年底掛牌,但到目前為止,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基本是“零”受案率。遼寧省作為較早成立環保法庭的省份,原有一批環保審判機構,成立十五年卻沒審理過一起環保公益案件,環保法庭銳減且功能只能退化為協助“執法”。
2.功能錯位。按國際司法慣例,環保法庭的主要職能是應對環境公益訴訟,輔以配合環保行政執法,但現在環保法庭保護環境公益的功能并未發揮出來。比如,遼寧環保法庭本有受理環境公益訴訟的職能,在實踐探索中卻出現職能“轉舵”,即審理環保公益案件的功能缺失,配合環保部門執法成為唯一的“職責”。
3.訴訟原告大多是行政機關或者檢察機關。檢察院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在訴訟過程中,檢察機關作為原告的身份極易異化為監督者身份。原被告地位不平等和原告身份的異化,容易引發裁判的不公正,影響到法院的中立立場。環境行政機關是實施環境保護監督管理工作的法定機關,對本應通過行政執法權處理的違法行為主張民事訴訟請求,背離了環境行政機關履行環境保護的職責,身兼“執法者”與“起訴者”雙重身份,會產生行政權力和民事訴權的混同,導致行政權力的弱化。
(二)分析
1.環境案件的特點決定。環境污染糾紛大多涉及環境公益,環境污染糾紛的形成原因非常復雜,環境污染具有緩發性、累積性、復合性、潛伏性等特點,環境污染舉證難,特別是環境公益糾紛中,很多污染行為還沒有損害到具體的個人身體健康或財產安全,但已經損害了環境,這使得獲取損害環境公益的證據難上加難。
2.環境公益訴訟司法依據不足。環境立法長期以來對于環境司法的制度支持不夠,最高人民法院迄今為止已經頒布了3400個司法解釋,其中與環境案件審判有關的司法解釋并不多,且主要針對環境刑事案件,而環境公益訴訟大多數是民事或行政案件。
3.環境信息公開不足。作為最重要的一項指標,企業日常超標、違規、事故記錄的公示依然是環境信息公開的一個薄弱環節。
4.環境管理體制和司法體制問題。中國目前的環境監管實行多部門負責制,容易導致沖突,造成環保執法難;同時,地方環保部門和法院在人事、經費等方面受地方政府制約,上級環保部門只能對下級環保部門實行業務指導。
5.環保團體發育不足。中國的環境團體發展很有限,在設立條件、專業化、經費來源、組織構成等方面都不能滿足環境公益訴訟的要求。
三、完善中國環境司法專門化與環境公益訴訟的若干建議
(一)擴大環境公益訴訟主體范圍
根據中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環境保護法》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中國目前的環境公益訴訟原告僅限于檢察院、特定國家行政機關和社會組織,其中社會組織要求必須是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且必須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這種制度設計阻礙了環境公益訴訟的發展。公眾既是環境公益的權利主體,也是環境保護最直接的監督者。應該擴大公眾參與環境公益訴訟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特別是賦權給公民。
(二)應設立環境公益訴訟支持起訴基金
為支持多元化的環境公益訴訟的起訴主體,特別是公民個人主體和資金有限的環境團體,中國有些環保法庭已經設立環境公益訴訟支持起訴基金。如昆明設立的“環境公益訴訟救濟專項資金”,資金來源由財政撥款、法院判決無特定受益人的環境損害賠償金、侵害環境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自愿捐贈款項等構成。專項資金主要用于支付環境公益訴訟所需的調查取證、評估鑒定等訴訟費用,對因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侵權人給環境造成的損害進行修復,對無財產可供執行的環境侵權案件的受害人進行救助。
(三)加強與環保部門的互相配合和司法監督
環保法庭可就如何提高環境執法規范性、提升行政執法水平,及時而中肯地向政府和環保部門提出建設性建議,從而有效地減少行政不作為或者錯誤作為現象的發生,促使環保部門加強制度建設,增強依法行政意識,進一步規范執法行為。同時,環保法庭要加強自身建設。比如,在環境法庭中還應當有技術方面的專家委員,包括但不限于城市規劃、環境科學、環境保護、環境評估、土地評估、自然資源管理等領域具有專業知識、經驗或適當資格的人員。
(四)環保司法有必要引入行政強制和處罰措施
根據中國法律的有關規定,環境刑事案件中的經濟處罰,可以通過單處或者附加罰金刑的形式進行,但沒有授予司法裁判對當事人處以罰款的權力,更沒有賦予行政管理(如誠信評價、資格限制、引咎辭職等),在司法裁判中有必要引入必要的行政強制和處罰措施建議。比如,環境公益訴訟原告勝訴后,可以建議對被告適用罰款、降低誠信等級、給予資格懲戒、建議引咎辭職制裁措施。加強司法建議,不是對行政權的侵犯,不是挑戰行政權威,而是改進行政執法、提升法治水平的外在力量。
(五)提高環保法庭級別和專屬管轄
環境公益損害多數是跨地區的環境污染、破壞等環保案件,涉及公安、檢察甚至環保、林業、城鄉建設等職能部門的管轄等問題,環保庭受理、審判案件的難度很大,司法成本較高。同時,目前中國環境法庭的設立大多集中在基層法院,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年7月設立了專門的環境資源審判庭,但目前中級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設立環境法庭的情況還很少。針對環保法庭多數為基層環保法庭的現狀,可考慮提高環保法庭的設立級別,并設立跨流域、跨行政區域的環保法院。
(六)環境公益訴訟可實行單位犯罪雙罰制
在近年來的司法實踐中,出現了除罰金、沒收財產等附加刑以外的其他刑罰的情形,如判決種樹、判決恢復植被、判決恢復和達到一定標準的生態條件等。另外,對一些主觀惡意不深,社會危害性不大的環境犯罪案件采取非刑罰手段,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在環境公益訴訟中還可借鑒刑法中關于單位犯罪的雙罰制度,在對行業單位處罰的同時,應考慮主要領導的處罰。這些判決方式彌補了傳統刑法關于環境犯罪所造成危害難以補救的缺陷,對環境和生態的恢復大有裨益。
(七)緊急情況,環境公益訴訟起訴人可申請禁令
在緊急情況下,不及時制止被告的行為會嚴重危害環境時,公益訴訟人可申請禁止令,禁止被告的相關行為。禁止令由人民法院作出,由公安機關協助執行。環境污染和破壞具有不可逆性,事后的補救往往耗資巨大甚至不可挽救,環境公益訴訟的目的不僅在于停止正在進行的環境污染和破壞行為,還在于恢復、治理已經被污染和破壞的環境。基于預防原則,在環境公益訴訟過程中,在被告的行為可能嚴重危及環境安全,可能造成環境難以恢復時,法院可以通過發布禁止令的方式停止正在進行的環境污染行為。
[1]徐詳民,胡中華,梅宏,等.環境公益訴訟研究——以制度建設為中心[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
[2]王萌.略談環保NGO在環境公益訴訟中的主體地位——由一個案例引發的思考[G]//李恒遠,常紀文.中國環境法治2007年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3]別濤,別智.環境公益訴訟破殼而出——環境公益訴訟進展概述[G]//李恒遠,常紀文.中國環境法治2008年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4]張杰.關于設立環保法庭及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思考[G]//李恒遠,常紀文.中國環境法治2008年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5]葉良芳.環保NGO與環境公益訴訟推動[G]//曾曉東,周珂.中國環境法治2011年卷(上).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