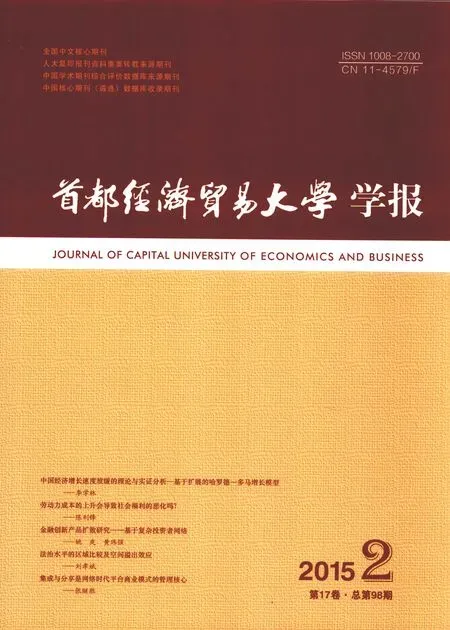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會導致社會福利的惡化嗎?
陳利鋒
(中共廣東省委黨校 經濟學教研部,廣東 廣州 510053)
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會導致社會福利的惡化嗎?
陳利鋒
(中共廣東省委黨校 經濟學教研部,廣東 廣州 510053)
構建基于包含家庭異質性消費偏好與失業的新凱恩斯主義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可用于分析由于勞動力成本上升引起的上行的名義工資剛性以及貨幣政策機制對于社會福利的影響。名義工資剛性的上升并不必然引起社會福利的惡化,當名義工資剛性程度較低時,名義工資剛性的上升會引起社會福利的改善;并且對勞動力成本上升做出反應的貨幣政策機制擴大了名義工資剛性對于社會福利的影響。這一結論對于勞動力成本上升背景下中國貨幣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異質性消費偏好;社會福利;名義工資剛性;勞動力成本;新凱恩斯主義
引言
經濟發展的理論與實踐均表明,在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上升和人口結構的變化,往往會出現勞動力成本上升的現象。勞動力成本上升意味著勞動力市場存在上行的名義工資剛性。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認為名義工資剛性具有重要的宏觀經濟含義,因為名義工資剛性的存在使得勞動力市場難以實現出清,進而導致了失業的存在或勞動力資源的浪費。而從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名義工資剛性引起的失業擴大了潛在產出與真實產出之間的差距,進而產生了產出缺口,因而政策制定者需要實施相應的貨幣政策來促進經濟增長。正是基于此,已有的研究均認為名義工資剛性的上升會引起社會福利的惡化。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長期依靠“人口紅利”帶來的低勞動力成本優勢日漸消失,即中國勞動力市場出現了勞動力供給拐點,進而引起“用工荒”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這意味著中國勞動力市場存在上行的名義工資剛性[1]。那么,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是否導致了中國社會福利的惡化呢?
基于這一思路,本文將構建一個新凱恩斯主義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New Keynesian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以下簡稱NK-DSGE)以考察名義工資剛性與貨幣政策機制的變化對于社會福利的影響。不過,不同于大多數已有的NK-DSGE模型,本文在建模過程中考慮家庭的異質性消費偏好。在NK-DSGE模型中考慮這一因素的原因在于:第一,伽里等(Galí et al.,2007)[2]發現家庭消費異質性偏好對于消費以及實際工資等變量具有重要的影響,而這些變量與社會福利密切相關;第二,家庭消費偏好的異質性與中國的現實情形也較為接近,現實生活中,部分家庭或者家庭成員可能由于收入水平相對較低或者奢侈的消費習慣等原因,導致其消費行為偏好于將每期收入全部用完,這類家庭或者家庭成員的消費顯然與理性人平滑化一生消費的行為存在顯著差異。另外,已有的研究如劉宗明(2013)[3]、陳利鋒(2014)[4]以及陳利鋒(2014)[5]均發現對勞動力市場做出反應的政策機制具有相對較小的社會福利損失,本文將引入對勞動力成本上升做出反應的政策機制,并比較政策對勞動力成本上升敏感程度的差異對于社會福利損失的影響。
一、模型與假設
假設經濟中生存著無數個家庭,依據消費偏好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家庭追求一生消費的平滑化,因而會將部分收入用于儲蓄或物質資本投資和購買債券,這類家庭稱為優化家庭或者李嘉圖型家庭,其所占的比例為1-λ;另一類家庭則不儲蓄,沒有物質資本投資和債券投資,這類家庭將其每期收入全部用于消費,其所占的比例為λ。通過這一設定,在NK-DSGE模型中引入了家庭異質性消費偏好。家庭的效用與消費正相關,但與就業負相關;并且家庭的效用函數關于消費和就業可分。與蒙斯(Merz,1995)[6]類似設定,兩類家庭內部成員之間完全風險共擔。中間產品生產企業從兩類家庭中雇傭勞動力,并租賃李嘉圖型家庭提供的物質資本,進而生產具有一定差異的中間產品。通過最優價格設定,中間產品企業實現其利潤最大化目標。最終產品生產企業采用一定的技術將中間產品加總為最終消費品,并提供給家庭消費;最終產品企業面臨競爭性市場環境,其目標為利潤最大化。
1.李嘉圖型家庭
(1)
(2)
2.非李嘉圖型家庭或拇指法則家庭
(3)
式(3)實際上也構成了非李嘉圖型家庭的預算約束條件。
3.勞動力市場
(4)
家庭的另一個決策為勞動力供給決策,即在怎樣的條件下家庭成員愿意放棄閑暇(即消費)而供給勞動力。古典經濟學基于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分析家庭的勞動力供給,但是其對于勞動力市場的刻畫主要是基于完全競爭的設定。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則設定勞動力市場為非完全競爭的,由于不同勞動者的教育背景、所接受的技能培訓以及自身素質上存在一定的差異,因而不同勞動之間并不是完全替代的。與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所認為的那樣,只有在閑暇的機會成本(即實際工資)至少等于閑暇的收益(勞動與消費的邊際替代率)時,家庭才愿意供給勞動。具體地,兩類家庭勞動力供給條件為:
(5)
(6)
4.最終產品生產企業
(7)
式(7)具有雙重含義:一方面,當滿足這一條件時,最終產品生產企業實現了其利潤最大化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最終產品生產企業的生產活動是基于對中間產品生產企業產品的加總,因而式(7)也構成了中間產品生產企業所生產的產品的需求方程。其中,Pt(j)為第j類中間產品Xt(j)的價格,與已有的新凱恩斯主義模型類似,其與消費者物價指數Pt的關系為:
(8)
5.中間產品生產企業
實現中間產品生產企業成本最小化的一階條件為:
(9)
以上問題的約束條件為式(7)。其一階條件為:
(10)
其中,Mp=εp/(εp-1)為穩態時價格加成。中間產品生產企業的技術、雇傭的勞動力、成本最小化條件、邊際成本、定價方式以及調整價格的一階條件,構成了中間產品生產企業優化問題的主要行為方程。
6.政府的行為
7.市場出清
當勞動力市場均衡時,總就業等于各企業就業之和(也等于兩類家庭的就業之和),并且勞動力供給等于總就業與失業(Ut)之和。具體的,勞動力市場均衡條件為:
(11)
Lt=Nt+Ut
(12)
二、模型的參數化
一般而言,NK-DSGE模型的參數化方法包括校準和估計。本文同時采用這兩種方法,原因在于思科菲爾德(Schorfheide,2013)[8]發現采用單一估計方法往往造成待估計參數過多,進而造成模型參數估計的脆弱性。*這一研究促進了校準方法與估計方法的合流。當前已有的研究已經開始將這兩種參數化方法同時使用,這樣做減少了待估計參數的數量,進而有利于降低參數估計的脆弱性。為了規避這一問題,對于一些模型對其取值不敏感的參數,本文采用校準的方法進行參數化;*已有的研究往往對這類參數進行了較為精確的估計,因而可以直接采用。而對于已有研究中并未進行估計或者模型對其反映比較敏感的參數,本文采用中國的現實數據進行貝葉斯極大似然估計。
1.部分參數的校準
(1)主觀貼現因子β,依據中國2002年第1季度至2012年第4季度物價上升的速度進行估算,這一參數的取值約為0.98;物質資本的折舊率δ與資本的產出彈性α,依據何等人(He et al., 2007)[9]估計的結果,將其取值設定為0.04和0.6;非李嘉圖型家庭所占的比例λ,國內已有的研究文獻未對這一參數進行估計,國外相關研究將其設定為0.5,并且模型對于這一參數的取值敏感程度較低,因而本文沿用這一取值。
(3)穩態時資本調整成本函數的二階導數S″(δ)的取值,楊柳等(2014)[12]盡管對中國資本調整成本進行了估算,但是由于其采用的是科里和納森(Cogley&Nason,1995)[13]的形式,與本文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中使用的資本調整成本函數存在較大的差異,因而本文無法采用其估計的結果。張(Zhang,2009)[14]采用貝葉斯方法估計的結果表明這一參數的取值為δ-1,由于其設定的調整成本與本文具有較大的類似,因而本文采用這一估計結果。
2.樣本的說明與數據處理
由于本文貝葉斯極大似然估計過程中使用的數據全部為季度數據,而已有的研究表明,季度數據本身所具有的季節性趨勢對于模型估計的結果可能造成不利的影響。因此,本文采用X12方法對以上各個變量數據進行季節性調整,進而剔除季節性因素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本文采用CF濾波法剔除各個變量數據的趨勢性成分,僅保留周期性成分以用于貝葉斯極大似然估計。估計過程中所使用的所有變量數據的時間跨度均為2002年第1季度至2012年第4季度;所有數據均來自中經網數據庫。
3.貝葉斯極大似然估計的結果
基于以上設定,表1給出了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主要參數的先驗分布、先驗均值、貝葉斯極大似然估計值以及對應的90%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區間。
注:貝葉斯極大似然估計值及其90%置信區間均為保留小數點后4位數之后的值。
名義價格剛性θp的先驗均值的設定參考的是伽里等(Galí et al.,2012)[15]的取值,其貝葉斯極大似然估計值為0.710 9,與王君斌和王文甫選取的取值以及何等人估計得到的數值0.75較為接近;不同中間產品的替代彈性εp與不同勞動之間的替代彈性εw的貝葉斯極大似然估計值分別為1.637 3和1.866 9,這一估計結果與直覺相符,因為不同中間產品以及勞動并非完全替代;基準政策中利率對產出缺口與通脹的反應系數ry和rπ貝葉斯極大似然估計值分別為0.477 8和1.602 3。
三、模型動態分析
1.貝葉斯脈沖響應函數
基于貝葉斯估計的結果,可以對模型進行動態分析。通過計算外生沖擊的貝葉斯脈沖響應函數,可以得到外生沖擊下模型主要變量隨時間的動態變化路徑。不過,為了考察家庭異質性消費偏好的影響,本文分別計算了存在異質性消費偏好(λ=0.5)與不存在異質性消費偏好(這意味著λ=0)情形下主要變量的貝葉斯脈沖響應函數。基于篇幅考慮,圖1僅給出了外生總需求沖擊的貝葉斯脈沖響應函數。
圖1表明,1個單位標準差的積極(Positve)的總需求沖擊引起投資和物質資本的增加,進而引起產出的增加;總需求沖擊引起Tobin’s Q的上升,刺激企業增加投資,而企業投資的增加也促進了就業的增加和失業的下降;總需求的增加引起了物價的上漲,繼而推動了實際工資的上升和工資膨脹率的上升。
圖1還表明,異質性消費偏好的存在顯著性影響了外生沖擊對于模型經濟主要變量的沖擊性效應。具體表現為在不包含異質性消費偏好的模型中,外生總需求沖擊引起了產出、投資、物質資本等模型主要變量更大的反應。原因在于非李嘉圖型家庭并不進行物質資本投資,這一消費偏好降低了物質資本投資,進而降低了經濟中的物質資本、產出、就業。
2.名義剛性與社會福利分析
與吉安諾尼和伍德福德(Giannoni & Woodford,2003)[16]類似,本文采用對效用函數高階逼近的方式得到如下社會福利損失函數:
(13)
式(13)表明,社會福利損失由就業、通貨膨脹以及工資膨脹的波動引起。并且非李嘉圖型家庭的數量占比λ能夠影響社會福利損失。基于式(13),本文主要考察不同的名義工資剛性程度以及不同的貨幣政策機制對于社會福利損失的影響。首先設定名義工資剛性為0.1、0.2、0.3以及0.9、0.8、0.7,并基于此比較社會福利損失的變化。圖2左圖給出了當名義工資剛性θw的取值分別為0.1、0.2和0.3時的社會福利損失,可以發現隨著名義工資剛性的上升,社會福利損失逐漸下降,這意味著名義工資剛性的上升引起了社會福利的改善。這一結論與已有的研究不同,因為已有的研究認為名義工資剛性的上升會帶來社會福利的惡化。圖2右圖給出了名義工資剛性分別為0.9、0.8和0.7時的社會福利損失,可以發現隨著名義工資剛性的上升,社會福利損失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這意味著名義工資剛性的上升導致了社會福利的惡化。這一發現表明,工資自由度的增加會帶來社會福利的改進。顯然,這一發現與已有的研究所得到的結論是一致的。將以上分析得到的結論總結為如下命題一:
命題一:當名義工資剛性程度較低時,名義工資剛性的上升會引起社會福利的改善;而當名義工資剛性程度較高時,名義工資剛性的上升會引起社會福利的惡化。
命題一意味著并非在所有的情形下名義工資剛性的上升均會引起社會福利的惡化,只有在名義工資剛性較高的情形下,名義工資剛性的上升才會引起社會福利損失的惡化。這一結論對于中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勞動力市場出現“民工荒”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現象,這一現象意味著中國勞動力市場存在上行的名義工資剛性[1]。命題一的結論表明,這一現象的出現并不一定意味著社會福利的惡化,關鍵取決于中國初始名義工資剛性的大小。
3.政策機制的影響
已有研究發現,相對于基準政策機制而言,對勞動力市場做出反應的政策機制具有更小的社會福利損失。基于這一思路,本文引入一個對勞動力成本做出反應的政策機制,并基于這一政策機制分析政策對勞動力成本反應的敏感程度對于社會福利的影響。具體地,引入如下備擇政策機制:
(12)
為便于比較,設定貨幣政策沖擊的持續性系數ρr及其標準差σr均保持不變。分別選取rw的取值為0.5、1和1.5且名義工資剛性系數θw取值為0.3,并計算各自對應的社會福利損失。圖3表明,隨著貨幣政策對于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反應程度的增加,社會福利損失呈現下降的趨勢。這表明,貨幣政策對于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反應程度越強烈,社會福利損失越小。同樣,比較圖2與圖3可以發現,對勞動力成本上升做出反應的政策機制引起的社會福利損失相對較小,這進一步證實了已有研究的結論。
命題二:在名義工資剛性不變的前提下,對勞動力成本上升做出反應的政策具有相對較小的社會福利損失;并且政策對于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反應越敏感,政策引起的社會福利損失越小。
仍然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如果名義工資剛性和政策機制同時改變,將會對社會福利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本文基于式(14)估算了對應于不同名義工資剛性和貨幣政策機制的社會福利損失。表2表明,當rw的取值為0且名義工資剛性θw的取值由0.3下降至0.2時,社會福利改進的程度約為12.71%;當rw的取值為0.5、1和1.5時,同樣的名義工資剛性的變化引起社會福利的改進程度分別為15.22%、17.03%和21.88%。相反,如果名義工資剛性θw的取值由0.2增加至0.3時,對應的社會福利惡化的程度分別為11.27%、13.21%、14.55%和17.95%。這表明隨著貨幣政策對于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反應程度的增加,名義剛性的改變引起的社會福利損失變化的幅度越大。本文將這一發現總結為如下命題三:
命題三:對勞動力市場做出反應的政策機制擴大了名義工資剛性對于社會福利的效應。
四、結論與展望
在一個包含家庭異質性消費偏好與失業的中等規模NK-DSGE模型中,本文考察了名義剛性以及不同貨幣政策機制對于社會福利的影響。異質性消費偏好改變了家庭勞動與消費的邊際替代條件,也改變了最優工資設定條件,進而改變了外生沖擊下產出、就業、投資等主要變量隨時間變化的動態路徑。而基于社會福利損失函數估算的結果可以發現:第一,名義工資剛性的上升并不必然導致社會福利的惡化。具體地,在名義工資剛性較低的情形下,上行的名義工資剛性會引起社會福利的改善,而下行的名義工資剛性則會引起社會福利的惡化;在名義工資剛性較高的情形下,下行的名義工資剛性才會引起社會福利的改善。第二,貨幣政策對于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反應越敏感,貨幣政策引起的福利損失越小。第三,貨幣政策對于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反應越強烈,名義工資剛性對于社會福利的影響越大,即對勞動力成本做出反應的政策機制擴大了名義工資剛性對于社會福利的影響。
本文的發現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首先,政策制定者不用過分憂慮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問題,因為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對于中國社會福利的影響取決于初始名義工資剛性,因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并不必然導致中國社會福利的惡化;其次,當前中國社會就業形勢日益嚴峻,并且以往依靠經濟增長推動就業的做法成效并不顯著。基于本文的研究,在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條件下采用對勞動力市場做出反應的政策機制,具有降低社會福利損失的作用。
本文在一個未包含勞動力流動和市場分割的中等規模NK-DSGE模型中考察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對于中國社會福利的影響,然而現實經濟中中國存在顯著的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現象,如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正規部門與非正規部門勞動力市場分割等,并且這些因素對于勞動力市場具有顯著性影響。因而本文一個重要的研究擴展方向就是在模型中引入這些因素,當然,在引入這些因素之后可能會得到一些與本文具有一定差異且更具現實性意義的結論。
[1]徐建煒,紀洋,陳斌開.中國勞動力市場名義工資粘性程度的估算[J].經濟研究,2012(4):64-76.
[2]GALI′ J,LOPEZ-SALIDO J D,VALLES J.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consumption[J].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s Association,2007,5(1):227-270.
[3]劉宗明.工資加成、就業抑制與最優貨幣政策分析—貨幣政策是否應該對勞動力市場做出反饋?[J].南開經濟研究,2013(1):68-90.
[4]陳利鋒.貨幣政策應該對勞動力市場做出反應嗎?[J].浙江社會科學,2014(2):15-24.
[5]陳利鋒.二元市場、信貸摩擦與貨幣政策—貨幣政策應對勞動力市場做出反應嗎?[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14(2):83-95.
[6]MERZ M.Search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real business cycl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5,36(2):269-300.
[7]CALVO G A.Staggered prices in a utility-maximizing framework[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3,12(3):983-998.
[8]SCHORFHEIDE F.Estimation and evaluation of DSGE models:progress and challenges[A]//ACEMOGLU D,ARRELANO M,DECKEL E.Advances in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theory and applications[C],2013.
[9]HE D,ZHANG W,SHEK J.How efficient has been China’s invest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data[J].Pacific Economic Review,2007,12(5):596-617.
[10]王君斌,王文甫.非完全競爭市場、技術沖擊與中國勞動力就業—動態新凱恩斯主義視角[J].管理世界,2010(1):23-36.
[11]陳利鋒,范紅忠.房價波動、貨幣政策與中國社會福利損失[J].中國管理科學,2014(5):42-50.
[12]楊柳,王笑笑,王曉敏.經濟轉型時期的資本調整成本、技術沖擊與擴張性貨幣政策效果[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4(3):56-73.
[13]COGLEY T,NASON J M.Output dynamics in real-business-cycle model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5,85(3):492-511.
[14]ZHANG W.China’s monetary policy:quantity versus price rules[J].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2009,31(3):473-484.
[15]GALI′ J,SMETS F,WOUTERS R.Slow recoveries:a structural interpretation[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12,44 (2):9-30.
[16]GIANNONI M,WOODFORD M.Optimal inflation-targeting rules[A]//BERNANKE B S,WOODFORD M.The inflation targeting debate[C].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責任編輯:周 斌)
Does Upward Wage Inflation Deteriorate Social Welfare?
CHEN Life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Party School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Guangzhou 510053,China)
This article considers an NK-DSGE model with heterogeneous consumption and unemployment,and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the upward nominal wage rigidities caused by the raise of labor cost and monetary policy regimes on the social welfare.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downward nominal wage rigidities do not improve the social welfare definitely.When the nominal wage rigidities are very low,the upward nominal wage rigidities may improve the social welfare.The monetary policy’s react to labor cost amplifies the effect of nominal wage rigidities on the social welfare.This conclusion may be helpful for the monetary policy authorities.
heterogeneous consumption preference;social welfare;nominal wage rigidities;labor cost;new Keynesian
2014-10-19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城鎮間真實差距與中國城鎮化研究”(13BJL056)
陳利鋒(1982—),男,中共廣東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為貨幣與金融經濟學、勞動經濟學。
F061.4
A
1008-2700(2015)02-0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