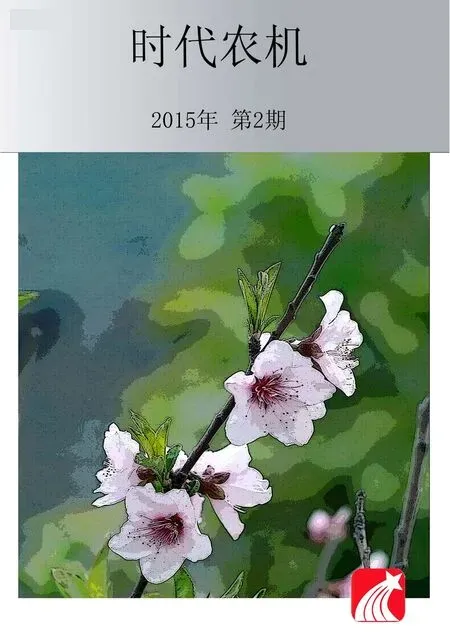清代永佃權性質概述
陳甲睿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3)
清代永佃權性質概述
陳甲睿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3)
清代永佃制是我國封建社會末期的一種新型的農業生產關系。永佃權是對田主土地產權的分割。它是佃農通過與田主協議的形式或斗爭的手段而獲取的一種特殊的土地權益——既可長久使用,又與田主共同占有了所耕作的租田。從這個意義上講,永佃農民與出租土地者是具有同等資格的兩個田主。
清代財政;永佃權;永佃權性質
1 土地“活賣”關系中的永佃屬性
這里講的“活賣”是一種以賣租為主的經濟現象,賣者與買者之間不存在產權的徹底變動問題,即土地主權并不真正轉移,而是買賣雙方結成合伙人,共同投資土地,共同食租。這是我國封建社會后期——明清時代陸續出現的一種特殊的土地租佃關系,它的存在和發展,逐漸地改變著傳統的土地經濟結構或農業生產關系。
清代文獻記到,江、浙、閩、粵、贛等省,特別是福建的云霄、漳浦、政和、龍溪等地方,自明朝以來,相沿有一田二主或一田三主的現象,其中有些就包含著永佃制關系。其形成或產生的情況,各地都大致相似。較為典型的是龍溪,該處在晚明濫征賦役、加派“三餉”的背景下,“邑民受田者(有土地的人),往往憚輸賦稅,而潛割本戶米(稅米)配租若干石,減其值以售,其買者亦利其賤而得之,當大造之年,一切糧差皆其出辦,曰大租主:有田者不與焉,曰小稅主,而租與田遂分為二”。就是說,土地所有者——后來的小稅主,為了讓別人來代替自己向官府納稅服役,便從本人所得的定額地租中(固定的)抽出一部分賤價賣給別人——大租主為代價,使對方也成了地租剝削者,與自己共同當田主(地主)。這實際上是雙方采用貨幣出納手段來劃分各自的地租收入的一種協作行為。學者劉堯庭曾說:“大租主,是土地的名義所有者,只取得地租的一部分,對政府承攬辦納賦稅、徭役。第二個叫做小租主(即小稅主),是實質上的土地所有者,只管征收地租,驅役佃戶,不納糧,不當差”。上面的所謂“租與田遂分為二”,就是指在以后的土地買賣中,小稅主可以賣地,大租主只可以賣租,不能干涉土地貿易之事:“得其租無田曰大稅主(大租主)”,“民間賣田契券,大率計田若干畝,歲帶某戶大租谷而已”。具體地說,賣田者是小稅主(小租主),在賣契上注明,買者每年要向大租主納租谷,即買者要把自己的地租收入分給大租主一部分,不能排除或排斥大租主,自己獨占田主的位置。這一小稅主的賣田活動(賣租)就構成了永佃權的基本內容——當小稅主(等于皮主或賠主)將此田賣給自耕農時(直接耕種土地的人)買者就成了向大租主交租的佃戶了,可同時買主又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他出價錢買得了這份地產,而大租主僅僅是其中一部分土地價值的所有者。由于買者雖然是佃戶,但卻和大租主共同掌握了土地所有權,所以大租主不能把這種佃戶趕走,實行自種或讓他人來租種土地,而必須讓其永遠佃種或長久使用,即承認其永佃權。這種土地永佃權,就是使用權和一部分所有權的結合。若耕者困難時,還可以將這部分田產(永佃權)再賣給別人;大租主(有時稱業戶)也可以將自已的這分田產(實際上是租谷)賣給別人。但不管怎樣交換,怎樣買賣,永佃權和所有權總是結合在一起的。
退一步說,即使是沒有后來這一連串的土地買賣活動,單就小稅主與大租主的關系講,也算大體上具備了永佃制的形式。小稅主一出現,就已經是永佃權的擁有者了,他對大租主來說,是交租的佃戶(形式上的),對耕種者——實際上的佃戶來說,他又是不折不扣的田主(地主)。所以,傅衣凌先生曾說:“小稅主(小租主)和皮主一樣,都是永佃權的所有者”。更為明顯、突出的事例是在廣東:史稱,粵南“惠陽的定額獲租制中,也有包租或包收田租的人們,俗稱為租客,這是與租額也很有關系的。惠陽和海豐的租客就是以前(清代)有威權而能抗稅的官僚巨商,一般小地主曾將所有田地活賣給他們(僅賣地租的一部分),所求得他們底保護,結果成了地主可賣田,而租客可賣租(指原來買取地主的那部分地租)。租客(相當于大租主),納糧輕而取租重。惠陽……每斗種(子)田,佃客(即佃戶)納田利(指地租)一石六斗給業主(地主),業主再納二斗谷給租客,租客只須納糧半升給政府”。在這里,我們可以更為清楚地看到業主(相當于小租主)身上的永佃農民性質。業主有著雙重的人格,他既掌握著主要的地產權,又享有佃種權——長久的使用權。此外的租客(相當于大租主),只購買了業主(地主)八分之一的土地價值——部分地租(名義上的或形式上的土地所有權),當然無權支配整個土地,在他出售所謂的土地所有權時(實際是一小部分所有權)只能出售所得的二斗租谷。地主將此田賣給自耕農時——“地主可賣田,租客可賣租”,買者同樣是向租客交租的永佃農民,他既有長久的使用權或永久的租佃權,而又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具體地說,該處田主從前是獨自占有或享受地租收入,而此時則是由田主拉攏別人入伙,與對方共同享受地租收入,共同剝削佃戶,即對方以較小的代價爭取到一個次要的二等田主的地位。這是一種以原田主為主體,以租客(新入伙者)為輔助的共同投資田產共同出租土地的新型的封建剝削方式。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晚清,政局動蕩,朝廷腐敗,割地賠款,民怨沸騰;內憂外患,四處交兵;國庫空,財政困難。為了維持殘局,清政府橫征暴斂,不斷地向人民加征苛捐雜稅,什么餉捐、防捐、隨糧捐、棉花捐、地畝攤捐,種種不經,難以枚舉。境內廣大人民紛紛破產,有很多人接連不斷地放棄部分土地所有權(賤賣或活賣土地),轉而謀求永佃權。特別是湖北天門、江樂平等地,百姓甚為苦累:“相傳該處農民欲逃避捐稅之累,故特將田低價售于富豪之家,惟保留其永久佃種之權”。一時間佃戶或佃民隊伍猛然增多,永佃權遍地出現。這些永佃權的存在,皆是以耕者保留了部分土地價值的所有權為前提或為基本條件的。
2 田產增值條件下的地權分割
永佃制在我國的南方較為多見,北方則很少。這是與南方普遍實行定額地租制有著很大關系的 (北方則較多地實行分成租制)。定額地租制給廣大佃戶帶來了很大的益處,也給永佃制產生或出現提供了客觀條件。廣大佃農為了維護和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一方面要繼續維護額租制,一方面又要爭取永佃權,以防止田主通過撤佃奪耕,使自己在租田上的利益受到損失。他們的理由一般是:長期為田主耕作,使田主的出租田不斷得到改良,并提高了土地本身的價值,故而應當得到永佃權。如清代江西人宣稱:“明季謝、閆二賊交織,凡閩廣僑居者思應之,皂隸何志源,應捕張勝、庫吏徐磯、廣東亡命徐自成、潘宗賜、本境(江西瑞金)慣盜范文貞等,效寧化、石城故,倡立田兵,旗幟皆書:八鄉均田。均之云者,欲三分田主之田,而以一分為佃人耕田之本。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無易人,永為世業”。意即佃農耕種地主的租田,付出了很多的工本,改良了地主的租田,提高了租田的地力、地質和地價,他們以工本為理由,要求得到永佃權,也就是要以工本為代價而換取地主三分之一的土地價值,將此三分之一的價值作為佃產或佃價——長期的耕作使用權。
3 永佃權的經濟影響
在一般情況下,田主雖然出資買回了上述新增的土地價值,但在定額地租制下,田主又不能從此新價值上獲得新地租,即不能在原額上加新額。田主只好再把這部分價值——田皮(永佃權)賣給新佃戶。這樣,不僅在佃戶之間互購田皮,而且在主佃之間也互購田皮(永佃權)?。從而在南方形成或出現了一田兩買之事:如廣東,用銀錢“買田收租納糧者名為糧業,出資買耕者名為佃業”。
永佃權是在交換的意義上出現的,它的價格因地而異,有高有低,是由其本身的價值決定的。在一些資料中可以看到,永佃權的價格和田主出賣租田的價格相等或稍低些,可是也往往有些永佃權(田皮)價格比田主的田產(田骨)之價還高。如陳盛韶在《問俗錄》中講:“田分根面,根系耕田納租,極貴;面系取租完糧,極賤”。在江西省的雩都,“田有田骨田皮,田皮屬佃人,價時或高于田骨”。這是因為永佃田經過耕者的努力后都成了肥沃土地,產量高而納租輕。即佃農使租田的新增價值超過了原來本身的價值,并將其居為已有(分割產權)。
當然,我們也不否認永佃權(田皮)的價格會受到供求關系的影響,但這是次要的,受價值關系的制約才是主要的。如有些極少數的永佃權是屬于單純的使用權——沒有創造新增價值。即個別佃戶因供求關系向田主買取了荒瘠田皮而取得永佃權,此田皮的價值幾乎是等于零,故價格也便宜,有時僅稍高于零。但一經佃戶的改良租田活動,田皮或永佃權就有了價值,價格也就會圍繞它(價值)上下波動。
一般講的永佃權,是以按時向地主交足地租為基本條件或前提的,否則就有被破壞被剝奪的危險。往往見“有田之家,或強奪佃者之田面(永佃權)以抵其租,而轉以售于人”。這又再一次地證明:永佃權與所有權之間有著不可忽視的連帶性,也就是說,土地使用權或耕作權與土地所有權雖已相對分行,但并沒有完全分離,有時甚到互為首尾。
就總體而言,永佃制是在我國封建社會后期,農業經濟相對發展之地區的產物,它以定額地租制為前提,分割地主土地產權,限制地租剝削,分明是佃農意志的體現。永佃制在一些區域的實行(特別是南方),曾于一定程度上調整了封建主義的農業生產關系,相應地刺激了佃農的生產積極性,從而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盡管永佃權是封建主義農業經濟的產物,不適應近代社會(易形成土地產權處分上的諸多糾紛),并在后來隨著封建制度的消亡而逐漸衰落下去,但是它曾經產生的歷史作用與經濟影響是應予以肯定的,我們有必要充分理解和正確認識它的經濟內含與經濟性質。
A overview of the Property of Emphyteusis in Qing Dynasty
CHEN Jia-rui
(Marxism College,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Hubei 430073,China).
emphyteusis in Qing dynasty was a new kind of productive relation at the end of the feudal society in our country.emphyteusis means the division of land property of the owners.It is a special land right which may be gained by the tenant peasants through concluding an agreement with the landlords or through conflicts,,the tenant peasants can exercise the right for a long time,and process the land along with thelandlords.In this perspective,both the tenant peasants and the land lessors are two landlords sharing the same qualification.
finance in qing dynasty;emphyteusis;,the property of emphyteusis
F329
A
2095-980X(2015)02-0122-02
2015-01-18
陳甲睿(1989-),女,河南人,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