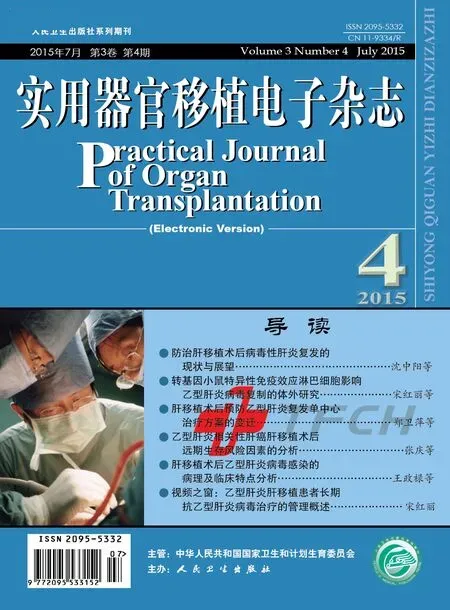肝移植患者的戊型肝炎病毒感染
張海明(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器官移植中心,天津 300192)
健康人群中戊型肝炎病毒(HEV)感染的流行特點因基因型和感染人群不同而異。它是包括肝移植在內的實體器官移植(SOT)受者慢性肝炎的病因之一。通過輸血傳播HEV是SOT患者感染的潛在來源之一。當移植物出現不明原因的肝炎時,應該提高警覺。免疫抑制可能在慢性感染的發病機制中起關鍵作用。肝移植受者似乎更容易發生急性感染后的慢性HEV感染,這會導致肝纖維化和肝硬化進一步加速發展。降低免疫抑制被認為是一線治療,而聚乙二醇干擾素被認為是肝移植受者的二線治療。目前,尚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使用利巴韋林對成人肝移植受者進行治療。
HEV屬于戊型肝炎病毒科(戊型肝炎病毒屬),是一種單鏈無包膜小RNA病毒。該病毒有3個重疊的開放讀碼框(ORF),ORF1編碼非結構蛋白(甲基轉移酶、半胱氨酸蛋白酶、解螺旋酶和HEV RNA聚合酶),用于病毒復制;ORF2編碼結構衣殼蛋白;ORF3編碼一種小型蛋白,與HEV復制有關,很可能從病毒感染的細胞內釋放出來[1-3]。
該病毒存在4種基因型(HEV1~HEV4),只形成1種血清型。HEV1和HEV2只在人類中發現,主要的傳播機制是糞口途徑,通過污染的水源傳播。亞洲和非洲病毒株為HEV2、HEV3和HEV4,可感染人、豬等哺乳動物。HEV3在世界范圍內分布,高發地區位于法國西南部的圖盧茲地區[4]。而HEV4在日本和中國曾被報道[5-7]。
1 HEV流行特點
在健康人群中HEV的流行特點因基因型和感染人群不同而異。HEV3和HEV4是發展中國家散發HEV病例的主要病原[8-9]。HEV感染在發展中國家可見散發的病例[5]。急性HEV感染通常表現為急性肝炎,有研究表明,血清抗體陽性率從30%~80%不等,主要影響年輕成年男性,病死率為0.2%~5%[10]。當研究對象中多數為妊娠女性患者時,病死率明顯升高(25%)[5,11]。HEV主要由糞便污染的水傳播,地方性感染也與動物傳播有關,來自感染的豬肉或野味,但很多病例沒有明確的感染源[12-13]。在歐洲、日本、新西蘭和美國,也已經有本土急性HEV肝炎的病例報道[5]。在美國,HEV相關的急性肝炎年發病率為0.7%,報道的血清陽性率為21%[14];其他發達國家血清陽性率少于5%,得出這些數據的檢測方法敏感性差異很大[5,15]。此外,誤診為藥物性肝損害的病例也較為多見。美國藥物性肝損害網的一項研究顯示,最初診斷為藥物性肝損害的患者中3%(9/318)為急性HEV[16]。英國的另一項研究表明,13% (6/47)的藥物性肝損害為急性HEV[17]。
2011年至2012年,在荷蘭的一項研究中,45 415次獻血者中,17次檢測到HEV RNA;同5 239次獻血者中,HEV免疫球蛋白G(IgG)抗體的血清陽性率為 26.7%(1 401/5 239)[18]。而采用相同的檢測方法,在英國西南部獻血者血清陽性率為16%[8],在法國西南部為 53%[4]。通過輸血傳播HEV是SOT患者感染的潛在來源,然而因為一般獻血人群HEV RNA血癥的低出現率,例行檢測獻血者性價比不高。
在法國西南的HEV高發地區,SOT患者HEV年發病率(HEV RNA陽性)為3.2%[19]。美國對送往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非甲型非乙型肝炎患者血液標本進行了一項研究,通過測定血清或糞便標本的抗HEV免疫球蛋白M(IgM),評估2005年至2012年HEV血清陽性率。結果顯示,17%(26/154)的標本檢測為HEV陽性,其中7例(27%)是SOT受者(肝2例、腎3例、腎胰腺聯合移植1例、心肺聯合移植1例)[20]。這些SOT患者均沒有出國旅行的經歷,他們感染的為本土HEV[3]。血清檢測anti-HEV IgM和IgG的敏感性和特異性為98%和95%。采用逆轉錄酶鏈反應(RT-PCR)檢測血清和糞便標本。患有HEV的SOT患者均沒有出現黃疸[21]。
2 肝移植受者HEV感染
2008年Kamar等[22]首次報道了法國南部慢性肝炎的病例。在該研究中,14例SOT患者(包括3例肝移植受者,9例腎移植受者和2例胰腎聯合移植受者)存在急性HEV感染,血清中發現HEV RNA。8例患者(57%)出現了慢性肝炎,血清轉氨酶持續高于正常水平,HEV RNA陽性,肝臟活檢有慢性肝炎病理表現;3例肝移植受者出現急性HEV后轉為慢性HEV,其中2例隨訪15~16個月發現,Metavir纖維化評分升高;8例SOT患者從移植到診斷為慢性肝炎的時間很短,白細胞計數、CD2、CD3、CD4和血小板計數降低。這14例急性HEV患者中,7例(50%)存在癥狀,包括乏力、關節痛和肌肉痛。所有病例病毒分型均為 HEV[3]。
此后有學者報道了2個肝移植受者出現慢性HEV感染后最終導致肝硬化的病例[23]。2例患者均進行了再次移植,其中1例在移植后10個月出現慢性肝炎復發,通過減少免疫抑制劑得以改善;2例均為HEV3感染。有報道表明,腎移植患者從慢性HEV進展至肝硬化的時間似乎更短[24]。總體上說,SOT患者HEV IgG的出現似乎不高于一般人群,所以感染的風險低[25-27]。然而當肝移植患者感染HEV時,增加了慢性感染和出現肝硬化的風險。荷蘭的一項研究報道了HEV在肝移植患者中流行情況[28]。在285例進行肝移植的患者中檢測到HEV感染的標志物,包括HEV RNA和HEV IgM和IgG抗體,肝移植術后HEV流行率為1%。根據移植后回顧分析冰凍血清標本HEV抗體的結果顯示,6例(2.1%)患者存在移植前HEV感染的證據,1例患者出現了慢性HEV感染,該病例移植后HEV RNA陽性,沒有出現HEV抗體,該患者肝移植后2~5年中經歷了輕度肝炎,通過HEV RNA、anti-HEV IgM和IgG、血清轉氨酶升高和組織學表現可以證實診斷。
當SOT受者急性感染HEV后,他們可能長期攜帶HEV。患者通常繼續存在HEV RNA陽性達數年,直至病毒清除,出現anti-HEV IgG陽性[26]。在1例73歲女性受者的報道中顯示,她接受了一個HEV感染的肝臟,移植物存在隱匿HEV感染導致的傳播[29]。移植前受者和供者的血清標本均為HEV抗體和HEV RNA陰性,然而在供者組織中被發現有高水平的HEV RNA。該受者在肝移植術后150天發現感染證據(anti-HEV IgG和IgM和HEV RNA),在15個月內出現肝硬化。
一些研究者對肝移植患者中伴有轉氨酶異常的移植物肝炎進行了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德國北部為5%[30],法國南部為10%[22]。德國北部一項單中心研究[30]評估了肝移植患者(226例)、慢性肝病的非移植患者(129例)和健康個體(108例)中HEV抗體出現情況,對肝移植患者也進行了血清HEV RNA檢測。肝移植患者被分為兩組,一組有移植物肝炎,一組無(通過肝酶升高來判斷移植物炎癥)。肝酶升高組中3例患者HEV RNA陽性,2例患者出現了慢性HEV3,其中1例在很短的時間內出現了嚴重纖維化(肝移植后22個月)。anti-HEV IgG抗體的出現情況為:肝移植患者中4.4%,非肝移植慢性肝病患者中3%,健康對照組1%。肝酶異常的肝移植患者中,anti-HEV的血清學轉換在發現血清HEV RNA后4個月出現,臨床上急性肝炎出現在肝移植術后5~7個月。西班牙的一項研究[25]評估了肝移植和腎移植受者anti-HEV IgG的情況,該研究包括了82例肝移植受者,21例腎移植受者和5例雙重器官受者。作者在3.6%(3/82)肝移植受者中發現anti-HEV IgG抗體,這些患者最初anti-HEV IgM和HEV RNA陰性,6個月后隨訪確認了anti-HEV IgG抗體陽性,但患者anti-HEV IgM和HEV RNA陰性,這就可以排除了急性和進行性的HEV感染。
法國的一項研究評估了700例SOT受者(腎移植529例,肝移植171例)中的HEV感染情況[19]。移植前抗HEV抗體(IgG和IgM)在14.5%(77/529)的腎移植受者中檢測到,其中肝移植為12.9%(22/171);移植前年度anti-HEV血清陽性率的8.7%到16.3%。SOT患者HEV感染的發病率為3.2例/每100人年。肝移植受者中,發病率為4.8例/每100人年,高于腎移植受者的發病率(2.7例/每100人年)。34例患者存在HEV感染,16例出現了慢性感染,其中47%存在血清HEV RNA檢測陽性大于6個月。18例患者的病毒血癥在急性感染后消失,他們中沒有人出現復發或再感染。多元分析顯示,HEV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為肝移植和移植年齡小(<52歲)。在歐洲和美國17個中心的一項回顧性分析中,對85例伴有HEV感染的SOT患者進行了評估[31]。56例患者(65.9%)出現了慢性HEV感染,這些患者包括46%的肝移植受者。一個單因素分析中,肝移植(相對于非肝移植)與慢性HEV感染相關,HEV診斷時他克莫司(相對于環孢素A)以及血小板計數降低是慢性HEV的獨立危險因素。
3 肝移植患者慢性戊型肝炎的治療
Kamar等2008年提出將存在HEV指標(定義為血清或糞便檢測到HEV RNA)持續超過6個月時可診斷為慢性HEV感染[22]。認為應將患者HEV血癥持續超過3個月作為新的慢性HEV感染的定義。他們研究了法國的77例SOT患者,這些患者在2004年至2012年間按標準診斷為HEV感染。之后Kamar等[32]進行了慢性HEV標準的修改試驗。他們通過RT-PCR檢測HEV RNA以確認HEV感染,對患者進行了1、3和6個月隨訪,直至病毒血癥清除[32]。共69例患者納入分析,59.4%(41/69)出現了慢性感染,HEV RNA只存在6個月;他們同時還發現所有HEV RNA轉陰的患者均在3個月時實現病毒清除。
還有研究發現慢性HEV的SOT受者,被發現CD4+細胞計數較低[22]。通過建議降低T細胞免疫抑制藥物(主要是鈣調神經酶抑制劑)的劑量,作為促進病毒清除的方法[33]。干擾素-α(interferon-α)信號通路(信號轉導活化因子1,STAT1)關聯的磷酸化過程在控制病毒復制方面起重要作用。通過使用HEV(A549)感染的細胞系進行體外研究表明HEV在抑制STAT1磷酸化通路和降低α-干擾素誘導的基因表達中的作用,能夠降低干擾素的抗病毒作用[34]。
聚乙二醇干擾素-α2a(PEG-IFNα2a)作為肝移植受者出現慢性HEV時的單藥治療方案[35]。3例患者接受了3個月的PEG-IFNα2a治療,在完成治療后24周和20周出現了病毒學改善。1例患者在完成治療后,出現了急性排斥反應,還有1例出現了HEV感染復發。干擾素治療被認為是誘發肝移植受者發生急性排斥的可能危險因素,由于它能增加急性排斥的風險,在腎移植患者中禁忌使用[35]。荷蘭的一個小組使用PEG-IFNα 2b治療2例肝移植受者[36]。1例患者治療了1年,第20周出現肝臟功能恢復正常和完全的病毒學恢復。另1例患者在第16周未出現病毒學上的恢復,停止了干擾素治療。然而當免疫抑制劑劑量減少后,肝功能測試恢復正常,患者血清HEV RNA轉陰。
使用利巴韋林治療1例伴有特發性CD4+T淋巴細胞減少癥和慢性HEV的胰腎聯合移植患者,利巴韋林12 mg/kg治療4周后肝功能恢復正常,病毒血癥被消除[37]。法國的一項研究評估了利巴韋林單獨治療6例HEV RNA陽性腎移植受者的情況。這些患者接受6個月的治療:4例患者存在持久的病毒學改善(SVR),2例患者在結束了利巴韋林治療后存在病毒復發[38]。利巴韋林已用于治療免疫健全患者的急性HEV3感染[39]。患者接受利巴韋林1 200 mg/d治療21天,肝臟功能、組織學異常和HEV RNA水平均明顯改善。
德國進行了一項前瞻性研究,評估了33例2008年至2012年間有HEV感染的SOT受者。45%患者(15/33)存在HEV RNA和轉氨酶水平升高大于2個月(病毒血癥延長)[40],免疫抑制劑減量治療在3/15例病毒血癥延長患者中消除了HEV血癥。接受利巴韋林治療的11例患者中,9例HEV RNA在3~6周后轉陰(中位時間5周),這些患者停止治療后無HEV感染復發,利巴韋林的治療劑量是每日600~1 000 mg。468例成人肺移植受者中,10例HEV RNA檢測陽性,發病率為2.1%[41]。8例患者出現慢性HEV感染,大于6個月時間內RT-PCR檢測陽性,2例患者接受利巴韋林治療400 mg,每日2次治療4個月,2個月后出現了HEV RNA轉陰,轉氨酶也恢復正常。
對于肺、心臟和腎臟移植患者,采用干擾素治療是禁忌的,因為排斥風險高。利巴韋林可作為慢性HEV患者一線治療的選擇[37,41-42]。免疫移植劑的減量對于肺和心臟移植受者可能不安全,這與肝移植受者不同[40,42]。利巴韋林單獨治療,在腎、心臟和肺移植的慢性HEV受者中似乎耐受和安全性良好,也能夠誘導持續病毒學應答(SVR)。然而,最佳的劑量和治療持續時間仍需經過進一步的研究確定。
總之,HEV感染在免疫抑制患者中是一個不常見的慢性肝炎病因,在SOT受者中的發病已有記載。慢性HEV的病情迅速進展,出現纖維化、肝硬化和移植物衰竭的情況,與肝臟移植受者相關性較強。直至目前,所有報道的病例均繼發于HEV3感染。SOT受者中急性或慢性HEV診斷的金標準是用RT-PCR檢測血清和(或)糞便中的HEV RNA。對不明原因的移植物肝炎患者,HEV感染需要作為鑒別診斷。有限的數據提示免疫抑制劑減量是慢性HEV感染的第一步治療,而對于肝移植受者的病例,PEN-IFN可能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