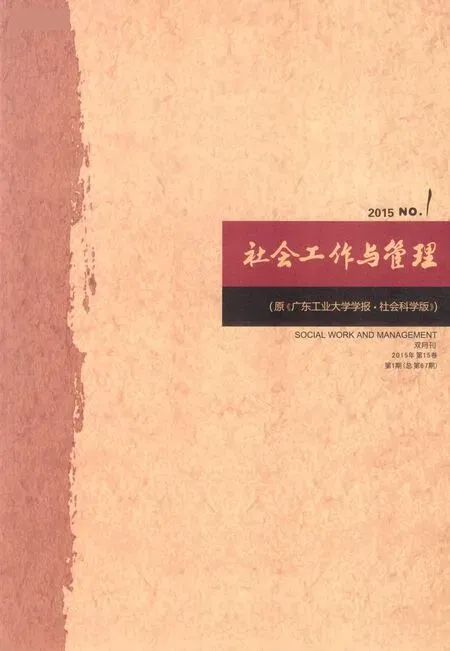美國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的發(fā)展及對(duì)中國的啟示
王曉慧,張婷旖
(1.中國勞動(dòng)關(guān)系學(xué)院工會(huì)學(xué)院,北京,100048;2.首都師范大學(xué)學(xué)校辦公室,北京,100048)
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是指將專業(yè)知識(shí)與方法運(yùn)用于工作場所,關(guān)注工作環(huán)境中員工的人性和社會(huì)的需求,通過設(shè)計(jì)和執(zhí)行適當(dāng)?shù)母深A(yù)措施,以確保健康的個(gè)人和工作環(huán)境的實(shí)現(xiàn)。[1]其起源于歐美,距今已有上百年的歷史,是社會(huì)工作最早發(fā)展起來的實(shí)務(wù)領(lǐng)域之一。本文試圖梳理美國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的發(fā)展歷程,以期對(duì)我國有所啟示與借鑒。
一、美國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的起源
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在早期被稱為工業(yè)社會(huì)工作(Industrial Social Work),第一位工業(yè)社會(huì)工作者出現(xiàn)在1875年。匹茲堡的海因茲公司設(shè)立福利秘書一職,由阿姬·杜恩(Aggie Dunn)女士為公司的年輕女性員工提供服務(wù)。自此之后的約半個(gè)世紀(jì)里,工業(yè)社會(huì)工作經(jīng)歷了發(fā)展和衰落的階段。
研究者波普爾(Popple)追溯了從1875至1930年間,社會(huì)工作在商業(yè)和工廠中的發(fā)展歷史,并識(shí)別其衰落的原因。他認(rèn)為,福利秘書的出現(xiàn)與當(dāng)時(shí)美國工商業(yè)領(lǐng)域內(nèi)的福利運(yùn)動(dòng)密不可分。19世紀(jì)末,美國工業(yè)化進(jìn)程加速,工業(yè)規(guī)模擴(kuò)大,勞動(dòng)力構(gòu)成發(fā)生改變,女性、移民更多地被雇傭。與此同時(shí),勞工裝病、破壞機(jī)器、流動(dòng)的比率也增高了,更多的工人加入了工會(huì)。為了應(yīng)對(duì)這些問題,資本家開始想辦法滿足工人的需要,為工人提供一系列福利項(xiàng)目,比如在企業(yè)內(nèi)部建立非營利的餐廳、商店、公寓、診所,為女工們提供健康有益的娛樂項(xiàng)目。[2]這些福利項(xiàng)目需要雇員來執(zhí)行,福利秘書職業(yè)應(yīng)運(yùn)而生。1900年之后,福利秘書人數(shù)開始增長,據(jù)美國勞工統(tǒng)計(jì)局1919年的調(diào)查顯示,美國的431個(gè)大公司中,有141個(gè)雇傭了至少一個(gè)全職的福利秘書,154個(gè)與外部機(jī)構(gòu)簽訂了社會(huì)工作服務(wù)合約。[2]
從事福利秘書工作的多為女性,她們通常具有教師或護(hù)士的背景,一些人有在慈善組織工作的經(jīng)歷。為雇員提供服務(wù)時(shí),她們經(jīng)常使用個(gè)案工作方法,解決工人的個(gè)人問題,如給予個(gè)人正確著裝的建議;當(dāng)工人遭受主管不公待遇時(shí),介入調(diào)節(jié);疏導(dǎo)工人的情緒等。也會(huì)使用小組工作方法,在工人中開展教育性的、娛樂性的、社會(huì)化的、性格塑造的小組活動(dòng)。她們的工作還包括一些行政職責(zé),比如管理所有雇員福利;培訓(xùn)、雇傭和解雇雇員;分配工作、定工資薪酬水平等。[2]
百貨商店、紡織廠是福利秘書們主要的雇主,她們主要為女性雇員服務(wù),后來擴(kuò)展至移民及整個(gè)工作群體。雖然福利秘書給予工人不少幫助,但她們實(shí)質(zhì)上是企業(yè)主管理工人的工具,所以工人不信任福利秘書,勞工組織也對(duì)她們的工作有強(qiáng)烈的指責(zé)。隨著20世紀(jì)30年代美國經(jīng)濟(jì)的大蕭條,福利運(yùn)動(dòng)衰退,加之工會(huì)的反對(duì),福利秘書被人事經(jīng)理取代了。當(dāng)時(shí)這個(gè)領(lǐng)域社會(huì)工作的教育更偏向于講授商業(yè)管理類的課程。1920年一系列社會(huì)工作研究都提到了工商業(yè)里的社會(huì)工作,都認(rèn)為它屬于商業(yè)管理。[3]
二、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者的再次出現(xiàn)與發(fā)展
福利秘書一度銷聲匿跡之后,美國的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在二戰(zhàn)期間再次出現(xiàn),為期較短。社會(huì)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數(shù)量,進(jìn)入到企業(yè)中。不同分支的軍事服務(wù)雇傭了專業(yè)受訓(xùn)的社會(huì)工作者,處理軍事人員與工作有關(guān)的許多問題。[4]最廣為人知的是全國海員工會(huì)和聯(lián)合海員服務(wù)的聯(lián)合項(xiàng)目。伯莎·卡彭·雷諾茲(Bertha Capen Reynolds)是其中特別有名的社工,她及同事們提供的服務(wù),成功地得到了海員和家屬認(rèn)可。1945年戰(zhàn)爭結(jié)束,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又再次衰退。
美國的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在20世紀(jì)70年代興起,隨著員工協(xié)助方案(EAP)在企業(yè)的推進(jìn),大量的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者開始進(jìn)入工作場所。[5]EAP為雇員及其家庭提供咨詢,處理包括情感、婚姻和行為—醫(yī)療問題。[1]據(jù)美國國家事務(wù)局統(tǒng)計(jì),全國的EAP項(xiàng)目在1950年代不到100個(gè),到1987年,則有10 000個(gè)。另一個(gè)評(píng)估顯示,在1986年,有12 000個(gè)咨詢項(xiàng)目服務(wù)于超過三分之一的普通勞動(dòng)者。[6]
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者大規(guī)模的出現(xiàn)與三個(gè)因素有關(guān)。首先,聯(lián)邦政府頒布了一系列與工作場所有關(guān)的法律,《職業(yè)安全健康法》《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就業(yè)年齡歧視法案》和《民權(quán)法案》的第七章以及《職業(yè)康復(fù)法案》的第五章對(duì)雇主和工會(huì)提出了新要求。[7]這些制度影響了雇主對(duì)待雇員的方式,是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出現(xiàn)的必要條件。其次,美國勞動(dòng)力構(gòu)成發(fā)生了巨變,女性、少數(shù)族群、殘疾人進(jìn)入勞動(dòng)力市場,尤其是已婚有孩子的婦女在其中的增長率很高。據(jù)統(tǒng)計(jì),1960年女性勞動(dòng)力的參與率是37.8%,1977年則攀升至48.4%。男性的參與率則從 1960年的84.0%降到了1977年的78.3%。同期已婚有小孩婦女的參與率增加了一倍多。[8]女性傳統(tǒng)角色發(fā)生了變化,沖擊了原有的家庭安排,家庭生活壓力增長,離婚率上升,小孩需要照顧的問題凸顯了出來。再次,工人不再只有經(jīng)濟(jì)方面的需求,他們希望被平等對(duì)待,既有經(jīng)濟(jì)方面的需求,還有心理和社會(huì)方面的需求。不僅企業(yè)主雇傭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者,工會(huì)在新形勢下,也改變了以往的立場,開始雇傭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者。有研究者認(rèn)為,從1960到1970年代,工會(huì)提供的社會(huì)服務(wù)受兩個(gè)宏觀發(fā)展的影響,一是進(jìn)入勞動(dòng)力市場的女性日益增長,構(gòu)成了服務(wù)增長的需求基礎(chǔ);二是福利國家的成熟。[9]
社會(huì)工作在工作場所運(yùn)用時(shí),所遇到的問題比其他的領(lǐng)域更復(fù)雜,因?yàn)槠髽I(yè)組織的穩(wěn)定和盈利的重要性超過對(duì)服務(wù)對(duì)象需要的關(guān)注,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者常遭遇價(jià)值觀上的困境。20世紀(jì)70、80年代,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快速推進(jìn)的時(shí)候,在研究和實(shí)務(wù)領(lǐng)域,存在著對(duì)其諸多的思考。在一篇題為“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有未來嗎?”的文章中,一位名為弗萊明(C W Fleming)的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者分析自己的工作,認(rèn)為在企業(yè)內(nèi)社工專業(yè)的邊界不清晰,專業(yè)技能水平低,可替代性強(qiáng),培養(yǎng)企業(yè)社工的大學(xué)課程設(shè)置不合理。其斷言,“除非社工能發(fā)展出工廠能使用并且能積極推銷的產(chǎn)品,否則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沒有前途。”[10]
研究者奧茲沃(Ozawa)認(rèn)為,工作環(huán)境中存在著諸如勞動(dòng)力構(gòu)成的變化、泰勒制下的勞動(dòng)異化、勞工不斷提高的預(yù)期等緊迫性問題。管理者和工會(huì)在尋找能應(yīng)對(duì)以上問題的專業(yè)人士,社會(huì)工作者是有機(jī)會(huì)的,通過提供服務(wù),產(chǎn)生工人、管理者、工會(huì)希望的結(jié)果。奧茲沃提出了工作場所社會(huì)服務(wù)的四階段模型。第一階段是處理一個(gè)或兩個(gè)特定的問題,比如酗酒或藥物濫用。第二階段是推進(jìn)更為全面的項(xiàng)目,因?yàn)槎喾N問題是互相關(guān)聯(lián)的。管理方或工會(huì)將會(huì)意識(shí)到酗酒或藥物濫用只是更大的、潛藏問題的癥狀。第三階段是組織化的介入,服務(wù)提供者可能參與同管理方和工會(huì)的協(xié)商,協(xié)商關(guān)于重組工作和工人關(guān)系的問題。第四階段,模糊管理方和雇員之間的界限,強(qiáng)調(diào)雙方有共同的利益。這四個(gè)階段從低級(jí)到高級(jí),對(duì)提供服務(wù)工作者的技能和知識(shí)的要求也會(huì)改變。在低階段,主要要求微觀介入技術(shù),工業(yè)心理學(xué)是必要的知識(shí)基礎(chǔ)。當(dāng)?shù)礁唠A段時(shí),要求宏觀能力,包括仲裁、協(xié)商、教育、咨詢的功能。要求工作者具有理解大型組織的知識(shí)基礎(chǔ),對(duì)其所處的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環(huán)境,以及影響它們的政治、經(jīng)濟(jì)力量都要了解。[8]奧茲沃四階段模型的提出,既可以視為對(duì)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的展望,也可以視為對(duì)當(dāng)時(shí)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實(shí)踐的批評(píng)。當(dāng)時(shí)推行的EAP項(xiàng)目依然是在微觀層面的介入,忽視了導(dǎo)致問題出現(xiàn)的工作環(huán)境因素。古金斯(Googins)和戈弗雷(Godfrey)指出,從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發(fā)源以來,一直都是臨床取向,重視解決個(gè)人問題,但如果它想對(duì)工作的性質(zhì)產(chǎn)生重要而持久的影響,就必須關(guān)注組織制度的改變。[1]
現(xiàn)實(shí)為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的教育提供了機(jī)遇和挑戰(zhàn)。相較于實(shí)務(wù)方面的進(jìn)展,教育相對(duì)滯后。梅登(Maiden)認(rèn)為,社會(huì)工作專業(yè)沒有站在為工作場所提供社會(huì)服務(wù)的前線,對(duì)于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的發(fā)展,一直沒有組織化的響應(yīng),直到1979年,全國社會(huì)工作者協(xié)會(huì)(NASW)和社會(huì)工作教育委員會(huì)(CSWE)才共同發(fā)起的一個(gè)項(xiàng)目,代表了推進(jìn)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的教育和實(shí)務(wù)的職業(yè)承諾。1982年,全國社工協(xié)會(huì)才組織了全國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特別小組。[3]20世紀(jì)70年代中期以后,美國的大學(xué)才提供專業(yè)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第一學(xué)位授予程序。建立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專業(yè)的有哥倫比亞大學(xué)、亨特學(xué)院、伊利諾斯大學(xué)、馬里蘭大學(xué)、錫拉丘茲大學(xué)、南加州大學(xué)。還有其他約15個(gè)大學(xué)提供雇員援助的特定課程,以及提供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的選修課程。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方向的學(xué)生要完成大量的實(shí)習(xí),要求九個(gè)月內(nèi)每周有三天的實(shí)習(xí),同時(shí)要接受有資質(zhì)的企業(yè)社工的督導(dǎo)。[3]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從業(yè)者要求取得碩士學(xué)位,哥倫比亞大學(xué)提供授予MSW-MBA的聯(lián)合學(xué)位教育。[11]
三、美國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的新變化
EAP項(xiàng)目是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者進(jìn)入就業(yè)場所的主要模式,到20世紀(jì)末期,中等規(guī)模或大公司三分之二的雇員被EAP項(xiàng)目覆蓋。[12]EAP模型所涵蓋的服務(wù)內(nèi)容日漸增多,從最初關(guān)注個(gè)人或人際關(guān)系的問題,到物質(zhì)濫用、殘疾、工作場所的健康和安全、離職的服務(wù),也包括對(duì)員工和管理者提供預(yù)防性騷擾、艾滋病等的培訓(xùn)。其他的非EAP項(xiàng)目,如工會(huì)會(huì)員援助項(xiàng)目、行為健康保健管理、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等亦有所發(fā)展。
20世紀(jì)90年代,經(jīng)濟(jì)的全球化與美國福利政策的重大轉(zhuǎn)變,要求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者突破傳統(tǒng)的提供服務(wù)的方式,面向新出現(xiàn)的就業(yè)人群,解決他們的就業(yè)問題。技術(shù)的進(jìn)步對(duì)勞動(dòng)力的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制造業(yè)向國外的轉(zhuǎn)移降低了美國國內(nèi)低端勞動(dòng)力的就業(yè)機(jī)會(huì)。在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上,信息服務(wù)業(yè)取代了制造業(yè),從事兼職或臨時(shí)性工作的新工人階層產(chǎn)生。[13]最大的挑戰(zhàn)來自福利政策的改變,以往的福利接受者必須要進(jìn)入勞動(dòng)力市場。
克林頓政府1996年頒布《個(gè)人責(zé)任與工作機(jī)會(huì)協(xié)調(diào)法案》,被普遍稱為“從福利到工作”。法律以TANF(貧困家庭臨時(shí)救助)取代了已實(shí)行60多年的AFDC(對(duì)有子女家庭補(bǔ)助計(jì)劃)。AFDC沒有時(shí)間限制,政府試圖通過TANF的實(shí)施,促使貧困家庭在兩年內(nèi)就業(yè)。所以TANF制度使得以往不用工作的福利接受者(多為單親家庭的育齡婦女)被迫進(jìn)入勞動(dòng)力市場,他(她)們?nèi)鄙倩镜穆殬I(yè)技能,許多人是第一次進(jìn)入勞動(dòng)力市場,找到的工作層次較低,工作難以維持,在精神上有巨大的焦慮和壓力。艾弗森(Iversen)認(rèn)為,近三十年來的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關(guān)注的是已經(jīng)被雇傭的工人,在政策發(fā)生改變的情況下,新的服務(wù)對(duì)象出現(xiàn)。企業(yè)社工們應(yīng)該系統(tǒng)性地運(yùn)用此前在工作場所積累的專業(yè)知識(shí)和技能的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將之運(yùn)用在從福利到工作的環(huán)境中。企業(yè)社工要重構(gòu)經(jīng)驗(yàn),同時(shí)在多個(gè)系統(tǒng)層次上扮演多面向的角色。[13]梅登(Maiden)提出,把 EAP 變?yōu)閭€(gè)案管理模式,優(yōu)先供給TANF制度下的前福利接受者,長期(1—2年)提供,兩周聯(lián)系他(她)們一次,做好預(yù)防酒癮、藥物濫用復(fù)發(fā)的工作。從社會(huì)工作人在環(huán)境中的視角,在個(gè)體和組織層面介入。因?yàn)榉?wù)對(duì)象女性居多,此個(gè)案管理模式要使用性別敏感評(píng)估。[3]
新形勢的轉(zhuǎn)變對(duì)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莫爾-巴拉卡(Mor-Barak)等認(rèn)為,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者、工作程序與社工教育從20世紀(jì)70年代以來是分離的。當(dāng)EAP在個(gè)人和組織層面介入時(shí),企業(yè)社工具有多樣性的角色,實(shí)踐要求整合的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實(shí)務(wù)教育,作為社會(huì)工作專業(yè)的實(shí)務(wù)領(lǐng)域之一。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要同社會(huì)工作專業(yè)的價(jià)值觀和倫理保持一致,在教學(xué)中,一定要有社會(huì)議題。他們以南加州大學(xué)的碩士課程為例,介紹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的教育課程要教授社會(huì)工作專業(yè)學(xué)生總體的價(jià)值觀、權(quán)利和責(zé)任,重視學(xué)生的能力,為學(xué)生提供在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領(lǐng)域運(yùn)用的機(jī)會(huì),讓學(xué)生理解此領(lǐng)域與多樣化的領(lǐng)域的相似與相異。[14]
四、美國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的發(fā)展對(duì)中國的啟示
我國內(nèi)地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21世紀(jì)初剛起步,在深圳、上海、蘇州等地已進(jìn)行一些實(shí)踐。美國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的發(fā)展,對(duì)中國有如下啟示與借鑒。
(一)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在應(yīng)對(duì)勞動(dòng)問題上有優(yōu)勢,我國應(yīng)重視這一領(lǐng)域的發(fā)展
在美國工業(yè)化的過程中,勞動(dòng)問題叢生,現(xiàn)實(shí)需求使社會(huì)工作得以應(yīng)用在企業(yè)界。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有專業(yè)價(jià)值觀、知識(shí)與技巧,它在美國有不同的發(fā)展階段。雖然爭議和困難始終伴隨,但依然是應(yīng)對(duì)勞動(dòng)問題,為員工服務(wù)的有效方式。不僅能夠整合資源,預(yù)防、解決問題,發(fā)展員工的能力,也為企業(yè)組織的效率提升、人性化工作環(huán)境的實(shí)現(xiàn)提供有力支持。當(dāng)前中國正處在城鎮(zhèn)化加速發(fā)展階段,截止到2010年,中國就業(yè)總數(shù)為7.61 億人。[15]從計(jì)劃經(jīng)濟(jì)向市場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中,中國的勞動(dòng)力構(gòu)成發(fā)生了巨變。2013年國家統(tǒng)計(jì)局發(fā)布的《2012年我國農(nóng)民工調(diào)查監(jiān)測報(bào)告》顯示,截至2012年末,我國農(nóng)民工總量達(dá)到26 261 萬人,已超 2.6 億人。[16]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企業(yè)職工面臨著諸多問題,比如基本權(quán)益受損、維權(quán)機(jī)制不健全、工資薪酬待遇低、精神健康需求得不到滿足、工作壓力大,工作與生活難以平衡。在農(nóng)民工群體那里,這些問題更為突出。在美國工業(yè)化早期出現(xiàn)的問題也出現(xiàn)在我國,雖然兩國國情不同,但在勞動(dòng)問題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在中國的發(fā)展具有很大的潛力,是當(dāng)前亟待發(fā)展的領(lǐng)域,我國政府、社會(huì)組織、企業(yè)、高校要重視這個(gè)領(lǐng)域,促進(jìn)新型勞動(dòng)關(guān)系的構(gòu)建。
(二)政府應(yīng)加強(qiáng)與完善勞動(dòng)立法,為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有利的制度環(huán)境
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最初在美國的出現(xiàn),由企業(yè)管理者的個(gè)人行為推動(dòng)。20世紀(jì)70年代大規(guī)模的發(fā)展,則與國家力量的介入密不可分。聯(lián)邦政府一系列在勞動(dòng)領(lǐng)域的立法帶來了勞動(dòng)力的變革,工人們的工作與生活不再割裂,工作場所不僅具有經(jīng)濟(jì)功能,還具有社會(huì)功能。立法賦予了勞動(dòng)者福利權(quán)利,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的實(shí)踐具有堅(jiān)實(shí)的制度基礎(chǔ)。中國政府近年來致力于勞動(dòng)力市場的制度建設(shè),1994年《勞動(dòng)法》的頒布奠定了我國勞動(dòng)立法的基礎(chǔ),2008年實(shí)施的《勞動(dòng)合同法》被認(rèn)為是中國就業(yè)保護(hù)的標(biāo)志性法律,此后中國政府相繼出臺(tái)了《最低工資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yè)促進(jìn)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dòng)爭議調(diào)解仲裁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guī)。雖然立法成績顯著,但距建立完備的勞動(dòng)法律體系還有一定的距離。[17]現(xiàn)行法律沒有徹底扭轉(zhuǎn)資強(qiáng)勞弱的格局,勞動(dòng)者的權(quán)利沒有受到充分的重視。基于此,中國內(nèi)地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的發(fā)展欠缺制度的支持。以廣受學(xué)者關(guān)注的珠三角的實(shí)踐為例,該地區(qū)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實(shí)務(wù)的開展,主要源于兩大力量:一是政府加強(qiáng)社會(huì)工作人才隊(duì)伍建設(shè)的“項(xiàng)目購買”試點(diǎn),推動(dòng)了社會(huì)工作民間組織實(shí)施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服務(wù)項(xiàng)目;二是企業(yè)社會(huì)責(zé)任運(yùn)動(dòng)促使草根民間組織或者企業(yè)推行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服務(wù)。從珠三角地區(qū)目前的發(fā)展?fàn)顩r看,第一條顯然更加重要并起到主導(dǎo)作用。[18]筆者在實(shí)地調(diào)研中發(fā)現(xiàn),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雖有所發(fā)展,但并沒有大規(guī)模出現(xiàn),勞動(dòng)立法不完善、執(zhí)行不力是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者面對(duì)復(fù)雜的勞動(dòng)問題,倍感無力的重要原因。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回應(yīng)勞動(dòng)問題,應(yīng)有國家力量的介入,對(duì)勞動(dòng)者形成制度保護(hù)。社會(huì)工作是福利制度上的一環(huán),制度不完善,只靠社會(huì)工作者的推進(jìn),力量非常弱小,可持續(xù)性不強(qiáng)。
(三)以工會(huì)為依托,推進(jìn)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的發(fā)展
美國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發(fā)展歷程中,工會(huì)最初持反對(duì)態(tài)度,后來工會(huì)意識(shí)到工人除了經(jīng)濟(jì)需求,還有心理和社會(huì)需求,就開始接納企業(yè)社工,或吸收社工進(jìn)入工會(huì)體系,或與社工機(jī)構(gòu)建立聯(lián)系,為工會(huì)會(huì)員提供服務(wù)。中國工會(huì)與美國工會(huì)體制不同,但既為工會(huì),其基礎(chǔ)都是工人,工會(huì)如要得到工人的認(rèn)同,必須要維護(hù)職工權(quán)益,為職工服務(wù)。自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工會(huì)一直具有傳遞國家福利給職工、為職工提供服務(wù)的傳統(tǒng),基層企業(yè)工會(huì)積累了大量的經(jīng)驗(yàn)。其提供福利與保障的工作被視為中國行政性、非專業(yè)化的社會(huì)工作。[19]轉(zhuǎn)型時(shí)期,工會(huì)工作的理念、工作方式必須轉(zhuǎn)變,工會(huì)要切實(shí)關(guān)注工人的利益。福利同樣是一種權(quán)利,維護(hù)職工的福利也是工會(huì)維權(quán)的表現(xiàn)。在加強(qiáng)福利服務(wù)上,工會(huì)可以通過引入社會(huì)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實(shí)現(xiàn)向服務(wù)型工會(huì)的轉(zhuǎn)變,尊重并幫助工人實(shí)現(xiàn)主體性,深遠(yuǎn)意義更在于構(gòu)建新型勞動(dòng)關(guān)系,為社會(huì)治理體制的創(chuàng)新發(fā)揮作用。社會(huì)工作受一個(gè)國家或地區(qū)文化和制度的影響,我們在發(fā)展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時(shí),既要有國際化的視野,又要重視本土的制度資源、文化背景、實(shí)務(wù)經(jīng)驗(yàn)。中國工會(huì)具有獨(dú)特的地位和較完備的組織體系,是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發(fā)展可以依托的主渠道。
(四)加強(qiáng)企業(yè)社工專業(yè)教育,提升實(shí)務(wù)工作者的能力
美國的一些高校為企業(yè)社工的人才培養(yǎng)做出了貢獻(xiàn),企業(yè)社工面對(duì)的問題更具復(fù)雜性,對(duì)人才的要求非常高。社會(huì)工作是強(qiáng)調(diào)實(shí)務(wù)的專業(yè),企業(yè)社工更應(yīng)具有實(shí)務(wù)能力。我國高校社工教育發(fā)展迅速,在老年社會(huì)工作、青少年社會(huì)工作、婦女社會(huì)工作、社區(qū)社會(huì)工作等領(lǐng)域推進(jìn)較快,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教育還很薄弱。建議有志于發(fā)展企業(yè)社工的院校,開發(fā)出合適的課程體系,打造高素質(zhì)的教師專業(yè)團(tuán)隊(duì)。鼓勵(lì)專業(yè)教師通過項(xiàng)目合作等方式進(jìn)入工作場所,積累實(shí)務(wù)經(jīng)驗(yàn),增進(jìn)理論與實(shí)務(wù)的融合。在加強(qiáng)國際交流的同時(shí),探索本土的經(jīng)驗(yàn),培養(yǎng)出大批優(yōu)秀的企業(yè)社工人才。
[1]GOOGINS B,GODFREY J.The evolution of occupational social work[J].Social Work,1985(9/10):396—402.
[2]POPPLE P R.Social work practice in business and industry,1875—1930[J].Social Service Review,1981,55(2):257—269.
[3]MAIDEN R PAUL.The evolution and practice of occupational social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J].Employee Assistance Quarterly,2001,17(1/2):119—161.
[4]POPPLE P R,LEIGHNINGER L.Social Work,Social Welfare and American Society[M].5th ed.Boston:MA.Allyn&Bacon,2002:n/a.
[5]TANNER R M.Social work:the profession of choice for EAPs[J].Employee Assistance Quarterly,1991,6(3):71—83.
[6]RAMANTHAN C S.EAP’s response to personal stress and productivity:Implications for occupational social work[J].Social Work,1992,37(3):234—239.
[7]KURZMAN P A,AKABAS S H.Industial social work as an arena for practice[J].Social Work,1981(1):52—60.
[8]OZAWA M N.Development of social services in industry:why and how?[J].Social Work,1980(11):464—470.
[9]MARTIN J G T.Social services and women’s work[J].Social Service Review,1985(3):62—74.
[10]FLEMING C W.Does social work have a future in industry?[J].Social Work,1979(5):183—185.
[11]AKABAS S H,AKABAS S A.Social services at the workplace:New resource for management[J].Management Review,1982(5):15—20.
[12]ROOT L S.Social work and the workplace[M]//M REISH,E GAMBRILL.Social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Thousand oaks,CA:Pine Forge,1997:134—142.
[13]IVERSEN R R.Occupational social work for the 21st century[J].Social Work,1998,43(6):551—566.
[14]MOR BARAK,MICHAL E.A model curriculum for occupational social work[J].Social Work Education,1993,29(1):63—77.
[15]蔡昉.人口與勞動(dòng)綠皮書 中國人口與勞動(dòng)問題報(bào)告[M].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2:188.
[16]國家統(tǒng)計(jì)局.2012年我國農(nóng)民工調(diào)查監(jiān)測報(bào)告[R/OL].[2014-10-26].http://www.gov.cn/gzdt/2013-05/27/content_2411923.htm.
[17]關(guān)懷.改革開放30年勞動(dòng)立法的回顧與展望[J].法學(xué)雜志,2009(2):10—13.
[18]李曉鳳.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社區(qū)綜合發(fā)展模式”的運(yùn)作路徑初探——以深圳某工業(yè)型社區(qū)的企業(yè)社會(huì)工作實(shí)務(wù)介入為例[J].社會(huì)工作,2012(2):13—16,44.
[19]王思斌.社會(huì)工作概論[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