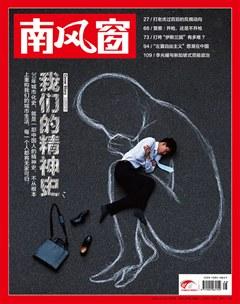警察:開槍,還是不開槍

編者按:
人民警察是可以合法使用武器的特殊人群,承擔著打擊犯罪,保衛人民的神圣使命。按照法律規定,有些情況下,要求警察敢于開槍,比如面對暴力恐怖分子正在實施危害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的嚴重犯罪行為;但在更多情況下,卻要求警察要謹慎開槍。這對人民警察應對復雜的情況、判斷能否開槍提出了技術性很高的要求。作為教育部重大攻關課題《完善基層社會治理機制研究》的前期工作,華中科技大學副教授呂德文在中部某縣公安局做了半個多月的實地調研,得到了公安局領導和基層干警的支持。他調研并真實記錄了基層警察用槍的一些情況,探討了用槍的現實和法律問題。
警察的重要標志就是可以合法地使用警械,比如槍支。
過去,警察濫用槍支的情況并不少見,以至于在上世紀90年代以后,公安部加強了對槍支的管理,情況因此有所改變。現在,一些地方的某些警種,在警務實踐中已甚少使用槍支,甚至“警察開槍”有時候會成為新聞事件。
最近我們在中部某縣公安局的調研發現,現在不少公安局內部人士都認為開槍實在是“麻煩”,原因很復雜。
通常情況下,槍支是基層民警擁有的最高強度的暴力。因其殺傷力強,具有震懾力,一度成為民警必備的武器,也的確在警察專政功能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正因為此,槍支也成為警察濫用權力的罪魁禍首。盡管濫用槍支的情況并不多見,但因其具有致命性,一旦發生警察違規使用槍支傷及無辜的事件,對警察的公信力就會造成很大傷害。這也給警察用槍管理帶來了挑戰。
首先,槍支是致命武器,從管理的角度上看,幾乎是不容許出現意外的,公安局和配槍民警都不愿意這個意外發生。但從概率上說,只要配槍,就不可能百分之百保證不出現意外。
公安機關強調紀律性,強調按相關法律規定進行嚴格的槍支管理,所以到了基層公安核心就變成如何嚴格執行的問題。比如,在公務活動的間隙飲酒,很容易因神志不清而濫殺無辜。為了杜絕此種情況的發生,2003年公安部頒布了五條禁令,其中前兩條都是關于槍支管理和使用的。分別是嚴禁違反槍支管理使用規定,違者予以紀律處分;造成嚴重后果的,予以辭退或者開除;嚴禁攜帶槍支飲酒,違者予以辭退;造成嚴重后果的,予以開除。但在基層實際執行中,一些地方還是出現了公務期間喝酒甚至酒后用槍的情況。
其次,盡管公安機關對槍支使用有嚴格規定,但在很多情況下難以判斷當時的場景是否適合使用槍支,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發更大問題。
當前,利益沖突和社會分化較為劇烈,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之間的轉化也較為復雜,在抗爭事件和群體性事件中,公安機關如何使用槍支是一個技術難度較高的動作。一方面,開槍是最為有效的防止群體性事件失控的手段,另一方面,開槍也非常可能是制造進一步混亂,甚至釀成政治事件的導火索。因此,槍支使用非常考驗人。客觀分析,一些群體性事件之所以演化為打砸搶的騷亂,與現場處警不夠果斷有密切關系;另一方面,也應看到,一些群體性事件之所以升級,恰恰是因為某些一線民警濫用槍支。
再次,哪怕是符合相關槍支管理和使用規定,大部分群眾仍然難以理解警察開槍的行為,群眾也形成了槍口不能對準老百姓的觀念。比如,2012年9月24日發生的遼寧盤錦拆遷現場民警開槍導致一村民中槍身亡事件,就掀起軒然大波。官方調查最終認定:民警接110出警,并非警察參與征地拆遷。出警后,遭拆村民王某和家屬潑汽油、追砍。在王某點燃衣服撲向民警時,受到威脅的民警開槍。盡管民警開槍合法,但此事還是引起輿論爭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對警察開槍的排斥感。
因此,一方面,公安機關無法百分之百完全杜絕警察濫用槍支,另一方面,客觀上又必須讓警察配槍,這就造成了槍支管理的兩難。從我的調研情況看,公安機關對槍支的管理是較為嚴格的,但警察不敢開槍,沒有能力開槍的問題也是值得重視的。
昆明暴恐案之后,公安部要求各地加強反恐工作,警察配槍巡邏是其中的一項重要措施。但就在這個措施實施不久,就連續發生多起警察開槍事故。這說明,很多基層民警一般情況下是不敢開槍的,但一旦遇到需要開槍的時候,開槍事故卻容易發生。
從我調研的情況來看,僅僅是20年前,農村警務實踐仍然是槍不離手。一位老公安講了一件他親身經歷的故事,很能說明警察開槍的辯證法。1992年,彼時的老公安還是一個年輕小伙子,剛剛從警校畢業參加工作,被分配到一個鄉村派出所。據這位老公安回憶,他剛到派出所工作的時候,所長就將所里唯一的一支步槍讓其佩戴。因此,每次跟隨所長出警的時候,總要背上這支步槍。久而久之,派出所極具權威,鄉政府要做一些中心工作,也要派出所民警參與。他雖然只是一個毛頭小子,卻也具有無上權威。有一次,街上一個人高馬大的小混混和人打架,個子矮小的他竟然獨自將其抬起來,吊在派出所倉庫,而小混混不敢反抗。事后,這位小混混每次碰到他都點頭哈腰,而他每次都一腳踢在小混混的屁股上,讓其趕緊滾。
1993年3月3日,當地發生了一起群體性事件,十幾個下鄉征收農業稅費的鄉干部與村民發生了沖突,村民敲鑼打鼓把鄉干部圍困起來。派出所接到報案時,所里只剩這位剛來不久的年輕民警在值班,其他民警都因公務外出了。情況緊急,這位年輕民警背上槍立馬騎上摩托車出警,達到現場后命令村民散開,毫不費力地把十幾個鄉干部救了出來。
這位老公安分析,如果這個群體性事件發生在現在,他肯定不敢一個人前去處理,也不可能像當時一樣大義凜然地對村民發號施令。
時過境遷,警察用槍情況的變化原因主要基于以下兩點:
第一,上世紀90年代開始,公安部發布了一系列內部文件,對警察執法行為進行了整頓。比如,禁止警察參與非警務活動,禁止聯防隊員有執法行為,嚴禁刑訊逼供。尤其是關涉槍支使用,出臺了更為嚴格的規定。1996年,國家發布了《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只有在15種列舉情形下才能開槍。同年出臺的《槍支管理法》,對公安機關的槍支管理做出了嚴格規定,警察配槍也受到了限制。這些規定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過度使用暴力、濫用槍支的行為,是法律上的硬約束。
第二,上世紀90年代以來,依法行政在警務思想里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傳統區分“敵人”與“群眾”的思維無法有效指導警察的一線實踐。警察開槍需要一定的意識形態支持。長期以來,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支配了警務實踐,警察在面對“專政敵人”時,可以采用暴力手段;而在面對群眾時,則主要依靠思想工作。上世紀80年代以來,基于階級劃分的“敵人”與“群眾”已經不存在,導致警務工作很難再有效地區分以采取暴力手段或思想工作。比如,在依法行政理念下,只要沒有犯法,那些為當地老百姓所深惡痛絕的小混混也是“公民”,警察不能對其懲罰。一樣的道理,在群體性事件現場,有的“群眾”事實上已經違法,甚至還比較嚴重,就不能因為他們是“群眾”而不去采取暴力強制措施。
1996年《槍支管理法》和《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頒布后,公安機關的槍支管理變得極為嚴格。為了防止違反條例被追責,許多地方的基層公安局在警務實踐中甚至盡量避免使用槍支。因此,近20年來,有些民警實際上是摸不到槍的。
不僅如此,很多基層民警開始大量承擔另一種形式的非警務活動。這種情況直接造成一個客觀現實:基層民警沒有多少時間參與訓練,而在日常的警務實踐中又沒有“實戰”機會,民警用槍的處置能力和戰斗素養難免下滑。我們訪談過一個1997年進入公安局的民警,據他回憶,他只參加過3次訓練,正式進入公安隊伍之前有過3個月的訓練,昆明暴恐案后全國公安系統大練兵訓練過半個月,中間只訓練過一次。他坦言,他只在這3個訓練中摸過槍。
開槍是技術性要求非常高的活,可想而知,缺乏足夠的訓練,要應對復雜情況,判斷能不能開槍,以及開槍的效果,是非常困難的。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另外,警察隊伍也發生了變化。在1997年以前,民警主要來源于兩大群體:一是從退伍、轉業軍人中招募;二是從警校畢業生中分配。但此后,縣公安局民警由市公安局、人事局統一招錄,民警的錄用需要通過統一的考試,尤其是現在,只能經過公務員考試。據統計,全縣公安系統的民警不到300人,真正警校畢業的民警不到一半,還有一多半都是通過公務員考試進來的。
顯而易見的是,從概率上說,非警校畢業生的戰斗綜合素養肯定不如警校畢業生高。由于條件有限,縣公安局沒有建立輪訓機制,唯一能夠保證戰斗素養訓練的機會,就是正式入職前3個月的集訓。僅僅通過3個月來訓練戰斗素養,顯然是不現實的。
從我們的調研情況看,不少地方的基層民警的職業素養堪憂。由于缺乏輪訓制度,基層單位也不可能建立日常訓練制度,再加上民警工作壓力大,民警的身體素質不一定很好。因此,普通民警只能執行一般任務,稍微遇到反抗,就有可能難以駕馭。2013年,該縣公安局曾經出過一起典型,當時幾個民警抓一個歹徒,其中一位民警在執行任務中奮不顧身與歹徒搏斗,結果被歹徒捅了幾刀。公安局領導覺得這種行為應該受到表彰,可報送到縣委縣政府,卻壓了下來。因為,縣領導擔心,一旦對這個民警做宣傳,效果可能適得其反:老百姓會懷疑,民警的素質怎么那么差,幾個民警連一個歹徒都對付不了,反而還受傷了!公安局內部,尤其是這位民警的直接領導覺得非常委屈,卻又無可奈何。
普通搏斗技能尚且如此,何況是開槍?開槍不僅需要射擊技能,且考驗民警的心理素質,由于開槍有條件限制,還要求民警對現場做出準確判斷。如果一個民警沒有經過嚴格訓練,沒有進行日常培訓,如何能達到開槍的技術性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