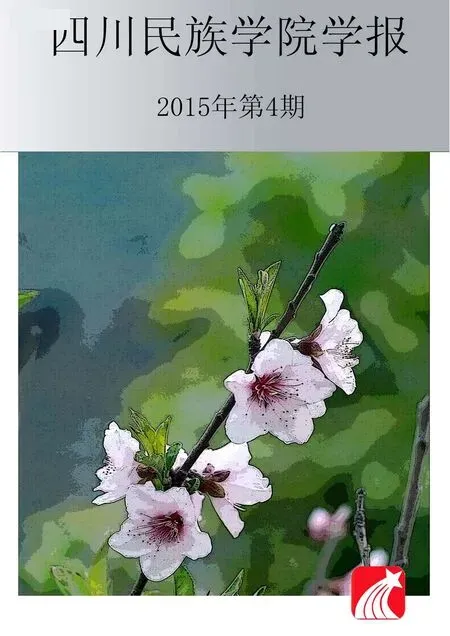中國 “自畫像”的演變
劉 爽
一、自畫像的記載與起源
回顧西方美術史的發展歷程,發現許多美術大師都為后世留下了記錄自己形象的自畫像、自雕像。中國古代的畫家卻鮮有自畫像傳世,以至于提到自畫像,我們都會不由自主聯系到西方畫家如達·芬奇、丟勒、倫勃朗等。這就讓我們產生一種錯覺——自畫像是西方畫家的首創。西畫歷來以人物為核心,而中國畫自宋代以來就以山水畫為核心,再加之山水、人物、花鳥、走獸的分科,使得人物畫在中國古代的繪畫中并不是畫家必備的能力,山水大家請人補景畫人物的事也不稀奇,作為人物繪畫的分支的“自畫像”自然難以吸引足夠的目光。
中國古代關于自畫像的受重視程度雖然不夠,但中國古代的自畫像活動一直就沒有中斷過,并且形成了一個不同于西方的自畫像發展之路。中國關于自畫像的最早歷史始見于《后漢書》,根據記載,漢獻帝時做過常卿的趙歧,通經學,多才藝,是畫“自寫真”可考的第一人。其后
北宋僧人畫家元靄,西蜀人,以擅長寫真聞名于世。有一次,太宗問他: “可能自寫形貌乎?”,說:“能”,遂寫沙門側面小影,果然逼真生動。詩人柳開見后,作詩贊道:“他人寫真,能寫他人,靄公自寫,如他人也。”宋代還有一些能“自寫真”的畫家。如三朵花,當事人不知其姓名,因他常戴三朵花,故而名之,又稱他“房州異人”。對他所畫的自畫像,蘇東坡曾有詩相贈,詩曰:“圖畫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白玉蟾,原名葛長庚,史籍上說他“自寫其容,數筆而就”。度宗的皇后全氏,善寫真,“入燕時嘗手寫己像,廣額鳳眼,雙眉入鬢,衣服道,女畫家能自寫真者,畫史上可謂鳳毛麟角。”[3]
僅從有關自畫像的記載來看,趙岐的卒年為公元201年,最早的畫自畫像的中國畫家生年早于西方1267年的喬托。哪怕是南北朝時期 (公元420-589年)的陸探微、張僧繇和智積等人的自畫像產生的年代也是大大早于西方的自畫像。對于中國的自畫像的確切記載是早于西方的,只可惜遺存作品少,參與創作的畫家也不多,再加上中國歷代宮廷都注重繪畫的社會功能,多用于表彰功臣。自畫像作品顯然又缺少以上功能,僅限于畫家的個人愛好,也是難以形成風潮的原因。
二、傳統自畫像的類型與技法發展
中國畫家現存最早的自畫像是北宋宋徽宗趙佶的《聽琴圖》,有趙佶的親筆題字“聽琴圖”和“天下一人”花押是徽宗的親筆題字當無疑,同時還有蔡京的題詩一首。可謂是中國存世最早的有署名的自畫像。由于宋徽宗擁有畫家和帝王的雙重身份,此作被懷疑是代筆作品;只因有了蔡京的題詩為證,當是親筆作品,而非代筆。
《聽琴圖》著力描繪的是君臣三人在松樹下聽琴的場面。分別為彈琴者徽宗自己,右側松蔭下,一人焚香撫琴,左右分別端坐著紅袍者蔡京、青袍聽眾童貫和一名童子。人物的舉止形貌傳神,背景描繪也極有情趣。由于作者高超的才藝,似乎可以從人物情態、松風竹韻和裊裊輕煙中,聽到悠揚的琴聲。《聽琴圖》中是以表達事件為主的一幅畫,也成為中國古代自畫像的第一種類型——以描繪具體事件為主的群像。
《聽琴圖》所開創的類型為任伯年《三友圖》所繼承,任伯年三友圖作于1884年,當時畫家45歲,是創作的高峰期,技法熟練,用筆精到。分別在畫上描繪了左側的自己,中間的曾鳳寄,右側的朱錦堂。彰顯了對于形的把握和筆的運用結合的恰如其分。
現存第二件自畫像作品是元代趙孟頫《自寫小像圖頁》。趙孟頫本人由于其顯赫的皇室出身,讓其背負了更多的道德包袱,投降元朝之后,又要受到元朝貴族的傾軋,同時又要提防元代皇帝的猜疑,只得將自己的才華全都用于書畫的創作之中以求寬慰。
《自寫小像圖頁》上的題款為“大德乙亥,子昂自寫小像”。在此畫中,趙孟頫把自己描繪為一個在竹林中漫步的雅士。頭戴烏巾,身著白袍,策杖而行。悠然的漫步在溪流涓涓的竹林之濱,身邊就是蘭亭序中所描繪的茂林修竹,溪流的形態也彎曲有致,就如《蘭亭序》說的溪流。全圖是以畫家自己置身于林中來烘托畫家的心境,這也是中國自畫像的第二種的創作類型——以營造氣氛為主的自畫像。
明代陳洪綬的《喬松仙壽圖》是他36歲時所創作的作品,他期待考中科舉,但并未如愿,以至于他的內心充滿了矛盾的情緒。在畫面上采用了松樹和溪流來烘托氣氛,與《自寫小像圖頁》所表達的情感大為不同,但用環境烘托氣氛,傳遞心情的做法卻是一脈相承的。清代石濤的《種松園小照》、項圣謨的《依朱圖》等也都是在這一類型上的延續和發展。
明朝《沈周畫像》是沈周的自畫像,衣紋平直厚重,為一般肖像宗法,面貌用筆輕重有致,雙目栩栩有神,兩頤的老人斑,賦色烘扦得宜,誠為肖像畫中的杰作。款為正德改元自題,時在1506年,沈周時年八十歲。題句為:人謂眼差小,又說頤大窄,我自不能知,亦不知其失。面目何足較,但恐有失德,茍且八十年,今與死隔壁。中國的畫家當中,沈周第一個直接用畫筆審視自己,他的一生都是中規中矩,八十歲的自畫像體現了自我的反省和對自我的解嘲。畫法上他力求真實,連老人斑都不放過,細膩地用咖啡色的赭石慢慢地點出臉上的老人斑與皺紋。在西方繪畫中的自己直接面對鏡子審視自己的畫法,第一次在中國畫家的筆下開始出現。沈周的自畫像就成為中國自畫像的最后一種類型——肖像式的自畫像。
從對趙佶的《聽琴圖》到趙孟頫《自寫小像圖頁》、明朝《沈周畫像》的考察,發現中國畫家一開始并沒有把自己作為一個獨立的表現對象來描繪,而是從群體演化為個體和環境,再從環境中獨立的過程。畫家自己的形象是逐漸變大,漸次成為重要主題。后世的自畫像都是在這三種類型中變化和發揮。尤其是趙孟頫《自寫小像圖頁》開創的通過環境來烘托氣氛表達主觀感受的做法在后世達到了極大的發展。
中國古代的自畫像的技法與人物畫技法緊密相聯,像趙佶的《聽琴圖》到趙孟頫《自寫小像圖頁》的技法還與李公麟的白描傳統相聯系。但是在后世也是及時的汲取了繪畫的最新成果來豐富自畫像這一古老的題材的。
三、傳統自畫像創作理念的演變
第一次給自畫像帶來巨大影響的是元代的王繹,他是肖像畫家,有《寫像秘訣》傳世。寫像秘訣系統的整理了肖像繪畫的要點,并對怎樣作到傳神提出了具體、明確的要求。我們也可以通過《沈周畫像》和趙孟頫《自寫小像圖頁》的人物面部處理可以看出來。趙孟頫《自寫小像圖頁》中,人物還大都依賴服飾、發型等易于辨別的特征來描繪,而沈周作品中已經注意到眼睛、額頭等更為個性的特征。也將臉上的皺紋和老年斑精細描繪,是前世畫家所沒有的。王繹的影響就是對寫真精神的把握上。
第二次則是來自曾鯨 (1568-1650)的“波臣法”肖像畫。曾鯨在世時結識了當時一批社會名流,利瑪竇1583年9月與羅明堅進入中國。他接觸到利瑪竇帶來的西方繪畫作品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曾鯨是在繼承粉彩渲染傳統技法的同時,汲取西洋畫的某些手法,形成注重墨骨,層層烘染,立體感強的獨特畫法。從學者甚眾,遂形成波臣派。
揚州畫派的羅聘創作的《羅聘自畫像》就是面部采用了波臣派的筆法,衣服等物采用了勾線的方法。波臣派描繪面部也成為后世自畫像慣用的手法。任熊《自畫像》。任熊把畫中的自己化成了光頭,表情是瞪著眼,雙唇緊咬的樣子;身上穿寬大的上衣和褲子,袒露右肩及胸部;足登布鞋,兩手緊握,兩腳分開。不像文人雅士,到像身赴法場的慷慨義士。任熊的畫法是借鑒了波臣派的分層烘染的方法畫面部,所以顯得很有立體感,而衣紋的處理就顯得很有寫實能力,屬傳統的寫真畫法,同時又加如來個性的用筆,所以在衣紋的張揚與面部的嚴禁之間就形成了生動活潑的畫面。任熊的畫法就是很客觀的作家畫。沒有文人畫率意的習氣,具備扎實的寫實能力。
第三次來自文人傳統的寫意精神。清朝“揚州八怪”中的金農畫自畫像最多,現傳世作品就有9幅。金農作畫的原因大都是為了贈送親友,其六十七歲自畫像是贈與老友鄭板橋,給項均的《七十二歲自畫像》和給弟子羅聘的《七十三歲自畫像》。清代金農《七十三歲自畫像》,采用了傳統畫法中的減筆描的畫法。在這幅畫的題款中金農寫道:“余因水墨白描法,自為三朝老臣七十三歲像,衣文面貌作一筆畫,陸探微,吾其師之。畫中是老者身著布衣的側面像,持杖而立,姿態篤定安詳,神情超然若思。其頭部畫法較為夸張,細細的發辮繞在腦后。有文人畫的特征,濃密的長髯,矍爍的雙目,真實傳神地描繪出金農本人奇倔傲世的性格。金農的文人畫的作風,是依托于傳統的十八描為基礎,同時將特征夸張強化,所以畫面顯得詼諧幽默,是文人畫中的自畫像。同時極其講究筆調的韻味,用筆熟中有生。金農的自畫像的畫法對后世的齊白石、陳師曾等人。
自清朝開始,中國畫的自畫像就成為兩個模式,一種是金農創造的文人畫程式的白描畫法,另一種為以波臣派寫真畫面部,白描畫法勾勒畫衣紋的寫真作派。金農的畫法重筆墨趣味,面部不做立體的渲染,其創作者多為文人畫家。
自畫像,作為一個具有悠久傳統的繪畫種類,是能夠很好的表達我們的情感和藝術觀的。而同時也是兼具了練習和創作的雙重功能。盡管在中國繪畫學習西畫之后,原有的國畫自畫像不被重視,但是并不是說明自畫像的消亡。相反只會更加促進自畫像在技術、觀念和表達方式上的創新。自畫像這一畫種并不是泊來的新觀念,而是一直就根植于中國的創作之中,他是中國畫家基于中國的哲學和理解為表達畫家的思想、情感、理念和認識自我的一種方式。
[1]鄭午昌.中國畫學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2][宋]張君房輯.云笈七讖[M].濟南:齊魯出版社,1988年
[3]陳瑩.略論中國古代“自寫真”像 [J].藝術探索,2006年第3期,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