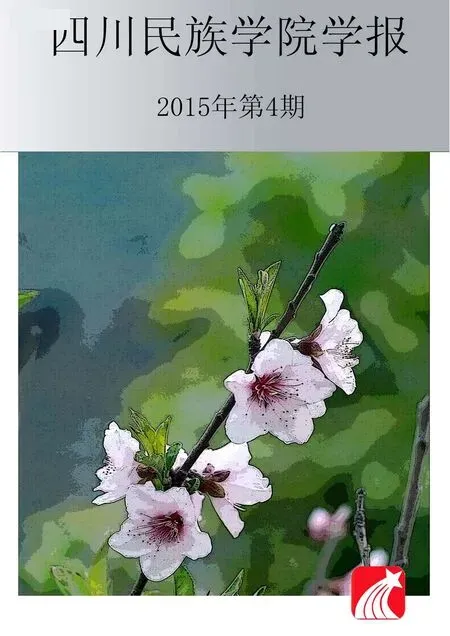論特殊教育研究方法的發展特點及趨勢
吳春艷 羅 娜 秦艷芳
特殊教育學是一門以各種生理、心理有障礙或有特殊才能的兒童的身心發展特點和教育教學為研究對象的學科。特殊教育學與教育學、心理學、生理學、社會學、醫學、法學等多門學科有密切聯系,是典型的交叉邊緣學科。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方面,特殊教育研究較好地遵循了實證科學研究的精神與傳統,以及社會科學共有的方法論、學術規范與具體的操作技術。與此同時,由于特殊教育研究對象和視角的獨特性,在長期的研究過程中,特殊教育的研究方法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趨勢和特色。
一、特殊教育研究堅持以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為主
以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為主的傳統,伴隨著整個特殊教育研究的發展進程。眾所周知,研究問題和目的極大的影響著研究范式的選擇。特殊教育研究最為重要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特殊兒童發展和教育現狀、明晰影響特殊兒童發展的因素、探尋促進特殊兒童發展的有效教育方法和途徑,以最終實現補償缺陷,發展潛能。這樣的研究取向造就了特殊教育研究的實證主義風格,從18世紀特殊教育誕生以來一直占據統治地位。19世紀,法國醫生伊塔德 (Itard)對狼孩維克多開展的教育試驗是典型的實證研究。實證主義研究范式,使特殊教育研究者們偏向于選擇實驗研究、問卷調查和干預研究等方法。它重視客觀測量工具 (如智力量表等)來診斷殘疾或障礙類型與程度,并據此發展相應的治療方法以及具有醫學特點的干預或訓練手段。[1]尤其是在與醫學、生理學、心理學等學科相關的特殊教育研究中,毫無疑問,以實證主義范式為基礎的量化研究以其追求數量化、準確性、可比較、可驗證、可推廣的特色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正如美國《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 (No Child Left Behind,2001)所明確提出的,當前呼喚更加精細化的教育研究。量化研究迎合了特殊教育發展的需要。
而在具體的量化研究中,除了與其他學科一樣廣泛使用現狀調查、分組實驗、相關關系研究等方法一下,特殊教育研究的突出特點就是單一被試研究 (single-subject research)備受青睞。Hammond和Gast(2010)研究了1983-2007年間8種特殊教育領域內有廣泛影響力的期刊,每種期刊每年隨機選一期作為分析對象,在總共的1936篇論文中,有456篇使用單一被試研究。[2]Mastropieri與她的同事 (2009)分析了11種特教領域關注率高的期刊1988-2006年間的論文。他們把干預研究分成三類:(1)一個組的前后測設計;(2)兩個或更多組的實驗或準實驗研究;(3)單一被試研究設計。結果發現,單一被試研究在特殊教育領域使用最廣。[3]
眾所周知,量化研究是以大樣本、廣抽樣作為其獨占鰲頭的法寶。樣本量越大信效度越高,科學性和推廣性越強。然而,特殊兒童的類型、障礙程度及特點千差萬別,居住和學習都很分散,在特殊教育的一些具體研究中,采用傳統的教育、心理實驗與統計方法,在樣本的同質性和樣本容量兩個問題上,很難達到研究的要求。特殊教育研究的對象往往更具有唯一性、獨特性。比如,即使是以10個以內的自閉癥兒童為研究對象,其個體差異 (智商、行為表現)也很明顯。在這種情況下,單一被試研究在特殊教育研究中脫穎而出。單一被試研究是以一個或幾個被試為研究對象,通過相關的實驗設計來研究干預是否有效的一種方法,適用于相互之間差異較大的個體,符合特殊教育研究的客觀情況。[4]該研究方法對被試的數量要求低,即使是一名被試,也可以滿足研究的基本要求。
單一被試的使用開始于半個世紀以前,已被證明是在個體學習者視角開展教育實踐的有效方法。教育者可以根據單一被試研究的結果制定個別化教育和支持計劃。霍納 (Horner,2005)等人認為,高質量的單一被試研究有如下基本特征:(1)將個別化被試作為分析單元;(2)對所研究特征的操作性定義,包括被試與環境設置、自變量、因變量等;(3)基線與干預條件的使用;(4)實驗控制;(5)重復測量目標行為;(6)干預措施的反復系統介入;(7)對干預有效性的可視化分析。與之相對應,特殊教育遵循問題解決原則,強調關注學生個體,積極干預,開展實針對具體的學校,家庭和社區環境的實踐,單一被試研究正好滿足這些要求。[5]當前,單一被試研究在特殊教育中的應用相當廣泛,尤其是在對特殊兒童的行為矯正和缺陷補償的干預研究方面。比如,自閉癥兒童的可視音樂干預研究;多動癥兒童的不良課程行為干預研究;智障兒童詞匯回憶能力研究;故事教學對提高聽障兒童聽理解能力的實驗研究等。
在特殊教育研究中使用單一被試研究的優點有:(1)便于開展低出現率特殊教育類別的學生的相關研究;(2)研究者可以測量被試的個體表現。在特殊教育中,研究者往往更關注個體而非整體。比如,對于一組智障學生來說,他們之中可能有輕度、中度、重度和極重度智障,整體的平均數并不能代表個體的具體表現;(3)研究者不必應付因設立控制組所帶來的研究倫理問題;(4)便于教師在學校中開展此類研究。[6]
但同時,單一被試研究在發展與運用中,容易受到兩個方面的限制。一是由于樣本量少帶來的信效度問題,二是如何對實驗結果排除主觀判斷,精確定量分析的問題。這也是特殊教育研究者一直在盡力完善的方面。比如,從提高數據來源的可靠性、判斷基線數據的適當性,以及精心設計研究模式等。[7]在實驗設計上,單一被試研究已經發展出單基線實驗設計、多基線實驗設計和U實驗設計等多種方案,通過精細的實驗設計來增強研究的科學性。與其他量化研究一樣,單一被試研究同樣需要有明確、可量化的目標行為,并要求對目標行為進行反復的測量。此外,為保證研究的信效度,對實驗場所、指導語及實驗工具、研究人員分工等也有嚴格的要求和控制。總的說來,單一被試研究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實證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符合特殊教育研究的實際,具有較高的應用價值。
二、人文主義范式在特殊教育研究領域日益受到重視
在科學理性指導下的特殊教育實證研究,更多的是關注通過先進的技術和手段來改變殘疾人的發展水平和特點,使他們能夠適應普通社會。然而,這樣的研究,很少關注到殘疾人本身的感受,較少考慮殘疾人個體的獨特社會文化的影響,改變往往是有限的。文藝復興以來,西方人文精神的發展成為了特殊教育發展的新動力。人道主義和人本思想成為特殊教育的出發點。建構主義以及后現代主義思潮的發展直接孕育了以激進的平等、個別差異和多元為核心價值觀的全納教育理念。人性與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張揚改變了社會文化氛圍,帶來了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多樣化,以實證主義、批判主義、建構主義為基礎的人文主義范式在特殊教育研究中掀起了新的波瀾,為特殊教育的發展奠定了新的基礎。[1]尤其是批判理論和建構主義認為:理解是一個交往、互動的過程,必須通過雙方價值觀念的過濾,帶有價值取向的研究者使用主觀的互動與交流的方法接近“他人”的內心世界。這些關于研究的認識論與當前特殊教育中所倡導的全納教育理念、多元文化價值觀等不謀而合。
以人文主義研究范式為基礎的質性研究,是在某一特定環境下,理解現象的質量和本質的系統方法。特殊教育研究中,質性研究重在理解殘疾人個體、殘疾人家庭以及與他們共同生活、工作的人;關注殘疾人群體與普通人的態度、觀點和信念,讓長期沉默和被邊緣化的人發出自己的聲音;考察個體對特殊教育環境及教學策略的反應;描述并追蹤有益于取得豐富性學習效果的教學實踐方式和有意義的生活安置形式;考察不同實踐方式對殘疾人及其家庭的影響,使研究的內容更深入等。[8]質性研究方法的在特殊教育領域的具體運用已有30多年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為了增強質性研究資料的確定性,提升質性研究的信效度,一系列的驗證性措施被廣泛使用。比如,對來自不同個體、不同類型和不同搜集方法的資料進行三角互證;讓被研究者對訪談記錄進行確認驗證;采用強大的數據搜集方法等。
當前,特殊教育領域最常用的質性研究類型是個案研究、扎根理論和民族志研究
個案研究是對一個案例的調查分析。案例可以是一個人,計劃,事件,學校,教室或小組。當明確了個案之后,研究者就要采用多種數據搜集方法,比如訪談,田野觀察和資料收集,對它們進行深入、典型的調查分析。個案研究不是為了追求一般化,而是在探索特定環境和典型個體的基礎上提出觀點和證據。比如,哈瑞等人 (Harry,1998)研究了一個剛從多明尼加共和國移民到美國的唐氏綜合癥的青少年。研究者跟蹤觀察了他及其三個兄弟每天的社區活動與學校活動,并與這幾個男孩及他們的父母進行訪談。這一研究揭示了融合環境下同伴關系的發展情況。[9]普萊斯利 (Pressley,2001)對一名27歲有教學經驗的一年級教室的個案研究,采用集中的課堂觀察,總結了一系列的關于融合教育的有效教學實踐方法。[8]另有研究者采用面談和焦點小組的方法,研究了關于殘疾兒童學前融合教育的五個方案的研究。在我國的特殊教育研究中,采用個案研究方法,能夠更全面地分析對象的獨特性和具體的社會文化背景,有助于本土特殊教育理論的形成。
扎根理論,是研究者在對現象進行研究的基礎上發展或發現理論的一種方法。研究者在遵循基本的科學原則的基礎上,根據搜集的材料,有足夠的靈活性地去解釋一個過程、行動或與被研究者的互動,并形成理論。這種基本理念允許有被研究者的聲音的表達,要求研究者通過資料驗證來自被研究者的主要思想和概念,并在形成理論的過程中考慮被研究者的視角。運用扎根理論的一個方法是不斷地回歸資料,通過比較,明確被試見的相似性和差異,關注主題間的相互關系。相較于傳統的特殊教育研究往往要求研究者站在“客觀”的角度去調查分析研究對象,容易導致殘疾人的聲音在研究中遭受抑制,而扎根理論要求研究者貼近生活、貼近實踐,和參與者建立良好的信任合作關系,在平等對話、交流互動中解讀殘疾人的內心世界與蘊涵于其中的深刻意義與本質。因此,研究者應懷有公平、人道的理想以及幫助弱者、改變社會的愿望,參與到殘疾人群的實際生活中,傾聽他們的聲音,記錄他們的現實生活,對他們的過去和現在的經歷經驗以及未來進行思考、探索,并幫助他們改變自己的命運,實現人生理想。比如,英國學者馬丁森 (Mattinson,1971)通過訪談和觀察離開特教機構、步入社會的人,發現這些人結婚后有能力相互扶持、獨立生活。這樣的研究結果表明,禁止有認知障礙的人結婚時不合邏輯的、耗費高昂且有違倫理的。[10]再如,有人曾用扎根理論研究了小學中特殊教育的教學領導。
民族志研究是對社會群體進行深入分析。一般通過觀察、訪談和文本分析搜集資料。人種志研究也就是關于一群人的故事,聚焦于這一群體的文化。需要研究者融入這一群體去理解他們的內部活動、結構和功能。這種類型的研究集中于記錄一組人在一個時期的行為和觀念。人種志研究的基本理念是,融入這一群體的文化,將使研究者從群體成員的視角來看問題,能夠更好地綜合、深刻地理解群體的行為和信念。為了理解當事人對隔離環境的感受,人類學家羅伯特·艾格頓 (Robert Edgerton,1967)訪談了48位被歸為智力發展遲緩,且大多數時間在特殊機構中度過的成人。他的研究揭示了這些人受到的不公平對待與痛苦感受,并引起了立法與法院判決中非自愿隔離者的關注。《被遺忘的人:盎格魯與芝加哥智障者的社會學研究》(Henshel,1972)一書中,作者通過人種志研究的方法,表明學校工作人員對種族差異的假設會影響他們在特殊教育中推薦、測試與安置程序。[8]此外,特殊教育研究中,聾人文化、自閉癥兒童的家庭教育、少數民族地區的特殊教育等領域,都可以采用人種志研究。
除此之外,個人敘事與生活故事也是人文主義范式中考察殘疾人生活經歷的經典方式。總之,特殊教育中的人文主義范式,最核心的目標就是理解,在此基礎上分析原因,提供策略。這種理解必須是綜合的、深入的、準確地表達被研究者的觀點,這樣他們的聲音才能被人們所了解。而讓被研究者的聲音得到清晰的表達,這是研究者應擔負的責任。
三、多元化的特殊教育研究范式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每一種單一的研究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而人類認知的發展則對特殊教育研究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一方面,特殊教育的研究范圍已經遠遠超出了學校中的典型特殊學生的范圍、全納教育理念已廣泛運用于教育實踐;另一方面,特殊教育的研究方法也受到跨文化研究方法、對研究者價值立場的追問等研究視角、現代化教育技術手段等方面的影響。比如,拒絕在社會生活中對殘疾人區別化對待,宣揚殘疾與人類的共存,堅持技術的廣泛開發與運用,主張全納教育實踐等,[11]這些價值觀直接影響教育研究中對人類的認知,以及研究方法的選取和使用。而根據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共有發展規律與趨勢,考慮到特殊教育的自身理論和實踐的需要,特殊教育的研究正在走向多元的研究范式。研究問題的特點影響研究方法的選取;研究方法則影響研究者的資料搜集。[12]對于一個特殊教育問題進行全面的分析,在可能的情況下,采用多元化的方法,更可能獲得客觀地、深入的研究結果。
在特殊教育領域,典型的研究方法有調查研究、相關研究、單一被試研究、分組和準實驗研究、質性研究等。在研究方法的具體運用中,從個案研究到現狀調查,從相關研究到干預正——被特教研究者所使用,則呈現出以下一些多元化的趨勢:(1)系統分析與系統綜合相結合。比如,既要運用分析的方法了解特殊教育作為一個系統所包含的要素、結構、功能等,又要運用綜合的方法從自閉癥兒童的行為問題表現分析其整體的發展情況。(2)還原論與整體論相結合。(3)定性描述與定量描述相結合。(4)局部描述與整體描述相結合。(5)確定性描述與不確定性描述相結合。[13]比如,對多動癥兒童的個案研究中,對于其短期可預測的行為采用確定性描述,對于其未來的不可預測的長期行為可采用不確定描述,并采取不同方法進行教育干預。在具體的方法中,則涉及到測量法、觀察法、調查法等靈活運用。
也即是說,即在堅守實證科學精神的同時納入建構主義和人文主義的情懷,在進一步規范邏輯驗證性質的量的研究的過程中,加強對歸納探索性質的質的研究范式的探索與運用。特殊教育研究者從實驗室走進殘疾人的真實生活,從閉關自守的學術象牙塔走向現實生活世界,從實驗室的控制環境走進自然的“田野”與特定情境。殘疾人則應從消極的被研究對象轉變為研究的主動參與者,從旁觀與被動接受調查走向主動敘述人生故事,改變自己的命運,由被控制與操縱的 “小白鼠”走向平等、大寫的“人”。[1]
總之,從傳統的單一研究模式走向多元研究范式,是特殊教育研究的必然趨勢,也將成為特殊教育領域彌足珍貴的特色。為了進一步提高研究水平,特殊教育研究者必須意識到不同的研究設計的優點與不足,認真考察適合自己的研究范式及其質量指標體系。
四、跨學科的特殊教育研究視角
從特殊教育的發展軌跡來看,這一領域最先涉獵的學科基礎是醫學。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20世紀中期,伊塔德 (Itard,1962)的《阿韋龍的野孩子》(The Wild Boy of Aveyron)開創的特殊教育研究的奠基性工作。許多為殘疾孩子服務的先驅也是醫生,比如伊塔德、塞甘、蒙臺梭利等。與此相適應的,早期為殘疾兒童提供的服務出現在以醫學照料傳統為基礎的寄宿制機構和訓練學校。后來,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成為學科之后,為特殊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革命性的研究視角。[14]比如,從社會學中的寬容理解視角來詮釋殘疾人教育,有力地論證了全納教育的價值與開展途徑。
特殊教育是具有多功能結構的動態系統,其復雜性不僅體現在特殊兒童群體的多樣性與差異性、特殊教育方式的豐富性,還體現下特殊教育系統內外、外部因素之間關系的復雜性。因此,特殊教育的目標 (矯治、預防與發展)和功能 (補救、預防和發展)皆是多元的。研究特殊教育這一復雜現象,需要采用跨學科的研究視角。即從特殊教育的立場出發,聚合多種學科觀點對特殊教育進行研究,從而獲得更加全面、深刻的解釋。對此,何侃 (2008)專門分析了特殊教育研究中,跨學科融合的典型途徑:(1)尋找焦點,建立融合,即運用兩種以上的方法與觀點分析同一個特殊教育問題;(2)相互啟示,挖掘共源。特殊教育通過“提問”為相關學科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相關學科同樣把自己的問題提供給特殊教育,相互提供新視角和方法論,共同成長;(3)擴大領域,靈活運用。以特殊教育問題為核心,將不同的學科范式在特殊教育研究領域內融合,為學科間的整合提供更多的可能性。[14]值得注意的是,特殊教育研究引入跨學科視角的根本目的是提升研究水平,各門學科運用自己獨有的視角解釋其比較適宜的問題,深化特殊教育研究。因此,不同學科應是相互補充、合作的關系。
五、特殊教育研究的應用——循證實踐的廣泛重視
特殊教育的發展歷程中,有人用畢生的努力去理解和解決人類發展和教育中的問題,最后卻發現是錯誤的,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布魯諾·貝托漢 (Bruno Bettelheim)曾經認為已經找到自閉癥的病因 (冰箱媽媽)以及治療方法。在整個20世紀六七十年代,貝托漢風靡一時。經過大量的投資、努力和失望之后,人們發現他的觀點是帶有欺騙性的。而他關于自閉癥病因是“冰箱媽媽”的言論,讓很多父母因自己對孩子的照顧不周而感到內疚和羞愧。再如“形式訓練”的問題,盡管有研究結果顯示形式教學的效果好,但實踐中的干預效果卻不理想,而不少特殊教育教師卻曾長期使用著這種明顯不當的方法教育孩子。在漫長的特殊教育歷史中,他們往往都僅是用“我自認為”或者含糊的“研究顯示”來作為自己教育實踐的基礎。
當前,人們普遍認為,科學的研究證據支持下的實踐是有效且更令人信服的。因此,包括教育在內的許多領域,都在大力推動循證實踐 (evidence-based practice)。美國2001年的《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NCLB)和2004年的《殘疾教育法》(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IDEA)都規定,教師必須使用科學的研究結果和最佳實踐方式 (best practice)開展教學,而不是教師隨意使用自認為有效的方法。[15]“經科學證明”成為評價教育實踐的主流方向,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加特殊教育實踐的有效性,從而也推動了人們對特殊教育研究的質量的重視。
循證實踐,必須建立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然而,如果沒有評估的標準的基準,很難判定一個研究是否可以作為循證實踐的研究。為此,特殊兒童協會研究分會開發了一套評價特殊教育研究的質量指標。《特殊兒童》雜志 (Exceptional Children)于2005年專門出了一期專刊,由五篇論文組成,討論包括單一被試研究、[5]分組實驗和準實驗研究、[16]相關關系研究、[17]質性研究[8]等各種特殊教育研究方法的質量指標,以及循證實踐的判定標準。例如,可作為循證實踐基礎的單一被試研究,需具備以下條件:(1)實踐方式經過了操作性定義;(2)界定了實踐的環境;(3)忠實于研究開展實踐;(4)單一被試研究指導下的實踐結果帶來了因變量的改變;(5)實驗效果可重復。[5]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研究者也對如何評價一個研究是否符合循證實踐的標準進行了探討。盡管研究者們對于哪些類型的研究可以作為循證實踐的依據爭議較大。但被廣泛認可的觀點是,一個達到循證實踐標準的研究,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要有充分的研究基礎,也就是研究本身的高質量。第二是研究中的積極干預效果要顯著。[18]總之,符合循證實踐標準的研究,就是那些經科學研究證明有顯著實驗效果的研究。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特殊教育的循證實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量化研究的影響。一方面是因為特殊教育中的量化研究的主體地位,另一方面,也源于當前對研究質量的評估,主要還是以量化研究為工具。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循證實踐使特殊教育研究的價值得以更充分的體現,但同時,也對研究的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對相關主題的研究進行居于循證實踐的評價,也成為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當然,關于循證實踐還有一些值得繼續探討的問題,比如,在缺乏充分而確定的研究基礎的情況下,如何開展教育實踐?循證實踐是為了盡可能地促進孩子的發展,減少教育中的失誤。那么,循證實踐的“證”從何而來?這些都成為了特殊教育研究中新的研究命題。
總之,世界范圍內,特殊教育研究方法的發展,即延續了多年的研究傳統,又與時俱進地增添了一些新的研究范式與視角,特殊教育研究方法正呈現出重心突出、兼容并包的發展趨勢。然而,相比之下,我國特殊教育界對研究方法的重視程度以及運用的規范性都不夠,方法論層次的反思與討論不多。質性研究方法運用較少。已有的量化研究質性研究里,數據或資料堆砌較多,理性分析與理論歸納提升的較少。本土化理論的生成與擴展更少。[1]因此,在明確特殊教育研究方法的發展總趨勢的同時,我們應結合本國的特殊教育實際,有針對性地改善特殊教育研究方法,豐富和發展特殊教育實踐。
[1]鄧猛、蘇慧.質的研究范式與特殊教育研究:基于方法論的反思與倡議[J].中國特殊教育,2011年第10期,p3-8
[2] Hammond,D.& Gast,D.L.Descriptive analysis of single subject designs[J].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2010(45):187-202
[3] Mastropieri,M.A.,Berkeley,S.,McDuffie,K.A.,Graff,H.,Marshak,L.,Conners,N.A.,Diamond,C.M.,Simpkins,P.,Bowdey,F.R.,Fulcher,A.,Scruggs,T.E.& Cuenca-Sanchez,Y.What is published in the field of special education Analysis of 11 prominent journals[J].Exceptional Children,2009(76):95-109
[4]杜曉新.特殊教育研究方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5] Horner.R.H..Carr.E.G..Halle.J..McGee.G..Odom.S.L.& Wolery.M.The use of single-subject research to identify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in special education[J].Exceptional Children,2005(71):165-179
[6] Cakiroglu,O..Single subject research:applications to special education[J].British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2012(39),1:21-29
[7]杜曉新.單一被試實驗法在特殊教育研究中的應用 [J].中國特殊教育,2001年第1期,p8-10
[8] Brantlinger,E.,Jimenez,R.,Klingner,J.,Pugach,M.,&Richardson,V..Qualitative Studies in Special Education[J].Exceptional Children,2005(71),2:195-207
[9] Harry,B.,Day,M.,& Quist,F.(1998)."He can't really play":An ethnographic study on sibling acceptance and interaction [J].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ersons With Severe Handicaps,1998(23):289-299
[10] Mattinson,J.Marriage and mental handicap Pittsburgh[M].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1
[11] Cardoso,B.,&Maria C.F..Values influencing the perception of the human being and research in special education:a reflection [J].Revista Brasileira de Education Especial,2011(17),1:17-22
[12] Graham,Steve.Preview [J].Exceptional Children,2005(71),2:135
[13]何侃.特殊教育研究方法論的突破路徑 [J].教育評論,2008年第5期,p71-74
[14] Odom,S.L.,Brantlinger,E.,Gersten,R.,Horner,R.H.,et al.Research in Special Education:Scientific Methods and Evidence-Based Practices[J].Exceptional Children,2005(71),2:137-148
[15] Martinez,A..Scientifically Based Research in Special Education [J].The Exceptional Parent,2008(38);4:82
[16] Gersten,R.,Fuchs,L.S.,Compton,D.,Coyne,M.,et al.Quality Indicators for Group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Special Education [J].Exceptional Children;2005(71),2:149-164
[17] Thompson,B.,Diamond,K.E.,McWilliam,R.,Snyder,P.,Snyder,S.W..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Evidence From Correlational Research for Evidence-Based Practice[J].Exceptional Children;2005(71),2:181-194
[18] Obiakor,F.E.,Bakken,J.P.,&Rotatori,A.F..Current issues and trends in special education:research,technology,and teacher preparation[M].Bingley,UK:Emerald,2010:1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