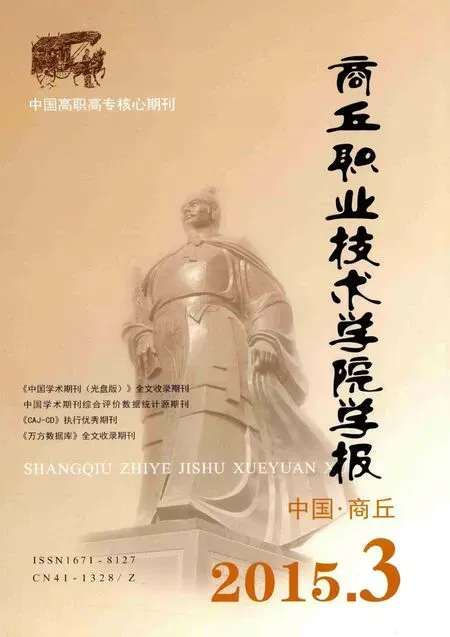探析男性身體書寫中的文化規訓
——以老舍、沈從文、郁達夫和白先勇的男性身體書寫為例
姚 婷
(華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20世紀90年代以來,女性作家以自我經驗為書寫對象“以擺脫男權中心文化對女性的限制和操控”[1]1,對身體書寫的主流界定是女作家書寫女性身體,但也有部分學者將對象擴展到男性,認為只要是“圍繞著對人的肉體描寫所展開的靈與肉、情與欲、意與性的升騰和搏戰”[2]1即是身體書寫。“身體”是富有生命活力和感情、敏銳而有目的取向的,而不僅僅是那個單純由骨肉聚集而成的物質性“肉體”[3]5。以性別為橫向坐標,以主流與邊緣為縱向坐標,身體寫作的范疇應當包含主流、邊緣的男性、女性身體書寫。本文以沈從文、老舍、郁達夫和白先勇的文本為例對應現代文學男性身體書寫的四個維度,通過男性對自我身體的想象,進一步了解其精神世界的生態環境。
一、湘西大自然之子與城市底層勞動者
沈從文湘西世界中的小伙子都“結實如牛犢”[4]64,儺送二老“黑臉寬肩膀,樣子虎虎有生氣的”[4]117,《丈夫》里的男人“誠實耐勞,年輕而強健”[4]164,即使是渡船的老人都“硬朗得同棵楠木樹一樣”[4]88。這些男人不論年紀和職業都有共同的特點,膚色呈現自然的黑,肌肉結實,骨架寬大,極具男性的陽剛與雄健氣質。成長于鄉村世界,他們如大自然的其他生物一樣生長,像小牛犢一樣結實,像老虎有生氣,像楠木樹一樣硬朗。體格健康的鄉村男性心靈世界也是質樸而純凈的,大佬和二佬以類似鳥類求偶的方式唱歌來獲取姑娘的芳心,老婆做妓女補貼家用被認為是正常的,水手和妓女之間存在著動人的真情。沈從文湘西男人的身體之所以能夠以健康狀態存在正是因為美好的自然環境與純善的社會環境。
不同于湘西男人如小牛犢般的健壯,祥子作為城市的底層車夫,身體是如鐵打一般的強壯。老舍認為人物的塑造是小說成敗的關鍵,“不可泛泛地由帽子一直形容到鞋底;沒有用的東西往往是人物的累贅”[5]443。老舍抓住了胸、背、肩、腳這幾個部分刻畫祥子的出場形象,可以依靠的“鐵扇面似的胸與直硬的背”,能夠承擔重任的“多么寬,多么威嚴”的肩,“出號”[6]5的大腳則是腳踏實地的象征,簡單幾筆勾勒出了車夫行業的佼佼者應當具備的骨骼框架。緊接著描摹祥子并不出眾的五官,永遠紅撲撲的臉上有圓眼、肉鼻子、很短很粗的眉毛,“腮上沒有多余的肉,脖子跟頭一樣粗”,顴骨和右耳之間那一個小時候被驢啃過留下的疤說明祥子來自農村,對于靠體力吃飯的勞動者來說,頭發這種修飾性的身體部件是不需要的,所以頭頂“永遠剃得發亮”。祥子對身體所有器官的看法是“只要硬棒就好”[6]6。祥子用自己年輕健壯的身體跑出了車夫行當中名貴的姿態,“活動,利落,準確;看不出急促而跑得很快,快而沒有危險”[6]7,來自農村的健壯男性初入城市即以身體作為資本換來了金錢與榮耀,獲得了心理上的滿足。他將自己辛苦買車的日子也作為自己的生日,在與車磨合的過程中,祥子把車變成了身體的一部分,“仿佛有了知覺與感情,祥子的一扭腰,一蹲腿,或一直脊背,它都就馬上應合著,給祥子以最順心的幫助,他與它之間沒有一點隔膜別扭的地方”[6]12,跑車的時候生怕碰傷了車便對不起自己,因為車是他的命,車是鐵做的,他覺得自己的身體也是鐵做的。
祥子對身體的自信在婚后發生了改變,同行那里學來的性知識使他將虎妞看作吸人血的妖精,他開始“曉得一個賣力氣的漢子應當怎樣保護身體,身體是一切”[6]163。陽剛雄健是社會訓規對正常男體的要求,當陽痿這種生理疾病與男性尊嚴掛鉤的時候,隨之而來的心理壓力遠遠大于生理上的痛苦。在這種令自己覺得可恥的病好了以后,祥子就幾乎變了一個人,“那股正氣沒有了,肩頭故意的往前松著些,耷拉著嘴,唇間叼著支煙卷”[6]223。從最開始對身體有著強壯的期待,婚后對身體的懷疑,病后對身體的否定,直到最后對身體的放棄,祥子漸漸明白拉車是怎么回事。王德威評論“小說的喜劇設計經歷了一個完整的過程——最后將人物變成了機器”[7]171。車曾被祥子看作身體的一部分,因為如同自己的四肢一樣硬棒的車,可以幫助他換取想要的美好生活,一旦自己的身體先垮了,他對車便“不再那么愛惜了”[6]226。祥子的精神世界也隨著身體的狀況一步步跌入深淵,祥子對車的放棄象征的是對自我的拋棄。
健康的男性身體與健康的自然生存環境結合才能產生健康的靈魂,沈從文湘西世界里的男人證明了這一點,他們是不受傳統規訓的大自然之子,身體與心靈都處于自然健康狀態。“健壯的身體與健康的自然生存環境分離的結果是,威嚴的肉體往往與邪惡的人格結合在一起”[8]329。一旦健康的男性身體脫離健康的自然生存環境,受到社會規訓對男性身體想象的制約,男性身體便走向異化了。如祥子一般強健的男性身體書寫中散發出來的身體焦慮感恰恰證明了男性群體在男權社會中受到的戕害和壓抑并不少于女性,男性為了達到社會規訓定義的剛強健壯付出了不容小視的代價。
二、男性邊緣化的身體形態
正常的男性身體描述為陽剛健康雄壯的,與之相反,那些非正常的男性身體被人們冠以“病態”“變態”的形容詞游走于話語體系的邊緣。郁達夫的自敘傳小說塑造了一系列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形象,他們的面孔都清瘦蒼白,或許因為生病的緣故染上一層紅色,纖長瘦弱的體型,情感豐富,淚腺發達。這群體弱多病、即使無病也愛呻吟的男性知識分子,跟祥子這種真正腳踏土地與生活角力的勞動者所處的社會階級不同,讓他們苦悶的原因也不盡相同。“大抵作家的人物,總系具有一階級或一社會的特性者居多”[9]439。“作家對于人物的性格心理的知識,仍系由他自家的性格心理中產生出來的”[9]438。所以結合郁達夫個人小說觀及其文中對男性身體的書寫,大致可以了解那個時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自我身體的想象。
郁達夫自敘傳小說中有許多因為性苦悶、偷窺癖、戀物癖、思鄉病和青春憂郁病而備受精神折磨的男性,他們矯情的表達和廉價的眼淚總是讓人無法相信那些赤裸裸的對自我靈魂的拷問是發自內心的。與其說他們因為自身的“病態”受到煎熬,不如說他們享受這樣一種正常話語體系中的“病態”狀態。《沉淪》中那個患了憂郁病的男主人公想起自己的苦處眼淚就如瀑布流下,在哭的同時大腦中出現幻象的聲音“你別再哭了,怕傷害了你的身體!”,緊接著“他覺得悲苦的中間,也有無窮的甘味在那里”[10]41。《茫茫夜》中的質夫用婦人的手帕擦被自己刺出血的臉頰,想象手帕主人的態度,“他覺得一種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透了”[10]117。《遲桂花》里的翁則生病到痰里有血絲,臉上蒼白,身體瘦削,家人都擔心得不得了,也依然覺得“沒什么驚奇駭異的地方”。郁達夫小說中的這些知識分子相當契合“文弱書生”的特質,病弱的身體或強作愁的心理狀態更能刺激他們對于頹廢美的追求,病態的身體讓他們更能藝術地生活在幻象中。擁有健壯身體的祥子至死不能正視自我的欲望,這些身體病態的知識分子清楚知道社會訓規對手淫、縱欲、偷窺的道德譴責,但依然選擇正視人性最自然最真實的欲念。
另一種處在邊緣的男性是被主流排斥為異端的男同。《孽子》中的男同性戀者是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猶自彷徨街頭,無所依歸的孩子們”。這個群體見不得日光,被人遺忘遭人唾棄,在黑夜的保護下他們才敢出來。記者在潛入安樂鄉后寫道,“這兒沒有三頭六臂的吃人妖怪,有的倒是一群玉面朱唇巧笑倩兮的‘人妖’”[11]300。這一發表于報紙的言論可見社會大眾輿論對于這些男性群體的不理解、不屑和鄙視。作者白先勇先生本身是一個男同性戀者,他的描寫足以反映一個男同性戀者對這個群體男性身體的想象。吳敏“兩腮全削下去,一雙烏黑露光的大眼睛,坑得深深的”[11]15;小精怪長得濃眉大眼[11]17;龍子“顴骨高聳,兩腮深削下去,鼻梁卻挺得筆直的,一雙修長的眉毛猛地往上飛揚,一頭厚黑的濃發,蓬松松的張起。……只有他那雙深深下陷,異常奇特的眼睛,卻像原始森林中兩團熊熊焚燒的野火,在黑暗中碧熒熒的跳躍著”[11]21;阿鳳“一雙長眉,飛揚跋扈,濃濃的眉心卻連接成一片。鼻梁削挺……一雙露光的大眼睛,猛地深坑了下去,躲在那雙飛揚的眉毛下……臉是一個倒三角,下巴兀的削下去,尖尖翹起。”[11]71白先勇對這些男性外貌的描寫特別關注眉眼、鼻梁和頭發,與老舍對祥子外貌的描寫相對比差異巨大,祥子外貌以實用為主,而這些男性面貌卻講究俊俏立體,講究審美的特點。除了面貌,這群男性的身材與穿著也是異于正常男性的。楊教頭“穿著一身絳紅的套頭緊身衫……一條黑得發亮的奧龍褲子,卻把個屁股包得扎扎實實隆在身后”[11]8;原始人阿雄仔是個門神一般的龐然大物,好像馬戲團里的大狗熊,嶄新的尼龍運動衫把他胸膛上的肌肉,繃得塊塊凸起[11]11;龍子身材高瘦,一身嶙峋的瘦骨,一根根往外撐起。深藍的襯衫好像繃在一襲寬大的骨架上似的[11]21;華國寶“身材很帥,長腿細腰,一個倒三角的胴體,寬厚的胸膛上,兩塊胸肌囂張的隆起”[11]97;鐵牛“一條黑帆布的臘腸褲,箍得腿上的肌肉波浪起伏。皮帶也不系,褲頭滑得低低的,全身都在暴放著野蠻的男性”[11]98。這群男性高大而強壯,但卻并非湘西男子或城市底層勞動者的模樣,因為他們的身體包裹在色彩艷麗的緊身衫下,以一種最能暴露身體曲線的方式吸引他人的注目,這樣性感的男體適合觀賞,卻不適合勞動。
他們并不是沒有正經工作的機會,不論是阿青、小玉還是龍子,都有男人愿意給他們一份正經的工作,但那樣體面的日子他們都過不慣,“仍舊會乖乖的飛回到咱們自己這個老窩里來。”[11]7這群野孩子追求的是一種精神和肉體上的自由,蓮花池這個老窩象征著精神自由的絕對領域。他們寧愿在蓮花池畔用自己身體短暫交易換取靈魂自由,也不愿被人用物質長久地束縛,就算是以愛的名義都不行,最典型的是黑暗王國的野鳳凰阿鳳,他深愛且深愛他的龍子將他們共同的家布置得衣食無憂,但阿鳳寧可出賣身體給不愛的男人換取金錢。面對一個愿意把心掏出來給自己的瘋狂愛人,這個不愿陷入愛情牢籠的野孩子說“我就是耐不住,一股勁想往公園里跑。”即使是愛也無法束縛骨子里向往自由的他。龍子越是深愛越是束縛,阿鳳便越想逃離。阿鳳必然是在愛與自由之間苦苦掙扎過的,他清楚自己活著一天身體就屬于自由一天,同時他愛龍子但無法給愛人想要的安定,他愛他,更愛自由,所以選擇了了結自己,所以倒在龍子懷里的阿鳳垂死的眼神一點怨毒都沒有,還露著令龍子心碎的歉然和無奈。
這些被正常話語稱之為變態的男性身體因為逐心隨性而顯得放蕩不羈,他們的靈魂卻不曾被肉體羈絆,他們骨子里流淌的野性血液是具有反傳統意義的,同性戀的身份使之成為異端,盡管正統話語對他們施以道德與輿論的封殺,這群不停飛翔的青春鳥依然追逐自己心靈的選擇,演繹一曲生之悲歌。
三、結語
“文化史一再證明,每一次人的解放……都是人的肉體與‘上帝’和‘撒旦’戰斗”[8]329。身體的想象是人們對形而下的“身體”的形而上“常識”,男性身體想象是長期社會訓規的產物。在陽剛健壯的“正常”男性身體想象的普遍性下,經濟狀況、社會階層和自我認知狀態等因素決定個體男性身體想象的特殊性。個人所處的話語圈影響男性對自我身體想象的期待:天然的湘西世界里,純樸如大自然之子的男性對于健康的身體有著深深的崇拜;黃包車夫這一行崇尚像鐵一般的硬棒身體,所以祥子評判自己身體各個獨立器官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硬棒實用;在男同性戀話語圈中,年輕漂亮的男性身體才有驕傲的資本,所以再有錢的盛公因為衰老也不能換來年輕一輩的真心陪伴,過氣的電影小生陽峰只能跟著華國寶性感騷包的身體哀嘆逝去的年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則在常人避之不及的病態身體中找到了過剩欲望的釋放窗口。
社會訓規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社會各個階層男性對自我身體想象的期待,當期待與現實發生沖突時,男性心理易走向崩潰。一味地將男性身體想象的可能形態單一化、強勢化和精英化使處在男權社會中的男性所受到的壓力和壓抑也并不小于女性。所謂正常的男性身體可能在心靈上受到的禁錮更加嚴重,祥子無法正視身體并非無所不能這一事實,生理的疾病與道德、尊嚴相捆綁,陽痿的男性背上的更多是心理上的沉重枷鎖。而低吼欲望的于質夫們、徘徊于蓮花池畔的野孩子們,這些男性邊緣身體形態的書寫與反抗男權統治的女性欲望書寫類似,都是以真正的人性抵抗社會的規訓。
[1]李廷茹.誤區中的女性話語——當代中國女性“身體寫作”的文化分析[J].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7.
[2]張志忠.眾聲喧嘩中的三重遮蔽——從郁達夫、王小波筆下的孽戀和虐戀談起[J].海南師范學院學報,2006(01).
[3]理查德·舒斯特曼.身體意識與身體美學[M].程相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4]沈從文.沈從文集[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7.
[5]吳福輝.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M].3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6]老 舍.駱駝祥子[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8.
[7]王德威.想像中國的方法[M].北京:三聯書店,1998.
[8]張 檸.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9]嚴家炎.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M].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10]郁達夫.郁達夫選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11]白先勇.孽子[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