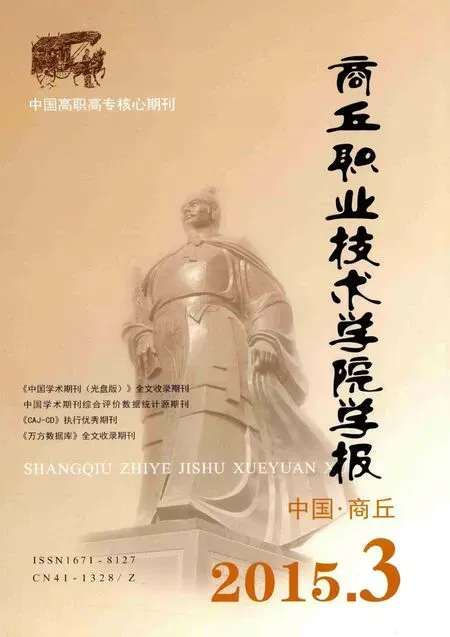女性主義批評課程設置難點及應對策略
趙思奇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一
女性主義批評是女權政治運動深入到文化領域的產物。它最早出現于18世紀的法國,1791年婦女領袖奧倫比·德·古日發表了著名的《女權宣言》,與此差不多時間,在與法國一水之隔的英國,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在1790年寫了《為人權一辯》,這些理論上的先導為日后女性主義的進一步發展鋪下了堅實的基礎。自19世紀晚期以后,出現了女性主義批評的代表人物,包括弗吉尼亞·伍爾夫、波伏娃、凱特·米利特、貝爾·胡克斯等人。弗吉尼亞·伍爾夫致力發掘獨立的女性文學傳統,從男性壟斷的文學史中梳理出一條清晰的女性文學脈絡;波伏娃批判了男性作家作品中對女性形象的誤讀,并對這些女性形象給予重新評價;凱特·米利特將兩性關系與男權社會權力結構聯系起來,對文學中的父權制進行了全面的批判,通過將男性作家勞倫斯、亨利·米勒和諾曼·梅勒的作品與同性戀作家讓·熱內作品的比較,指責男性作家文本中的性別歧視;貝爾·胡克斯則從黑人群體的立場,批判了主流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對種族問題的忽視。上述批評家們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女性主義批評的不同緯度和層面,雖然立足點各有側重,但無一例外開拓了傳統文學領域研究的另一維。由此可見,女性主義批評是一種用女性意識關照文學作品,凸顯女性視角和女性審美追求的文學批評方法。作為西方文論流派的一個重要分支,它在對男性中心詩學進行全面反思的基礎上,糾正單一男性視角建構文學史的偏差,模塑新型兩性關系的未來趨向。尤其20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登陸中國,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已經演變成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流派。作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促進了中國女性研究的興起和女性文學的繁榮,它從性別的角度打開了一個沉睡千年的女性世界,構筑了文學研究的新層面。
二
正是鑒于女性主義批評的重要價值,目前,國內越來越多的高校開設了性別研究課程。其中,講授方法各有不同,要么以講述女性主義批評家的批評思想為主,要么用性別視角解讀國內外文學作品,要么用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闡釋女作家生平與創作。可見,女性主義批評作為一種理論,在文學研究中的作用舉足輕重。目前國內從事性別研究的人員數量龐大,專業繁多,使得女性主義批評在理論研究和批評實踐的層面,都存在著概念誤用的狀況,甚至出現概念的含混不清、闡釋的簡單化和機械化等問題。鑒于此,開設女性主義批評課程,不僅對于幫助學生厘清女性主義批評的一系列概念至關重要,對于完善大學生的知識體系大有裨益,同時,對于引導他們以一種新的視角解讀文學作品,培養他們敏銳的性別視角和性別意識,糾正傳統性別觀念中的偏差有著現實意義。鑒于西方女性主義批評流派的紛雜以及批評家的眾多,且女性主義批評和哲學、社會學及政治學都有密切聯系,不同專業研究者研究的切入點各有不同,即使同在文學領域,不同方向的研究者也會有各自的研究視角,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給學生梳理出女性主義批評的主體框架和脈絡,課程設置的立足點至關重要。而且,要在有限的時間內把這門課程核心脈絡講述清楚,時間的把握也非常重要,如何減少不必要的教學資源浪費,成了女性主義批評課程設置的首要問題。如果采取傳統的以批評家為主體的教學方法,雖然知識面很普及,但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同一個理論問題會反復地講。
以“姐妹情誼”這個理論問題來說,“姐妹情誼是女性主義的理論和批評的基本原則,也是女性文學樂于建構的理想國,它的動因在于女性作家、批評家爭取女性團結以獲得力量的愿望,也基于女性四分五裂而無力反抗壓迫的實際”[1]89,對于這個理論話題,白人女性主義批評家探討過,黑人女性主義批評家也探討過,如果以批評家為主體來講,倒是可以講清楚各自對這個問題不同的看法,但白人女性主義批評家之間有什么差異?白人女性主義批評家和黑人女性主義批評家之間又有什么不同?為什么會產生這些不同?很顯然,這種教學方法缺乏一種縱向的比較,造成學期課程結束后,學生掌握的知識點猶如一盤散沙,無法形成一個整體的知識體系和清晰的知識脈絡。而關鍵詞的課程設置恰恰可以避免這個問題,不僅讓課程條理清晰,而且學理性強,節約教學資源,彰顯文藝理論專業特色。鑒于此,以“關鍵詞”作為入手點,以點帶面,進而讓學生了解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全貌,掌握女性主義批評的本質內涵,是一種有效且可行的授課方法。具體而言,梳理出女性主義批評的關鍵詞匯,包括“女性文學傳統”、“女性寫作”、“女性形象”、“姐妹情誼”、“雙性同體”等,以上述關鍵詞作為專題,分課時給學生講述。在授課過程中,先從理論的角度入手,厘清概念,然后介紹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發展歷程中,不同批評家對這個概念的各自看法,歸納出她們的相同點和不同點,挖掘出產生分歧的深層原因。
以“女性文學傳統”為例來說明,英國女性主義批評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女人的職業》一文開頭中寫道:“多年以前,范妮·伯妮、阿芙拉·貝恩、哈麗雅特·馬蒂諾、簡·奧斯汀、喬治·愛略特等人就已開拓出一條道路——許多著名的女人,和更多不知名、被人們遺忘的女人都曾先于我,鋪平道路,規范我的腳步”[2]1366。很顯然,她提出了一個女性主義批評中重要的話題——即探尋女性文學傳統的問題。自伍爾夫之后,英美后世的女性主義批評家們就沒有放棄過建構傳統的努力,雖然各自的側重點各有不同,如肖瓦爾特提出“女性亞文化群”,從文化層面上凸顯女性傳統的獨特性;愛倫·莫爾斯將女性文學史作為與主流文學并行的潛流;吉爾伯特和古芭用現代批評理論闡釋女性文學傳統存在的原因等,她們側重于“建構”,樹立一種傳統和規范。而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們則采取“解構”的立場,她們認為“傳統”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命題,女性的寫作身份才是關鍵,“哪里有壓制,哪里就有女性”[3]8。由上可見,英美派和法國派雖立場不同,但基本都將討論的立足點放在女性寫作的領域內,這是白人女性主義批評的特色。相應的,黑人女性主義批評也提出了建構“文學傳統”的命題,主旨和英美派一致,側重于“立”,但突破了寫作的領域,而深入到文化范圍,將音樂、建筑、花草樹木包括黑人女性的生理特征等都納入到傳統之內,對白人女性主義批評是一個補充。在此基礎上分析不同的女性主義流派產生上述分歧的原因。
每一個論題都采取上述授課方法,不僅能讓學生準確地把握理論內涵,而且清楚每一個概念流變的來龍去脈。上述關鍵詞匯講述結束后,學生就會對西方女性主義批評有一個宏觀且細致的把握,實現教學目的。具體到教學過程,女性主義批評關鍵詞之間不是相互隔離的,而是有內在聯系,所以在教學過程中,把握好先后次序,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可讓教學過程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具體而言,將“女性文學傳統”放到首位,因為它是總綱性的論題,牽涉到對“女性文學”的定義;然后由此發散出“女性形象”這個理論話題,因為“女性形象”來源于“女性文學”對于文學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分析,由此可以洞見男性文本和女性文本在塑造女性形象時的性別意識差異;在此基礎上引出“女性寫作”這個論題,分析女性寫作的含義,挖掘隱藏于其中的女性視角、女性身份以及女性心理;個體女性在女性心理、女性視角等要素之間存在差異,導致“姐妹情誼”建構的困境,就此引出“姐妹情誼”這個論題,如此遞進。抓住關鍵詞這條線索,依照教學規律,由知識點入手,由點及面,向學生呈現出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全貌。鑒于女性主義批評的理論特性,在授課過程中,將課堂板書與多媒體結合起來,運用圖片和視頻,使課程充滿活力。以問卷調研的方式,了解學生的興趣點所在,融入教學中,真正做到讓書本知識活起來,而不再是枯燥的理論。最后以論文考察的形式,檢測學生對理論問題的理解和掌握情況。
三
具體到教學過程,首先注重女性主義批評的本土化闡釋。女性主義批評作為西方文論的重要流派,屬于外來理論,其內容和話語形式具有明顯的異域色彩,造成了學生接受的陌生感和艱澀感,總感覺與課程“隔著一層”。這就需要教師盡可能用本土理論去包容、去覆蓋這些外來理論。當然,這種闡釋不是生硬地把外來理論變成中國理論,中國的女性文學和女性批評已經有了獨立的學科和獨立的研究范式,所以用本土理論去統領西方女性主義批評中相通的部分,是行得通的。比如“女性寫作”,白人女性主義批評執著于在寫作領域對性別權力的占有,而黑人女性主義批評則傾向于通過寫作達到男女兩性的和諧。這些問題,中國的女性作家也會遇到,因此借用西方女性主義批評,可以實現中西理論的有效對接。對于那些在本質上與本土理論不相容的批評,自然可以另換一種方式來闡釋。其次,將鮮活的感性知識融入課堂中,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女性主義批評作為一種理論話語,本身缺少栩栩如生的文學文本作為感性支撐,而對文學作品的閱讀量少是本科生的通病,這會造成他們接受上的困難。因此,在講解每個論題的過程中,將一些生動鮮活的文學作品融入課程的各個知識點,讓學生從感受作品出發,去領悟女性主義批評的內涵,降低理論的難度,培養學生的興趣。比如,在講述女性形象這個理論問題時,可以將《傲慢與偏見》、《陽光下的葡萄干》、《最藍的眼睛》等西方女性主義文本納入到課堂中,白人女作家和黑人女作家都會談到女性形象,她們筆下所塑造的女性類型,必然不同。白人女作家一般擅長描繪“天使”與“妖婦”,黑人女作家一般描繪“女保姆”、“女家長”等等,這是文化差異造成的必然結果。這些女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和男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有什么不同,這些不同反映了什么深層問題。從文學作品入手,讓學生在形象思維中接受理論知識。再次,將小組討論融入課堂中。借鑒西方女性主義團體注重開展討論小組的方式,將課堂分組討論和小組交流與教學結合起來,激發學生參與課堂的積極性,增強師生互動,讓理論有生命力,而不再是枯燥的書本知識。
[1]魏天真.“姐妹情誼”如何可能?讀書[J].2003(06).
[2]弗吉尼亞·伍爾芙.伍爾芙隨筆全集[M].王 斌,王保令,胡龍彪,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3]瑪麗·伊格爾頓.女權主義文學理論[M].胡 敏,陳彩霞,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