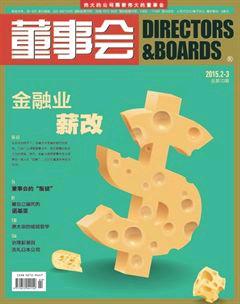員工持股破題內部監督
李駿

十八大以來,在政府高調反腐的背景下,不少國有企業高管腐敗案例被先后曝光。諸多的案例都在說明,國企的公司治理是存在一些問題的。
我們通常所說的公司治理,實際上是有兩層含義,一層是外部監督機制,包括法人治理結構的建立(引進三會制度、建立外部董事機制、職工董事制度等),推動企業上市(依靠資本市場的力量監督),規范國有股權轉讓(管控過程)等。另外一層是內部監督機制,也就是通過產權制度的改革,實現經營者和所有者利益的綁定,同時在利益一致的情況下,經營者之間形成自我監督和相互監督的關系。
2000年以后,國企的外部監督機制不斷完善。例如從2003年起國資委相繼出臺多部法律規范國有股權轉讓(《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企業國有產權向管理層轉讓暫行規定》等),相關公眾公司的制度建設也不斷出臺。但從目前的案例來看,似乎外部監督機制并沒有發揮其理想的作用。
以三會制度為例,三會制度本質上是在公司內部劃分權力,即決策權屬于股東大會,經營管理權屬于董事會或執行董事,監事會則行使監督權。通過權力的分配與制衡,使三大機關既能各司其職,又能相互制約,保證公司順利運行。同時,董事會和監事會還分別通過設立外部董事、職工監事,分別代表中小股東和職工權益,在董事會和監事會內部再形成一次權力的劃分和監督。
雖然這些看起來非常合理,但實際上忽視了外部監督機制有效運作有其賴以生存的背景,包括市場力量強大、股權相對分散、資本市場成熟等。倘若沒有這些條件,外部監督機制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就目前的國有企業而言,國有股一股獨大(就算是上市公眾公司,也多數如此),另一方面,由于所有者缺位,出資人難以監管,市場控制權又太小,董事會、監事會、獨立董事實際上就是由內部人控制,外部監督機制難以發揮其效果。
因此,最終要解決國企的治理問題,還需從內部監督機制著手,從產權制度著手。
內部監督機制通過管理層持股(或者說員工持股),將公司利益與每個員工利益進行緊密掛鉤,促使內部員工自發地去監督企業的重大決策和重大經營活動,有效地防范企業家的短期行為,甚至是損公肥私行為,這是實踐證明非常有效的公司治理手段。例如中聯重科和張裕A,在進行過“小改”之后,管理層的積極性被激發出來,公司業績迅速增長,一舉成為行業龍頭。
雖然內部監督機制是解決國企治理的良藥,但由于涉及國企競爭與壟斷之爭、管理人員行政化、利益平衡等敏感話題,在2004年以后,內部監督機制的實施相當困難。
近年來,隨著民營企業實踐的“倒逼”,國企人才流失,管理層也開始重視起了這項機制建設,逐漸摸著石頭過河。自從2006年起,允許國有上市公司開展期權激勵;2012年至今,國資委在中關村的分紅權激勵試點;還包括后來的上海張江、武漢東湖、合蕪蚌試驗區和長株潭高新區等。這一系列政策出臺均體現了管理層對加強國企治理緊迫性的認識,但更多地類似領導人薪酬改革,仍然受到條條框框限制(如收益封頂),尚未觸及公司治理的核心問題。
十八大以來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更加關注產權改革這一核心問題。例如上海率先出臺國企分類,各地也先后出臺類似政策,通過分類允許一些競爭性的行業走向市場化,混合所有;而降薪,重提去行政化,引入職業經理人制度也在逐步實施;搭建國有控股平臺,從管國企到管國資的思路轉變,也為產權改革搭橋鋪路。
同時,最近基金公司已允許管理層持股,證券公司也在試點激勵,相信不久以后,隨著人才競爭的加劇,金融行業的國企激勵能率先破冰,國企公司治理會再上一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