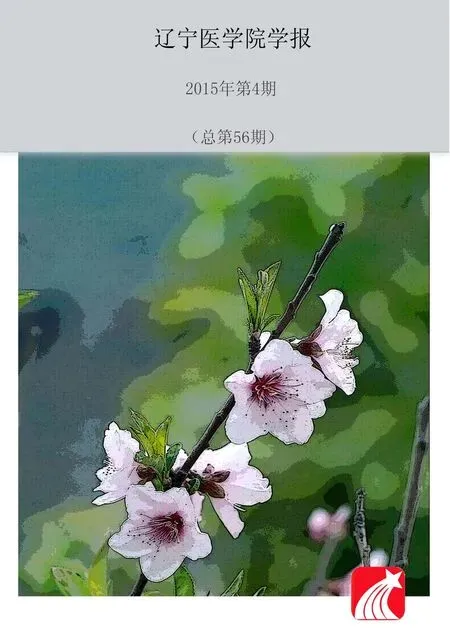話語的權力研究
逄勃
(錦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遼寧 錦州 121001)
話語的權力研究
逄勃
(錦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遼寧 錦州 121001)
話語的權力在很多學科都受到過廣泛的關注和研究,學科領域不同,研究范圍和視角也不盡相同。通過界定社會權力的屬性及話語權力的核心問題將有助于對特定話語類型的權力進行分析。對新聞話語的權力研究主要可以分為三個層面:宏觀層面研究、中觀層面研究和微觀層面研究。跨學科、跨文化的新聞傳播研究發展趨勢,也為新聞話語的權力研究開拓了新空間。
話語;話語權力;新聞話語;權力分析
“話語”一詞源自拉丁語discursus,意思是“運行或分散的過程”,最早用于語言學中,常用來強調口頭或書面語言的高級結構屬性,在語義分析和話語分析中,“話語”泛指所有模式和情境下的“談話”的概念。[1]當“話語”是指與給定的社會實踐類型相匹配的語言編碼類型及使用時,則可具體稱為:法律話語,醫療話語,宗教話語,新聞話語等等。在福柯和其他社會理論家的著作中,將“話語”定義為一個可以進行陳述的符號序列的實體。因此,話語是由主體、客體和其他陳述的關系序列構成的,而生產話語的規則被定義為話語格式。
一、話語的權力
很多學科都對話語的權力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且大多都限定在社會學和政治科學領域。在歐洲和拉丁美洲,學者對語言、話語、權力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作出過許多有趣的研究。有的學者將話語研究限定在語言與權力的一般關系上(Kramarae, Shulz,&O’Barr,1984;Mey,1985);有的針對人際傳播領域的話語權力進行研究 (Berger,1985;Seibold,Cantrill,&Meyers,1985);有的學者以人種學方法關注地域文化(Bauman& Scherzer,1974;Saville-Troike,1982)或跨文化傳播中權力的作用;而女性研究的學者則已經對男性在語言中的支配地位和權力進行了討論(Kramarae,Thome,&Henley,1983)。[2]
1.社會權力的屬性。梵迪克在他的《話語結構與權力結構》研究中重點關注了在社會情境中作為一個特定的語言“文本”形式使用的話語以及一些涉及支配或權力在語言的變化和風格中的作用的社會語言學研究(Scherer&Giles,1979),他主要關注和研究西方文化背景下,社會或社會交往中權力的作用。他認為社會權力是群體、階級,或其他社會形態之間,或者作為社會成員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屬性。雖然我們也會談及權力的個人形式,但是這種個體權力與我們系統論述的作為社會互動的話語權力的作用關系不大。
現代西方社會的所有社會控制都是由權力機構限定權力的領域和范圍。行使權力控制需要有基礎即社會資源,這些資源通常是具有社會價值但卻分配不均的社會財產,例如:財富、地位、官銜、身份、知識、專業、特權,甚或是主流群體的成員身份。同時,社會權力的行使和維護是以意識形態框架為先決條件的。這個框架是由社會共享的、利益相關的群體及其成員的基本認知構成的,并主要通過傳播和話語獲得、確認或改變。
2.話語權力。通過話語進行社會控制即為話語權力的行使,它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對話語的控制和話語生產本身。所以話語權力的核心問題就是:誰在什么情況下可以給誰說或寫什么?誰能接近不同形式的或流派的話語或者話語的生產手段?
權力不只出現在或貫穿于話語中,它是隱藏在話語背后的社會力量。有權力的群體及其成員對話語的作用、流派、場合、風格行使著越來越廣泛的控制。他們控制著公共話語的主動權,為公共話語設定基調和話題,為文本或談話設定風格,決定話語的參與者和接受者。話語權越少的人對不同形式的文本或談話的接近越少,即使是偶爾有機會參與對話也只是被動的回應和簡單的接受,并最終成為“沉默的大多數”。對于大多數正式的、公共的或印刷話語類型(包括那些大眾媒介),沒有話語權的人通常只能是受者。
話語生產模式是由“符號精英”們控制的,例如:記者、作家、藝術家、導演、學者及其他群體以“符號資本”為基礎行使話語權力(Bourdieu,1977,1984;Bourdieu&Passeron,1977)。這種符號權力不只限于話語本身,還延伸到影響模式:設置公共討論議程、管理信息量和信息類型、影響話題相關性,特別是以何種方式公開描繪誰。他們是公共知識、信仰、態度、規范、價值觀、道德和意識形態的生產者,因此他們的符號權力也是一種意識形態權力。
二、不同視角的新聞話語權力研究
對新聞話語的權力研究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個是宏觀層面研究,主要涉及將新聞話語權力與國家的政治經濟、宏觀的社會歷史結構相結合的媒介環境研究等視角;一個是中觀層面,涉及到新聞組織研究,微觀社會學等視角;第三個層面是微觀研究,主要是運用話語分析方法對制約新聞生產的符號權力和意識形態權力進行研究。
1.話語的“符號權力”—布爾迪厄的實踐語言觀。布爾迪厄認為,語言本身就是社會歷史現象,語言傳播就是包含利益和權力關系的實踐行為。布爾迪厄把他的語言研究深深地推進到政治、意識形態批評及純粹語言學批評都未曾涉及的領域,他論證了“語言關系總是符號權力的關系,通過這種關系,說話者與他們所屬的各種群體之間的權力關系轉而以一種變形的形式表現出來”(布爾迪厄,實踐與反思,p189)。這是布爾迪厄的原創性研究:解釋語言與權力的關系。
布爾迪厄強調社會環境、權力秩序的決定性作用,更傾向于從實踐社會學的關系視角探討權力關系的支配現象。布爾迪厄的實踐主義語言觀是試圖超越社會科學領域里長期對立的建構主義和結構主義理論視角,將語言視為處于實踐語境中的行動。他認為,要理解語言的邏輯,就必須要理解語言市場中的語言行為及其權力和資本的關系。換句話說,他強調語言交流中的社會結構的決定因素,他認為“整個社會結構呈現在傳播中(自然也包括話語),生存的物質條件通過語言生產關系決定著話語,語言生產關系使話語成為可能并建構話語”。
2.新聞的“框架”生產——塔奇曼的新聞“知識”。塔奇曼(1978)認為[3],話語的自反性和索引性構成了新聞生產的組織語境。話語的索引性和自反性是構成語境的兩大要素,通過“索引性”和“自反性”的循環往復,形成了人們理解解釋生活世界意義和秩序的一個個“框架”。新聞話語的自反性和索引性表現為組織內部的協商和借助組織語境進行新聞生產從而證明組織的合法性。
新聞知識是一種歷史的現實再建構。社會關系建構了知識,而知識組織了經驗,規范了社會意義,這種相互建構的關系包含人類活動和權力,而新聞機構正是人類生產知識(社會資源)和權力(分配資源)的機構。新聞的生產過程本身是由新聞價值體系和有關新聞和新聞價值的專業意識形態來控制的,而這恰恰是為精英階層的興趣和關注點服務的。同樣的,新聞生產的日常組織管理也要服務于機構情境下的新聞采集,如國家的主要政體、警察、法院以及大型公司這些機構為新聞組織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新聞源保障(Fishman,1980;Tuchman,1978)。當記者與機構的傾向和要求發生矛盾時,新聞規范仍舊是指導行動的意識形態。
3.話語分析——新聞話語權力的研究工具。在《作為話語的新聞》中,梵迪克從社會認知的角度出發,對新聞制作和新聞理解中的新聞結構與認知過程進行分析,清楚闡釋了新聞價值和意識形態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他認為,新聞制作和新聞理解是在新聞源所給出的定義之上的一種意識形態的建構,而媒體從本質上說,就不是一種中立的、有常識的或者理性的社會事件的協調者,而是幫助重構預先設定的意識形態。
無論從宏觀社會學還是微觀社會學的新聞組織研究,都是從研究者或從權力主體的視角進行研究,雖然有關注社會互動中的權力變化,但仍呈現出對新聞話語權力行使的被控制方,即新聞受眾研究的忽視或模糊。
三、新聞話語權力研究的新空間
1.不可忽視的受眾效果分析—質化與量化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如同梵迪克在他的新聞話語研究中指出的那樣,對新聞話語的權力進行研究,受眾研究和效果分析應該是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隨著大眾傳播研究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新聞的跨學科研究已經成為主導趨勢,而質化與量化相結合的跨學科研究方法的運用將有助于對新聞話語權力進行更加科學的分析。[3]
在大眾傳播研究中,運用豐富的統計分析工具來研究傳播效果的方法也可以借鑒到新聞話語的選擇控制及效果分析中。例如,研究媒介對政治傳播的誘因效應就是將微觀層面的心理學理論與宏觀層面的政治傳播理論聯系到一起,通過由媒介參與或發起某些議題,忽略其他議題并以此改變某些選舉候選人的評估標準的過程。很多的政治信息處理研究還反映了圖式理論的基礎應用,因為心理圖式一旦激活就會促進和塑造信息的加工,從而為個體形成評價和理解他們的社會環境提供原材料(Graber 1988,Fiske and Taylor 1991)。正如許多學者認為的那樣,媒體在公共話語中不只是起到一個議程設置的作用,通過新聞和輿論的選擇和“框架”,媒介在建立構建、辯論、解決社會問題的標準尺度上起著關鍵作用(Gitlin 1980,Graber 1988,Gamson 1992,Neuman etal.1992,Shah etal.1996)。西方的大選研究表明,選民對問題形成不同的心理圖式鏈接是基于他們的核心價值觀與媒體報道的互動;反過來,這些問題的解釋也塑造了信息的加工和判斷(Domke&Shah 1995,Shah etal.1997)。
2.跨文化傳播語境下的新聞話語權力研究。新聞話語權力的巨大研究潛力和空間期待研究者盡可能地開展多視角多維度的研究,大眾傳播的跨學科跨文化研究趨勢也是新聞話語權力研究的必然發展趨勢。自19世紀后半葉起,媒介開始將地方層面的社會互動嵌入到民族國家情境,到20世紀90年代,媒介的高速發展使之沖破國家屏障,成為全球化進程的強大支撐。在全球化時代,媒介不僅為各個國家及其人民提供了傳播渠道,而且還建立了跨地域跨民族的網絡。越來越多的媒介產品的涌入和跨越國界的傳播,使得新聞話語的權力結構與功能在新的社會情境和社會互動中發生著變化并產生了新的社會意義。國家間的政治、意識形態、文化或地區差異都可能會影響不同國家受眾對新聞事件的感知、解釋和描述,尤其是在沖突事件的新聞報道上則會更加典型。依據新國際信息秩序討論框架,在國際傳播中出現的新聞圖式西方化是因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媒體對西方通訊社的主導地位和權力有歷史的和專業的依賴,因此,來自和關于第三世界國家的新聞或者由西方記者來報道,或者使用西方通訊社的報道格式,絕大部分都是刻板印象化的“第三世界”報道,以便能夠被這些國際通訊社采用或提供給他們的客戶[4](Van Dijk,1984b,1987c)。雖然西方學者通常認為上述討論是對新聞“自由”的攻擊,但是這里面自由只是權力與控制的代名詞而已。◆
[1]張意.文化與符號權力—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導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2]Smitherman-Donaldson,G.and van Dijk,T.A.(eds),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Detroit,MI: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Tuchman,G.Making News: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New York:Free Press.1978.
[4]van Dijk,T.A.Prejudice in Discourse,Amsterdam:Benjamins. 1984.
An Analysis on Discourse Power
Pang Bo
(Jinzhou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Jinzhou Liaoning,121001)
The discourse power has received wide attention and research inmany disciplines.With different disciplines,research scope and perspectives are also different.Defining the attribute of social power and the core issue of discourse power will contribute to analyze the power of specific discourse types.The research on news discourse power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macro research,mezzo level and micro level.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new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 cross-disciplinary and cross-cultural also has created new space for the study of the powerofnewsdiscourse.
discourse,discourse power,news discourse,power analysis
H315
A
1674-0416(2015)04-0142-03
[責任編輯:王靖宇]
2015-07-11
逄勃,女,1981年生,遼寧錦州人,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