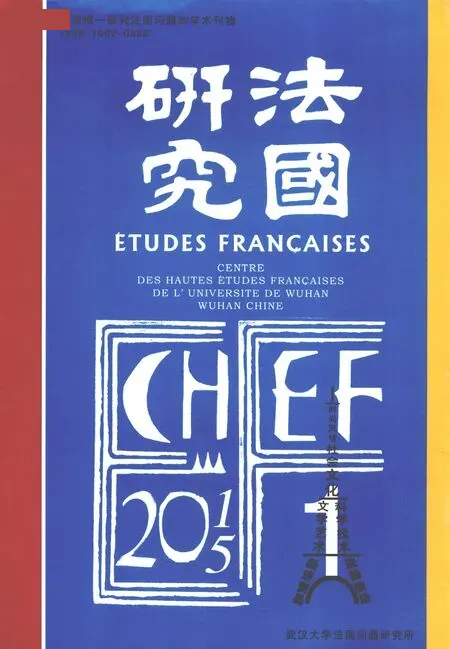“我是查理”:《查理周刊》①據新華社參考消息譯名室李學軍:《查理周刊》的法文刊名為《Charlie hebdo》, “hebdo” 意為”周刊,按照法語音譯規則,Charlie應被譯為“沙爾利”,因此,《Charlie hebdo》的正確譯法是《沙爾利周刊》。但是,由于《查理周刊》這一轉譯自英文的譯法已經廣泛傳播,為避免誤解,本文沿用,特此說明。的謔虐傳統
程 平
?
“我是查理”:《查理周刊》①據新華社參考消息譯名室李學軍:《查理周刊》的法文刊名為《Charlie hebdo》, “hebdo” 意為”周刊,按照法語音譯規則,Charlie應被譯為“沙爾利”,因此,《Charlie hebdo》的正確譯法是《沙爾利周刊》。但是,由于《查理周刊》這一轉譯自英文的譯法已經廣泛傳播,為避免誤解,本文沿用,特此說明。的謔虐傳統
程 平
【摘要】《查理周刊》繼承了其前身《切腹》雜志目空一切、尖酸刻薄的精神,是法國頗具激進自由主義傳統的諷刺性雜志。它用大量篇幅刊登一些搞笑、傷人甚至蓄意挑釁的漫畫,諷刺極端右翼分子、天主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總統、富商、各種意識形態等。在《查理周刊》遭受伊斯蘭極端分子恐怖襲擊的大背景下,通過梳理該雜志的前世今身可以分析《查理周刊》在法國賴以生存的政治土壤和社會氛圍,揭示該刊在法國民眾中的影響力和象征意義,并表達作者個人對“我是查理”和“我不是查理”這兩個貌似矛盾口號的獨立思考:前者是捍衛言論自由的誓言,而后者則強調的是對言論自由這一原則不同維度的微妙理解,探討的是新聞自由背后的倫理共識。
【關鍵詞】《查理周刊》 “我是查理” 謔虐
[Résumé] Charlie Hebdo, à l’esprit caustique et irrespectueux hérité de Hara-Kiri, est un journal satirique fran?ais de tradition libertaire. Il fait une large place aux caricatures dr?les, blessantes ou même délibérément provocantes, qui se moquent de l’extrême droite, du catholicisme, de l’islamisme, du juda?sme, des présidents, des hommes d’affaires ainsi que de différentes idéologies. Au lendemain de l’attentat djihadiste contre le journal, le présent article, tout en faisant l’historique de Charlie Hebdo, a analysé son arrière-plan politique et social, révélé son influence et son image symbolique parmi le peuple fran?ais et exposé des réflexions personnelles sur les deux slogans ---- Je suis Charlie et Je ne suis pas Charlie --- apparemment contradictoires:si Je suis Charlie proclame la défense de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 Je ne suis pas Charlie souligne plut?t les différentes interprétations subtiles de ce principe dans sa concrétisation ainsi que la morale derrière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2015年1月7日,法國政治諷刺雜志《查理周刊》遭到恐怖襲擊,包括雜志主編夏爾伯在內的10名漫畫家、編輯和記者及負責雜志社安保的2名警察失去了生命,另有5人身負重傷! 傷亡之慘重、場面之血腥,在戰后的法國是絕無僅有的。各路媒體對此事件的報道,紛紛使用了“血洗”、“滅門”等令人膽寒的詞語,正如總理瓦爾斯所說:“它擊中了法國的心臟,每個人都感到恐懼”。
在經歷了第一波恐懼、震驚、悲傷的反應后,全球迅疾形成對《查理周刊》的強有力聲援力量:眾多媒體、普通百姓、甚至多國首腦,喊著統一的口號:“我是查理!”,共同譴責慘絕人寰的恐怖主義,并悼念在《查理周刊》事件中逝去的生命。一時間, “我是查理”、“我們是查理”的口號波及法國各地,并從法國席卷到世界多個城市,以及各大社交網站,最終演進成一場全球性事件:四十多個國家領導人、一百五十多個國家的代表參加了支持《查理周刊》的巴黎共和大游行。
“查理”,何許人也?《查理周刊》又是一份怎樣的雜志?為什么它是警方的重點警衛對象?為什么該刊物遭此滅頂之災?解開這些疑問,需要對《查理周刊》的前世今生進行梳理。
1.《查理周刊》的前身
《查理周刊》的前身為《切腹月刊》(《Hara Kiri》),它是創刊于1960年的諷刺性雜志,其創始人及靈魂人物弗朗索瓦?卡瓦納(Fran?ois Cavanna)和喬治?貝爾涅(Georges Bernier)相逢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前者是《零》雜志的銷售總監,后者是該雜志的副總編輯。
50年代末因與老板不和,卡瓦納決定單干。當時他是創刊于1952年的美國雜志《瘋狂雜志》(《Mad Magazine》)的狂熱讀者,該雜志通過各種諷刺戲謔的模仿,丑化美國社會,嘲笑一切人和一切事,在高興和愉悅的笑聲中,挑戰一切固有秩序。這種品味和風格令卡瓦納頗為喜愛和欣賞,于是,在法國自辦一份同類雜志成為他的夢想。經過反復爭取,他的計劃得到了貝爾涅的支持。貝爾涅不僅自己離開了《零》雜志,還帶走了《零》雜志的銷售網絡。于是,卡瓦納帶領一幫追隨他的年輕且不知名的漫畫家,貝爾涅率領他的報刊零售商販,兩支隊伍合二為一自立門戶,成立了新的《切腹月刊》雜志社。
1.1.刊名的來歷
這份新雜志的命名,采納了卡瓦納的主張——《Hara-Kiri》。該詞來自日文的“切腹”,代表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最高境界,即通過切腹這一壯烈的儀式,宣告對武士精神的忠誠和堅決。使用這一短促但沖擊力十足的外來語,表現出新雜志試圖一舉顛覆傳統新聞標準的強烈、甚至野蠻的意愿和決心。《切腹》完美地集合了新團隊對新雜志的全部期許:首先,《hara-kiri》(qui rit)中包含笑聲,足以表明“笑”是雜志的主要元素,諷刺與幽默是雜志的最大特征,對于嚴肅或非嚴肅的事情,處理方式一律是滑稽的,以博得讀者一笑,那“笑”可能是詼諧風趣的,或者尖酸刻薄的,也有可能是厚顏無恥的, 甚至是淫穢下流的,但“笑”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其次,“切腹”代表一種接近靈魂的方式。古時候,許多國家和民族認為人的靈魂寄宿于肚腹,如果想將自己的靈魂向外展示,通常會采取剖腹示眾的方法和儀式。因此,《切腹》雜志試圖通過這一刊名,傳遞用靈魂與讀者交流的目的,希望讀者透過嬉笑、戲謔的表象,領略他們不循規守舊,挑戰標準、挑戰制度、挑戰權威的精神和品格;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切腹”凝聚著雜志為了追求“笑”果,追求“靈魂表達”而不惜一切代價,甚至不惜自我毀滅的義無反顧,宣示著用生命捍衛靈魂的堅定不移的意志。
1.2. “愚蠢和惡毒”的幽默
《切腹》雜志的創刊號封面:血紅的背景里有一位正在開腸破肚的日本武士,“切腹”刊名下印著一行副標題 “Honni soit qui mal y panse”。顯然,副標題運用了一個同音異義詞的文字游戲,用 “panse”替換了同音的“pense”,讓一句話擁有了“未包扎好者遭唾棄”和“有邪念者被唾棄”兩層含義。聯系畫面,既有一種幽默藏在其中,又有提醒讀者不要對雜志中過激文字和漫畫神經過敏的含義。 而后面幾期雜志的副標題先后又用過“開懷大笑”和“諷刺月刊”,直到第7期,副標題成為“愚蠢和惡毒的雜志”(《Journal bête et méchant》),并從此固定下來,似乎成為該刊物自詡的座右銘。
雜志將發展方向定位為“愚蠢和惡毒”,是雜志挑戰傳統的法式幽默和主動選擇讀者的舉措。從一開始,《切腹》的定位就是小眾刊物,卡瓦納尋求的是少數對幽默質量有“高標準”要求的知音。 根據他掌握的情況,上世紀60年代,法國閱讀諷刺幽默類報刊的讀者總數約有200萬,而《切腹》面向的只是其中的10%。到1966年,《切腹》月刊的每月銷售量已經突破了25萬①Stéphane Mazurier,Hara Kiri , dans la revue Histoires littéraires, n° 26, avril-mai-juin 2006.,超過了卡瓦納的預期。
《切腹》的“愚蠢和惡毒”,具體表現在對傳統權威的象征——宗教、軍隊、警察等的強烈不滿,它會使用極為粗野強暴的方式,對它們進行反諷,比如,用糞便來隱喻它們的卑鄙和荒誕。1970年11月,甚至刊出了“大糞專號”,封面上的主編卡瓦納臉上涂滿了大便,卻仍然哈哈大笑。《切腹》中的幽默就是這樣謔而近虐的丑惡、變態、扭曲、瘋狂、令人作嘔。它追求一種讓人在大跌眼鏡的同時又被當頭棒喝的打擊力度。
除此以外,《切腹》中對廣告的滑稽模擬、放縱的色情畫面以及瘋狂的攝影小說等內容,嚴重扭曲著社會面貌,傳播著與傳統價值觀相背離的謊言、偷盜、懶惰、仇恨等負面觀念。出于對青少年的保護,并反對對老年人和家庭主婦的歧視,1961年和1966年,《切腹》曾兩度遭到停刊懲罰。
1.3. 政治轉向
起初,《切腹》月刊基本不問政治,從它每月一期的出版頻率即可推斷出,它與時事政治結合不緊。貝爾涅甚至認為,與時政脫鉤的幽默才是真正的幽默。
然而,1968年“五月風暴”之后,《切腹》月刊的主要讀者不少也是激進的“五月風暴”的參與者,他們不再滿足這樣一份與政治關聯并不緊密的雜志,他們需要的是一份能夠對當代政治、社會問題做出積極或及時反應的雜志。在這一歷史條件下,《切腹周刊》②《切腹月刊》仍然保留,卡瓦納將主編的位置讓給了熱貝(Gébé),自己只擔任《切腹周刊》的主編。(Hara-Kiri Hebdo)應運而生,在“五月風暴”之后的第8個月,其創刊號問世,與先前的《切腹月刊》相比,《切腹周刊》的時政色彩明顯增強,但與其固有、傳統的“愚蠢和惡毒”的幽默手法一脈相承。
1970年11月9日,法國總統戴高樂在科隆貝 (Colombey)的家中逝世。而此前8天,當地一家名為“五七俱樂部”(Club Cinq-Sep)的夜店發生大火,造成146人死亡。11月16日,《切腹周刊》出版了一期紀念專號,標題為《科隆貝的悲劇舞會:一人死亡》。用“1人”換下“146人”,顯然在暗諷高高在上的戴高樂。因此,該周刊被內政部責令停刊。 在很多文化中,人們講究“逝者為大”,法國也不例外。而《切腹周刊》連死人也不放過,可見它“惡毒之至”了。
為了躲避禁令,《切腹周刊》的原班人馬,僅在停刊一周后,便以《查理周刊》為名繼續出刊。之所以選擇“查理”作為刊名,原因大約有二:
一,《切腹月刊》一直持續轉載美國漫畫《花生》,其中的主人公名叫查理·布朗,他是一名單純善良的小學生,同時也是一個受人欺負的受氣包。他志向遠大,但時常碰壁,是作者查爾斯·舒茲(Charles M. Schulz)為取悅讀者而創作的一個“失敗者”形象。使用“查理”作為刊名,是有意向《花生》系列漫畫致敬①Florent Deligia,Quelle est l’origine du nom Charlie Hebdo ?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0108/;二,Charlie同時還是Charles的昵稱,而Charles又是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名字的組成部分。這樣一來,以“查理”作為新的刊名,既能繼續暗諷戴高樂,又能影射致使《切腹周刊》被迫更名的事件。
從更名過程來看,《查理周刊》重視的是它與《切腹周刊》的關聯,努力維護著兩者之間的血脈關系,同時,我們也能看出,《查理周刊》面對政府的新聞審查禁令所表現出的執拗和倔強。
《查理周刊》從《切腹周刊》脫胎而出,從未換骨,思想自由、挑戰禁忌、謔而近虐的“血統”更是一再彰顯。它繼續以既粗俗又無情,且帶有惡意攻擊性的幽默方式,攪亂新聞、漫畫和幽默傳統的道德底線,其尺度大膽充滿爭議,與其前身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2.《查理周刊》的現狀
《查理周刊》自誕生之日起,體內就流淌著將“愚蠢和惡毒”進行到底的血液。它以夸張、冒犯的方式,嘲弄宗教或世俗的一切權威,其諷刺對象是全方位的,從穆罕默德、耶穌、圣母、教皇、猶太教教徒到總統、議員、富商、金融巨頭以及不同意識形態集權政府,無一不被《查理周刊》挖苦、丑化,其中宗教和政治是該雜志最熱衷的主題。
近年來令人們印象深刻的宗教題材漫畫委實不少:先知穆罕默德赤身裸體趴在地上,說:“我的屁股呢?你們愛我的屁股嗎?”(漫畫的上方寫著“那部席卷伊斯蘭世界的電影”,暗指美國拍攝的《穆斯林的無知》這部電影,這部電影曾引發了穆斯林世界的廣泛抗議);蹲著的穆罕穆德雙手抱頭,痛苦地說:“被一幫蠢貨追捧太難受了”;正在生產的圣母瑪利亞光著并岔開大腿,小耶穌從中爬出;退休教皇摟著一位老太太感慨道:“終于自由了!”……
這些作品顯然刻意侵害宗教信仰者的感情,明知伊斯蘭教忌諱用圖畫表現真主和先知的形象,它們卻要用恣意夸張的漫畫形式來表現他們,甚至用裸體的形式來諷喻他們;因為基督教信仰童貞受孕,它們就夸大其詞地予以諷刺;因為天主教神父不能結婚,它們就反其道而行之地給教皇安排一個老太太,這一切可以說已經到了顛覆宗教傳統儀軌的地步了。
對政客的揶揄同樣是毫不留情、極富挑釁性的。當法國現任總統奧朗德傳出“性緋聞”時,《查理周刊》直接讓西裝革履的總統露著生殖器上了雜志封面;法國政治極右翼的領袖是瑪麗·勒龐( Marie Le Pen),她上《查理周刊》封面的畫面是一團熱氣騰騰的,“奉送給勒龐以及給她投票的選民”的大便……,畫面極為不雅。
然而,這樣一份雜志如何能夠在法國生存45年?它如此地百無禁忌,自由表達無下限卻沒能受到根本遏制,是否因為它具有特殊的條件和土壤?它是否遭遇危機?它的存在價值又是什么?
2.1.《查理周刊》的政治土壤
在這個世界上,也許只有法國可以孕育和容忍《查理周刊》這樣的雜志,因為,法國一直將“自由”排在國家格言的第一位,而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當為要沖。早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政治活動家米拉博就向三級會議呼吁:“讓法律的第一條永遠奉獻給出版自由,使它居于神圣的地位。在所有的自由中,它最不能觸犯,最不受限制。假如喪失了它,其他自由便永遠得不到保障。”①《資本主義國家民權法則及其簡析》,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編: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1頁。果然,在1789年制定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中,法國人用綱領性文件的形式確立了新聞出版自由、輿論自由和言論自由的重要地位,其中第十條明確規定:“任何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即使是宗教上的意見——而不受打擊,只要他的言論不擾亂法定的公共秩序”②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de1789, http://www.textes.justice.gouv.fr;第十一條進一步規定:“思想和見解的自由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除非根據法律決定的情形而必須為這項自由的濫用負責,每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
這些國家意識形態的價值體系,恰好是《查理周刊》40多年來敢于理直氣壯地把尖酸刻薄、粗魯無禮作為辦刊特征的政治根源。雖然,法國大革命已過去了200多年,但法國激進主義政治傳統并沒有漸行漸遠。1968年的“五月風暴”給這一政治傳統注入新的能量。誕生于“五月風暴”的《查理周刊》,隨即被公認為是一份極左翼的激進雜志。年長的和年輕的“查理們”前赴后繼、崇尚絕對自由,嘲諷所有道德和宗教權威,毫無顧忌地沖撞各種禁忌。這份雜志能夠在法國存在40余年,離不開法國特定的政治環境與社會氛圍。《查理周刊》前任記者伊蓮娜·康斯坦蒂認為,《查理周刊》意味著“絕對的言論自由”,“我們可以沒有阻礙地寫任何事情,不需要敬畏任何機構。”“在我們這里,漫畫家是老大。”③符遙、王思婧,《<查理周刊>諷刺了誰?》,《中國新聞周刊》,2015年1月20日。
除了自由的精神之外,平等的邏輯也是《查理周刊》的重要支點。被寫入1789年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的“生而平等”思想,長期以來在法國深入人心。推而廣之,諷刺面前當然是人人平等。以法國前任總統薩科齊為例,盡管他的私生活、相貌、言行、執政,曾都遭到過無情的嘲弄,但是無論嘲諷得多么過分,薩科齊依然認同“諷刺象征著一個自由空間,如果有人阻止,民主就會感到非常遺憾。”這一價值觀念。薩科齊還認為,“宗教應該像權力一樣,應當善于接受批評、諷刺和嘲弄。這些做法對于所有的宗教——其中包括對于最后來到法國的伊斯蘭教——來說,都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伊斯蘭教在義務上不同其他宗教平等,那么它在權利上也不能同其他宗教平等。實際上,所謂對穆斯林的最大不尊重,不是像嘲笑上帝一樣諷刺穆罕默德,而是把法國的穆斯林看作是一些與眾不同的公民。”①尼古拉·薩科齊:《薩科齊自述:見證》(曹松豪譯),《見證》第二部分:“我的思想遭到過諷刺(1)”,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正因具有由法律支撐的“自由的精神”和“平等的邏輯”形成的雙保險,才得以使法國社會對《查理周刊》有著強大的寬容度和接受度,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飽受羞辱的奧朗德總統,能夠在查理慘案發生后1小時以內親臨現場,將血案定性為 “挑戰新聞自由”的恐怖襲擊,并將此事件中的逝者稱為國家英雄,說他們“為捍衛共和國立國之本的自由精神而死”。
2.2.《查理周刊》的坎坷命運
雖然有法律保障,并有“自由的精神”和“平等的邏輯”兩大支撐,《查理周刊》的命運仍然歷經坎坷。了解《查理周刊》身世的人都知道,它的誕生緣于其前生《切腹周刊》遭到了查禁。改頭換面,重出江湖之后,苦苦撐到1981年,由于銷量過少,也沒有廣告收入,經費嚴重不足,再次被迫停刊。而1992年復刊后至今的20多年間,又接連遭遇到50多起官司,平均每半年1起②? Charlie Hebdo ?, 22 ans de procès en tous genres,Le Monde.fr – jeu. 8 janv. 2015。
在所有官司中,《查理周刊》與伊斯蘭教的積怨最深。一切緣起于2006年。當年,由于轉載丹麥《日德蘭郵報》 (Jyllands-Posten)關于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查理周刊》就遭到過穆斯林世界的強烈抗議。2007年3月,巴黎大清真寺和法國伊斯蘭組織以違反法國仇恨言論法為由將《查理周刊》告上法庭。盡管法庭最終裁決該刊無罪,但自那以后,周刊常會受到來自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威脅。而作為回應,該刊則開始登載更多關于穆斯林世界、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諷刺漫畫。此后,《查理周刊》經歷過網站被黑客入侵、編輯部遭到燃燒彈襲擊等惡性事件,為此,巴黎警方將周刊編輯部列為重點保護目標,并罕見地派專人值守(2011年起)。不幸的是,即便如此警衛,執勤的警察也未能保住《查理周刊》的安全,甚至自己也在恐怖襲擊中喪生。
然而,這一歷史性的悲劇,似乎闡述著一個悖論——伊斯蘭極端分子在摧毀雜志社同時,似乎又“拯救”了這家雜志。1981年的《查理周刊》因經費不足停刊,1992年復刊后,由于它執意秉承獨立的辦刊理念,拒絕廣告③“我們沒有廣告,沒有靠山,查理只有玩家和用戶。感謝你們在報攤購買查理。新聞自由,除了你,我們還能指望誰?”《查理周刊》網站首頁顯眼位置的這句話,無疑是其辦刊理念的一種折射。,致使其全部收入只能來源于銷售。可悲的是,由于該雜志的“重口味”,它的讀者注定為小眾,雜志印刷量多為5-6萬份,但往往只能售出一半,因此,在經營上陷入難以為繼的困境。2014年11月,周刊向社會公開求助捐款,希望以眾籌方式尋求100萬歐元以維持運轉,但最終只獲得2.6萬歐元,似乎瀕臨破產。而當慘案后的特刊《幸存者專刊》于1月14日如期上市時,當期的雜志印數達到了創紀錄的700萬。當然,這個印數是暫時的,一個多月后的2月25日,《查理周刊》推出恢復正常發行后的第一期,發行量降至250萬,銷售情況已經遠不如《幸存者專刊》時那么火爆。
從某種意義來說,一個雜志的死亡,大概不是它失去了多少優秀的漫畫家、記者、編輯,而是失去讀者和市場。由于《查理周刊》的表達方式追求極端化,致使它的受眾也逐步僅限于極端人群。受眾面的不斷縮小,固然可以使刊物日趨“特色化”,但更令它面臨困境。
2.3.《查理周刊》的獨特身份
《查理周刊》并不是社會主流媒體,這個讀者為小眾的雜志,運用反教權、反軍權、反政權的理念,并用極端的闡釋方式來解構一切神圣、一切標準和一切價值體系。它不設任何禁區地恣意妄為,似乎陷入“為否定而否定,為諷刺而諷刺”的虛無主義之中。 法國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的客座教授馬克·李·亨特(Mark Lee Hunter)寫道:“《查理周刊》從來不是事實的反映,但它很好地運用了事實(……)它出售的是一種態度,(……)但一直缺少的是解決方式。”①Mark Lee Hunter,Remembering Charlie Hebdo in the 90s,8 January 2015,https://www.opendemocracy.net。
《查理周刊》追求的根本目的不是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而是凸顯“表態的自由”,即按自己的方式作出任意表態的自由。 當人們紛紛站出來,喊著“我是查理”的口號時,所聲援的其實并非它長期以來所表達的極端內容,以及極端的表達方式,而是它“捍衛言論自由”的立場與勇氣。
在當今法國,媒體其實并不具備足夠的獨立性,它們必須迎合各種權力,以此來適應新聞管制,或者獲取大額合同,達到經濟上的目的。針對這一現象,英國《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西蒙·庫柏曾以《法國媒體與權力“同床共枕”》②西蒙·庫柏,《法國媒體與權利“同床共枕”》,見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012年3月26日文章為題撰文列舉了一系列事實,證明法國媒體和權力水乳交融的關系。比如:部長和資深記者的同窗關系;部長與電視新聞女主播的婚姻關系等等,用“利益共同體”來形容法國權力和媒體的關系似乎并不為過。
由此看來,《查理周刊》所持有的質疑和批判精神,便顯得尤為可貴。它帶著棱角、帶著挑剔、帶著狡黠、帶著殘酷的激進方式,直面法國政治、宗教以及一切社會現象,其具有的挑戰性和勇氣,在略顯溫順的眾多法國媒體中,可謂非同凡響。
3.《查理周刊》帶來的反思
《查理周刊》因對伊斯蘭先知的謔虐而招來殺身之禍。此次慘案在發生之時就沒有任何疑團,襲擊者以“為真主復仇”的名義開槍殺死了他們心目中的仇人,不像有些恐怖事件,通常發生后幾小時或幾天,才有人或組織出來宣布對事件負責。事件中雙方的恩怨由來已久,一方堅持有權挑釁、有權過份、有權不負責任的言論自由,另一方深信宗教信仰神圣不可侵犯,而這一次是“真主至大”與“言論自由”面對面的拼殺。
《查理周刊》遭遇恐怖襲擊事件,開啟了關于言論自由與宗教信仰的激烈討論。在第一時間,多數人選擇站在言論自由一邊,喊出“我是查理”的口號,聲援《查理周刊》所象征的新聞自由原則;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查理血案后的《幸存者特刊》出版后,這場反思進入第二個富有爭議的回合,“我不是查理”的聲音漸漸多了起來。如何解讀以上兩個看似相互矛盾的口號,需要我們將它們置于法國當前政治生態的背景之下認真解讀。
3.1.“我是查理”
《查理周刊》的悲劇發生后,社會輿論基本一邊倒,從國民到媒體到多國元首,都用自己的聲音喊出 “我是查理“的呼聲。據《巴黎人報》民調①Sondage Odaxa, réalisé le 13 janvier, auprès d’un échantillon de 1005 personnes interrogées par internet représentatif de la population fran?aise agée de 18 et plus. Méthode de quota.顯示,巴黎共和大游行之后,87%的受訪者對身為法國人而驕傲,73%的受訪者對主要政治黨派的反應感到滿意。
“我是查理”,一樣的口號卻蘊含著豐富而多層面、多角度的觀點。有些人借此表達對恐怖主義的堅決譴責,他們信奉無論什么原因,血腥屠殺無疑都是可鄙和野蠻的;有的則表達捍衛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立場和決心,他們認同不受限制的自由構成西方新聞自由觀的基本內涵,而《查理周刊》用粗俗的語言、裸露的圖片來譏諷穆罕默德,也與他們信奉的“新聞自由”相吻合;還有一部分人,通過口號傳遞對伊斯蘭文明的仇視,試圖用“查理”暗指歐洲歷史上的另一位“查理”②Florent Deligia,Quelle est l’origine du nom Charlie Hebdo ?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0108/---查理·馬特爾(Charles Martel),其人為歐洲中世紀的名將,其著名之戰為公元732年的圖爾戰役,他成功地阻擋了信奉伊斯蘭教的倭馬亞王朝侵襲法蘭克王國的軍隊。此戰制止了穆斯林勢力對歐洲的入侵,因此許多歷史學家認為,查理·馬特爾以此拯救了歐洲基督教文明。顯然,歷史上這位查理的名字,寄寓著這部分人意欲抵制穆斯林勢力、拯救基督教文明的愿望。
盡管 “我是查理”這一口號能夠表達譴責、哀悼、示威乃至聲援等內涵,但因為大多受制于情感和情緒因素,且多屬于對事件的初始反應,因而局限性顯而易見。
3.2.“我不是查理”
相比之下,“我不是查理” 的口號則是漸漸冷靜后思考的產物,更多地上升到思想層面,因而包含更多的理性色彩。《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1月8日刊發文章直言:“我不是查理”。這位較早喊出這一口號的人認為,查理事件之后的公眾反應表明,很多人可以將《查理周刊》冒犯穆斯林的諷刺神圣化,但對于那些冒犯“自己人”的內容卻沒那么寬容,因此他并不認同《查理周刊》所擅長的用幽默的方式刻意冒犯他人的做法。
的確,在《查理周刊》的歷史上存在那種“自己人”碰不得的例子。《查理周刊》的前身《切腹周刊》被查禁的原因,不正是冒犯了戴高樂嗎?后來,著名的西內(Siné)解雇案,不也嚴重抹黑了《查理周刊》以捍衛新聞自由之斗士稱名于世的形象嗎?西內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就擔任《查理周刊》的漫畫家,名氣很大。2008年7月,他在專欄中諷刺了時任總統薩科齊的兒子讓·薩科齊,結果遭到當時雜志社總編菲利普·瓦爾(Philippe Val)的解雇,理由是他的反猶言論①相關文字的譯文:“讓·薩科齊,他爹的好兒子,已經是人民運動聯盟的省議員了,交通肇事逃逸,可陪審團竟然免于起訴,走出法庭時,人們還恨不得給他鼓掌!還有:他剛剛宣布,他要先皈依猶太教,然后再和他的猶太人未婚妻、達爾迪(DARTY)家族繼承人成婚。這小子,真會為自己鋪路啊!”(2008 年7月2日的《查理周刊》)。其后西內將《查理周刊》告上法庭,法庭判西內無“反猶”違法,相反,《查理周刊》侵害了新聞自由原則。此案啟示人們,《查理周刊》的“言論自由”其實具有選擇性:用于挑釁伊斯蘭可以,諷刺“自己人”不一定行。
在《查理周刊》受襲后的《幸存者專刊》出版當口,其主題依然對準伊斯蘭宗教,封面上刊發穆罕默德流著淚,手持“我是查理”牌子的漫畫。由于題材比較敏感,致使世界各國媒體對于是否轉載這幅具有挑釁性的封面態度不一。各國媒體態度明顯分化,有轉載和拒絕轉載者,也有打馬賽克轉載者,更有拒絕轉載并嚴重抗議者。法國本國讀者也不再眾口一詞地擁護《查理周刊》。據法國《星期日報》1月18日民調顯示,認為《查理周刊》不應刊登該漫畫者達42%,支持刊登者為57%。另有50%的受訪者表示支持“限制網絡與社交媒體的言論自由”。這一調查結果說明,歷經時間的積淀與反思,已有半數的法國人開始意識到,自由并非毫無邊界。
在自稱“我不是查理”的人群中,有兩種情況值得注意:
一,支持《查理周刊》新聞自由的原則,但反對它激進、敵意、卑劣的幽默方式。
西方的“新聞自由”,是其政治體制和社會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是西方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也是全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作為原則,作為觀念,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但在現實具體的社會環境中,不同族群之間存在明顯的壁壘和落差,這些壁壘和落差,根據馬克思的思想,主要產生于階級和意識形態的不同,而按照亨廷頓的說法,則更多緣于不同文化傳統間的差異,因此,任何一種價值觀的絕對擴張和勝利都不可能實現,它必須保持與其它價值體系的互動。具體到《查理周刊》所捍衛的言論自由,在實踐中被“唯我獨尊”,被自命為惟一的普世價值,沒有對其它價值體系,如伊斯蘭教,給與足夠的尊重,逐漸淪為嘲弄的自由、冒犯的自由、挑釁的自由,甚至是色情、猥褻和暴力的自由。
這樣任性的、排他性的言論自由顯然已經偏離了人們所追求的原初的言論自由的理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不是查理”表面上是對粗俗不雅、惡意冒犯的漫畫手法的不認可,實質代表了對言論自由原則的不同理解。
二,“我不是查理”,是因為“查理”跟“伊斯蘭極端分子”有著太多的共性:
首先,兩者皆強迫對方認同和接受自身的文化理念。伊斯蘭極端分子從神學意識中尋找安慰,通過殺戮、暴力、精神控制等手段,將他們的世界觀強加給別人,而查理們則打著言論自由的旗號,以褻瀆、侮辱、顛覆破壞等方式攻擊別人的精神信仰,同時還要求天下所有人具備歐式幽默感和自嘲精神;其次,兩者均不畏死亡,一方愿意為了自己的神殺人而且不惜自身的滅亡,另一方也誓死捍衛自己言論自由的權利,“我不害怕報復。我無妻無子,沒車,沒貸款。這也許聽起來有點自大,但我寧愿站著死,也不跪著生。”②Le monde:? Je préfère vivre debout que mourir à genoux ?,septembre 2012.面對如影隨形的死亡陰影,多次受到死亡威脅、甚至被列入基地組織通緝名單的周刊主編漫畫家夏爾伯曾向法國《世界報》這樣表示。推到極致而言,《查理周刊》與伊斯蘭極端分子之間進行的是一場將生死置之度外的戰斗,一方通過武器發言,另一方則把言論當作武器,以牙還牙、以血還血、以暴易暴。“我不是查理”意味著拒絕暴力,反對極端,包括過度的、以自由為名的語言暴力,當然,但絕不包含對恐怖分子的原諒和姑息。如果說“我是查理”是讓人團結在“言論自由”旗幟下的號令,那么,“我不是查理”其實并不是它的反腔,后者強調的是對言論自由這一原則的不同維度的微妙理解,探討的是新聞自由的背后的倫理共識。
3.3.《查理周刊》何去何從
當今的法國,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成為一個不是移民國家的移民國家,其中,穆斯林占法國總人口的10%左右。但是,很多穆斯林進入法國生活后,卻又無法真正融入法國社會,因此,雖然法國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但是多元社會卻一直沒有實現。作為最晚進入法國的宗教,伊斯蘭教沒有像其它宗教那樣,共同經歷漫長的世俗化過程,其直接后果就是它與法國的世俗價值觀之間(其中包括言論自由、自嘲精神等等)形成激烈的摩擦、碰撞和沖突。這一現狀既讓穆斯林倍感“被邊緣化”,又讓法國傳統主流社會感到“被伊斯蘭化”,甚至在部分社會人群中, 出現“伊斯蘭恐懼癥”。
法國著名作家烏勒貝克在2015年初出版的小說《屈從》就展望了這一擔憂。作者講述了2020年法國通過選舉產生出一名穆斯林總統,從而法國全面進入伊斯蘭化的故事。雖然所有描述只是一種文學想象,但是,這已足以用藝術的方式讓法國人看到了一種極端的國家未來。
《查理周刊》正是在這一政治背景下拿起捍衛言論自由的武器,并一再挑戰穆斯林的敏感神經。但此舉不僅無法化解或調和法國社會內部的價值沖突,反而火上澆油地激化矛盾。今天的巴黎悲劇恰恰驗證了,《查理周刊》的作法,非但沒有令這種文明沖突降溫,相反使之更加激烈。
在《查理周刊》事件后的反恐大游行中,游行的行進路線是從共和國廣場到民族廣場。不知是巧合還是刻意,專門設計的游行線路似乎正好映射著法國的歷史和未來。作為起始點的“共和國廣場”,素以倡導“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和精神而稱名于世,同時也象征著法國傳統主流價值。當龐大的游行隊伍從該廣場出發時,此舉別有深意地隱喻著從傳統邁向未來的起步;而作為游行路線終點的“民族廣場”中“民族(nation)”一詞,仿佛提醒每一位參與者,法國已經從一個單一民族國家變為多民族國家,民族的團結、民族的融合是法國當下最主要的社會問題,“民族廣場”既是此次游行的終點,更代表法國最終形成多元的、和諧的、新的法蘭西民族的終極目標:不同族群、不同種族在法蘭西大旗下求同存異、和平共處,再一次向世人證明法蘭西文明一再宣稱的開放、博大的胸襟。允許并包容本土文明和外來文明、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在法蘭西大地上的相容共生,并行不悖,業已成為這個國家、乃至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所面臨的重要課題。在這一背景觀照下,法國現行的傳統政治諷刺以及新聞自由觀,當如何與時俱進地適應法國民族融合的進程,具體到《查理周刊》的何去何從,勢必不可避免地成為擺在世人面前的一道必選題。
綜上所述,《查理周刊》的前景依然嚴峻,它絕對無法變更現有風格,形勢已將它推到“沒有退路”的困難境地。首先,遍布全球的東西方文明沖突不僅沒有緩解跡象,反而大有不斷激化的趨勢,部分熱點地區的武裝沖突正在給世界人民的和平與安寧帶來巨大威脅;此外,法蘭西本土日益蔓延的民族文化矛盾、因“查理事件”帶來的全社會的強大逆反心理,把《查理周刊》推上民族文明沖突的風口浪尖;加之《查理周刊》自身的經營日益風雨飄搖,困窘的經濟狀況導致其難以為繼,而意外的“查理事件”無疑為其注入一劑強心針,這家名聲原本有限的刊物,一躍而為稱名全球的著名期刊,其帶來的不僅是名聲,更是可觀的發行收益……
可以判斷,已經付出血的代價的《查理周刊》,將會在今后一段時期繼續捍衛和保持已有的“謔虐血統”,繼續以無情嘲諷和有力攻訐作為刊物特色。因為它除此之路,別無他途。只是人們對它的前景存有擔憂——戲謔之路還能走多遠?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外語學院
(責任編輯:羅國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