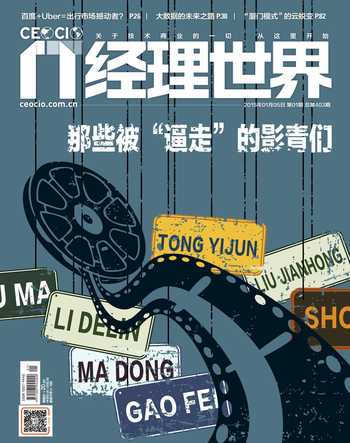2014,張瑞敏和任正非的大變局
胡泳 郝亞洲
如若評選2014年中國商界頭等大事,阿里巴巴在紐交所上市無疑會成為首選。這家代表了中國互聯網的公司,以全球第二大網絡股的姿態登臨紐交所,相比之前騰訊在港交所的上市,阿里巴巴的勝利似乎多了些“中國夢”的味道。就像馬云沒有參加敲鐘的環節,而是邀請了阿里的8名客戶,這個更高級的“中國合伙人”版本向外界不遺余力地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阿里強調用戶至上,用戶才是這家公司最重要的“合伙人”。
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細節,因為“用戶”幾乎正在成為中國企業的“奉天承運”。2014年,如若我們盤點影響中國商界的流行概念,“互聯網思維”,“社群經濟”這兩個名詞無疑也會榜上有名。除去其過度包裝的成分,兩個詞的核心意思都是一致的:如何讓用戶加入到你的決策行列中。
“用戶”在整個2014年都讓中國商界心向往之。然而,就在互聯網公司們為如何劃分“用戶割據勢力”而激戰時,傳統企業卻面臨一個相對低級的問題:如何找到用戶?如何留住用戶?如何響應用戶?
我們在今年的專欄中,用了不少篇幅強調傳統組織結構和流程在互聯網時代遇到的問題,究其根本,這些問題都是源于無法解決和用戶的距離。而要想解決用戶的問題,就需要將員工不斷往一線推,不斷將決策權釋放到市場中。所以,組織變革的核心便是,如何激勵員工,進而也就導向薪酬分配體系的調整。
2014年年初,我們看到了張瑞敏被外界認為是激進的講話,海爾要向互聯網企業轉型,海爾的員工有了新的身份——“創客”。人們還未來得及參透其用意,便發現郁亮、任正非也頻頻向外界傳達變革意圖:這一次不再是局部調整,而是整體轉型。郁亮喊出的“合伙人”模式讓相當一部分保守派學者認為不靠譜,誰能想象沒有職業經理人的組織會是什么樣?任正非則在一次內部人力資源會議上提出了“獲取分享制”。人力資源專家康至軍認為這是員工持股的升級,因為持股會增長惰性,“獲取分享”則直接將員工的個人收益和組織收益掛鉤。
事實上,創客制也好,合伙人制也好,獲取分享也好,都堪比當年的“家庭聯產承包”模式: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分享個人的。
三家各自行業里的領軍企業,三個體量無比龐大的傳統企業,在2014年集體轉身,表面看似CEO們動動嘴皮子、翻翻PPT般的輕松,實則步步驚心。產業巨變、盈利艱難只是表象,深層次的是人與人的關系模式發生了根本變化。尤其是,小米的飛速成長,將“用戶”這個詞作為重磅概念托出水面,傳統的組織和消費者發生關系的界面產生了位移。
以往,消費者只有在“消費場”通過產品才能和企業發生關系,而從“消費者”向“用戶”的轉變,意味著人們一直處于“使用”狀態中,“消費場”充其量只能成為一個完整體驗鏈中的一節。所以,企業如何搭建一個讓人始終在“用”的界面,就變得至關重要。
“界面”需要在兩個層面進行搭建:組織結構和薪酬激勵,這是內動力;傳播產品化,企業媒體化,這是外因。
張瑞敏和任正非雖然在組織變革力度上略有不同,但都認識到了一點:讓聰明的人、勤奮的人獲益。張瑞敏選擇的是徹底平臺化,任正非選擇的是金字塔蜂窩,即拉開金字塔的頂端,形成蜂窩狀,異化金字塔的內部結構。任正非還強調了KPI考核中的戰略貢獻,“戰略KPI和銷售收入KPI不能一致。將來公司所有指標都要關注到搶糧食,關注到戰略指標。”張瑞敏在海爾中采用的是二維點陣模式,張瑞敏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提升創新容錯率,本質上也是將組織戰略完成度納入到考核體系中。
而在傳播產品化、企業媒體化的層面,華為在手機業務上大放異彩。有觀察家說,華為完全走的是小米路線——粉絲搭臺、饑餓營銷開路。問題是,學習小米的公司有很多,華為為何成功了?任正非明明表示過不要事事互聯網,為何華為觸網之后表現會如此優異?這恐怕不是一個“學得好”就能解釋的。
海爾的動作更加直接,干脆做出漂亮的企業自媒體。海爾的文化中心在這次變革中充當了“急先鋒”的角色,一改以往上傳下達的指令控制職能,變身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媒體部門。在新媒體運營中,故事化的講述方式賦予了“海爾”新的人格,而這些都超越了時下流行的“發稿即公關”的模式,用企業文化中心負責人的話來說,現在是一個“行為即公關”的時代。
2014年,對于中國的互聯網企業來說,概念在繼續炮制,尋求上市的步伐依然緊促,場面看上去依然繁榮。而對于曾經代表中國走上國際舞臺的傳統行業公司而言,他們的呼吸更加急促,因為要拖著巨大的身軀趕上時代的步伐。目前來看,似乎只有一條不算捷徑的捷徑: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小,身體越來越輕盈。歸根結底,若要完成這個任務,非具有大變局能力者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