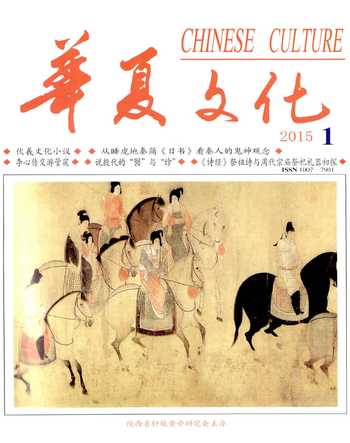南宋宰相黃潛善政治地位再評價
黃澤凡
黃潛善(? -1130年),字茂和,邵武(今福建邵武)人,北宋元符三年(1100)進士及第,南宋初期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建炎年間,黃潛善擔任宰執一年有余,任職期間“獨當國柄,專權自態而卒不能有所經畫”,為時人所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十八,以下簡稱《要錄》)后揚州潰敗,高宗“決意渡江”,黃潛善罷相,被后世史家列入《宋史·奸臣傳》。較之南宋初期其他宰執,目前學界對黃潛善少有專文論述。然而,建炎初期,趙宋政權初立,一直任職地方的黃潛善僅憑弄權之術,怎能任相一年有余?況且任相伊始,高宗堅信“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同事不濟?更同心以副朕之意”(《要錄》卷一) 本文擬以建炎年間的兩起歷史公案為巾心,重新解讀黃潛善任相期間的政治地位。不當之處,尚祈方家賜教。
一、黃潛善與李綱罷相
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宋高宗即位,起用力主抗金、聲望甚隆的李綱為相,以振軍心。同時,任命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為知樞密院事,二人掌握朝政實權,牽制李綱。不久,在對金和戰、軍力配置、任用官員、籌措財政等方面,李綱與黃潛善等人發生嚴重分歧。七月初.為應對金軍南犯的局勢,南宋朝廷內部展開了關于中央政權臨時駐蹕地選擇的討論。十七日,李綱認為南陽交通便利,物產豐富,為“天設以待臨幸之地”。高宗“雖用李綱議營南陽,而朝臣多以為不可”(《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一,以下簡稱《綱目》),黃潛善“力請幸東南”。最終,高宗改變主意,決定巡幸東南。此后,李綱“所進機務,多未降出”(《續資治通鑒》卷九九)。不久,曾受黃潛善舉薦的侍御史張浚上書彈劾李綱,指其“私意殺侍從,且論其招軍賣馬之罪”(《宋史》卷三五八)。八月二十匕日,李綱罷官。
李綱執政,固然引起“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要錄》卷五)的黃潛善的不滿。然而,李綱任職時期的諸多措施亦值得深究。如,在偽楚朝臣的處置問題上,李綱堅持嚴格處置,與黃潛善等人“廷辯”,后岡黃潛善等不及“李綱氣直”,宋高宗按李剛的建議處置此事。張邦昌被遠貶潭州,“嘗事偽廷”的范宗尹等也遭到嚴厲處罰。此舉固然很重要,但對根基不穩,頻受外敵侵擾的趙宋王朝而言,似乎并不是最迫切的政治任務。時任宰執的黃潛善,引薦朝中務實型大臣,為重振南宋中央政權集聚人才。比如,他推薦元帥府舊臣張愨出任同知樞密院事,此人熟悉財政事務,廣開財源,“文移所至,破奸若神”,頗受高宗重視,他成為黃潛善的重要支持者。
在處理同盟者之間的關系問題時,李綱、黃潛善大相徑庭。當時,李綱在內執政,但與在外征戰的宗澤分歧頗多,不愿對宗澤妥協。在對金戰略上,宗澤主張攻,而李綱傾向于以守為主;在駐蹕地選擇上,宗澤請幸開封,李綱請營南陽,李、宗各持己見,互不相讓。兩人始終沒有形成內外相互照應的政治局勢。(胡文寧:《主戰派宗澤和李綱政見分歧及其影響》,《史學月刊》2013年第1期)以致李綱罷相后,宗澤并沒有激烈反塒 主和派同盟內部則相對牢同,誠如史籍經常以汪、黃并稱所揭示的:汪伯彥和黃潛善,其表現如同一人,且二人所持意見一般出自黃潛善,汪伯彥加以附和,基本保持一致,即使后來二人政治地位對調,亦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張浚好友宋齊愈被處死是李綱被彈劾的重要原因,也是李綱被罷的直接原因。李綱在執政后提出的施政方針,有的嚴重觸犯了趙宋祖宗家法。比如建藩鎮、用土豪守衛地方的主張,企圖分散權力到地方,嚴重刺激朝廷上下的神經,成為其最終失去高宗信任的深層次原因。后世史家僅因張浚由黃潛善舉薦,便認定是黃潛善用權謀借張浚之力攻擊李綱,頗有失當。
二、黃潛善與陳東、歐陽澈案
李綱罷相之后,黃潛善便出任右仆射兼中書侍郎,成為宋高宗朝第二任宰相。任相伊始,黃潛善不得不面對由自己任相引發的政治風波,即其政治生涯中為人詬病的陳東、歐陽澈案。建炎元年八月十四口,太學生陳東應詔人京,議論時政,恰逢李綱罷相。于是,他分別以是月十七、十九、二十五日連上三書,直言“宰執黃潛善、汪們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二帝”。(《要錄》卷八)幾乎同時,布衣歐陽澈徒步到達南京,伏闕上書,力言李綱不能罷相,黃潛善、汪伯彥、張浚等主和派不可重用,并清御駕親征,以迎二帝等。陳東、歐陽澈的上書“詆時事,語侵宮掖”(《宋史·奸臣三》).黃潛善以二人言語會導致群眾騷動,請求將二人誅殺 宋高宗應允,并將此事交給其負責。二十五日,開封府尹以議事為名召陳東。隨后,陳東、歐陽澈同遭殺害。
陳東、歐陽澈二人上書議政由來已久,積極性頗高一然就上書中提及的諸多方針政策,如反對李綱罷相迎同二帝等主張,實在難以獲得高宗支持。在地方財政上,李綱提出:“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三)。如此以地方財政養藩鎮,是南宋中央不能接受的。除拜黃潛善,足高宗對豐扭轉政局的一種嘗試。至于陳、歐陽二人提出的御駕親征、迎還二帝,純屬妄談,后來宋金戰爭證叫了這個事實。陳東、歐陽澈一案牽涉頗多,時人以此為黃潛善“怙寵擅權,蔽賢嫉能”的重要證據。陳東、歐陽澈上書之時,黃潛善任相小久,趙宋政權更是國事維艱。黃潛善所說的群眾騷動此前已有發生,早在靖康元年正月初,軍軍圍汴京,徽宗在蔡京、童貫等人的陪伴下出逃。二月初一,京畿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擅自偷襲金營失敗,李綱罷相。二月初五,陳東率太學乍數百人伏闕宣德門,為李綱請命。當時,汴京軍民十余萬人不約而期,打破登聞鼓,殺宦官數人。 欽宗.不得不恢復李綱職務。當時趙宋中央王朝風雨飄搖,陳東以書生之力,企圖聯合群眾并脅迫朝廷任命官員,這不能不令朝廷震驚和擔憂。
陳、歐陽二人的上書是群眾對南宋政權術米走勢的一種理想假設,雖在氣節方面有值得稱道之處,但其中書生紙上談兵、意氣用事的元素似乎更多,其主張對于亟需實務的南宋政權作川有限。黃潛善認為由此引起群眾騷動的判斷也仃例可引。他決定處死二人,并非僅僅是保全棚位
三、黃潛善任相期間的政治地位
南宋政權建立初期,宋高宗的核心統治地位雖已確立,但整體局勢動蕩不定。一方面,宋廷南渡,民意希望迎回徽、欽二帝,而此時以康王身份登基的宋高宗帝位并不穩固。另一方面,金軍南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的宋高宗“冬不得其溫,夏不得其清,昏無所于定,晨無所于省”(《要錄》卷五二)。他急需贏得朝野上下輿論的支持和認可以穩同皇權,任命一位能統領局勢的宰相成為當務之急。此時,抗金名將李綱聲望甚隆,高宗即任命李綱為相。然而李綱確立的政治綱領與施政計劃讓高宗頗為不滿,最終被罷相。
南宋初年,無論哪一位宰相在位期間都固執獨斷,專權自恣。如李綱執政期間力主營都南陽,盡管朝臣多以為不可,他卻一意孤行。后來黃潛善當國,“專務壅蔽,自汪伯彥而下,皆奴事之,不敢少忤其意”(《要錄》卷五),亦不為怪:身處動蕩時代的宋高宗生性多疑,誠如王夫之所言:“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鑒陳橋之已事,懲五代之前車,有功者必抑,有權者必奪。即至高宗微弱已極,猶畏其臣之強盛,橫加鋟削.”《宋論》卷十)李綱罷相,是宋高宗維護皇權、捍衛中央地位的一次努力。而隨后黃潛善任相,則是高宗執政方針的重大調整。
靖康年間,因為陳東領導的太學生運動,李綱得以繼任,宋高宗對此心有余悸。陳東、歐陽澈二人的激烈言辭,不僅可能引發威脅政局穩定的群體事件,更是干預朝政,嚴重威脅皇權,這是宋高宗不能接受的,黃潛善請求誅殺二人與高宗不謀而合。因此,黃潛善在陳東、歐陽澈的被誅殺的過程中,只是一個執行者。其實,以親王身份即位的宋高宗,面對強敵內亂,再考慮到他在此前并沒有接受過系統的帝王教育,處理這一公案,沒有完全遵守祖宗之法,不足為奇。建炎四年,朝廷“追贈歐陽澈、陳東為承事郎,以歐陽澈一子為官,下令州縣撫諭其家人”(《宋史·忠義傳》),也不過是宋高宗籠絡士人的手段。紹興四年,中書舍人居正指責黃潛善: “操鄙夫患失之心,遽昧臣無作威之戒,使人主蒙拒諫之惡,朝廷有殺士之名”。(《要錄》卷八二)把誅殺陳、歐陽二人的罪責推給黃潛善,這正中高宗下懷,使其達到限制相權、鞏固皇權的目的。
建炎初期,宋高宗頻頻換相。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當時國內外局勢復雜,宰執們舉措失當、無力應對;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當時皇權與相權的關系,即宋高宗對任命宰相有很大的自主權 宋高宗可以根據實際政治的需要,選擇不同的宰執,以達到穩定政局的目的。此時,南宋中央權力也是很弱的,皇權與相權相互依存,沒有某一方面占絕對的主導地位,只有二者合力才能重建南宋政權。黃潛善任相僅一年有余,勢力有限,與紹興年間秦檜獨相,不可同日而語。
此外,宋室南渡,朝廷內部存留了北宋統治后期的諸多問題。士大夫們黨爭激烈,任何一派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遭到攻擊排斥、逐出朝廷,因此維護集團內部政治利益成為執政者們施政的出發點。故而宰執打擊異己毫不手軟,力求全而盡地將政敵掃地出門。而其他朝臣明哲保身,多不作為,建炎年間參知政事王絢便是“鉗口尸祿,不敢吐一言”《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十四)。紹興六年,趙鼎.張浚共同當政,期間大力引用元祐子弟,監察御史劉長源質疑: “或謂應系元符以前人臣之子孫皆可用,臣恐其失近于官人以世,而其人未必皆賢。” “勿拘于家世,則開天下之公道。”趙鼎、張浚聞后大怒,責罵劉長源“不學無識”,將其罷職(《要錄》卷-O四)。紹興名臣為保住政治地位,不惜用盡手段排除異己。建炎初期,黃潛善為保證自己的政治主張得以順利實施,采取一些政治手段排除異己,應當可以理解。
綜上所述,黃潛善的政治生涯相對短促,但他在執政前后審時度勢,為重建、穩定南宋政權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時人因后來揚州潰敗、中央政權幾近覆滅,推定其“無遠識見,無公議論,偏頗回通,惟富貴是念”(《宗澤集》卷一),似乎在理。然南宋的政局復雜、軍事軟弱等歷史現狀,也是歷代中原王朝所罕見,黃潛善不應對此負全責。史書中對黃潛善幾大政治過失的記載,在經過仔細分析后,筆者頗不以為然。黃潛善在宋高宗的支持下擔任宰執,主要負責執行高宗的決策。后世史家為回護宋高宗,將歷史過錯推給黃潛善,實在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