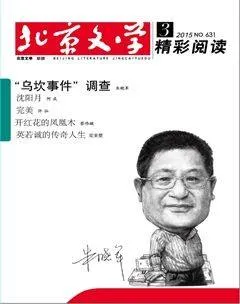墳上丁香花
1.陷在影像記憶里
我至今忘不了她——我的曾外婆。她的百歲的人生歷程,應該擁有許多的故事,可我并不全部了解她的歷史。
當我想起她的時候,隨之想起的也是和我有關的一個又一個往事。恰恰就是這些細節,維系著豐富而又高尚的一種魅力,讓我在想她時,將略帶感傷的懷念和悠遠意味的思念躍然紙上。也許,這也是我作為第四代人一定要展現的鮮明情緒。
“想我的時候,就把你媽媽當成我。”她這話曾讓我無法理解。我困惑,難以判斷她說這話的初衷。但分明又理解她對我失去她以后的日子的擔憂。她這話,仿若將壓在箱底的東西翻騰到箱子外面,讓人在異樣的氣息中沉醉于一種想象。
她就是她,誰也代替不了她。當她那裹著的一雙小腳一步一步走在路上時,我跟在她身后,體驗著逆時代存在卻又無以言表的柔美與自信。
她會在做著手中的活時,講一些她近乎透明的遐思,那些話語對于幼年的我而言,魅力四射,透析著神話般的美麗色彩,構建著傳統以外的自我意識。
“你就是你,不是別人。”
“你在這個家里長大,這里就是你全部的家。”
“想得越多,翅膀就會越沉,還飛得起來嗎?”
“大人說的話也不一定全對,他們不對的地方你也能指正。”
“新式樣的日子我過上了,舊式樣的日子卻在心里過不去。”
……
沒有層層疊疊的掩飾,那話就這么一點一點說開來。
敬重曾外婆的人,更多的是敬重她有思想。雖然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個性”的元素尚不鮮明,但曾外婆留給人的印象居然是濃重的卻又最放松的一種狀態。那種超越自我的生活本身的東西,其實一直在追趕。
夜晚睡覺前,我們洗腳。我愿意用手撩起盆中的水沖洗她因常年裹著而被壓平了的腳趾。問她,疼嗎?也不知問過多少遍,她也不知道回答過我多少遍。但因為知道是腳在走路,所以格外關注她的痛。我總以為她的神經末梢會感覺到痛,那雙變異了形狀的腳就像失敗了的一件作品,會讓她傷感一生。然而,她在我成長的日子里,用她的言行告訴我的,遠不是這樣的結論。
裹腳,竟然于她有溫馨的少女記憶,是牢牢嵌在她靈魂深處的一種與愛有關的記憶。都裹腳的時代,她認為愛她的家人視為“時尚”和愛護,裹腳似乎不是平庸的隨大流,更是家人對她未來生活的修整。望著自己扭曲的腳,她回答我問題時,總說,我不恨家里人。
每次去西單商場,看到擺放在老字號貨架上的那雙尖頭皮鞋,就想起我的曾外婆。這對于我來說,是個缺乏歸屬感的夢了。
每到春季,她都盼望我們從頭到腳都煥然一新。所以,她可是作準備,從身上的著裝到個人的精神面貌,再到家居環境,她都想辦法調節。
直到現在,我都會對家紡用品情有獨鐘,更多的也來自于她。一個新的靠墊,布藝的,明快的顏色,擺在椅子上,整個居室似乎有了勃勃生機。
那晚,我靠在沙發上,靜謐中,我想到了她老人家。如果,此時此刻,她還在,她會如何把脈現在的生活?她帶給我的如同萬花筒里的碎片一樣的美感,是她不經意間培養起來的,可她卻不一定知道。審美影響了她的個人風格。除了母親之外,她是我認識美的啟蒙老師。有審美意識,她的見解就獨特,品位也特別。這表現在她對于生活的自信態度上。
有一個時期,我琢磨一句話:創造自己的天空。
這個時候,我也會想到她。
她其實一直就是沿著這個目標走過來的。只是,她沒有顧及自己是否在做什么,但軌跡就是如此。
她說愛我,愛我們一家人。但我們似乎沒有說過愛她,至少語言上沒有表達出來過。但她感覺我們愛她。記得,她擦窗玻璃時靠在窗框上,認真地瞇眼看著天空,陽光照耀得她睜不開眼睛,而她說:這個家擁抱了我。
擁抱?這個家?她享受嗎?一天一天忙家務那么地累?
今天,我靜下心來發現了我以前不懂她的許多事。只有感覺到了的時候美才存在。對我而言,在她身邊長大的所有日子,讓我覺得生活可以如此豐盛。
她的魅力緣于她的自然、自信。我有時候不禁想,如果今天的我再和她生活在一起,我會利用這些寶貴的時間進行深度思考嗎?她繁忙的主旋律里會不會也衍生出更多的內容?
她養育我的成果歷史不能抹殺:我孩子一樣的心態伴隨我走到永遠。
2.不是叛逆,是因為太懷念
如果,我的曾外婆能活到今天,看到我坐在女人街的小吃攤前吃麻辣燙,她肯定臉上掛不住。“吃”的行為應該只在家里。
這是她遵循的作為女人的行事規則。我心里知道,但也想,她畢竟不知道今天的變化。我做一些事情的時候,總會想起她。行為規范在心里依然有條底線。盡管朋友們一起坐在露天的小攤位上說笑、吃小吃。但我知道,就這樣,我已經超出了她的要求。為此,我盡量避開這樣的聚會。其實,每次想來,還都是我提議上這樣的地方吃小吃的,因為我比較喜歡。有時候,常常讓朋友們很為難,因為他們未必就喜歡這樣的地方、這樣的小吃。所以,我是明知故犯。
逆反的心理并不說明我怎么樣了。但至少說明我自從失去了曾外婆就沒有了規律的生活章法。我不斷變更著生活習慣,不斷地讓自己嘗試一種又一種對我來說全新的生活方式。以前看人家做的所有事情,我都想自己體驗一遍,我甚至在獲得了或許并不快樂、并不享受的感覺后,還欣然讓自己有一副滿足的表情。就為給自己看。
以往,一個人去一個地方,會多少有些羞澀。但現在練就的臉皮厚實了許多。嚴格說,是和年齡有關和閱歷有關。但我知道,也和一種放不下的思念有關。我好像沉浸在一個氣場中,一切看不見,甚至想不到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做,完全不知道這樣做的時候是個什么樣子的自己。我想沖垮什么,也想升華什么,更想超越什么,但我沒有目的和目標,一味地折騰。
總想喊些什么,但無聲。所以,我像一匹沒有韁繩的馬,東跑西跑,胡亂找尋什么。又像失了音的歌者,流著淚聽別人蹩腳的歌唱。
許多的有關曾外婆的氣息在世間淡了,但她的影像揮之不去。
曾外婆走遠了。她似乎真的就不存在了。我看著天空,能看上一個小時或者更長時間,我極力地想把寫在天上的心里話組成她的臉。她應該是笑著看我的。我能跳出她以前的窗欞看她忙忙碌碌的身影,卻無論如何看不到屬于她的那一片云。
外婆,外婆……放大了幾萬倍的她依然在我的手心里微笑,她的身后,是15歲的我和11歲的弟弟。這樣的照片僅僅只有一張。我在今天復制了這僅有的一張,并且,在心里放大了。
從孩子開始,我大寫她的一切,她也大寫我的一切。
難受了,委屈了,她在,我會找她。她不在了,我讓自己成了她。傾訴變成了化解,我的心胸愿意為所有的不快打開。這是她教給我的吧?什么時候教的?我竟然就這樣長大了。她默默保佑著的是一個心地純正的女孩子,她走的時候我24歲。
曾外婆希望我成為什么樣的人,她說不清楚,但希望我好是無疑的。她的愛心傳遞給我無形的力量,讓我在長大過程中的每一天無意識地享受著。她的衣服因為常是黑白兩色,所以,她讓我看世界的眼光里黑白分明。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這成了我的性格。為此,亮麗了容貌,卻也吃了許多困惑。其他的色彩是我骨子里的,因為黑白的分量大也重,就少有機會浮出來。
3.她不是傳說里的“老絕戶”
在我們山東老家,沒有兒子的人家被稱為“老絕戶”。而在我的印象里,沒有兒子的母親才被人稱作“老絕戶”。這種印象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有其根據。當然,肯定是通過誰誰的事如實套來,以增加我這種“印象”的說服力。
我不用去遠處費勁兒地尋找這種“佐證”,現成的,只要靜下心來的時候,翻看我曾外婆的照片,就能翻出她——一個“老絕戶”的故事。
所以,我說,“老絕戶”一詞,是在我翻開我曾外婆照片的時候想起來的。
她一生就我外婆一個獨生女。
但沒有人認為她是老絕戶。因為她的女兒承擔了兒子一樣的擔子——走到哪里就把母親帶到哪里。從農村到城市,從城里到城外,曾外婆都樂觀地陪伴著外公外婆。直到外婆衍生出5個兒女,5個兒女又分別有了自己的家,曾外婆都伴隨左右。
只不過,這時已不是跟著外公外婆她們過日子了,而是來到了我們家。
因為我母親是她一手帶大的,母親結婚了,她自然又會陪伴左右。
而我,又是她一手帶大的,到我結婚的時候,她依然陪伴我左右。
1987年2月我的兒子出世了。而曾外婆,在他出生前兩個月仙逝。
原本擁有一個“老絕戶”的名,卻享受過了比有兒子還強的命。
在世俗的思維定勢里,“老絕戶”的凄美婉約的人生境遇,被曾外婆一輩子理直氣壯、毫不遮掩的亮麗追求詮釋出新的傳奇。
知情的人,從沒有一個人叫過她“老絕戶”,甚至她老家的人,都用“三奶奶”的敬語問候她。特別是,當她90高齡的時候,所有認識她的人,一律喊她“姥姥”。
大家都說曾外婆要強。她不承認,也不否認。但她眼里有一種渴望。這在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就感覺到的。她為我們在夏日的夜晚不停地搖著扇子,眼睛一會兒看著天上的月亮,一會兒看著安靜地躺在她身邊的我。直到今天我心里之所以會莫名地盛滿了美麗的愛,和她那種深深的、寧靜的注目分不開。我會懷念那一刻的默默芳香。
我是她最在乎的人。
從心靈深處我感到溫暖。
曾外婆的虔誠和熱情,都有一些感人的故事。她望著你時,傳遞出一種你信賴她、想走近她的氣息,出門在外不管多長時間,想回家看到的第一個人永遠是她。或許因為,我從小獲得的所有夸獎,大部分都是從她那里得到的。她的肯定很吝嗇,但我期待。一旦得到了,有一種動人心弦的、特別亢奮的穿透力。
和曾外婆接觸過的人很多。就在我家住的那個足有100多人家的家屬院里,老老少少都知道她,有的老人一提起曾外婆,都這樣說:
人家那老太太,干凈、利落。
姥姥啊,干凈。一身黑一身白,穿在她身上顯得那么是樣。
姥姥心眼好,人緣也好。
老人家有功啊,帶大了三代人啊。
這老太太是菩薩啊。
……
曾外婆讓原本普通簡單的生活有了靈動的內心的纏綿。她無論做什么,都放射著她自身的光芒。她不忽略親情中的小細節,也不忽略親人以外人的小感覺,她幸福的狀態其實就是最真實最淳樸最無私的一種大愛。
在我成年以后的一個清明節,有一個朋友面對著我擺放在影集里的曾外婆照片,說,她應該是你心靈的另一扇窗。
心里,又多了一扇敞亮的窗戶,也就多了一種色彩。何況,這豐富的色彩全用在了我一個人的身上。
“老絕戶”一詞,沒有讓曾外婆的人生走得曲折,相反,卻讓她經營出一種輝煌家族的希望。
在她曾經看似凄涼的“沒有兒子”的現實一瞬間,誰也不知道她想的是什么。但時光切換到今天,我敢說,我的曾外婆在無意識中用對外婆深情的愛,規劃出了所有未來的希望主題。
那個詞或許在別處存在,但在我們這個大家庭里,曾外婆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她讓她養育的三代人都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世間真情難求,世間親情可貴。
她用心愛過我們每一個人。
4.她的墳上開滿丁香花
每年的春季,乍暖還寒時節,總有人到剛剛返青的麥田里尋找故去親人的墳塋,象征性地祭奠時,擺一些水果點心之類的供品,奉上一堆不知道那邊能不能花的紙錢。然后,自以為心安理得了,再離開那些在寂靜中永遠沉睡了的親人朋友。
曾外婆去世后一周年前夕,在濟南工作的大舅澤君回來了。一家人商量著回東阿鄉下老家給曾外婆掃墓。當時,考慮怕去太多人給鄉親們增加麻煩,人家待人如火但經濟條件又力不從心,所以,就在我和澤君大舅的堅持下,由我們倆人代表全家前往東阿。
那年,我24歲,澤君大舅46歲。
那天,我們每人騎了一輛自行車,在寒風中上路。
因為知道我最親愛的曾外婆在前方等待我們去看她,所以,那一路60里地的跋涉絲毫沒有感覺到累。
我曾外婆走后,我感覺她的音容笑貌似乎蘊藏在所有健在的老人們的身上,我只要留意就能捕捉得到。有時,我會讓自己的臉貼在照片上的她的臉,努力重溫那種不能言傳的深情,我會拼命地讓自己無言地喊她、喚她,然后一腔熱血沸騰,沖到眼睛發燙,眼淚就滑進了嘴里。沒想到,思念的淚水也如此咸澀。
我一直有個愿望,給我曾外婆立個碑。但總是想,實現不了。因為,老家不時興這樣的形式,也不贊賞這樣的形式。我得尊重老家人的習俗,便把那碑立在了我的心里。
我和澤君大舅跟著曾外婆的遠房侄子來到村外的田野上,找到了曾外婆永遠安歇的地方。這時,陽光燦爛起來,在寒冷的冬天顯得又暖又亮。我們把帶來的供品擺放在墳前,跪了下來。曾外婆墳前的土壤極像她在世時揉好的面,光滑、潤澤、溫厚,我仿佛依偎在她的懷里。
周圍的地里,沒有一點生氣,寒冬把一切生機都掩蓋在這土地里。我卻想象著,這周圍的土地一年四季都長滿了花草,特別是在我曾外婆的墳上開滿了丁香花。奇怪的是,后來的夢里,我真的就夢到了這樣的場景。那花不止開在墳上,甚至開在了那一大片土地上,一片連成一片,連成了花海。而我知道,我的曾外婆在這花海里住著。
鄉村外的田野寂靜、空曠,似乎沒有一點生命的色彩。但在這厚實的土地下面隱藏著一種力量,一種讓人在春天或秋天一下子就能想到的力量,那力量有著躍躍跳動的激情,也有著擋不住的火熱。我說不清楚我的曾外婆現在好不好,但我來到這里,體驗到了一種意境,就在世界之外的空間,升華了老人家的去處。
生活在瑣碎的枝節中累積著曾外婆曾經留在這里的氣息,歲月在流逝的同時,也累積過曾外婆在這里有過的喜怒哀樂。她堅強走過的地方,注定了帶有她音符的精彩旋律。
記憶里深深鐫刻著曾外婆的笑容,生死隔不斷的親情滿是一田野的溫馨。
我們掃完墓,一直不想馬上離開。因為曾外婆,我們留戀著這里的一切,也關心著這里的一切。
遠處的地頭邊上,種滿了花椒樹。在這清涼的畫面里,我竟然又把它們看成了丁香花。那是我夢里永遠的風景。
責任編輯 黑 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