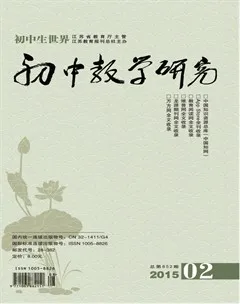理解學生 等待花開
當初,有一位“老教師”私下里給我介紹“經驗”說,你對學生不要太好,尤其是剛接班時,要給學生一點下馬威,否則后面的日子不好過。這大概就是教育的“潛規則”吧。于是跟著學,但終究憋不住,24小時后又跟孩子們“混”到一起了。所以,我一直對評選出來的各級各類“優秀班主任”“優秀教師”懷有一種天然的警惕,擔心他們為了優秀,傷害孩子們太多。事實上,在評價體系還不是很科學的情況下,“優秀”的背后往往隱藏著一種叫“專制”的東西。
杜威先生說過,“兒童不是尚未長成的大人,兒童期有其自身的內在價值。”如果想用我們的看法和感情去衡量他們的,那是愚蠢的事。兒童總處在未完成之中,人的生命處于不停息的變化之中。我們所要做的是為學生創設一個有助于其生命充分生長的情境,把兒童的生命力量引出來,使學習過程成為學生生命成長的歷程。
學生總是以形形色色的個性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每一個學生來到學校的時候,除了懷有獲得知識的愿望外,還帶來了他們的情感和感受的世界。注重生命發展的教學是讓學生的情感、意志都參與到學習中來,使學生在學習知識的同時,感受和理解知識的內在意義,獲得精神的豐富和完整生命的成長。
或許,真的有了這些認識后,我們就不會再浮躁,也不會“好心辦壞事”了,更不會“揠苗助長”了,當然也就不會“氣死了”。理解了學生、理解了教育,我們的“愛”才會有所附著,才能真正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
有了對于學生的理解,你還會產生一種重要的教育心理——等待。記得楊瑞清提出過一個“花苞心態”的概念,他說,我們一些老師總是喜歡那些盛開的荷花,對于旁邊的花苞抱著“人家都開了,你怎么還不開?你再不開,我就把你給掰開”的急躁心理,于是,太多含苞待放的鮮花因被“掰開”而枯萎了。
2005年,有媒體披露了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昔日大名鼎鼎的“神童”寧鉑如今出家為僧、干政“自我封閉”、謝彥波“有心理問題”的不幸命運。中科大少年班再次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少年班是培養人才還是摧殘人才?到底還要不要辦下去?”的討論在校內外激烈展開。“生活自理能力差、心理問題嚴重、人際交往困難”的文章也不斷見諸報端和網站。一位全國政協委員干脆提交了一份《請求停辦少年班》的提案。
我承認的確有“天才”的存在,但我很害怕“造就天才”的教育,劉鐵芳教授說:“任何縮短個體發展歷程的教育模式,都不過是揠苗助長,盡管可能促進個體某方面特殊才能的發展,但就個體精神世界的整體完善,顯然是‘欲速則不達’。”
教育是一種等待的藝術,教師需要有足夠的耐心來等待學生生命世界的慢慢生長、生成。遲開的花兒同樣鮮艷,這是一種“花苞心態”,與此相對應的是“揠苗助長”,后者未必是出于“歹意”,有時恰恰是“好心”,但缺少科學意義的“好心”往往更具有破壞性。
教育要走進孩子們的心靈,這是“公理”,如何走進,各有其道。但不管道有多少,理解兒童、等待花開是繞不開的天衢。很多人喜歡把學生比作花朵,那就讓我們來做一名花工,懂得陽光、雨露與土壤之于花開的意義,聽得懂花開的聲音,“情在左,愛在右”,靜靜地等待每一朵花兒的次第開放。
(作者單位:江蘇省鎮江市外國語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