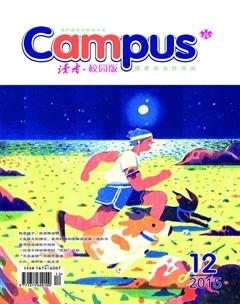一位語文特級(jí)教師的“悲壯”試驗(yàn)
陳璇
近一兩年來,每周五晚上,語文特級(jí)教師曹勇軍都會(huì)有一種“朝圣”的感覺。
到了晚上6點(diǎn)半,曹勇軍習(xí)慣性地打開一間教室的日光燈。這亮起的燈光在他看來,有些像接頭暗號(hào)。不一會(huì)兒,十幾個(gè)高中生從學(xué)校的各個(gè)角落里冒了出來。
燈光會(huì)持續(xù)兩個(gè)小時(shí),這是曹勇軍和十幾個(gè)高中生的夜讀時(shí)間。從2013年冬天起,這位南京知名的語文老師辦了一個(gè)“經(jīng)典夜讀小組”,帶著學(xué)生讀經(jīng)典著作。
這在其他高中語文老師的眼里,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山東一位語文老師聽說后感嘆:“毫無疑問,曹老師做了一件很多語文老師想做卻未必能做到的、意義深遠(yuǎn)的事。”
如此贊譽(yù)卻讓曹勇軍高興不起來。他回憶:當(dāng)時(shí)辦“經(jīng)典夜讀小組”,是因?yàn)榭吹讲簧賹W(xué)生到了高中,“除了考試和練習(xí)冊(cè),早已不知閱讀為何物”。于是,快要退休的曹勇軍試圖給學(xué)生上自己心目中的閱讀課。
語文閱讀教育正在被“異化”
2013年11月23日,曹勇軍第一次帶著學(xué)生夜讀。
頭一次辦這個(gè)活動(dòng)時(shí),他等了半個(gè)小時(shí),才來了3個(gè)學(xué)生,其中兩個(gè)沒看完他指定的書目。當(dāng)時(shí),曹勇軍有些沒底氣,而學(xué)生們也不理解曹老師為什么要搞閱讀小組。
畢竟,高中生要閱讀的課文和考試素材并不少。但在曹勇軍看來,在應(yīng)試教育的環(huán)境下,那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閱讀。
他走訪過不少中學(xué),發(fā)現(xiàn)了一個(gè)現(xiàn)象——相當(dāng)一部分學(xué)生,把大量時(shí)間花在操練跟閱讀無關(guān)的現(xiàn)代文閱讀題上。
這位江蘇省特級(jí)語文老師直言了一個(gè)“慘烈”的現(xiàn)實(shí):語文閱讀教育正在被“異化”。
教齡超過30年的曹勇軍不否認(rèn)現(xiàn)代文閱讀題的“特殊功能”——“大量、快捷、低成本測(cè)試閱讀能力的一種手段”。不過,他擔(dān)憂這種“測(cè)試性閱讀”會(huì)成為一些高中生最重要甚至唯一的閱讀文本。
曹勇軍第一次和學(xué)生在燈下夜讀,擺在他們面前的是沈從文的《湘西散記》。他給學(xué)生列了一個(gè)有分量的、“傳遞價(jià)值”的書單。其中有尋找自然和詩情的《給孩子的詩》和《大地上的事情》,有反思極權(quán)主義的《1984》和反科學(xué)烏托邦的《美麗新世界》,還有一些文史哲著作《美的歷程》《萬歷十五年》和《中國哲學(xué)簡(jiǎn)史》。
按照現(xiàn)代文閱讀考試要求而進(jìn)行的對(duì)“文章細(xì)部刻意的、人為夸張的理解”,被這位語文老師完全摒棄。對(duì)像講解考試題那樣告訴學(xué)生“這個(gè)是‘關(guān)鍵詞理解、這個(gè)叫‘把握作者的情感、這個(gè)叫‘手法鑒賞”的做法,他顯得很不屑。
“任何正常人都不會(huì)這樣去讀文章。”他說。
“在真實(shí)的精神中讀真實(shí)的書,
是一種崇高的訓(xùn)練”
自從有了那晚“格外明亮”的燈光后,閱讀教室的燈幾乎每周五晚上都會(huì)亮起。
“經(jīng)典夜讀小組”里的女生霍晨這樣回憶夜讀時(shí)的心情:“在大多數(shù)人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中時(shí),我們?cè)谶@里開始了屬于自己的‘閱讀盛宴。”
一份《夜讀記》記錄了學(xué)生口中“閱讀盛宴”的一些片段。在讀梭羅的《瓦爾登湖》中《閱讀》這一章時(shí),曹勇軍讓學(xué)生找出讀到的最受啟發(fā)的句子,并談?wù)劯惺堋?/p>
這是當(dāng)時(shí)討論的部分對(duì)話——
朱冠怡:“‘不管我們?nèi)绾钨澷p演說家隨時(shí)能展現(xiàn)出來的好口才,最崇高的文字通常還是隱藏在瞬息萬變的口語背后,或超越于它之上,仿佛繁星點(diǎn)點(diǎn)的蒼穹藏在浮云后面一般。那里有眾星,凡是觀察者都可以閱讀它們。我他感覺這個(gè)句子很有哲理,又有美感。”
曹勇軍:“這句話的意思其實(shí)就是說,不要迷惑于華美的言辭,關(guān)鍵要看其背后的思想。”
楊思羽:“我最喜歡的是‘我愿帶著最微薄的行李和最豐富的思想,來到瓦爾登湖。思想的豐富是無窮的,能引發(fā)人生的徹底改變。”
曹勇軍:“本章第3節(jié)‘讀得好書,就是說,在真實(shí)的精神中讀真實(shí)的書,是一種崇高的訓(xùn)練,是花費(fèi)一個(gè)人的力氣,超過舉世公認(rèn)的種種訓(xùn)練。——我們的夜讀活動(dòng),正是對(duì)這個(gè)句子最好的注解。”
十幾個(gè)學(xué)生圍坐在橢圓形的木桌前,不是在聽老師向他們灌輸方法和道理,而是按照要求先將指定的書目讀完,在周五夜讀時(shí)參與討論。之后,他們還要完成讀書報(bào)告。
在描述這種難以傳遞的“私密”閱讀體驗(yàn)時(shí),霍晨用散文化的語言寫道:“每次結(jié)束夜讀之后,我都久久無法平復(fù)自己激動(dòng)的心情,走向?qū)W校大門的步伐更加堅(jiān)定,風(fēng)在耳邊沙沙作響,腦海中還在不斷回憶著之前激烈的討論和老曹說過的話。”
帶著十幾個(gè)學(xué)生一年讀完17本經(jīng)典著作,讓曹勇軍獲得不小的成就感。不過,在那間教室之外,高中閱讀教育的現(xiàn)狀仍然令他擔(dān)憂。
跟美國教育界一位同行的交流,加深了他的這種憂慮。曹勇軍曾問美國佛羅里達(dá)大學(xué)教師學(xué)院教授傅丹靈:“美國中學(xué)如何上閱讀課?”傅丹靈介紹,美國的九年級(jí)學(xué)生(高中一年級(jí)學(xué)生)每周的閱讀內(nèi)容,除了精選的作業(yè)(平均每周3篇到4篇故事和散文)外,還有13個(gè)短故事和7個(gè)說明性文本。學(xué)生在家里閱讀,在課堂上討論,課后還要完成一篇文章。
從直觀的閱讀數(shù)據(jù)和方法上,曹勇軍看到了中美母語基礎(chǔ)閱讀教育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這位蘇教版語文教材編寫者憂心忡忡地說:“很多學(xué)生不僅不讀課外書,連語文課文都不好好讀了。”
在曹勇軍看來,這并不能怪學(xué)生,更荒謬的現(xiàn)狀是,不少老師自己都不讀書。他曾問一些年輕教師是否讀過某些書,那些“80后”老師表情尷尬,只能不好意思地?fù)u搖頭。
“這些年輕老師可以被稱為‘做卷子長大的一代。”曹勇軍形容道,“他們能做的就是捧著教材,把答案搬給學(xué)生。難怪現(xiàn)在很多學(xué)生都很鄙視語文課。”
在宏觀的教育設(shè)計(jì)中,“讓學(xué)生讀整本書是被倡導(dǎo)的”,有的課程標(biāo)準(zhǔn)中還會(huì)列出書目。不過,在教育一線實(shí)踐30多年的曹勇軍深感,“紙上的東西落實(shí)起來很困難,并且這些要求沒有配套措施”。
高考命題者試圖用考試指揮棒來引導(dǎo)師生們重視經(jīng)典閱讀。曹勇軍介紹,江蘇將《紅樓夢(mèng)》《三國演義》《哈姆雷特》等10本名著列入高考必考書目。在江蘇文科高考語文試卷的40分附加題中,這些名著會(huì)以兩道解答題的形式,占據(jù)影響考生命運(yùn)的10分。
但聽上去有些諷刺的事情發(fā)生了。“有些老師如何講《紅樓夢(mèng)》呢?他們將這本名著的一章一回‘碎尸萬段,變成一個(gè)個(gè)考試點(diǎn),讓學(xué)生讀。”
這位年近60歲的老教師很無奈:“好好的《紅樓夢(mèng)》變成了‘紅樓夢(mèng)復(fù)習(xí)資料大全。”但他也能理解,在應(yīng)試教育的濃郁氛圍下,“不少老師變得短視和急功近利。”
“想要?dú)У裟囊槐緯桶阉胚M(jìn)高考必考書目里。”他開玩笑地說。
“溫情的教育改良者”
并不能完全跳出應(yīng)試的話語體系
回到校園,每周五晚上的那束燈光,有時(shí)在曹勇軍心里“顯得有些孤獨(dú)”。
他翻出一本厚厚的黑皮筆記本,里面是學(xué)生們輪流寫的一頁頁閱讀記錄。筆記本中間夾著幾張請(qǐng)假條,大多數(shù)請(qǐng)假的原因是“補(bǔ)課”或“家里有事”。
這些夜讀的高中生,平日里要忙著上課和補(bǔ)習(xí),有很多的考試要應(yīng)付。為了挪出讀書時(shí)間,他們有的攥住課間和午休時(shí)間,有的抓緊晚上睡前的20分鐘。
“經(jīng)典夜讀小組”成立后,有新成員加入,也有不少人“艱難”地退出。一個(gè)學(xué)生在給曹勇軍的《退出經(jīng)典夜讀小組申請(qǐng)書》里寫道:“這些天我經(jīng)歷著復(fù)雜的思想斗爭(zhēng)。斗爭(zhēng)圍繞‘我是否學(xué)有余力展開。雖不愿意承認(rèn),但我確實(shí)不是學(xué)習(xí)輕松的學(xué)生,如果我繼續(xù)維持這種狀態(tài),很可能到頭來竹籃打水一場(chǎng)空。”
退出的學(xué)生大部分是因?yàn)檎n業(yè)負(fù)擔(dān)太重。曹勇軍解釋:“有的學(xué)生考試成績(jī)有了波動(dòng),心理壓力就會(huì)很大,家長就會(huì)擔(dān)憂,甚至有的老師也會(huì)有意見。”
在召集“經(jīng)典夜讀小組”成員時(shí),曹勇軍也設(shè)立了門檻,其中包括“學(xué)習(xí)成績(jī)排名”。他承認(rèn),這種特殊的閱讀課是對(duì)優(yōu)秀學(xué)生的“私人訂制”,面對(duì)的是“考有余力”的學(xué)生。他將自己的閱讀課視作對(duì)應(yīng)試化閱讀教育的“一種突圍”。
有人問曹勇軍:“經(jīng)典夜讀究竟對(duì)學(xué)生的考試成績(jī)有沒有影響?”盡管創(chuàng)辦初衷不是為了應(yīng)試,但這位自稱“溫情的教育改良者”的教師,并不能完全跳出應(yīng)試的話語體系。
他可以給出滿足功利主義者期待的答案。他介紹,在一次模擬考試中,南京市語文考試作文得分65分以上的考生中,有4人是“經(jīng)典夜讀小組”的成員。
另一個(gè)例子聽上去也很符合現(xiàn)實(shí)主義者“有用”的價(jià)值觀。“經(jīng)典夜讀小組”的一位學(xué)生,在申請(qǐng)一所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試時(shí),高校老師聽說他跟著老師一年讀了17本經(jīng)典著作后,對(duì)這個(gè)學(xué)生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
幾天前,在北京大學(xué)教育學(xué)院,面對(duì)著坐滿一間小報(bào)告廳的教育研究者和工作者,曹勇軍分享著他的語文教育故事,其中包括“經(jīng)典夜讀小組”。在場(chǎng)的一位高中語文女教師私下說:“他做的事情,普通老師做起來是很難的,畢竟他有特級(jí)教師的能力和威望。”
而曹勇軍周五晚上從閱讀教室的窗戶向外望去,有時(shí)一片寂靜,有時(shí)夜雨敲窗。抬頭看看頭頂上的亮燈,他有時(shí)會(huì)感覺到“孤獨(dú)”,甚至是“悲壯”。
不過他說,這里的“悲壯”不是一個(gè)貶義詞。
(岸芷汀蘭摘自《中國青年報(bào)》2015年4月1日,康永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