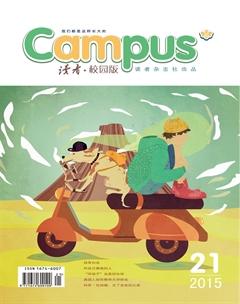找李白去
閻連科
總是想出走。
出走的念想,是每一個(gè)少年成長(zhǎng)中無(wú)來(lái)由會(huì)產(chǎn)生的想法和必需的營(yíng)養(yǎng)。直到現(xiàn)在,盡管我已經(jīng)50多歲了,離家出走的念想還會(huì)時(shí)不時(shí)地冒出來(lái),一瞬間成長(zhǎng)為一棵參天大樹(shù)。用出走的方式告別和背叛,怕是我一生一世的事,是一種事業(yè)和未來(lái)。我每天都在告別、背叛的想法中寫(xiě)作和生活。每每想到告別和背叛,我就會(huì)有一種興奮和不安。人——尤其是孩子們——如果從未想過(guò)不辭而別、離家出走和背叛,那樣的人生將是多么怯弱、單調(diào)和無(wú)趣啊!
出走和背叛,是少年時(shí)代揳進(jìn)我腦子里永遠(yuǎn)也拔不出來(lái)的一根樁。
成長(zhǎng),是由無(wú)數(shù)次想要出走(背叛)而又不得不留下的過(guò)程疊加起來(lái)的;而成熟,是人生歷練中靜默不言的一種光。然而一次次地想要離家出走,想要把自己放逐,也許正是長(zhǎng)大、成熟的一種準(zhǔn)備。除了饑餓帶來(lái)的痛苦,我們家不缺少溫暖、悠閑、苦累和兄弟姐妹間的爭(zhēng)執(zhí)和謙讓。那個(gè)家,是鄉(xiāng)村家庭的典范。父母謙卑和睦、通情達(dá)理。家里的生活雖然貧窮,可在村里還是讓很多更為貧窮的人家羨慕和尊崇的。在那偌大的田湖村,父母給我們的愛(ài),多得常常從小院里漫出來(lái)。然而,這種愛(ài)還是不能消除一個(gè)男孩想要離家出走的念想。
有一天,我決定出走了。
父母下地,姐姐和哥哥們不在家,我獨(dú)自在小院里寫(xiě)了一會(huì)兒作業(yè),看著母雞在窩里生了一個(gè)蛋,又看著那只母雞邀功一樣在我面前“咕咕”地叫著轉(zhuǎn)了幾圈,我給它抓了一把玉米粒兒作為獎(jiǎng)賞后,“哐”的一下——決定離家出走。好像決定出走完全是因?yàn)槟侵幌碌暗哪鸽u,想到我才十幾歲,不能如一只雞一樣在一個(gè)小院里了此一生。
我要到外面的世界去。
我要到外面的世界走走和看看。
想到我決定要出走,就有一種興奮勁兒在我身上鼓蕩著,仿佛不立刻離開(kāi)那個(gè)家、那個(gè)院子,我便會(huì)窒息在那個(gè)家、那個(gè)院子的溫暖里。說(shuō)走就走,我把作業(yè)、課本收起來(lái)扔在窗臺(tái)上,把屋門、大門鎖起來(lái),把家里的鑰匙塞進(jìn)家人可以找到(其實(shí)所有的外人也都能找到)的門楣上方的一個(gè)小墻洞里,就這么匆匆離家上路了。
離家出走時(shí),我朝見(jiàn)娜家(我已經(jīng)很久沒(méi)有想起過(guò)見(jiàn)娜及其家人了)的壓水井那兒看了看。然后,我朝寨墻外早時(shí)和見(jiàn)娜經(jīng)常一塊上學(xué)、放學(xué)的小路走去,到了北寨墻的寨門外,又沿著河邊的大堤朝著正東走。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兒,但又好像早就計(jì)劃好了要去哪兒一樣。直到沿著大堤離開(kāi)村莊,東山漸近,田湖漸遠(yuǎn),一片柳林外的伊河,白花花地瀉在我面前,我才知道我要離家去哪兒——我要獨(dú)自蹚過(guò)伊河水,爬到對(duì)面伏牛山的九皋山主峰上。
老師說(shuō)過(guò),九皋山是伏牛山余脈東延的主峰,海拔900多米,中國(guó)第一本詩(shī)集《詩(shī)經(jīng)》中的“鶴鳴于九皋,聲聞?dòng)谔臁保f(shuō)的就是那座山峰。據(jù)說(shuō),唐朝的李白曾獨(dú)自從龍門走來(lái),上過(guò)那座山峰,而且還在那兒留過(guò)一首名為《鶴鳴九皋》的詩(shī)。這首詩(shī)有啥意味和意境,那時(shí)的我完全不懂(現(xiàn)在也不甚懂),但我覺(jué)得人們很難讀懂的詩(shī)反而好寫(xiě),倒是像《靜夜思》那樣的詩(shī),因?yàn)槿巳硕级炊鴮?xiě)不得。
我總以為自己能寫(xiě)出那種人人都讀不懂的詩(shī),也就蓄意要爬到那座山上,和李白一樣坐在山頂,詩(shī)興大發(fā),寫(xiě)出一首好到別人都看不懂的詩(shī)。當(dāng)然,寫(xiě)不寫(xiě)詩(shī)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終于離家出走,獨(dú)自走了很遠(yuǎn)的路,遇上了很多事,經(jīng)歷了很多的艱辛和奇遇,它們都被我一一征服,我成了站在山頂上的一個(gè)大人物。
浪漫和草率,在我幼稚的胸膛里發(fā)酵、鼓脹著,使我有了一種從未有過(guò)的英雄氣概。我也就一路昂首闊步、義無(wú)反顧地到了伊河最寬、最淺的河灘上了。有來(lái)往的行人,舉著他們的衣物和行囊,踏水朝著對(duì)岸蹚。我在前一年的盛夏,同鄰居家的孩子們到伊河里游泳,“狗刨”著游到河中央,被漩渦卷進(jìn)急流里,差點(diǎn)兒死在伊河里,后來(lái)被鄰家的一個(gè)張姓孩子救了出來(lái)。把我救出來(lái)后,他抓著我的雙腿,把我腳朝上、頭朝下地抖了大半天,待我把喝進(jìn)去的伊河水全吐出來(lái)后,他說(shuō)了一句極為經(jīng)典的話:“淹一次,你就學(xué)會(huì)游泳了。”
我真的學(xué)會(huì)游泳了。
我可以獨(dú)自無(wú)所畏懼地走過(guò)齊腰深的伊河了。和別人一樣,我脫光衣服,把衣服舉過(guò)頭頂,半游半蹚地將過(guò)河水時(shí),迎面游來(lái)一個(gè)過(guò)河的人,他很驚奇地望著我,大聲說(shuō):“這娃兒,你去哪兒?你不怕被淹死嗎?”我沒(méi)有告訴他我是離家出走,有一股破釜沉舟的勇氣正在我身上激蕩著。我只是很不屑地朝他看了看,更加無(wú)所畏懼地游向河心。
河心的水流沒(méi)過(guò)我的脖子,我差點(diǎn)兒被沖倒。及至對(duì)岸,濕漉漉地再穿衣服時(shí),我便更加擁有了一種無(wú)所畏懼的勇氣。走小路,過(guò)村莊;在村頭遇到土狗追著我咆哮和撕咬;遇到一匹驚馬從我身邊飛馳而過(guò),揚(yáng)起的灰塵落在我臉上,我都沒(méi)有絲毫的恐懼和驚異。我是離家出走的人。我要和李白一樣,獨(dú)自登上那很少有人能爬到山頂?shù)木鸥奚剑ㄒ欢ㄒ獙?xiě)詩(shī)),我當(dāng)然不能有任何恐懼或擔(dān)憂。我就那么獨(dú)自沿著東山下的村莊走,不和人說(shuō)話,不和人來(lái)往,旁若無(wú)人,義無(wú)反顧,至多在有些寂寞無(wú)聊時(shí),從地上撿起一根細(xì)柳枝,邊走邊在地上掃;至多在看見(jiàn)路旁的樹(shù)上有了金黃色的知了殼時(shí),摘下來(lái)在手里拿一會(huì)兒,覺(jué)得無(wú)趣、沒(méi)有意思了,便把柳枝和那知了殼一并扔到路邊的草地里。
轉(zhuǎn)眼,我走到了九皋山下那條“牛瞪眼”的小路上。路是泥土路,可在那干硬的路面上,接連不斷嵌有突出的碎石子,好像那石子是專門鑲在地上,等人爬山時(shí)可以蹬著石子用力一樣。山在頭頂,我在山下,正南方的太陽(yáng)烤在我的發(fā)梢上。我知道自己不久就要登上九皋山,爬上主峰振臂高呼了。我已經(jīng)把在峰頂上要高呼的口號(hào)都想好了,我要站在峰頂,讓風(fēng)吹著我的頭發(fā)和衣服,環(huán)顧四周,最后把我的胳膊高高舉起揮動(dòng)著,用我最大的嗓門對(duì)著天下喊:
“有一天我要吃得好,也要穿得好!”
“有一天我要吃得好,也要穿得好!”
那一天的離家出走,我決計(jì)要讓它成為我人生的宣誓,寫(xiě)在我生命的旅途上,成為我不凡命運(yùn)開(kāi)始時(shí)最巍峨的紀(jì)念碑。可我沒(méi)想到,我宣誓的胳膊都還未舉起來(lái),就被變故和偶然把我雙腳、雙臂行走和伸展的方向改變了。原以為人生是一條充滿必然性的河流,哪知人生中的偶然才是我們過(guò)河時(shí)的墊腳石。那些不可思議的事,都是無(wú)法擺脫的偶然。為了不在寫(xiě)詩(shī)和爬山的路上碰到三姑家的人,走過(guò)了兩個(gè)村莊后,我到了我三姑家所在的梁疙瘩村(這村名,煩),就有意繞過(guò)村莊,從村旁的一片莊稼地里穿過(guò)去,沿著溝崖小道,攀著荊棵、野榆樹(shù)走了很遠(yuǎn)的路。到了終于可以看清山頂時(shí),我以為峰頂?shù)搅耍╊h(yuǎn)方、振臂高呼口號(hào)的那一刻,卻從不遠(yuǎn)處的山崖邊爬上來(lái)一個(gè)人,收拾捆綁他在崖頭砍拾的柴火。我們彼此一望,都驚呆了。
他竟是我要躲避的三姑父。
三姑父就好像在那兒專門等我一樣出現(xiàn)了。
我待在崖頭邊兒上,三姑父看著極吃驚的我,很快平靜下來(lái),連說(shuō)了三句話:
“你怎么在這兒?”
“是你三姑讓你來(lái)這兒找我的?”
“走,我們回家吃飯去。午飯都錯(cuò)過(guò)時(shí)辰了。”
我就這樣莫名其妙、前功盡棄地被三姑父強(qiáng)拉硬拽到他家了。路上我掙著身子對(duì)他說(shuō):“我是專門來(lái)爬山的,我一定要爬到山頂。”三姑父扛著柴火,提著我的胳膊抖了抖(像提著抖一只小雞、小狗一樣),說(shuō):“山上有啥好看的啊?除了石頭就是兩棵野榆樹(shù),連點(diǎn)花草也沒(méi)有。”再進(jìn)一步知道我父母都不知道我離開(kāi)了家時(shí),他連連罵我:“咋就這么傻!”他把我拽回他家匆匆吃了飯,又趕在日落前,帶著我下山和過(guò)河,把我送回田湖村了。
一場(chǎng)盛大、莊重的離家出走,就這么草草地收了兵。一場(chǎng)夢(mèng)想中的人生莊嚴(yán)的宣誓,還未及最后登上宣誓臺(tái),就被人從夢(mèng)中叫醒了。現(xiàn)實(shí)總是比夢(mèng)想有力量,少年明亮、美好的夢(mèng),被現(xiàn)實(shí)一碰即破后,我這一生再也沒(méi)有機(jī)會(huì)登上那座山,再也沒(méi)有可能在李白待過(guò)的山頂坐坐或站站,高舉著胳膊大喊了。
我的少年時(shí)光就這樣過(guò)去了,還是那時(shí)候的李白好。
可我連李白的影子也沒(méi)找到,就那樣在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交叉口和李白分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