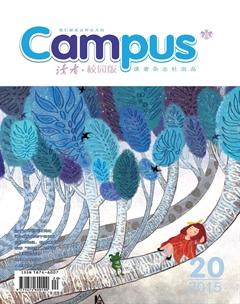有些事,想起來濕潤而美好
王太生
蟲鳴夜,翻張岱《夜行船》,有“郭林宗友人夜至,冒雨剪韭作炊餅”之語。夜雨剪春韭,寥寥數筆,把二人關系的親疏遠近,交代呈現得像虎皮西瓜,紋路清晰。
有些事情,想起來濕潤而美好。
下雨天,家中來了人,又沒有什么好招待的,就想到屋后有一畦地,雨中春韭,長勢喜人,便撐一把傘,或戴斗笠,摸黑下地,剪一把綠韭,烙韭菜餅。
剪下的韭菜,露水晶瑩。烙韭菜餅,韭菜一點一點細細切碎,面糊拌青末,用柴火鐵鍋去烙,鍋不熱,餅不貼,小屋里很快韭香四溢。窗花燈影,映著兩個人,這時候不一定需要酒,客隨主便。他們的感情,像雨和葉子一樣親近。
有些事,想起來本身就濕潤而美好。
祖宗留下的一對舊桌椅,包漿沉靜。一年四季,磨蹭擦拭,碗盤磕碰,湯水潑溢。冬天冰冷堅硬,夏天大汗淋漓。盤髻女子、垂髫小兒、耄耋老者……上面坐過什么人,有過什么心思?或者擺放過什么東西?
小時候,聽外婆說,從前的生活樸素貧困。一天,有個親戚上門,外婆的缸中沒有米,她趕緊到鄰居家去借。外婆借來3斤米,親戚并不知情,外婆瞞著親戚借米,還打腫臉充胖子,笑嘻嘻地對客人說:“缺錢、缺煤,不用愁,有什么事,盡管提。”
我十五六歲時,到鄉下走親戚。住在一座村莊里,散步到一戶人家,主人見有客登門,頗感意外,忙不迭地不知拿什么東西招待才好,正搓手猶豫著,忽然看到屋外有一株梨樹,累累梨子壓彎樹枝。秋天正是梨樹掛果的時候,主人喜出望外,趕緊直奔門外,抱回一大捧梨子。
梨樹本在門外,春天開花,潔白芬芳;秋天結果,闃靜無言。摘一只梨子,伸手可及,可有時主人會忘了這一樹梨子的存在。
我從百里之外的小城坐船而來,先住東莊,有個親戚打聽到消息,步行15里,從西莊趕到東莊,接我到他家。中午吃飯,坐著閑聊,親戚說:“小孩子大老遠地來,鄉下沒有什么好吃的。”說著話時,忽然一拍大腿,說:“想起來了,谷雨在東頭河對岸的地里邊,點過幾顆瓜種,不知結了沒有?”親戚把飯碗一撂,就到那塊地去了,翻騰了半天,摘回了兩只瘦香瓜。
其實,在我看來,鄉下的香瓜最宜入畫。瓜色溫碧,瓜有清香,瓜紋清晰,《本草綱目》里說:“二、三月種下,延蔓而生、葉大數寸,五、六月花開黃色,六、七月瓜熟。”
濕潤而美好的事,大都與情境有關。比如,杏花春雨、涼風好月、坐對一扇窗喝酒、二三摯友結伴而行。有時,人在旅途,也會遇上一兩個素不相識的人。
我到山里看湖,住在縣城。晨起,推窗,見對面樓上陽臺站著一個女子,晨風中梳頭,湖在身后不遠處微微呼吸,人在風景里。
在江南小鎮尋茶,遇雨。看到那些賣茶人,不緊不慢,坐在半明半暗的鋪子里,浸在茶香燈影之中,街道狹窄,燈火可親。
民國閨秀張充和的《小園即事》,有一段童年趣事,小充和還在襁褓時,就過繼給了叔祖母李識修。識修是李鴻章的親侄女,從小給予小充和最柔軟的親情之愛。張充和童年時,對于母親的概念是模糊的,與叔祖母一道生活,她甚至認為“我是祖母生的”,童言稚語,濕潤可愛。
我小時候也有過類似的經歷,以為自己是從漁船上撿來的,弟弟是鄉下姨媽生的。那時候,姨媽常從鄉下來,一住就是十天半個月,姨媽常哄著弟弟睡,手工做小衣裳。我常和弟弟搶牛奶喝。那時的牛奶真香啊,醇香濃郁,比現在的牛奶好喝多了,那可是上個世紀70年代的牛奶。
樸素的事,都是從前的事。有些事隔了多年,想起來,感覺濕潤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