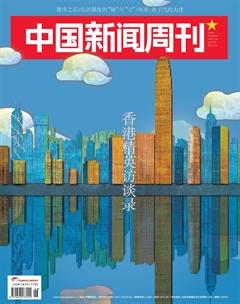全球化“新常態”下的中國外交
何亞非
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博鰲論壇提出建設人類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后,關于全球化與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關系之討論再趨熱烈。
希臘債務危機引發了對歐元區未來的憂慮。烏克蘭危機使人們對歐洲安全乃至全球安全架構塌陷憂心忡忡。美聯儲將于年底前加息的信號,強化了全球資金回流勢頭,發展中國家金融再次面臨流動性危機。
全球化繼續深入發展,勢頭迅猛,進入了新時代和“新常態”。凡此種種,需要各國進行深刻反思,并探討21世紀全球化發展的新思路、新路徑。
全球化“新常態”五大特征
之所以說全球化進入“新”時代,而且已成為“常態”,主要因其有以下五大特征:
一是隨著全球化深入世界各個角落,各國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已經結成事實上的利益共同體。至于是否能成為命運共同體,現在還難以下結論,因為這涉及各國在政治、安全、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深入合作。
目前,全球生產要素的流動無論從規模還是速度看,都是空前的。過去那種“某國制造”的概念已經被徹底顛覆,除了自產自銷的農產品以外,工業產品和消費產品的設計、生產、營銷等都已經全球化、扁平化了,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制造”。
中國是制造業第一大國,然而從全球范圍計算,中國的順差并不大,因為中國需要從世界各地進口大量的資源、原料和零配件,來生產最終的產品,再出口到其他各國。
二是“去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同步發展,全球化出現碎片化和無序傾向。
在世界貿易領域,世界貿易組織(WTO)已經名存實亡,作用式微。而各類雙邊和區域性自貿區安排卻如雨后春筍般紛至沓來,包括《跨太平洋經濟戰略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以及中韓、中澳、美韓自貿協定等。有的已經結束談判,即將進入實施階段,有的正在積極推進。
再如,在核不擴散領域,超過190國簽署加入的《核不擴散條約》框架岌岌可危。條約規定的有核武器國家僅有五國,但事實上現在大大小小擁有核武的國家不下40個。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權威性和監督能力不斷削弱。國際社會面對伊朗和朝鮮半島核問題的重大挑戰,只能依靠“臨時性”的談判機制。伊朗核問題靠的是6+1,即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德國加歐盟,而朝鮮半島核問題則依靠“六方會談”機制。
三是全球化打破了邊界和領域的界限,使全球性挑戰增多,風險和危害跨國界、跨領域傳遞速度驚人,沒有國家能獨善其身。而國際社會團結應對的決心不強、機制不靈、辦法匱乏。
從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到至今還在發酵的歐洲債務危機(希臘就是最新的案例),從核武器和核材料擴散,到應對氣候變化,各國自身利益與國際社會整體利益往往錯配。人類利益共同體的意識依然淡漠。今年年底將在巴黎召開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各方對此期望很高。目前看,能否如期達成有實際意義、可操作、符合各國期待的協定,尚難確定。持悲觀看法者也不在少數。
四是從宏觀的角度看,金融資本主義依然主導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走向。金融資本主義雖然經歷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威風不再,但是金融資本繼續控制著全球生產鏈和價值鏈,支配著全球的利潤財富和經濟利益的分配。只要國際體系包括全球治理體系沒有重大調整,這一局面就難以改觀。
五是經濟全球化的風險已經外溢至政治、安全、社會等其他領域,經濟停滯、失業高企、債務沉重、貧富差距擴大等經濟頑疾成為導致許多國家政治動蕩、社會混亂、國家破碎的主要根源。
中國應對“新常態”的五大重點
經過數十年的艱苦奮斗和改革開放,中國已深深卷入全球化,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成為全球生產鏈和價值鏈的重要一環,現在正站在世界舞臺的中央,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核不擴散條約》規定的五核國之一、20國集團(G20)核心成員,2016年將接任G20輪值主席國。凡此種種都說明,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和全球性大國,責任重大,需要以更大的勇氣和決心,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補充和完善,以適應世界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全球化“新常態”。重點可以從五個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和相關機制的改革、補充、完善。
一要增加中國、印度、巴西、印尼、南非、土耳其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體系包括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決策權和國際機構中的投票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權和份額的改革與調整首當其沖。二要加強大國之間的深入合作,增加共識和互信,尤其是中美兩國需要減少疑慮和摩擦。現實是,全球治理離開了中美的合作將“寸步難行”。我們需要考慮“G2+”的模式,來處理許多棘手的全球挑戰。
其次,改革國際貨幣體系,以減少過度依賴美元的跨國金融風險。金融是經濟運行的命脈,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世界各國的教訓太刻骨銘心了!金融危機最艱難的時刻過去以后,對金融體系改革的勢頭明顯減弱。這點需要引起G20的高度關注。
G20應該加大宏觀經濟和金融政策的協調;主要儲備貨幣國應該有大國擔當,負起穩定貨幣幣值和利率的責任;大宗商品定價貨幣需要實現多元化;全球金融監管要繼續加強,IMF和金融穩定論壇(FSB)等要按照G20的授權,制定監管規定并加強各國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盡快將人民幣納入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中國自身則要繼續堅定不移地穩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第三,嘗試并推廣新的國際和區域合作模式。中國在習近平總書記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思想指引下,倡導并積極實施“一帶一路”建設構想。這是中國在總結近年來全球化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理念為核心,提出的全新的國際和區域合作模式,以期與沿線國家結成廣泛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最近,習近平總書記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共同商定,將“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就是體現了這種合作共贏的精神。
中國積極推動、倡議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絲路基金、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上海合作組織銀行等,有的已經成立,有的即將問世,標志著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和許多發達國家,希望補充、完善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以更好地服務于世界經濟的復蘇和可持續發展,特別是為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籌集資金。以亞洲為例,到2030年就需要基礎設施投資11萬億美元。
第四,國際社會需要高度重視發展議程。可以說,沒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就不可能有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繁榮穩定。這是常識,但也是過去被長期忽視或者“口惠而實不至”的領域。
今年是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DG)的收官之年,9月聯合國將制定到2030年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DG),目前各方正在緊張地談判。各國務必重視這些目標的制定和實現,加大一國國內和對最不發達國家的扶貧減貧力度。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和新興大國,不僅要繼續大力提供國際援助,更要與各國分享自身的發展經驗。同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訪問蒙古時所說,歡迎其他國家搭乘中國發展的“便車”和“快車”。
最后,中國需要更加深入地參與全球治理及其體系的改革和完善,運用“中國智慧”,提出“中國思想”和切實可行的“中國方案”,并身體力行,提供適合發展中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合適技術、產能及配套資金。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實現國家治理能力和體系的現代化”,與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相輔相成,密切相關。我們需要有全球主義的胸懷,有大國的擔當,站在21世紀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前列。
全球化“新常態”,說到底是國際規則的競爭、人才的競爭。我們亟需在各領域培養、儲備一大批精通國際規則、精于國際談判的優秀人才。這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需要,也是中國全面走向世界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