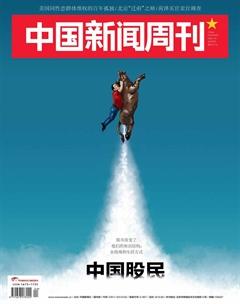檢察院“插手”公益訴訟
韓永
中國公益訴訟或將迎來“強勢”主體。
6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了一份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提交的《關于授權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公益訴訟改革試點工作的決定草案》。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最高人民檢察院開展提起公益訴訟的試點。試點的區域包括北京、廣東等十三個省市自治區,試點的領域有四個方面: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國有資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食品藥品安全。
分析認為,檢察機關介入公益訴訟,有助于改變公益訴訟主體長期以來弱勢的現狀,但也要對其是否會過于強勢保持警惕。
從“民告官”到“官告官”
最高人民檢察院之所以要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是因為在目前有權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中,并不包括檢察機關。
201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決定》。新《民事訴訟法》第55條規定:“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這是中國法律第一次對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做出規定。但“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的規定屬于準用性規范,只是原則上打開了公益訴訟的大門,但到底哪些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起訴,有待相關的法律予以細化。
2013年,《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修訂,新法第47條規定,“對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中國消費者協會以及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的消費者協會,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省級消協及中國消協由此獲得了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
2015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新《環境保護法》第58條規定: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符合下列條件的社會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一)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二)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
2015年1月6日,最高法對外發布新《環境保護法》的司法解釋。民政部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末,中國在各級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組織有56.9萬,其中生態環保類的社會組織約有7000個,而符合《環保法》及其司法解釋的有700余家。
消協和環保組織都屬于民訴法中“有關組織”的范疇,而該法中所說的“法律規定的機關”一直未予明確。于是,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資格,在法律上一直是空白。
而那些有權提起公益訴訟的社會組織,則因一些現實的困難,而無法滿足提起公益訴訟的需求。北京林業大學生態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楊朝霞多年從事環境公益訴訟的研究,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環境公益訴訟方面,雖然有起訴資格的環保組織有700多家,但真正有起訴能力的只有三四十家,截至目前提起的環境公益訴訟只有六七十件。而中國每年的環境糾紛,有七十多萬起。
楊朝霞說,對于環保組織來說,提起公益訴訟既有資格方面的限制,也有資金方面的困難,還有人才方面的匱乏。“錢的問題是很大的,一項鑒定就要幾十萬元。另外,環境法的專業性很強,全國各地的環保組織中真正懂環境法能起訴的人不多。”
大量的環境糾紛進入不了訴訟程序,一方面使得環境保護失去了司法保障,另一方面,專門為審理環境案件設立的環保法庭,也面臨無米下鍋的尷尬境地。今年6月2日的《人民法院報》報道稱,有的環保法庭自成立以來從沒審理過環境糾紛案件,許多環保法庭則名不符實,主要審理與環保糾紛不相干的各類案件。
廣東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鄭紅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對檢察機關介入公益訴訟的必要性,分三個方面進行了闡述:從刑事訴訟的角度看,一些嚴重侵害公共利益的危害結果,可能是由輕微事件累積造成,難以追究眾多違法者的刑事責任。
從民事訴訟的角度看,一方面,由于法律規定必須與損害結果有直接利害關系才可以提起訴訟,限制了一些公益團體和公益人士起訴的主體資格;另一方面,與損害結果有直接利益關系的主體,往往考慮訴訟成本過高、得不償失而缺乏起訴的動力。
從行政訴訟的角度看,對環境污染等損害公益的行為,個別行政執法機關存在不作為、亂作為的情況,疏于監管或者以罰代刑,導致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
擴權質疑
但要將檢察機關納入公益訴訟的主體,又面臨一些至今無解的質疑,其中最主要有兩點:一是檢察機關在監督職能和訴訟主體角色之間如何自治;二是檢察機關是否會借此擴張權力。
這些質疑,已經在6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對草案的審議中有所體現。不止一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指出,檢察機關如果提起公益訴訟,則其既是案件的監督機關,又是案件的原告,即“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是否能在身兼二職時保持公正,本身就是一個問號。
廣東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鄭紅認為,應正視檢察院身兼二職的問題,他主張應當參照刑事公訴的制度設計,通過合理分工,實行訴訟職能與訴訟監督職能相分離,由不同的部門或檢察官承擔,避免角色定位交叉。
另外,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擔憂,在環保法和食品安全法已經明確公益訴訟社會參與的大背景下,此法案的出臺效果可能會南轅北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辜勝阻提出了一個問題:檢察院成為公益訴訟主體后,與同樣是該類訴訟主體的社會組織是什么關系?
也有人擔心檢察院會借機擴權,并挑戰現有的權力秩序。吳曉靈委員認為,檢察院的主要監督對象應該是公安機關和法院,行政監督應該更多地放在人大制度的框架下。
還有人質疑,檢察機關連現有職權范圍內的事都沒有做好,沒有理由再去“插手”公益訴訟。“檢察院負責對貪腐的偵查起訴,它做好了嗎?這個都沒做好,它還能把公益訴訟管好?”第九、十、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遲夙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對于以上質疑,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的一個解決辦法,是充分利用訴前的程序。即在提起民事公益訴訟之前,檢察機關應督促或支持法律規定的機關或組織向法院提起訴訟;在提起行政公益訴訟之前,應先行向有關行政機關提出檢察建議,督促其糾正違法行政行為或依法履行職責。
“法律上有一個窮盡現有制度的原則,現有的制度能用就用,如果這些制度都不行,再由檢察機關起訴。以環境公益訴訟為例,即先讓NGO起訴,如果NGO沒有能力起訴,或者不愿意起訴,檢察機關再作為一個候補主體起訴,即作為最后一道防線。”楊朝霞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
這與在6月25日的審議中有些委員提出的建議如出一轍。吳曉靈建議檢察院完善訴前程序的使用,培育社會組織擔當公益訴訟的主體,而不是自己來擔當訴訟主體。
一位希望匿名的檢察系統官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檢察機關作為公益訴訟主體的法律之所以遲遲不能出臺,與有關部門,包括司法機關和行政部門,對檢察院擴權后格局會發生變化的擔憂有關。“如果是社會組織告行政部門,就是‘民告官,勝訴的比例不大;如果是檢察院告行政部門,就是‘官告官,勝訴的比率會大幅提高。”
楊朝霞還提出了另外一個約束檢察機關的辦法,即增加檢察機關的舉證責任。原來,在環境訴訟中實行的是因果關系證明的舉證責任倒置,即不由權利受到侵害的一方,即起訴方承擔此舉證責任,而由污染環境的一方承擔此舉證責任,其邏輯主要是權利受侵害方往往處于弱勢,很難證明污染或破壞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如果由檢察機關起訴,就不能這樣安排了。因為檢察機關很強大,就應該沿用‘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由其承擔 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
試點的顧慮
事實上,由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此前早有試點,并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以后迎來了一股熱潮。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要“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
律師姜丹和馬維秋對2013年1月至2015年5月期間的環保公益訴訟進行了研究。他們通過公開信息,搜集了21個已裁決案例和8個尚未裁決的案例。研究發現,在21個已經裁決的案件中,檢察機關出庭支持起訴的僅有6例,占比28.9%;而在2015年1月1日后新發生的8起案件中,檢察機關出庭支持起訴的案件已達5件,占比62.5%。
在公益訴訟的探索方面,廣東省檢察院的有些做法可圈可點。該院的數據顯示,從2005年至2014年12月,廣東全省檢察機關共提起民事公益訴訟33件,在全國領先。2015年5月5日,廣州市天河區檢察院、天河區環保局、廣東省環境保護基金會簽訂環境公益訴訟三方協議,開啟了由起訴人、檢察機關和行政監管部門聯動的訴訟模式。
2014年12月30日,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成立。其職責的第五項規定: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制定管轄的其他跨地區重大環境資源保護和重大食品藥品安全刑事一審案件。
檢察機關介入公益訴訟的威懾力,已在具體案件中顯現出來。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閉幕不久,貴州省金沙縣就因該縣環保局怠于處罰逾期不繳納排污費的企業,將金沙縣環保局告上了法庭。該案也被稱為全國首例由檢察機關提起的行政公益訴訟,此前檢察機關介入的公益訴訟,絕大多數是民事訴訟。
這起舉國關注的訴訟,尚未開審就結了案。金沙縣環保局在收到法院的《應訴通知書》后,就對涉事污染企業做出了行政處罰決定,該縣檢察院認為訴訟的目的已經達到,就提出了撤訴。
一位常年研究公益訴訟的學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此前的試點中,由檢察院參與的公益訴訟,有的不排除有作秀的嫌疑。“檢察院在提起訴訟之前,要做很多的協調工作,要跟法院協調好,被告不能反對檢察機關起訴,地方黨委也會出面說話,選的被告通常也是‘軟柿子。這一切都是為了確保能打贏。”
對于草案提出的試點范圍,有些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也提出了疑問。李景田委員指出,如果試點范圍包括省市縣檢察院,而且還在13個省市自治區進行試點,試點范圍已經超過31個省市區的40%。為了防止負面影響,他建議縮小試點范圍至總體的20%。
這一建議獲得多位委員附議。李智勇委員建議,可以先確定小范圍試點,一年后互傳經驗,擴大試點,再試行一年。
律師遲夙生則再次提到了個人提起公益訴訟的資格問題。在2012年民事訴訟法修改時,她曾經建議將公民納入有權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但民訴法最終只確定了兩類主體: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
楊朝霞也認為,應當授予公民提起環境訴訟的資格。
遲夙生說,許多應當提起公益訴訟的問題,就是由于有關機關和社會團體應當作為而不為造成的,僅僅把訴訟權利授予他們,相當于沒有完全建立起公益訴訟制度。“應當將公益訴訟的權利交給每位公民,并且大力鼓勵,才會治療社會的‘冷漠癥。”
針對有關部門提出的將公益訴訟資格授予個人可能會引發濫訴的擔憂,她覺得大可不必:“濫用訴權可以判敗訴嘛,濫訴也得花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