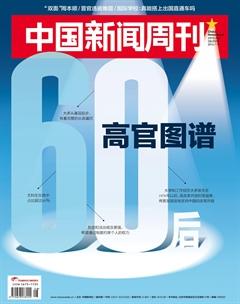與白公館比鄰而居
徐有威

這棟隱在茂密花木后的小樓,氣質超級美,就像美女誰都忍不住看她
1984年到2004年,我在上海徐匯區楓林路醫學院路的一處新工房內住了20年。向北越過東西向的肇嘉浜路,就是屬于“上只角”(上海話中高尚地段的意思)的岳陽路。
岳陽路為南北向,長僅947米,南起肇嘉浜路,北至桃江路。沿途近代名人故居和機構之多之密,在上海名列前茅。
那段時間,我帶著臺灣朋友打車去淮海西路游玩,這是必經之路。我總是請司機開慢些,好向朋友做介紹。
“看左面這個建筑,原為中央研究院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建于1930年,由日本人設計,與日本東京大學工學院大樓相似。右面是宋子文故居,建于1928年,現在是上海老干部活動中心……再看左面,現為上海京劇院,原是京劇大師周信芳舊居。右面現在是上海教育會堂,1971年3月時為上海少年科技站,林彪的兒子林立果曾經聚眾在此商議發動政變……”
可以想象,此刻坐在出租車里的朋友,頭一定轉來轉去如同撥浪鼓了。出租車司機也忍不住表揚我的博聞。“他是上海很有名的導游。”一位臺北朋友幽默地向司機介紹我。
出租車抵達岳陽路最北端后,向右拐上汾陽路。
我繼續介紹:“左面那棟洋樓是白崇禧公館,抗戰勝利后白崇禧全家曾經居住這里。白家五少爺白先勇曾經回憶說,1947年爸爸去臺灣處理二二八事變時,10歲的他就住在這里,家中經常開舞會。”
聽到這里,臺北客人情不自禁欠身抬頭,朝車外張望著這棟隱蔽在茂密花木后面的小樓。
白公館,實乃上海人給這棟洋樓的綽號。據載,它建于1919年,最初是一位法籍冒險家的私家花園。1941年,日本軍隊進入租界,偽國民政府監察院長兼立法院長梁鴻致鳩占鵲巢。抗戰勝利后,這里成了時任國防部長白崇禧的府邸。解放后,它的主人走馬燈似的一換再換:上海中國畫院、上海越劇院、越友酒家……如今,它成了臺灣人經營的日本料店“仙炙軒”。
有網友點評說,白公館“氣質超級美,就像美女誰都忍不住看她”。白崇禧和白先勇當年的臥室都在二樓,現在是店中最貴的包間。可惜餐廳中的油畫主題不倫不類,如果換成和本樓相關的資料照片,無疑會更顯其文化底蘊,開價也可以更高些。餐廳門口站立著一座不知道哪里搞來的石制武士像,遠遠望去還以為是白將軍的雕像,令人忍俊不禁。
1987年,50歲的白先勇再次來到上海,訪問了這童年故居。彼時距他離開,38年已經過去了。昔日王謝堂前的歡聲笑語已煙消云散,不知白五少爺感覺如何。
今年5月中旬,我來到臺北訪學,恰逢白先勇先生在臺北“國家圖書館”舉辦他的歷史紀錄片《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的首發式。2014年白先勇在臺北出版了歷史著作《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紀錄片就是在此基礎上制作的。朋友問我去不去,我欣然答應,馬上電話預定好了圖書館的座位,提前半小時抵達會場。
白先勇比照片上看到的好像胖一些,依舊風度翩翩。朋友熱情地把我介紹給他,我正想抓緊時間向他提及汾陽路白公館時,旁邊圍過來打招呼的人越來越多,白老師忙于一個個寒暄,我再問這個問題好像不太識相了。到活動結束我還是沒有找到合適的時間請教他重返白公館的感覺,留下了一個遺憾。

來參加首發式的人很多,會議室坐得水泄不通,連走廊上的加座也滿了,其中老人居多,年輕人也不少,臺灣各界名流和學者云集。坐在我身邊的先生身材魁梧器宇軒昂,一看就不是尋常人,請教大名,原來是臺灣抗日名將李友邦先生的公子李力群。
“昨晨往吊白崇禧之喪,其實此人為黨國敗壞內亂中之一大罪人也。”這是白崇禧追悼會的第二天,即1966年12月10日,蔣介石在他的日記里寫下的文字。當紀錄片播放到這里時,會場上一陣騷動。
白崇禧和蔣介石的關系,是海峽兩岸民國史學者最為關注的話題。白先勇出版的《白崇禧將軍身影集》沒有使用《蔣介石日記》中的史料,學界前輩楊天石教授等認為是美中不足的。這次的紀錄片,可以算彌補了這個遺憾。白先勇曾經回憶,他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看到這段日記時,嚇了一跳:“沒想到他(指蔣介石)對我父親那么忌諱。”
1949年入臺,到1966年去世,在臺灣的歲月中,白崇禧走到哪里,身后都有情治人員如影隨形。1956年5月2日,他曾經親筆寫了一份密函,由張群轉呈蔣介石,同時將副本送陳誠,詰問派出情治人員跟蹤的原由。陳誠敷衍他:“便衣人員是保護你的,我也有人跟隨。”白崇禧回答:“你現在是‘副總統,當然有此需要,我并無此必要。”但是直到去世,這輛載著三個人的黑色吉普車一直緊跟著他。直到今天,白先勇還能清楚地背出50年前這輛吉普車的車牌號碼:155429。
晚年的白崇禧,和一位廣西老家的世交晚輩栗明德過從甚密。栗明德回憶,白崇禧曾告訴他一個小故事。一次,白崇禧和顧祝同、何應欽等幾位老友在臺北美而廉咖啡廳聚會。咖啡廳中有幾十桌客人,結賬時,白崇禧替其中兩桌素不相識的人結了賬。原來,這幾位就是負責盯梢的情治人員,白崇禧早就認出他們的廬山真面目了。栗明德說,這幾位情治人員后來告訴他:“你的這位廣西白老頭子,真厲害啊。他不是小諸葛,而是真諸葛!”白崇禧則不無黑色幽默地向他解釋,他們跟我跟得很辛苦,付錢是應該的。
會場上一片笑聲。白先勇也笑道:“父親在世時對我們很嚴格,我都躲著他,只知道自己寫小說。可惜我知道的事情,還沒有栗先生多。現在我很后悔,沒有多問爸爸過去的事情,否則我就是白崇禧研究專家了!”其實,這位78歲老人為記錄父輩的歷史所做的努力,已經足以令人既感且愧了。一位參加首發式的朋友說,他前幾天遇到薛岳將軍的兒子,對方就有生子當如白先勇之嘆。
散會后,我碰到了也來參加首發式的老朋友陳三井教授。陳三井曾擔任過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長。我請教這位老前輩:您曾經在上世紀60年代參與白崇禧口述史工作,您有什么親身體會嗎?
陳教授哈哈大笑,他告訴我,當時他們采訪白崇禧時,有一位“有關方面”人士自始至終坐在一旁。采訪稿必須一式二份,在近代史研究所留底的同時,另外一份呈送有關部門。“和現在的情形完全不一樣的。”
1963年2月7日,在時任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郭廷以的牽頭下,近代史所研究人員開始采訪白崇禧。因為這是近代史所采訪過的唯一一位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郭所長高度重視:“即使二三次的訪問,僅訪得一二句我們所未知或有啟發性的話,就算有其收獲了。”
采訪共進行了128次。其中,1963~1964年間的第22~53次采訪,就是由陳三井負責的。后陳三井去法國讀書,他的同事繼續采訪。
據采訪者們回憶,他們對這位抗日名將都有久仰之心,覺得采訪是一件樂事。白崇禧和藹可親,常使訪問者如沐春風。白崇禧本人對訪談也非常重視,稱之為“開會”。為了準確,他不但向相關人員相詢,要他們提供資料和意見,還自己動手尋找資料和準備訪談大綱。
1966年11月24日,白崇禧接受了第128次采訪,講述廣西和國民黨中央決裂的過程。還未談完,就于12月2日去世。
1984年,《白崇禧先生訪問記錄》在臺北出版。2013年,該書簡體版在北京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雖然采訪在蔣介石情治時代進行,受到諸多限制,但畢竟是白崇禧親口所述,因此成為研究白崇禧乃至民國史的重要文獻資料。
回到上海后,我細看白先勇的《白崇禧將軍身影集》的大陸版,意外發現,白崇禧在臺灣時,原來一直住在臺北松江路127號!去年和今年,我兩度去臺北從事研究,前后在松江路63號的長榮桂冠酒店(臺北店)住了近一個月呢。
從老照片上看,白崇禧的住處是一個有著籬笆墻的平房花園。這讓我很是吃驚。花園就在我所住酒店的馬路同側,我無數次走過松江路,必然路過此地,為什么從沒注意到?
我馬上請臺灣朋友代我去探訪松江路127號。現場拍來的照片顯示,松江路127號已經翻建為大樓,現為味全公司和Toyota汽車展示場。我這才釋然。
我在上海和白公館比鄰,沒想到,到了臺北,還是和白公館比鄰,甚至比上海還近了好幾個街區!
(作者系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