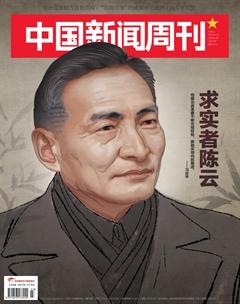不囿專業的梁啟超
徐賁
近讀丁曉原的《媒體生態與現代散文》,書里說到梁啟超的“非學術”寫作對開拓清末民初公共空間的篳路藍縷之功。今天,許多人把“學術”視為傳世的功業,而“非學術”則成為一個鄙夷非議之詞。但是,在啟蒙的“覺世”與學術的“傳世”之間,梁啟超選擇的是前者。他是一個真正的公知,不僅通過大眾媒體來把公眾作為自己的聽眾,而且,他自己就是一個積極營造媒體的人。正是通過他自己創辦的許多報刊,他成為那個時代公共言論界的驕子。梁啟超以言論起家,一生中所創辦并親自主持的報刊有十多種。以《中外公報》《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報》《政論》《國風報》《庸言報》《大中華》等九種最為出色,影響也最為深遠。
這些刊物與今天許多消遣性的刊物不同,都是以注重于迫切而嚴肅的公共問題討論而著稱。例如,《中外公報》與《時務報》創辦于甲午戰爭后不久,當時國人創巨痛深,力謀報仇雪恥,這兩個報紙應時而生,檢討敗挫的由來和積弱不振的原因,進而要求授權國民,讓全國人民共同負起國家興亡之責,開了清末鼓吹民權的先河。
鼓吹民權和鑄造新民是梁啟超公共言論的兩大目標。他為這兩個大目標不懈地進行民眾啟蒙,涵蓋了廣泛、多樣的話題,采取了多種多樣的言論與話語策略。所有這些,以今天學院專業知識的狹隘標準來看都是不專業,甚至很不專業的。但是,這一點也不能動搖梁啟超作為近代中國民眾啟蒙先驅的地位,更不要說是他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所發揮的作用了。
一個知識分子言論如果可以稱得上是“公共”,那么,他所懷抱的社會、政治目標必然是在狹隘專業之外的。梁啟超那個時代還沒有我們今天學院式的專業和非專業的劃分。在他所接受的儒家教育中,學問并不是它自身的目的,重點不在學問本身,而在其道德目標(“志于道”)和在追求這一目標中實現的人格境界(“養性”)。如果說道德內容必須支配學問內容是儒家思想的特征,那么,這種道德在公知梁啟超那里則被明確為一種現代意義的“公德”,而不只是儒家傳統的“私德”。無論是鼓吹民權還是鑄造新民,都離不開這個公德,一直到今天,與“新公德”緊密聯系的倡導民主和國民啟蒙仍然是公知的主要社會責任。
作為一名公知,梁啟超辦的不是像我們今天“學報”或“學刊”一類的出版物,而是有公共言說目標和作用的報刊。他在《論報館有益于國事》中這樣述及其目標:“觀國之強弱,則于其通塞而已。血脈不通則病,學術不通則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視肥瘠漠不相關;言語不通,故閩粵之與中原邈若異域。惟國亦然,上下不通,故無宣德達情之效,而無舞文之吏,因緣為奸;內外不通,故無知己知彼之能,而守舊之儒乃鼓其舌,中國受侮數十年 坐此焉爾。”
他宣稱《清議報》 的多種公共目的(倡民權、衍哲理、明朝局、厲國恥)中,尤以倡民權為最要,“始終抱定此義,為獨一無二之宗旨,雖說種種方法,開種種門徑,百變不離其宗。海可枯,石可爛,此義不普及于我國,吾黨弗措也。”清亡之后,他又說:“在橫濱開一清議報,明目張膽,以攻擊政府,彼時最烈矣。”
他在《新民叢刊》的發刊告白中說,“本報取大學新民之意,以為欲新我國,當先維新我民。”他把重點從政論的國民政治啟蒙轉向更深層的國民文化教育和觀念啟蒙,他名聞遐邇的《新民說》論及的議題,即使在今天看來,仍然是一個思路周密的公民教育課程,其中論進取和競爭、論權利思想、論自治、論進步、論愛國、論自尊、論合群、論生利分利,比今天報刊上許多單單以時論為主的公知批評議論要眼光遠大得多。然而,啟蒙的面越廣、點越多,也就越顯得“不專業”,但梁啟超并不在乎這個。
所為“專業”,乃是一種最狹隘意義上的知識,一種以其自身為目的,也就是完全無目的的知識。這顯然不是梁啟超所追求的那種知識,甚至也不是傳統儒學提倡的那種知識。儒家也講究“經世致用”呢。
在梁啟超那里,我們看到的是一種“點”很多,“面”也鋪得很開的知識,那未必非常精深的知識,但卻始終是致力于“經世致用”的知識。正如他在給女兒的信里所說,他一輩子對知識充滿好奇,不斷由于實際的需要而轉換知識領域,無暇專精。專家們可以批評他的不專精,他們所不知的是,他本來就對他們那種瑣碎而無關緊要的學問不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