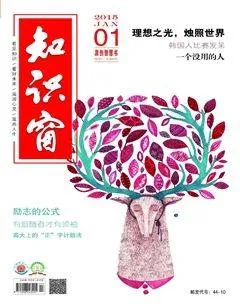撐胖一個書名號
肖爻悄悄
我是在大學附近超市兼職的時候認識胖子的。
胖子是超市的全職員工,寸頭、肥胖,年紀不過二十歲。據(jù)我觀察,胖子的體重怎么著都有150斤;而身高,如果拿搟面杖將整個人朝頭腳兩端碾到頭也就1.6米。他是大舌頭,音色雄渾,讓人覺得他嘴里老是含著一塊糖,又或是藏著一個話筒。每當胖子說話的時候,聲音隨著兩頰上下滾動的肉,顫抖而有力地摔進空氣,能把既膽小又愛發(fā)呆的人嚇懵。嘴角兩側(cè)永不干涸的兩灘口水,成了胖子臉上不可忽略的小小積水潭。
“大姐,來貨了!”胖子的聲音能震下貨架上的兩袋方便面。
言畢,他扭過頭,又沖我笑瞇瞇地喊道:“小妹,你收銀!我搬貨!”
胖子招呼我們做事的時候,從不用“說”,都是帶“吼”的,跟他的身材一樣很有重量感。不過,胖子干起活來卻手腳麻利、身輕如燕,絲毫不留拖泥帶水之痕,絕對不見笨手笨腳之跡。在同等時間內(nèi),需要三個送貨員搬運的貨物,他一個人就能搞定。
“真看不出來,長得像頭大笨熊,卻勤勞得像只小蜜蜂。”唐姐本是一位發(fā)福的中年婦女,但只要和胖子的身體和名字站在一起,就覺得自己正以跌落懸崖般的速度,在拼命掉體重。
盡管如此,胖子卻全然不理會唐姐的戲謔和調(diào)侃,總是干完活就躲在一角,低頭擺弄手機,寡言沉默得仿佛判了自己說話的死刑。
雖說是兼職,但我每天至少有六個小時,和曾姐、唐姐,或者胖子待在一起。事實上,只要條件滿足兩人以上,且每天不間斷地待在同一個屋子里,就會構(gòu)成一個人際圈,就得面臨不得不處理的人際關系。不管這個圈多么迷你,不論這些人多么煩你。
我本也是舌顫蓮花隨意聊、天南海北胡亂侃的饒舌,和曾姐、唐姐處得像被置于微波爐里的一盤菜,熱度居高不下,每天娛樂樂翻天。但只要和胖子搭班,我的情緒和干勁就會慘遭滑鐵盧。干完活的胖子豈止是一根木頭,簡直就是一塊活生生的凍肉。縱觀胖子全身上下,唯一在動的就只有眼珠和手指了。胖子總是倚靠在顧客看不見的盲區(qū),一頭扎進手機里茫茫的資訊汪洋中,一連游上幾個小時也不愿上岸。
我受不了胖子周身散發(fā)出的高冷氣質(zhì),終于在某次上完貨物后,湊到胖子眼前,快速掃描了一遍將他捆綁至不能動彈的手機。
“你到底在看什么啊?玩Dota?看球賽?”當我瞟到屏幕上正在輸出的密密麻麻的字,我若有所悟般地點頭八卦道,“哎喲,不好意思,你繼續(xù)編織你的愛之密網(wǎng)。”
胖子立馬臉紅了,支支吾吾地說:“不是……沒有……也有……但不是我個人的……我是在用手機寫小說。”
“真沒想到,你彪悍的外表下還隱藏著一個詩意浪漫的靈魂!”我睜大了眼睛,“都發(fā)表在哪兒?我想去看看。”
“它們都還是面團和作料,面包還未新鮮出爐。” 胖子羞赧地笑笑,“不過,我會堅持下去的。”
從那以后,我不再花大把時間和曾姐、唐姐湊在一起磨碎嘴皮子。胖子的專注像是一記耳光打在了我的臉上,喚醒了我對時間不痛不癢、渾渾噩噩的隨性態(tài)度;胖子的執(zhí)著像是一根鞭子抽在了我的身上,抽中了我滿嘴跑火車、不做實事的務虛嘴臉。
事實上,我曾多次打開WPS,試著將那雪白的頁面填滿。但我漸漸發(fā)現(xiàn),我的注意力不能集中超過三十分鐘,寫起文章來磕磕絆絆、氣喘吁吁,像個不善長跑的胖子。網(wǎng)上、身邊的資訊和八卦就像一片片炫邁口香糖,嚼過就根本停不下來。那些我花費在發(fā)微博、聊微信和逛淘寶上的時間,我自以為極其碎片和微量,但殊不知長此以往,它們已經(jīng)長驅(qū)直入、潛移默化地占領了我的注意力,剝削了我的專注度。而胖子,就是我在不加節(jié)制的信息高速公路上橫沖直撞時,那盞大大點亮的醒目紅燈,那個高高舉起的“STOP”標示牌。
我開始加入胖子的隊伍,關掉Wi-Fi,打開WPS,只關注關心手中的文字,仿佛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只留心留意手里的念珠一樣。胖子常常告訴我,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堅持,唯一的目標就是撐胖一個書名號。盡管直到現(xiàn)在,他也從未發(fā)表過一篇文章。
在我兼職快要結(jié)束的那個冬天,胖子滿臉紅光,手里拿著一本雜志,腳步輕快地邁向了我:“面包新鮮出爐了,還熱氣騰騰的呢。”
不用說我也知道,胖子將先前瘦瘦的書名號撐胖了。
我看著胖子興奮的臉和他嘴角極具代表性的兩個小小水潭,覺得他像極了一名船長,即使船身陳舊、桅桿折斷、帆布破爛,還是竭盡全力前往夢想的彼岸。我仿佛聽見了孤獨出發(fā)的馬達聲,和屬于那個人收獲的勝利號角。
而我自己,也即將揚帆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