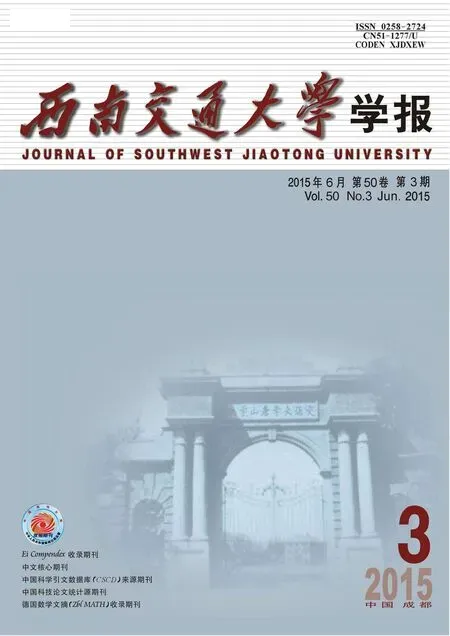蘆山地震觸發(fā)崩塌滑坡的優(yōu)勢方向與機理
段書蘇, 姚令侃,2,3, 郭沉穩(wěn)
(1.西南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院,四川成都 610031;2.抗震工程技術四川省重點實驗室道路與鐵道工程抗震技術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31;3.高速鐵路線路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四川成都 610031)
2008年發(fā)生在龍門山地區(qū)的“5·12”汶川地震是有現(xiàn)代觀測儀器以來世界上地震觸發(fā)崩塌滑坡災害最嚴重的一次大地震.2013年4月20日08:02(北京時間),龍門山地區(qū)的雅安市蘆山縣又發(fā)生了Ms7.0級強震,是本世紀以來我國地震觸發(fā)山地災害嚴重性僅次于汶川地震的事件.
統(tǒng)計滑坡頂點至山脊距離占坡體總長0.4倍以內的滑坡數(shù)占滑坡總數(shù)的百分比,汶川地震為65%,蘆山地震為44%.這些坡位較高的滑坡,由于在啟動階段獲得地震動賦予的初始速度,導致運移距離較遠.所以,評估地震觸發(fā)崩塌滑坡危害范圍時,除運移距離外,運動方向也是重要參數(shù).
汶川地震前,李忠生根據(jù)對已有滑坡調查資料的統(tǒng)計,認為地震誘發(fā)的滑坡方向與地震波傳播方向之間無明顯聯(lián)系[1];Kamp等對2005年巴基斯坦Kashmir地震誘發(fā)滑坡的研究發(fā)現(xiàn),70%的滑坡發(fā)生在朝南的斜坡上,認為這與南向坡降雨量大、風化嚴重有關,而沒有從地震波傳播理論上進行解釋[2].汶川地震后,黃潤秋等認為在強震作用下,地形條件對滑坡的滑動方向不再起絕對的控制作用,起控制作用的是斷層的強大慣性運動,而不是重力和地震波[3];許沖等通過繪制滑坡面積和數(shù)量的坡向分布直方圖、計算滑坡的點密度和面密度、對坡向進行確定性分析,認為地震誘發(fā)滑坡或是受地殼主應力方向、上盤逆沖方向或地震波傳播方向的影響[4-6];許強等統(tǒng)計了不同坡向上滑坡災害的發(fā)育密度和大型滑坡坡向與發(fā)震斷層之間的關系,認為汶川地震誘發(fā)滑坡具有“背坡面效應”和“斷層錯動方向效應”[7].上述文獻在表述上不同,但汶川地震誘發(fā)的崩塌滑坡方向受發(fā)震斷層運動慣性力控制這一觀點是共識.
蘆山地震的能量只相當于汶川地震的1/32,且為典型的盲斷層型地震[8],斷層運動慣性力不明顯,汶川地震中滑坡發(fā)生優(yōu)勢方向的認知不能直接用于推斷蘆山地震滑坡的易發(fā)坡向.因此,影響蘆山地震觸發(fā)崩塌滑坡優(yōu)勢方向的因素及其控制機理,已成為新的科學問題.
1 蘆山地震觸發(fā)崩塌滑坡概況
蘆山震區(qū)基本屬于青衣江流域,青衣江主源為寶興河,在飛仙關處與天全河等河流交匯后,于樂山草鞋渡處匯入大渡河.流域地形大致以雙石-大川斷裂為界,分為東西兩大類.東面(下盤)屬低山丘陵區(qū),地勢平緩,海拔約600~1 100 m,河谷呈“U”型,有寬闊的漫灘和階地,河道比降約1.8‰.西面(上盤)由寶興河流域和天全河流域組成,多為高山峽谷,海拔一般在1 000 m以上,河谷多呈“V”型,河道比降大于8‰,見圖1(地震烈度劃分根據(jù)中國地震局網站 http://www.cea.gov.cn提供的圖片矢量化得到).

圖1 蘆山震區(qū)地形及災害點分布Fig.1 Topography and landslide distribution of Lushan earthquake area
使用的震區(qū)航空、航天遙感影像資料:(1)中國科學院遙感與數(shù)字地球研究所提供的3批航空遙感數(shù)據(jù),覆蓋蘆山、寶興、邛崍等縣市約5 000 km2.第1批航片獲取時間為2013年4月20日10:30—12:40,分辨率0.6 m;第2批航片獲取時間為4月20日15:00—17:00,有0.4和2 m兩種分辨率;第3批航片獲取時間為4月21日上午,有0.4和2 m兩種分辨率;(2)四川省測繪地理信息局蘆山地震信息發(fā)布平臺公布的蘆山震中區(qū)的航片影像資料(影像獲取截止時間為4月25日,分辨率0.5 m);(3)國家測繪局公布的龍門鄉(xiāng)、太平鎮(zhèn)、寶盛鄉(xiāng)三地的航片影像資料(影像獲取時間為4月20日18:28,分辨率0.16 m);(4)資源三號衛(wèi)星影像數(shù)據(jù),衛(wèi)星影像區(qū)域面積2 657 km2,包括天全縣、雨城區(qū)、滎經縣的大部分區(qū)域,影像獲取時間為5月13日,分辨率2.1 m.對以上遙感影像資料進行幾何糾正、融合、拼接、圖像增強等數(shù)據(jù)處理,獲得了蘆山震區(qū)遙感數(shù)據(jù) 5 655 km2(102.461 3°E~103.514 0°E,29.742 0°N ~ 30.448 5°N),具體范圍見圖1.
由于震區(qū)植被發(fā)育較好,多為常年生灌木,地震后崩塌滑坡造成地表破壞,且由于遙感影像是從上方垂直拍攝的,故比現(xiàn)場拍攝的照片更容易判識崩塌滑坡的方向.對坡度在20°以下的解譯點,由于存在較多農田、裸地、取土場、砂石料堆放場等,必須經過實地考察刪除這些誤判點.如圖2所示寶盛鄉(xiāng)變電站上方的一處取土場,若僅根據(jù)航片上識別,極易造成誤判.結合野外300余處災害點的實地考察,最后解譯出崩塌滑坡1 754處(圖1).

圖2 誤判點:寶盛鄉(xiāng)變電站上方的取土場(103.039 7°E,30.311 4°N)Fig.2 A miscarriage of justice:a quarry above the electricity substation in Baosheng County(103.039 7°E,30.311 4°N)
2 自然坡向對崩塌滑坡方向的影響
龍門山主要由北東走向(約北東50°)的山脈組成,宏觀上看以分水嶺為界,存在著東南、西北兩組優(yōu)勢坡向.進一步將蘆山震區(qū)內所有坡體的坡向按10°分組繪制玫瑰圖(圖3),優(yōu)勢坡向為東南(30°~45°)、北西(45°~80°).可見,蘆山震區(qū)自然坡體的優(yōu)勢坡向與龍門山脈的宏觀地貌格局相符.

圖3 震區(qū)內自然坡體坡向分布Fig.3 Distribution of natural slope aspects in the seismic area
位于斜坡上的物質,其重力沿坡面向下的分力是造成斜坡上物質不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因此理論上震區(qū)自然坡體的兩組優(yōu)勢坡向對滑坡運動的優(yōu)勢方向都有控制作用.將蘆山地震觸發(fā)的崩塌滑坡的運動方向按10°進行分組,繪制崩塌滑坡數(shù)分布的玫瑰圖(圖4).可見,崩塌滑坡的優(yōu)勢方向明顯集中在東南方向,即與自然坡體優(yōu)勢坡向中的東南方向吻合;而另一優(yōu)勢方向——西北方向,并未呈現(xiàn)出崩塌滑坡運動方向集中的現(xiàn)象.顯然,這與理論推斷不完全一致.

圖4 不同滑動方向滑坡數(shù)量統(tǒng)計結果Fig.4 Statistical result of landslide number in different slip directions
我們認為,這與龍門山推覆構造形成的不對稱地形有關.龍門山由一系列大致平行的疊瓦狀沖斷帶構成,具有典型的推覆構造的地貌特征,體現(xiàn)為山地走向為北東方向,但東南坡與西北坡并不對稱.如東南方向的平均坡度為24°,而西北方向的平均坡度僅為22°,即東南坡陡于西北坡,導致地震觸發(fā)崩塌滑坡更集中地發(fā)生在東南坡上.一般情況下,自然坡體的兩組優(yōu)勢坡向都可能是滑坡運動的優(yōu)勢方向,但在具體地域,必須考慮不對稱地形造成的山地災害分布的坡向分異現(xiàn)象.
3 新構造應力場和地震加速度對崩塌滑坡方向的影響
3.1 廬山震區(qū)的新構造應力場
20世紀70年代末,瑞士學者Scheidegger提出了地表發(fā)育形態(tài)的對抗性原理,從全球構造的觀點認識內營力作用,成為地球表面動力學的基本理論之一[9].對抗性原理指出,在新構造應力場作用下,巖體內部會形成一對共軛的剪裂面(X型破裂),在硬巖地區(qū)易于形成崩塌的有效結構面(圖5);在軟巖、土質地區(qū),由于地表徑流的作用,易于形成滑坡底部的軟弱結構面.在應力場主壓應力方向上,坡體長期處于擠壓狀態(tài),易發(fā)生崩塌、滑坡災害[10].已有實震資料表明,地震觸發(fā)的崩塌滑坡也有這樣的規(guī)律.如艾南山等通過對天水地震和通渭地震中形成的長度大于500 m的386次滑坡的分析發(fā)現(xiàn),滑動的優(yōu)勢方向與該區(qū)域新構造應力場的主壓應力方向一致[11].由此我們認為,在蘆山地震中,新構造應力場是影響崩塌滑坡方向的一個因素.

圖5 寶盛大橋處崩塌及節(jié)理對崩塌方向的影響(103.034°E,30.309°N)Fig.5 Effects of collapse at Baosheng bridge and joints on the collapse direction(103.034°E,30.309°N)
一般情況下,可以通過鉆孔資料或震源機制解推求構造應力場方向,但這顯然需要做大量工作.本文基于對抗性原理,采用一種簡單的推求新構造應力場方向的方法.根據(jù)對抗性原理,在新構造應力場作用下,沿共軛剪切方向,巖石容易因遭受破壞而形成斷裂帶,平行于活動斷裂方向上的巖石抗侵蝕能力減弱,這就為水系大致沿平行于活動斷裂走向的方向發(fā)展演化提供了有利條件,因此沿節(jié)理破裂發(fā)育的水系排列的優(yōu)勢方向可以反映新構造運動以來的應力分布狀態(tài).根據(jù)莫爾強度理論,共軛剪節(jié)理的銳角角平分線即為主壓應力方向.若將區(qū)域內的河流看作一組共軛剪節(jié)理,考慮巖石內摩擦力的影響,剪裂角一般在30°左右[12],則共軛剪節(jié)理的夾角至少應大于30°.
提取蘆山震區(qū)內的河網,將河流的自由端或交匯點作為結點,用直線連接結點,得到該水系的折線圖(圖6(a)).以折線線段的長度表示相應的權重,則每條線段就變成了一個包含方向和長度2個變量的統(tǒng)計單位.根據(jù)上述資料統(tǒng)計繪制水系方向玫瑰圖,見圖6(b).這里用極方向(pole direction)代替河谷走向(將河谷走向旋轉90°).圖6(b)中,線的間距為10°.用非參數(shù)統(tǒng)計方法,可從玫瑰圖中發(fā)現(xiàn)河谷的第一優(yōu)勢方向為90°;在第一優(yōu)勢方向兩側30°以外的區(qū)域尋找第二優(yōu)勢方向,為145°.將這2個方向視為在構造應力場作用下的一對共軛剪切方向,則該共軛剪切方向相交的銳角等分線代表主壓應力方向為東偏南23°(圖6(b)中的有向線段).

圖6 蘆山震區(qū)內的河網折線化、方向分布玫瑰圖及主應力方向Fig.6 Drainage linearization,rose diagram of water system distribution and direction of field stress in the Lushan seismic area
3.2 蘆山地震臺站最大累計加速度方向
地震荷載通過坡體波動震蕩產生的累進破壞和觸發(fā)效應致使邊坡失穩(wěn)[13].累進破壞效應是指在某一強度的外力或地震荷載作用下,作用一次巖土體并不破壞,但是這一強度的外力或地震力反復作用多次后引起巖土體破壞.觸發(fā)效應是指無論是經過反復震蕩的斜坡,還是天然斜坡處于或者接近極限平衡狀態(tài)時,坡體繼續(xù)受波動震蕩作用時,震動產生的慣性力會激發(fā)坡體下滑,發(fā)生崩塌滑坡.因此,地震加速度累計量最大的方向更容易發(fā)生崩塌滑坡.
已有研究證明,水平地震加速度對崩塌滑坡的發(fā)生起主導作用[14],故以水平方向的地震加速度作為研究對象.在加速度記錄過程中,正號分別代表北、東方向,負號分別代表南、西方向,將地震動記錄中每個時間點的南北方向和東西方向的加速度矢量疊加,然后遍歷整個地震動過程,將方位角相同的加速度大小累加,累加得到的最大值對應的方位角即為某臺站最大累計加速度的方向.最大累計加速度綜合了臺站記錄振幅、持時、方向等信息,比受干擾因素影響多的峰值加速度更能準確反映真正的地震動水平,比一些表征能量的參數(shù)(如Arias強度)增加了方向屬性,與崩塌滑坡方向的關系更為密切.
考慮地震波傳播的地形效應,將研究區(qū)劃分為下盤、寶興河流域和天全河流域3個分區(qū),見圖7.上述劃分是基于以下考慮:蘆山地震發(fā)震構造下盤區(qū)域地形簡單,主要由平原、丘陵和中低山組成,地形效應對地震波傳播的影響較小,故將下盤作為一個單元處理;蘆山地震發(fā)震構造上盤區(qū)域由中高山組成,主要由寶興河流域和天全河流域構成,兩流域地形地貌差異明顯,因此,對上盤采用按流域分區(qū)的原則.

圖7 地震臺站分布、臺站最大累計加速度方向及分區(qū)結果Fig.7 Seismic stations'distribution,their maximum cumulative acceleration directions and partition results
根據(jù)已有研究,地震臺站周圍20 km范圍內的地震動可由臺站記錄代表[15],據(jù)此從圖7可見,位于下盤的臺站基本隨斷層展布均勻分布,可將下盤內災害點覆蓋在影響范圍內;位于上盤的臺站分布在寶興河流域內,影響范圍也僅限于寶興河流域.
根據(jù)以上分析可知,下盤區(qū)域內有4個加速度臺站,從左下到右上的最大累計加速方向依次為南東—北北西、南東—北西、南東南—北北西、南—北.左下方3個臺站的最大累計加速度方向大體一致,與斷裂方向垂直,最上面1個臺站的最大累計加速度方向與斷裂方向的夾角較大.寶興河流域內的臺站集中在左上角,臺站最大累計加速度方向分別為南—北、南西西—北東東、北北東—南南西,大體與斷裂方向平行或有較小夾角.天全河流域內沒有加速度臺站.
3.3 基于確定性系數(shù)分析的崩塌滑坡方向影響因素
滑坡的確定性系數(shù)分析方法是根據(jù)概率函數(shù)計算確定性系數(shù)CF,用CF表征影響滑坡發(fā)生各因素的敏感性.它最早由E H Shortliff和B G Buchanan提出[16],D Heckerman 進行了改進[17]:

式中:ξa為單元a中滑坡面積的百分比;ξs為整個研究區(qū)滑坡面積的百分比.
CF表征各坡向組對崩塌滑坡發(fā)生的影響程度.CF的變化區(qū)間是[-1,1],CF>0且 CF越大,表示崩塌滑坡發(fā)生的可能性越高;CF=0表示崩塌滑坡發(fā)生與不發(fā)生的概率接近;CF<0表示崩塌滑坡發(fā)生的可能性較低.
在每個分區(qū)內,將崩塌滑坡方向和研究區(qū)域坡向均按10°分組,根據(jù)式(1)計算每組的CF值,定量確定各方向的滑坡敏感性,CF值較大的方向即為敏感方向.將每個分區(qū)內各方向的CF值與新構造應力場的主應力方向、最大累計加速度方向疊加,見圖8.
從圖8可知,下盤崩塌滑坡的敏感方向非常集中,基本上在東—南區(qū)間內;區(qū)域內均勻分布的4個臺站的累計加速度優(yōu)勢方向完全控制了崩塌滑坡的敏感方向,新構造應力場主應力方向代表了其中一個崩塌滑坡的敏感方向.

圖8 各區(qū)域內崩塌滑坡方向敏感性分析Fig.8 Sensitivity analyses of landslide direction in each region
在寶興河流域,崩塌滑坡的敏感方向集中在東北、西南、東、西北西方向;臺站最大累積加速度方向和主應力方向共同控制所有崩塌滑坡的敏感方向,具體為①—①'、②—②'、③—③'和④—④',敏感方向與影響因素的方向差在10°以內(關于方向④—④',新構造應力場與板塊運動相關,斷層兩側可能出現(xiàn)方向正好相反的情況,但只要在一條直線上,就認為方向一致).在天全河流域,東北、東南、南、西等方向都是高敏感方向;新構造應力場方向控制了南東東這一敏感方向.從以上分析可知,新構造應力場方向在各區(qū)域內代表了崩塌滑坡的一個敏感方向;在寶興河流域和下盤區(qū)域內,最大累計加速度方向反映了除構造應力場以外的敏感方向.
4 結束語
(1)蘆山地震屬于典型的盲逆斷層型地震,斷層運動慣性力對崩塌滑坡的控制作用不明顯.自然坡體的優(yōu)勢坡向是預測滑坡運動優(yōu)勢方向的基本依據(jù),但具體應用時需考慮山地災害的坡向分異等因素(如在具有推覆構造地貌特征的蘆山震區(qū),地震觸發(fā)的崩塌滑坡多發(fā)生在坡度較陡的東南坡).新構造應力場也是崩塌滑坡方向具全局性的影響因素.此外,各區(qū)域最大累計加速度方向也反映了當?shù)乇浪碌拿舾蟹较?
(2)關于新構造應力場方向,可以基于對抗性原理利用當?shù)厮但@得,并建議與中國大陸現(xiàn)今地殼運動GPS速度場的最新觀測結果進行校核.如本文計算的雅安地區(qū)新構造應力場主應力方向為113°,GPS速度場的觀測結果約122°,二者僅相差9°,可以認為計算的青衣江流域的新構造應力場主應力方向得到了檢驗.關于研究區(qū)最大累計加速度的方向,可以根據(jù)當?shù)氐摹秷龅氐卣鸢踩栽u價報告》中對應于3種不同隨機相角的3條加速度時程曲線,將其兩兩組合,分別將其設定為沿東西、南北方向傳播,按照矢量疊加原理得到累計加速度方向分布玫瑰圖,取累計加速度最大的方向作為當?shù)刈畲罄塾嫾铀俣确较?
(3)地震觸發(fā)的崩塌滑坡優(yōu)勢方向的預測是其危害范圍評估的重要內容,可為制定減災對策提供科學依據(jù).以高烈度地震山區(qū)選線設計為例,若線路位于地震觸發(fā)的崩塌滑坡危害范圍內,且崩塌滑坡運動方向與線路大角度相交時,是最不利的情況,可考慮線路外移等平面繞避措施,或修建棚洞、明洞等遮擋構筑物防護;當崩塌滑坡運動方向與線路小角度相交或者平行時,線路可能只處于危害區(qū)邊緣部位,可考慮在線路上方設置攔截構筑物.
致謝:中國地震局工程力學研究所、國家強震動臺網中心為本研究提供了強震動數(shù)據(jù),中國科學院遙感與數(shù)字地球研究所提供了的3批覆蓋蘆山、寶興、邛崍等縣市約5 000 km2航空遙感數(shù)據(jù),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1]李忠生.國內外地震滑坡災害研究綜述[J].災害學,2003,18(4):64-70.
LI Zhongsheng.The state of the art of the research on seismic landslide hazard at home and abroad[J].Journal of Catastrophology,2003,18(4):64-70.
[2]KAMP U,GROWLEY B J,KHATTAK G A,et al.GIS-based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mapping for the 2005 Kashmir earthquake region[J].Geomorphology,2008,101(4):631-642.
[3]黃潤秋,唐川,李勇,等.汶川地震地質災害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268-278.
[4]許沖,戴福初,姚鑫,等.基于GIS的汶川地震滑坡災害影響因子確定性系數(shù)分析[J].巖石力學與工程學報,2010,29(增刊 1):2972-2981.
XU Chong,DAI Fuchu,YAO Xin,et al.GIS based certainty factor analysis of landslide triggering factors in Wenchuan earthquake[J].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10,29(Sup.1):2972-2981.
[5]許沖,徐錫偉,吳熙彥,等.2008年汶川地震滑坡詳細編目及其空間分布規(guī)律分析[J].工程地質學報,2013,21(1):25-44.
XU Chong,XU Xiwei,WU Xiyan,et al.Detailed catalog of landslides triggered by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and statisticalanalysesoftheirspatial distribution[J].Journal of Engineering Geology,2013,21(1):25-44.
[6]許沖,戴福初,肖建章.“5·12”汶川地震誘發(fā)滑坡特征參數(shù)統(tǒng)計分析[J].自然災害學報,2011,20(4):147-153.
XU Chong,DAI Fuchu,XIAO Jianzhang.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landslides triggered by the May 12,2008 Wenchuan earthquake[J].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2011,20(4):147-153.
[7]許強,李為樂.汶川地震誘發(fā)滑坡方向效應研究[J].四川大學學報:工程科學版,2010,24(增刊1):7-14.
XU Qiang,LI Weile.Study on the direction effects of landslides triggered by Wenchuan earthquake[J].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Engineering Science Edition,2010,24(Sup.1):7-14.
[8]XU Xiwei,WEN Xuze,HAN Zhujun,et al.Lushan Ms7.0 earthquake:a blind reserve-fault event[J].Chinese Science Bulletin,2013,58(28/29):3437-3443.
[9]SCHEIDEGGER A E.The principle of antagonism in the earth's evolution[J]. Tectonophysics, 1979,55(3/4):7-10.
[10]艾南山,唐少卿.地表形態(tài)發(fā)育的對抗性原理[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2):122-130.
AINanshan,TANG Shaoqing.The principle of antagonism in the surface morphology development[J].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1983(2):122-130.
[11]SCHEIDEGGER A E,AI Nansha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otectonic stress field and catastrophic landslides[C]∥27th 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Moscow: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1984:180-189.
[12]何銘勛.構造地質學中的赤平極射投影[M].北京:地質出版社,1979:130-131.
[13]毛彥龍,胡廣韜,趙法鎖,等.地震動觸發(fā)滑坡體滑動的機理[J].西安工程學院學報,1998,20(4):47-50,54.
MAO Yanlong,HU Guangtao,ZHAO Fasuo,et al.Mechanics of the landslide sliding caused by seismic[J].Journal of Xi'an Engineering University,1998,20(4):45-48,54.
[14]王秀英,聶高眾,王登偉.利用強震記錄分析汶川地震誘發(fā)滑坡[J].巖石力學與工程學報,2009,28(11):2369-2376.
WANG Xiuying,NIE Gaozhong,WANG Dengwei.Analysis of landslides induced by Wenchuan earthquake by ground motion records[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09,28(11):2369-2376.
[15]王秀英,聶高眾,張玲.汶川地震觸發(fā)崩滑與Arias強度關系研究[J].應用基礎與工程科學學報,2010,18(4):645-656.
WANG Xiuying, NIE Gaozhong, ZHANG Ling.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lides induced by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and Arias intensity[J].Journal of Bas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10,18(4):645-656.
[16]SHORTLIFFE E H,BUCHANAN B G.A model of inexactreasoning in medicine[J]. Mathematical Biosciences,1975,23(3/4):351-379.
[17]HECKERMAN D. Probabilistic interpretation for MYCIN's certainty facters[C]∥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Conference on Uncertainty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Los Angeles: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1985:167-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