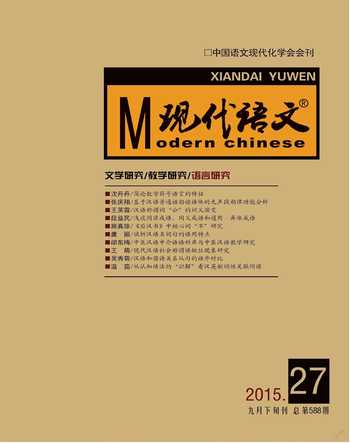漢語數量名結構語序類型研究

摘 要:名詞性短語的語序類型是語序類型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作為參項之一的數詞與名詞的語序關系似乎很明晰,但在漢語中的情況卻因量詞參項的介入而變得復雜。文章對漢語數量名結構的語序類型進行了共時描寫,并從歷時角度對漢語數量名結構的各種語序類型進行定量分析,討論了各語序類型的關系,并構擬了漢語數量名結構的演變軌跡。
關鍵詞:數量名結構 語序 類型學
一、漢語數量名結構的語序類型
在現代漢語中,名詞的數量表達式通常由數量短語和名詞組成,以“數詞+量詞+名詞”為語序類型為主,如“一匹馬”“三只熊”等,另外還有“名詞+數量+題詞”格式,如“牛肉二斤”“家書一封”等。在古代漢語中,由于量詞不夠發達,數詞可直接修飾名詞,組成“數詞+名詞”和“名詞+數詞”格式,如“忽有一狐,……”和“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等。因此,漢語數量名結構共有四種語序類型,即“數詞+量詞+名詞”“名詞+數詞+量詞”“數詞+名詞”和“名詞+數詞”。這四種語序類型在共時和歷時層面分別是什么關系,這些問題將在下文詳細討論。
二、各種語序類型的關系
(一)研究現狀概述
漢語史上共出現了“數詞+名詞”“名詞+數詞”“數詞+量詞+名詞”和“名詞+數詞+量詞”四種名詞的表達式,它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在這四種語序的起源和發展層次的問題上,學界觀點一致,即按照“名詞+數詞”“名詞+數詞+量詞”“數詞+名詞”和“數詞+量詞+名詞”的順序先后出現在漢語中,但是關于“數詞+量詞+名詞”格式的成因,學界觀點不一,主要有“移位法”和“替換法”兩種觀點。
支持“移位法”的學者如王力[1]、黃盛章[2]、高名凱[3]劉世儒[4]等,認為“數詞+量詞+名詞”格式中的數量短語是從名詞后面移到名詞前的,王力指出上古漢語中,數詞兼有度量衡量詞和天然單位詞的性質,其位置在名詞之后。吳福祥[5]、張赪[6]等支持“替代法”的學者則認為“數詞+量詞+名詞”格式不是由數量短語移位產生的,而是通過“替換”的方法產生的。他們認為“數詞+量詞+名詞”與“數詞+量詞+之+名詞”有關,由于“之”脫落而產生的“數詞+量詞+名詞”格式。“數詞+量詞+名詞”與“名詞+數詞+量詞”的句法和語用功能均不相同,前者是修飾性的,而后者是計量的,二者完全沒有關系。
(二)關于各語序類型的數據分析
本文參閱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選取了一些經典文獻,對其中的數量名結構進行窮盡式統計,希望從數據上考察數量名結構各語序類型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關系,具體數據見下表:
通過對上表數據的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1.“數詞+量詞+名詞”格式在文獻中所占比例與“數詞+名詞”格式成反比
“數詞+量詞+名詞”在漢語歷史上經歷了由無到有,由少到多的歷時發展過程。在商周時期,找不到一例“數詞+量詞+名詞”,到春秋時期開始出現,在《呂氏春秋》中共有3例,而到了現代,“數詞+量詞+名詞”格式成為了絕對優勢語序,在《圍城》中占94.6%。“數詞+名詞”是春秋時期的優勢語序,占數量名結構的86.4%,春秋時期之后,“數詞+名詞”的使用頻率逐漸降低,而在現代文獻中幾乎找不到它的身影,在《圍城》中只占3.4%。
2.漢代以后,“名詞+數詞”格式幾近消亡
在商周金銘文中,“名詞+數詞”格式是數量名結構的主要語序類型,所占比重為39.7%,僅次于“名詞+數詞+量詞”格式。而到了春秋時代急劇下降至3.4%,《呂氏春秋》中只有2例,漢代以后“名+數”格式并沒有得到發展,而是逐漸從漢語的歷史中消失。在漢代以后的文獻中,僅找到3例,明清時代開始就找不到“名詞+數詞”的影子。
3.自春秋時代起,“名詞+數詞+量詞”在各歷史時期文獻中所占比重較穩定
“名詞+數詞+量詞”是數量名結構中最早產生的格式,甲骨文金文時期就有記錄[7],同時也是最穩定的格式。縱觀表1數據,“名詞+數詞+量詞”在各歷史時期文獻中所占比重呈現出如下特點:在商周時期是數量名結構的優勢語序類型,占總量的一半,從春秋時期開始“名詞+數詞+量詞”的比重大幅下降,但始終保持在2%以上,不超過8.8%,是四種格式中最穩定的。
(三)數量名結構各語序類型之間的關系
1.“數詞+量詞+名詞”與“數詞+量詞”的競爭關系
在語言系統中,語序是比較穩定的參項,為了實現語言的交際作用,語序不會輕易變化。而且,即使在特定因素的促進作用下語序發生改變,這種變化通常也要經歷較長的時期,不會在短期內完成。在變化期,新語序與舊語序共存,互相競爭,最終新語序戰勝舊語序,成為優勢語序,而舊語序則逐漸消亡[8]。
從數據上看,“數詞+名詞”與“數詞+名詞+量詞”所占比例成反比。春秋時期,“數詞+名詞”是優勢語序,在數量名結構各種語序類型中占有重要比例,而“數詞+量詞+名詞”是新語序,所占比例很小。隨著漢語個體量詞的發展,“數詞+量詞+名詞”所占比例逐漸增加,到宋元時期,“數詞+量詞+名詞”取代“數詞+題詞”成為優勢語序。
2.“數詞+量詞+名詞”與“名詞+數詞+量詞”的互補關系
一般來講,語言經濟原則要求一種格式表達一種語義關系,如果多種格式表達同一種語義關系,那么各種格式是競爭關系。然而,“數詞+量詞+名詞”與“名詞+數詞+量詞”卻能在漢語中共存千余年,這不符合語言競爭規則,只能說明它們并不是競爭關系。二者不發生競爭關系的原因有二:其一,“數詞+量詞+名詞”與“名詞+數詞+量詞”的結構類型不同,“數詞+量詞+名詞”是偏正結構,而“名詞+數詞+量詞”屬于主謂結構[9]。其二,二者所表達的語義重心不同,“數詞+量詞+名詞”語義重心在名詞上,而“名詞+數詞+量詞”的語義重心在數量上,前者側重于表達有多少數量的事物,而后者則側重表達該事物的數量是多少。由于兩種格式的句法關系和語義重心均不同,它們形成互補關系,在漢語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因此才能在漢語中長期共存。
3.“名詞+數詞”發展為“名詞+數詞+量詞”
“名詞+數詞”和“名詞+數詞+量詞”的結構類型、語用功能都相同,不同之處是“名詞+數詞”以數詞單獨作謂語,而“名詞+數詞+量詞”則是以數量短語作謂語。在漢語的量詞還處于萌芽期的上古時期,量詞在數量名結構中屬于可選參項,可有可無。有的文獻中出現前面使用量詞的例文,后面出現時量詞又省略了,甚至還有同一名詞使用多個量詞的情況,例如“牛三千”“臣五人”“庶人五十夫”“人十又六人”等。因此,這一歷史時期的“名詞+數詞”和“名詞+數詞+量詞”是共存的。到了漢代,量詞逐漸成為數量名結構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名詞的數量表達式中必須要有量詞,因此“名詞+數詞”逐漸發展為“名詞+數詞+量詞”。
4.漢語數量名結構的演變軌跡
本文在對大量文獻進行統計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漢語數量名結構是沿著兩條軌跡發展演變的,數量名結構的演變與量詞的發展過程是同步的。第一條演變軌跡是“名詞+數詞”發展為“名詞+數詞+反響型量詞”,再發展為“名詞+數詞+量詞”。第二條演變軌跡是由“數詞+名詞”發展為“數詞+量詞+名詞”。兩條演變鏈不是按先后順序,而是并行發展,共同經歷了一千多年的發展演變歷程,最終形成現代漢語的以“數詞+量詞+名詞”為主,以“名詞+數詞+量詞”為輔的局面。
“名詞+數詞+量詞”之所以能夠成為商周時期的優勢語序,是由商周時期金文的歷史作用決定的。金鼎文是指刻在金鼎或鐘等金屬器物上的文字,用來頌揚王候的功德或記錄大事件等。戰爭獲勝后,王候贈予大臣的財物會鑄鼎記錄,而“名詞+數詞+量詞”格式主要用于記錄賜封的財物。到了春秋時期,“名詞+數詞+量詞”的語用功能受到限制,而“數詞+名詞”代替其成為優勢語序。因此,“名詞+數詞+量詞”和“數詞+名詞”屬于互補關系,兩條演變軌跡是共同發展的。
三、量詞的語法化與漢語數量名結構
數量名結構演變過程中的一系列重要變化,如“名詞+數詞”消失、“數詞+量詞+名詞”替代“數詞+名詞”等都是個體量詞語法化作用的結果。量詞語法化是從“名詞+數詞+量詞”開始,直到宋元時期“數詞+量詞+名詞”在主語位置出現時結束[10]。本文表1數據也支持該觀點,從數據上看,“數詞+量詞+名詞”在元代成為優勢語序類型。
從“名詞+數詞+反響型量詞”發展到“名詞+數詞+非反響型量詞”是量詞語法化歷程中一次質的飛躍。“名詞+數詞+反響型量詞”為量詞的語法化創造了句法空間,而“名詞+數詞+非反響型量詞”使量詞的句法地位和語用功能等得到鞏固和加強。量詞語法化的完成標志著量詞成為數量名結構的必要參項,也就是說數詞修飾名詞必須加入量詞。于是,“名詞+數詞”開始向“名詞+數詞+量詞”發展,而“數詞+名詞”逐漸發展為“數詞+量詞+名詞”。因此,漢語數量名結構的歷時演變過程與量詞的語法化過程息息相關,數量名結構的演變為量詞的語法化提供可能性,量詞語法化決定了數量名結構的演變和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1]王力.漢語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80.
[2]黃盛璋.兩漢時代的量詞[J].中國語文,1961,(8).
[3]高名凱.漢語語法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4]劉世儒.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1965.
[5]吳福祥,馮勝利.黃正德.漢語“數+量+名”格式的來源[J].
中國語文,2006,(5).
[6]張赪.漢語語序的歷史發展[M].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2010.
[7]裘錫圭.四十年來文字學研究的回顧[J].語文建設,1989,(3).
[8]施春宏.語言調節與語言變異[J].語文建設,1999,(4).
[9]蔣穎.漢藏語系語言名量詞比較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
[10]李訥,石毓智.中心動詞及其賓語之后謂詞性成分的變遷與量
詞語法化的動因[J].語言研究,1998,(1).
(黃平 吉林長春 吉林省經濟管理干部學院文化旅游學院 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