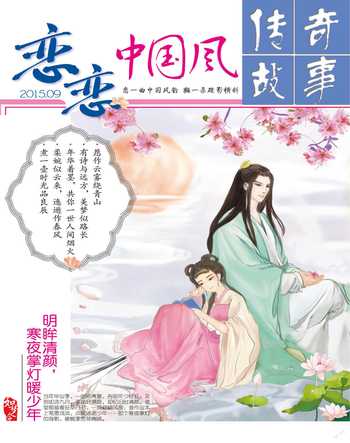當時筑音終漸離
婷婷花下人
他獨立深宮,著一襲白衣,只為此生最后一曲。指尖撫摸著那陪他度過亂世風云的筑,他已不是當年無憂無慮的少年。
百步青衫,人聲漸稀,如今在高漸離心中只殘留著那些故人的影子,他為了片段的回憶而活,直到此時才發覺回憶終究是回憶,逝去的人永遠不會再回來,正如此刻他的心,已隨著年少時的筑音漸漸遠去。
宮人匆匆的腳步聲似乎在提醒他死亡的來臨,他抱著灌滿鉛的筑,緩緩走向嬴政的寢宮。在路的盡頭,等待他的是早已寫進史書的命運。
那時正值暮春三月,他于市井之上結識荊軻,兩人無話不談,相識恨晚。他習慣了與荊軻在一起的日子,舉手投足間皆是與旁人沒有的默契。
清風依舊,伴著淡淡花香,他擊筑,他舞劍,一劍一筑讓他們暫時忘卻了人間是非,忘記了身處亂世。他們談笑江湖,過著快意的日子。
兩人常在巷口飲酒歡唱,我自傾杯,君且隨意。酒盡之時,兩人也曾抱頭痛哭。高山流水,知音難覓,他多想停留在這一刻,永遠不要看著眼前的人離去。
他堂堂七尺男兒,為荊軻流淚,心也為他滴血。因為他知道荊軻是刺客,他無法阻止他要走的路,無法打消他的執念。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看著這個好友與他漸行漸遠。
他不明白荊軻為何要答應太子丹去刺秦。嬴政雖是暴君,可畢竟與他們這些百姓無關,嬴政一死,天下必亂。
他只想平平淡淡過完此生,至于天下蒼生,與他這個琴師毫無關系。那時的他并非冷漠,只是自私。
高漸離雖不能理解荊軻的選擇,但他還是堅持為他送行。
那年寒秋,易水之濱,清冷的氣息回旋于碧藍蒼穹,他為荊軻擊筑送行,沒想到竟成永別。
那天荊軻仰天高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返……”他望著荊軻越走越遠的背影,自始至終荊軻都沒回頭。
高漸離遠遠望著那個身影,希望荊軻可以為他停留,可他終究沒有停下,孤單又執著地遠去。
筑聲越來越輕,直到荊軻的身影消失在他視線里,他才緩緩放下竹尺,撫摸著筑上的細弦,無語凝噎。易水寒怎敵他的心寒?壯士一去不復返,他真的不會回來了。
得知荊軻已死的消息時,他如舊時那般靜靜哼著那首曲調。音律回旋間,他仿佛又回到了那年繁華的燕國小巷。
他呢喃著故人的名字,荊軻、太子丹、秦舞陽,這些人都已遠去,聽說太子丹被父親追殺,身首異處;秦舞陽被嬴政處死;荊軻……他不愿去想,因為心會痛。
夜未央,他緩緩合上眼,斷了這一世的紅塵舊念。故人走的走,散的散,他不得不改名換姓,寄人籬下做別人家的傭保。
可他不想這般茍且偷生。于是,那天在主人家的宴席上,他故意漏出破綻,讓人看出他是精通音律之人。而后,他經常出入各種高官貴府,擊筑唱歌,聞者皆稱贊不已。他這般出入人前,為的就是讓嬴政發現他。
終于,他的目的達到了。那夜,嬴政派人把他“請”入咸陽宮。嬴政熏瞎了他的雙眼,卻蒙不住他的心,鎖住他的手腳,卻困不住他的夢。
他已經一無所有了,亦不懼怕嬴政,自燕國滅亡的那刻起,他的希望與光明便已不復存在。該怕的是嬴政才對,一個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才是最可怕的。
他抱著僅剩下的殘筑走進咸陽宮,空蕩蕩的巷子里無人為他送行。昔日的門客也都刻意避開他,他不禁感嘆世態炎涼。
恍惚間,他想起了那日易水之畔的離別,想起了英雄末路的無怨無悔。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像荊軻那般待他,當然,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做高漸離。
他從容地走著,看不見這里究竟有多奢華,可黑暗中能感覺到這里充滿了熟悉的味道。這座大殿上,荊軻來過,他的血就濺在這里!這里每一塊磚瓦都在提醒他,荊軻就命喪于此,死不瞑目。
那一刻,他明白了荊軻刺秦的意義。有些事情無論對錯,結果如何,都是一定要去做的。易水送行之日,荊軻分明知道這一去必死無疑,可還是選擇去面對。今日的他正如昔日的荊軻,明知是絕路,卻還要走在路上,絕不回頭!
他在這里度過了許多個日夜,可他已失明,只能憑借宮人的腳步聲來判斷時辰。他這般卑微地活著,僅僅是為了一個目的,那個與荊軻一樣的目的。
他負著沉重的筑登上高臺,風起,衣衫飛揚,一如他往昔的瀟灑。如往常一樣擊筑,并無異樣,只是今日的曲子暗含著說不清的愁緒。
忽然,他憤然起身,將那灌滿鉛的筑向嬴政砸去。伴著筑毀弦斷之聲,他露出了微笑。嬴政的生死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明知結局是死卻偏要一試。
自踏入咸陽宮那日起,他就沒打算活著離開,來這里只為求死。
他沒有荊軻那般好的武藝,沒有太子丹那樣的謀略,到最后也不過是個樂師,他唯一能做的便是放下尊嚴向宮人討要廢棄的鉛。
他終于得到了想要的結果,刀劍刺心的那一刻,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解脫。他雖不是君王,卻有兼愛天下的決心;雖不是俠客,卻有壯志凌云的勇氣;雖不是英雄,卻有救眾生于水火的心愿。誰是誰非真的已經不重要了,他從未后悔踏入這片土地,亦如他從未后悔認識荊軻。
他的一生如同高漸離這個名字一般悲傷,漸聞漸遠,漸疏漸離。
昔日筑聲,終成絕響,一紙史書是誰還在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