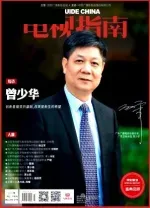影視作品呼喚悲劇英雄
王曉華
悲劇英雄都是承擔者。承擔的能力源于自由意志。沒有自由意志,就無所謂承擔。只有當個體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自己時,他才能以承擔者的姿態在宇宙中亮相。
近幾個月來,連續劇《花千骨》在電視和網絡上熱播,觀眾已達3億人次。隨著情節的展開,粉絲們愈發關注主人公的結局。根據網絡上顯現出的強大民意,喜劇式的收場更符合觀眾的主流心愿。為了影響劇情的走向,許多網民頻頻發帖,懇求導演讓有情人終成眷屬。在由此形成的言論空間中,一種集體無意識頑強地自我展示。
意味深長的是,這部仙怪劇的主流觀眾是8O后和90后,但所折射出的社會心理卻擁有悠久的歷史。在瀏覽網友留言時,筆者恰好剛剛讀過蔣觀云先生于1905年所轉述的評論:“中國之演劇也,有喜劇,無悲劇。每有男女相慕悅一出,其博人喝彩多在此,是尤可謂卑陋惡俗者也。”(《中國之演劇界》)1905年的中國處于晚清末年,也是啟蒙文化正在興起的時期。為了改造國民性,蔣觀云倡導“能鼓勵人之精神”的悲劇創作。然而,100年過去了,中國的文化舞臺上風云變幻,戲劇表演、制作、傳播的方式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蔣觀云等人眼中的“卑陋惡俗”依然延續下來:觀眾最欣賞的還是“男女相慕悅”的情節,粉絲孜孜以求的仍舊是喜劇式結局,悲劇性的收場方式同樣為大多數人所排斥。為什么歷經百年風云,我們的欣賞偏好沒有出現根本性的改變?進化論是否失效了?國人緣何如此排斥悲劇?難道存在不可改變的文化基因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叩問:什么是悲劇?何為悲劇精神?它擁有怎樣的社會學背景?
在影響深遠的文藝理論名著《詩學》中,古希臘大哲亞里士多德曾給悲劇下了這樣的定義:“悲劇是對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模仿”。或者說,悲劇的主人公必須能夠獨立完成“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成為自己生活的舵手(“他們的幸福與否取決于自己的行動”)。在他看來,悲劇人物為自己負責的重要方式是在公開場合表達思想。作為《詩學》的譯者,陳中梅先生曾特別強調:文中“像政治家似的發表議論”也可以翻譯為“像公民似的講話”。在做出這個解釋之后,他又著重指出:古希臘的“政治是全體公民的事”,“關心政治(即城邦事務)是全體公民的義務”。這幾條注釋非常重要。它間接地向漢語讀者敞開了悲劇精神誕生的政治學機制:在所有公民都能參與城邦(國家)事務的共和社會里,個體(公民)有權利和義務公開表達自己的思想,進行“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于是便有了自我決定、自我塑造、自我承擔的悲劇精神。
作為悲劇學說的創始人,亞里士多德也是公民理論的闡釋者,這并非巧合:悲劇精神實際上就是公民精神。恰如悲劇研究專家保羅·卡特萊茲所說,古希臘悲劇誕生和興起于古希臘實施民主政治時期,是“民主的創造物”。它以 “民主之棱鏡檢視傳統神話”,從屬于新興的雅典公民文化。悲劇的創作者、演出者、觀看者皆是公民,所體現的也是公民文化的法則和精神。根據亞里士多德的定義,公民就是“既能出色地統治,又能體面地受治于人”的城邦成員。
悲劇英雄都是承擔者。承擔的能力源于自由意志。沒有自由意志,就無所謂承擔。只有當個體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自己時,他才能以承擔者的姿態在宇宙中亮相。自我塑造需要一定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前提。輪流統治和被統治的公民法則給了每個自由人站立起來的機緣,雅典公民則是最原始的悲劇英雄。從這個角度看,古希臘悲劇不過是公民文化的特定形態。在公民文化尚未誕生或受到壓抑的地方,悲劇精神或者無法誕生,或者處于蟄伏狀態。體悟到了這個秘密,我們就會破譯中國人的深層心理:從先秦到晚清,中國始終沒有公民大會,沒有人民普遍參與的法庭審判,沒有輪流統治和被統治的政治理念;缺乏自由、自治、自律的個體精神,就不會有相應的承擔情懷和罪責意識;對于一個無法介入公共生活的人來說,他/她所能做的不是喜劇性的嘲諷和戲謔,就是把任何苦難都改造成甜蜜的記憶;于是,喜劇流行,人們普遍期待大團圓式的結局。
由此可見,中國人的喜劇情結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它至今仍在流行,很可能是意味深長的癥候。由于復雜的博弈,公民文化的建設在華夏大地上一波三折,至今仍未完成。比之于前現代階段,我們參與社會生活的渠道雖然大大增加了,但還不足以使大多數個體完全站立起來。在現實生活中,不少人依舊會體驗到深入骨髓的無力感。對于他們來說,悲劇中的苦難和承擔意味著生命不可承擔之重。經過短暫的猶疑之后,喜劇再次成為唯一的選項。為了將自己的愿望投射到虛擬的劇情中,以80后和90后為主體的網民們迷戀大團圓的結局。如果少數電視劇制作者違背其心愿,他們就會憤憤不平地進行聲討(電視劇《絕愛》就因悲劇性結局而獲得差評)。這折射出一種精神上的“輕”。它顯然與大國崛起的宏大氣勢不相稱,只能是過渡性的精神屬性。事實上,新的地平線已經因此顯現出來:只有建構公民文化,我們才能成長為能夠承擔歷史進程的主體。對于藝術家來說,這既意味著呼喚,又意味著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