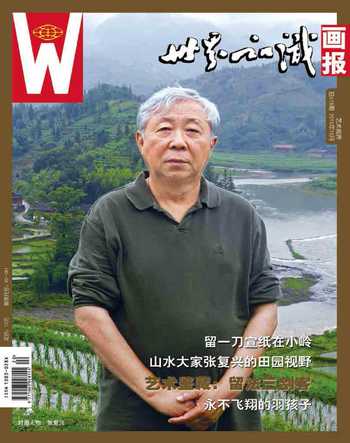瀘溪儺面師:定格巫儺文化表情
雷虎
Nuo culture is th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among the original customs originated in the Yuan river, western Hunan Province. “Nuo” also called“Nuo Sacrifice” or “Nuo Ceremony”was originally a type of sacrificial and magical ritual held to expel evil spirits and pestilence. Persons wearing the Nuo masks could communicate with God just like the Saint of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Nuo mask makers also emerged as the times required.
湘西沅水流域,自古以來便是漢苗土三族混居之地。因為高山路遠,交通不便,因而各種原始風俗得以保存下來,巫儺文化便是這原始風俗中最突出的代表。
沈從文《湘行散記》中的湘西,是一個民風原始的“失落世界”。趕尸、下蠱、落洞的故事,盡管誰都沒有見過,但是湘西邊民卻都深信不疑。湘西人都認為這個世界是人神共處的,但神放不下架子直接與凡人溝通,于是巫和儺——這樣的人神中介就誕生了。神選擇代言人,不能空口無憑,得有信物證明,儺面具便是這樣的證物:戴上面具,立馬化身為神——就好比圣斗士,穿上戰甲,立馬成為雅典娜的護法。
在交通不發達的年代,水路是溝通湘西和外界最重要的紐帶。沅水流域各族在通過沅水交通時,也把自己的文化融入沅水中。沅水之畔的浦市古鎮是湘西北經濟最發達處,因而也是文化融合最緊密處。沅水流域巫儺文化尤為興盛,因而浦市也成為了巫儺文化大本營——在民國時期,也就是沈從文寫《湘行散記》那會兒,是儺面藝人的黃金時代,僅浦市一鎮,就有大小廟宇72座。每次節假廟會,各路神仙就會集體登場。而作為神仙們主要的行頭——儺面,就會得到集中展示。因而,對于儺面藝人來說,每一次節日,都是他們的才藝大賽。
1950年出生的劉明生,是湘西屈指可數的儺面師。因為我們的到來,劉明生從堂屋里搬出一塊已經雕出模糊人臉的木料開始演示如何制作儺面。
“儺面的木料沒有太多講究,一般是就地取材。因為戴儺面的就是普通百姓,太名貴的木材沒必要,也沒人要。”劉明生邊把面具粗胚在案板上固定,一邊自嘲:“外人把儺面師看得很神秘,我們湘西人可不這么認為,拋開儺戲,儺面師其實就和木匠差不多。”
粗胚固定后,劉明生就開始拎出工具箱,像哆啦A夢一般從工具箱里拿工具:鋸子、斧頭等大件擺在地上;刨子、錘子、斧頭等中號放在案板邊遠一點的地方;圓鑿、方鑿、油刷、調色板等小件則放在右手邊。
“你姓雷,我今天就雕一個雷公吧。”說著劉明生就拿起筆刷在木質粗胚上畫起來。刷刷幾筆,木胚上就出現一幅似人似鳥的類漫畫肖像。
“雷公名字雖然威風,可是長得可有點慘不忍睹啊!《西游記》中,孫悟空經常被罵成‘毛嘴雷公臉,你看和這像不像?”劉明生畫得不夠精細,甚至可以用粗陋、夸張來形容。儺面主要是儺祭時的道具,儺祭是驅鬼逐疫的儀式。在古代,儺祭是全民參與的。按規格不同,有“天子儺”、“國儺”和“鄉儺”之分。“天子儺”為天子專用,“國儺”參與者為王公貴族士大夫,而“鄉儺”的主體則為下層百姓。“天子儺”或“國儺”后來慢慢發展成陽春白雪的“雅”文化,而“鄉儺”則慢慢成為“俗文化”的典型。瀘溪儺戲便是鄉儺的一種。
“鄉儺時,來唱儺戲,看儺戲的都是鄉里鄉親,太精細的東西他們體會不了,所以儺面的造型越夸張、雕工越粗陋反而越能引起他們共鳴。”劉明生左手握鑿,右手掄鐵錘。手起錘落,木屑橫飛。幾分鐘功夫,地上木屑散落一地,木胚上雷公臉也逐漸從平面變為立體。最后臉錘落在雷公的眼睛上,只聽兩聲輕脆的聲響,雷公的兩只眼睛終于洞穿了。這時,劉明生拂去雷公臉上的木屑,把儺面貼在臉上。一瞬間,他便“變身”,從和藹風趣的老者變成兇神惡煞的雷公。
雷公臉雕好后,劉明生從屋里端出一個搪瓷臉盆,把地上的木屑都放進臉盆中生起一盆火。待臉盆中生起青煙時,劉明生把剛雕好的儺面湊到青煙上。
“這是雕儺面的儀式么?讓剛雕好的儺面‘吸煙?”我忍不住問了一個很外行的問題。
“哈哈,的確是讓儺面‘吸煙,但你把這一行想得太神秘了,這可不是什么儀式。用煙熏,就像熏臘肉一樣,一是為了讓儺面防腐,二是讓儺面看起來更有生氣。”劉明生把儺面按在火盆上,烤一兩分鐘換一個位置,動作像燒烤攤的小伙子在烤肉串一般嫻熟。烤了十分鐘,看儺面里外都熏得泛黃后,劉明生這才把儺面放在案板上讓其冷卻。
當然,劉明生也沒閑著,他端起案板上的調色板,開始不緊不慢的調色。調好色,拿起儺面,就像京劇演員畫臉譜一般給雷公“化妝”。
上色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先涂上一層底漆,待底漆干了后,再往上加一層……因而僅給儺面上色這一道工序,有時就要持續兩三個月。好在儺面顏色往往都比較單一,要么大紅,要不大紫,更多的儺面,像是牛頭馬面、無常等往往都不用上色,只需要刷幾層桐油就完工了。刷完漆、上完油,裝上供佩戴用的帶子,儺面的制作階段就已經完成。
如果是普通的木匠,在這個階段,作品已經完工了。但是對儺面師來說,儺面卻還不能“出廠”。因為儺面是溝通人神的道具,要出現在儺祭儀式上,還缺最后的流程——開光。其實,不僅僅是儺面,在湘西,任何神像都需要開光。而且開光時,不同的神像開光還需要念不同的咒語。
接下來,劉明生帶我們走進另一個房間。房間四周墻壁上,掛滿了各式兇神、惡煞、陰森、扭曲的臉。這是劉明生的儺面陳列室,羅列了六七十件儺面。有牛頭馬面、小鬼判官、黑白無常、十二生肖、三十六天罡,也有雷公電母風神,還有地藏王菩薩和十八羅漢……佛家、道家神像皆有,苗、土家巫術人物也不缺——走進這房間,就如同走進了一個眾神集聚的世界。
“這是祭祀面具,這是開山面具,這是跳香面具,不同的面具有不同的功能,有的驅鬼,有的逐疫,有的用在儺戲和祭祀等民俗上。”劉明生站在那列儺面墻邊,每拿起一個儺面時都滔滔不絕。
儺戲是人類祖先自然崇拜的殘留,也是先輩生活場景的再現。儺戲,最開始只是一種人類取悅神靈的儀式,后來慢慢演化成娛神娛己的活動。在65歲的儺面師劉明生身上,則將儺戲從娛神到娛人的趨勢體現得淋漓盡致:他集聚了一幫巫儺發燒友組建了一個儺戲班子,逢年過節就到湘西各地演儺戲。
“我不知道我會影響多少人對儺戲感興趣,但起碼我影響了我的家人,我孫女在我的影響下學了民俗藝術專業,她對我這個儺面師爺爺引以為傲。這對一個儺面師來說,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