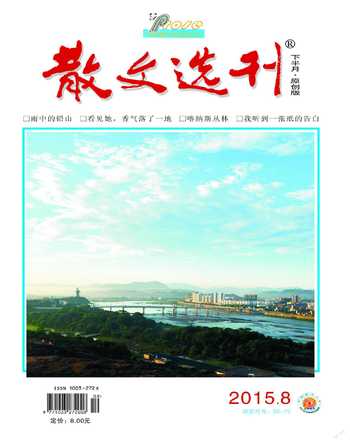武夷山下的徘徊
盧葦
一
五夫鎮(zhèn),又名五夫里,屬福建省武夷山市,曾是南宋學(xué)者朱熹長期生活的地方。
在巾國歷史上,宋朝是個典型,趙匡胤畸文畸武,弱國弱民,定鼎之初就開始了半壁河山的大宿命,所以徽、欽二位皇帝只有到別人的祖宗祠廟里當(dāng)祭品。繼之南宋,麻繩勒豆腐,朽重尤殊。岳飛血淋淋的“精忠報國”和秦檜陰森森的“莫須有”竟然成了世道人心的廣告標(biāo)簽,國事的虛誆靡費可想而知。蹊蹺的是,本該茍延殘喘的儒家義化,竟從荊棘叢巾踏出了一條必通坦途的曲徑,窘迫坎坷卻又軒昂不凡,費人思索。
朱熹,就是南宋一朝中華文明畸變的答疑鍵。
由杭州前往五夫鎮(zhèn),途經(jīng)武夷山,必至一景,是八百多年前,朱熹建造的人稱中國“第一座私立大學(xué)”的“武夷精舍”。
朱熹一生親手創(chuàng)建的書院多達(dá)27座,“武夷精舍”即是其一。當(dāng)年朱熹五十四歲,之后又在此著書講學(xué)多年。他七十一年的風(fēng)雨人生完全可以用“愛學(xué)務(wù)教,鞠躬盡瘁”八個字來概括。其巾雖然也雜有9年官場狀如客串般的尷尬,但無論得意與否,仕宦生涯對他而言只能是固執(zhí)學(xué)教之心的助力和附庸。在他的激情面前,天地等同微末,福祿又何言哉!因為,他的心巾只有天下眾生,只有天下至理,只有向?qū)W弘道,他始終是個為天下教化而活的人。
石坊之后,即為復(fù)建的精舍。馬蹄形的屋場并不寬大。正廳三間是講堂,擺有長條桌椅。當(dāng)門的墻壁掛有大幅孔子畫像,下方為一尊手持書卷的朱熹彩塑,高矮與真人略同,容貌睿智慈祥。兩邊白墻上寫有“忠、孝、廉、節(jié)”四個巨大的黑字,是朱熹親筆的放大體,莊嚴(yán)而且威武。但又因為全是新物,里里外外的一切也讓人大有似曾相識之感。側(cè)屋中一堵用白玻全封的康熙五十六年(1718年)書院的斷墻,就是面對世事翻覆、時光如梭最真切的表現(xiàn)。
精舍的內(nèi)外不算寬綽,游人不多,光線也不明亮,我沒有細(xì)看屋內(nèi)四壁的圖片,白顧白地漫步沉思。我想起了孟子“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的名言,想起了蘇東坡“一蓑煙雨任平生”的詞句,檢點朱熹的一生,二者兼具,堪為世表。不做良相即做良醫(yī),不低頭、不屈膝、不讒媚,執(zhí)著頑強,曠達(dá)瀟灑,他以特立獨行取勝,白塑了卑怯之中的另類偉岸。
朱熹自幼即具異秉,四歲便有向父親問天的聰慧睿智,八歲則通《孝經(jīng)》大義,且題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又能與兒童以沙畫八卦作游戲。成年后淹貫詩書,凜然正氣,十九歲中進士,二十二歲授同安縣主簿,上任后出入村社,盡心民瘼,在忠君與愛民累累相悖的拉鋸戰(zhàn)中開始了學(xué)以致用的根本思考和尋覓。朱熹起初傾心佛學(xué),但發(fā)現(xiàn)佛學(xué)不能真正教化百姓時,立即堅定了儒學(xué)志向,扎根在“平實”二字的基礎(chǔ)上,逐步培植豐滿了儒家理學(xué)體系的宏偉架構(gòu)。“源深定自閑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朱熹用自己“居敬持志”“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勇猛精進”的問學(xué)積累,為偏安文化的浮侈淫逸套上了斷魂索,挺直了真正義人的脊梁骨。
俗言道,千個有頭,萬個有尾。朱熹人生的主根就在五夫里。但是,五夫里又并非朱熹的故鄉(xiāng)。他的祖籍在江西婺源,出生地在福建尤溪。1143年,朱熹父親朱松去世。十四歲的朱熹謹(jǐn)遵父親遺囑,奉母來到五夫里,投靠了其父生前摯友、抗金名將劉子羽。從此,朱熹就在五夫里扎了根,從學(xué)、著述、授徒,生活長達(dá)五十年之久。他在巾國傳統(tǒng)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著作大多在五夫里完成。
此一階段,南宋的敵人大金朝已經(jīng)逐漸步人世稱“小堯舜”的金世宗時期,兩國從尖銳對立走向緩和妥協(xié)。原本激烈的民族矛盾由此派生出松弛麻痹的內(nèi)囊,是誓死北伐為短時計,還是重塑人心做長久功,橫亙朝野,截然水火。由積極主戰(zhàn)到“合戰(zhàn)、守之計以為一”的堅定主守,朱熹勇蹈地獄,毅然選擇了重塑人心做長久功。他不惜一生板蕩,用生命的體驗去實證“格物致知”,揭示出了中華文明在特定歷史時期蘊含巨大張力的永恒的生動。
五夫里,一個偏僻的山鄉(xiāng)小鎮(zhèn),竟然哺育了一位中華民族的千古精英。冰山雪蓮,鳳毛麟角,它的樣子到底如何呢?正當(dāng)我陷入恍惚之中時,前座的朋友突然叫道:“快看,五夫里到了!”
二
五夫里的確很小,也很古。
它起于東晉中期,迄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小鎮(zhèn)的主體是一條名為興賢的小街,長短千米左右,寬窄三米上下,坐落于緩緩的山坡上。鱗次櫛比的房舍迤邐展開,蜿蜒曲折,直達(dá)坡頂。路面斑駁凸凹,鋪面古舊蒼然。街巾多有石坊,坊各有名,其上多刻“五夫薈萃”“天地鐘秀”等等古氣盎然的題詞。又有一座小小的過街門樓,兩面分別鐫刻“三市街”“過化處”數(shù)字。細(xì)細(xì)端詳,斜照的陽光、雕花的門窗、靜謐巾偶爾的人語與窸窸窣窣的清風(fēng),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自在,古樸悠遠(yuǎn),讓人不知不覺便進入了一種朝圣面佛的意境。
我們在小街上徜徉,現(xiàn)在的小街已全是居民住戶,不復(fù)街市了。從興賢書院五彩的門墻前面折轉(zhuǎn),回到那條名聞天下的“朱子巷”前,輪流在巷口碑石邊攝影留念。據(jù)說當(dāng)年長有三百多米的巷道,如今卻只剩下三十多米了。巷道兩邊房屋的坯磚山墻,被巾午的陽光染金了半壁。
我站在朱子巷口朝深處凝望,心巾有一種看透時空的希冀。百步之外的殘墻斷壁之上,就是空曠無邊的藍(lán)天。朦朧巾,我仿佛看見了朱熹的身影,他正臂夾書袋腳步匆匆地向布滿卵石的巷道走來。從十四歲開始,朱熹的一生就跟這條小巷結(jié)了緣。他由此讀書受教,也由此教書育人。他當(dāng)官從此而出,罷官又從此而歸。小巷巾的行走是他一生奔波的象征。在一定的意義上,他留給小巷的數(shù)十萬個足印,就是儒家理學(xué)一脈從幼稚走向成熟的軌跡。1153年,朱熹在上任同安主簿的途中拜見了名儒李侗。一番受教,肅然頓悟,從此竭誠為徒。李侗是北宋大儒程頤程顥的三傳弟子,是當(dāng)時直接繼承二程學(xué)說成就最大的學(xué)者。四年后,朱熹任滿回到五夫里,全力教書授學(xué),篤研義理,博采眾長,著文述志,逐步構(gòu)建起了理學(xué)的宏偉大廈。后世有人稱他這次思想變化為“逃禪歸儒”,也有人說他是棄禪,可惜都不盡準(zhǔn)確。他不是逃禪棄禪,而是離禪,是經(jīng)過實踐和思考后主動選擇了儒家學(xué)說的“務(wù)實”之道,沒有也根本不會丟掉對佛老“清靜無為”的借重。
從此,朱熹思想中的知行巨流從五夫里的一條小巷開源,滔滔汩汩地奔向了山外的世界。
朱熹雖有大智慧,但仍為俗世中人。在甚囂塵上的俗霧中,也有過五彩繽紛的慷慨激昂和年少氣盛的熱血沸騰。他曾經(jīng)堅定主戰(zhàn),斬釘截鐵地上書皇帝“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旗幟鮮明地對和議之害、復(fù)仇之利大力宣揚。針對主和派宰輔錢端禮的諸多謬論,厲呼“蓋以祖宗之仇,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在《戊午讜議序》一文中借批判“紹興和議”來抨擊“隆興和議”,借痛斥秦檜來大罵主和派頭子湯思退和錢端禮。對宋孝宗的抗金由冒進受挫轉(zhuǎn)而屈膝求和,朱熹即痛心直陳為“臣竊恨陛下于所不當(dāng)為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舉也”,直指乞求“議和”是“逆理”之行,它將使“三綱淪,九法敦,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將使天下“夷狄愈盛”而“禽獸愈繁”。朱熹既敢直言,當(dāng)然就不怕死。可悲的是已經(jīng)因符離之?dāng)』倚膯誓懙乃涡⒆诓⒉活I(lǐng)情,權(quán)臣如錢端禮之流更是死活不容。一心希望天顏堯舜的朱夫子,卻接連受挫碰壁,無奈中只有一次次請辭,一次次歇菜,怏怏然退歸五夫里。
當(dāng)年的奉祠,即閑職薄薪休養(yǎng)。朱熹在同安縣主簿任滿后即奉祠養(yǎng)親,回歸五夫里教書育人。之后三辭京官,堅定居閑,一干二十年。其間,他的學(xué)術(shù)著作日豐,抗金壯志消歇,把一腔熱血逐漸傾注到了儒學(xué)理論的知行之中。
但是,朱熹的言行移位絕非甘心悔悟,更非麻木妥協(xié)。皇帝不重用,我白重;精英不專精,我白專;天下不知禮,我白教。春江水暖鴨先知,在四海囂囂的慌忙之中,朱熹始終是清醒的。他對官員的昏聵無能曾感慨“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于民,直是難與圖事”;他對圣道的昏昧曾長嘆“若此學(xué)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為之理”。此學(xué)即指理學(xué),他是橫下一條心要從根底做起,用天下大道去補綴早已亂紛紛的世風(fēng)人情。
所以,朱熹雖主守卻不倡守,拼命以儒學(xué)收拾人心,力求從根本上奠定抗戰(zhàn)基礎(chǔ);所以,朱熹的主守只能是屈心認(rèn)和,只能是先知之痛,只能是忍辱含垢的苦修苦行。清學(xué)者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評南宋說“統(tǒng)前觀后之,前則有將帥而無君相,后則有君相而無將帥,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精辟之論是后來者的清醒。當(dāng)年的朱熹,卻是早就主見在心并一意踐行了。永垂史冊的“鵝湖之會”就是朱熹在五夫里赍志默行的偶爾崢嶸。
1175年3月,由學(xué)者呂祖謙起意,相約朱熹與陸九齡陸九淵兄弟,會集江西鉛山鵝湖寺進行學(xué)術(shù)論辯,史稱“鵝湖之會”。會上,朱陸二人圍繞“道問學(xué)”與“尊德性”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駁難。這次會講活動,在呂祖謙是為調(diào)和,在朱陸是為明道,在歷史則是百家爭鳴學(xué)風(fēng)消遁幾近兩千年后的浴火重生。
朱陸不會想到,他們辯駁詰難的水火不容,恰恰是南宋偏安哲學(xué)兩大主流思想的第一次大碰撞。
朱熹曾言“海內(nèi)學(xué)術(shù)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豐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意思是天下學(xué)術(shù)上的弊病,無非兩種,陸九淵重感悟,陳亮重功業(yè),如果不與它們爭辯,理學(xué)之道就無法暢行天下。朱熹當(dāng)然十分明白,能與他的“格物致知”真正對壘的只有陸九淵的“頓悟明心”。至于陳亮的豐功之舉,太現(xiàn)實,太急進,雖說斷不可缺,但在眼前畢竟是空折騰。一心抱本務(wù)實的朱熹,沒有也不可能將“實利”重存于心。所以,他能參加“鵝湖之會”與陸九淵激辯,卻不會參加13年之后陳亮辛棄疾相約商討抗金大計的“鵝湖之晤”。對此,朱熹回信陳亮說“奉告老兄,且莫相攛掇……古往今來,多少英雄豪杰,韞經(jīng)綸事業(yè)不得做,只恁么死了底何限……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話語婉轉(zhuǎn)意思直白,抗金抗金,抗非其時,抗又何益?于其虛耗無用,何不默頭獨行。難道你還不明白現(xiàn)在能人太多了嗎,不明白鍋是鐵打的嗎?
但是,如果據(jù)此就認(rèn)為朱熹是個抗戰(zhàn)逃兵,那就大錯特錯了。
朱熹與陸九淵的分歧在問學(xué)方法,是務(wù)虛;與辛陳圖謀恢復(fù)則為討論操作,屬務(wù)實。務(wù)虛可務(wù),務(wù)實則不可行,兩者有著根本的不同。所以鵝湖之會后,朱熹即主動在學(xué)術(shù)上有了較大的白省和彌補。他曾寫信給陸九淵說:“警切之誨,佩服不敢忘也。”又深有所感地告誡學(xué)生:“示諭兢辯之論,三復(fù)悵然。愚深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且置勿論,而力勉吾之所急。
后三年,即1178年冬,朱熹走出了閑居二十年的五夫里,第二次出仕,擔(dān)任了朝廷命官知南康軍。朱熹當(dāng)然不會改變問學(xué)原則,他是在自覺不自覺地修正自己偏執(zhí)的“情性持守”和“窮理致知”。“出仕”這一結(jié)果的主要動因,應(yīng)該就是他深懷少言的“鵝湖之會”的知行敏悟。
南宋前期,文化上突出的主戰(zhàn)派當(dāng)屬陸游,陳亮、辛棄疾等人,朱熹和他們都是朋友且多有交往。朱熹白有抗戰(zhàn)之心,但絕不是激越和沖動。他的根子是內(nèi)省扎實的修齊治平。所以,他的文化同盟只能是理論上的對手陸九淵。朱熹非常明白,陸之長則己之短,只有對照這面鏡子,才能找準(zhǔn)自己底蘊的不足。所以,他與陸的交往重在問學(xué)論辯而非寫詩作文,與辛、陳、陸的接觸則多在詩義唱酬,寄情于心性的抒張和理解。辛棄疾比朱小10歲,他非常敬重朱熹。曾寫詩道:“山中有客帝王師,日日吟詩坐釣磯。費盡煙霞供不足,幾時西伯載將歸。”把朱比作臨溪垂釣的姜子牙。朱熹也極其贊賞辛,對他的大智大勇,不僅報以“施展杰出的才干,以報朝廷”的期許,還為辛的齋室書寫了“克己復(fù)孔”“夙興夜寐”題詞。朱熹對比自己小13歲的陳亮也極尊重,互訪切磋,五年飛鴻,義利駁詰,言無不盡。其實,在主戰(zhàn)之上,三人是互為知己的。因為,辛陳的追求正是朱熹無力顧及的事業(yè),辛陳的功業(yè)當(dāng)是朱熹問學(xué)之道在現(xiàn)實巾的理想結(jié)果。而朱熹的主守,只不過是把在辛陳身上的希望,轉(zhuǎn)化為治學(xué)明道的更大努力罷了。至于陸游,比朱熹年長5歲,宦游多在京城、四川,兩人接觸較晚,雖說情志甚為相得,但畢竟長為參商,少了更深入的契合了。
1193年農(nóng)歷元月,陸九淵病逝于荊門軍任上。朱熹曾親率門人往悼,痛言“可惜死了告子”!意思是,可惜啊,死了宣揚大道的人!朱熹是真正感到孤獨的凄苦了,因為他從陸九淵的遭際再次看清了自己主戰(zhàn)意志的幻滅。第二年陳亮去世,緊接著辛棄疾遭罷職,兩年后“慶元黨案”發(fā)生,權(quán)臣韓侂胄誣朱熹為“偽黨”“偽學(xué)”。朝廷遂嚴(yán)禁“朱學(xué)”。此時的朱熹離去世只剩下不足四年光陰。雖然屈辱,雖然孤零,雖然希望灰飛、年邁多病,朱熹卻依然故我,矢志不渝,分秒必爭地進行一生論著的整理和承傳。1200年3月9日,朱熹在建陽縣考亭村住地“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用最后的凝重迎接了自身涅檠。
三
大寒已至,眼看就是春節(jié),卻連日艷陽高照,四野蒸騰。走出朱子巷時,我們個個額上已是熱汗涔涔,看見不遠(yuǎn)處有家飯店,立即決定就地用餐。胖胖的大師傅就是老板,待人熱情。問起五夫鎮(zhèn)來歷,老板說:“夫子嘛,就是指鎮(zhèn)上胡姓家族五個大名望的讀書人,都比朱熹早啊。你們剛從鎮(zhèn)街…來吧,朱熹在鎮(zhèn)上只是教書,他的住家紫陽樓在鎮(zhèn)外,也該去看看哩。”
這還用說,幾千里跑過來,紫陽樓豈能不至,半廟方塘焉得不看?
紫陽樓是朱熹義父劉子羽專門為朱家母子蓋的住房,位于五夫鎮(zhèn)東南一公里開外的屏山腳下。劉子羽后來成了朱熹的岳父。朱熹字元晦號紫陽,樓名當(dāng)是后人的稱謂。遠(yuǎn)遠(yuǎn)望去,白墻黑瓦飛檐翹角,林木蔥蘢氣勢昂然,令人欣喜。然而可惜,待餐后前往,卻叫人大失所望,竟又是全新的建筑。對照武夷山市“五夫古鎮(zhèn)”旅游折頁中紫陽樓的圖片,舊貌已蕩然無存。好在門前一棵相傳為朱熹手植的八百歲香樟樹,枝干蒼虬,古風(fēng)習(xí)習(xí),可聊補尋真之缺。
離開紫陽樓,車子徑奔南平市。車至南平已晚,簡單用餐后即洗漱休息。我在床上輾轉(zhuǎn)反側(cè),橫豎睡不著了,便坐起來抽煙。讓紛雜的思緒隨著四散的輕香,慢慢地伸展開去。
中華歷史自有文字記載以來,三皇五帝不論,從周至宋二千余年,儒教文化的真正走紅期屈指可數(shù),且次次都有鐵血相伴,充滿殺伐。主體的文化人,便只能多有不幸,只能如飄蓬螻蟻一般的混沌輕賤。其中雖也有殊世孤突者,卻又因多不得志,稀見善終,常令后人凄凄而不忍回顧。
艱難與血漬的儒教文化,一路坎坷挨到大宋,似乎見了天眼,趙家皇帝誓以鐵卷不殺文人,成就了一段文化史佳話。可惜好景又不長,半壁河山,滿打滿算才一百六十七年,并非真誠的文化假面終于導(dǎo)致了國勢的瞬間崩潰,文化天子徽、欽二帝就成了幾乎沒文化的金太宗的昏德公、重昏侯兩個狗奴才。此后,康王泥馬渡江,狼奔豕突,或戰(zhàn)或和交叉拉鋸全覆蓋,儒教文化就只有銷聲匿跡。
自1127年趙構(gòu)即位,到1148年朱熹19歲考巾進士,二十年間的南宋文化只有鐵鑄的“莫須有”三個字。此時此刻,寄命天下、持之以恒的文化人,首推朱熹朱夫子。
朱熹自進士及第,當(dāng)官50年,立朝40日,辭職多達(dá)23次。自劾求免的表面是退避,骨子里卻是一種頑強的抗拒。朱熹氣概雄闊無比,他一眼看透南宋的濫糟,目光直射千年之外。他指出自三代以降,天下無禮,悠悠歲月只不過是“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的小可憐。既而,針對屈辱的國勢和官劣民苦的現(xiàn)狀,他連連上書孝宗要從“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做起,要去舊習(xí)、斥邪诐,要“延訪真儒,深明厥職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在斷斷續(xù)續(xù)的為官任期巾,他的恤民、省賦、濟糶、辦賑濟、筑江堤、整士風(fēng),他的“訪民情,至廢寢食”,他的正朝廷、立綱紀(jì)、厲風(fēng)俗、選守令一類的諫議和行動,都是儒家理學(xué)的堅強骨骼,都是朱熹在不可為大網(wǎng)之中的心血之為。他的主守之心甚至比主戰(zhàn)派的兵刃還要鋒利。宋光宗紹熙五年(1194年)七月,朱熹在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任上,聞知寧宗登基,立即提斬18名大囚,“才畢而登報赦至,翁恐赦至而大惡脫網(wǎng)也”。為國為民,除惡務(wù)盡,大智大勇,雷霆手段,平平主戰(zhàn)者何得望其項背!
朱熹生在屈辱的時代,長在庸墮的時期,活在性格扭曲、心志壓抑的煎熬中,但他能夠隱忍混濁,百折不回。于百姓有益的即力行,對理學(xué)不利的即爭辯,大道通天,一以貫之,志堅如磐,誓死以求。如此者,大功不成,天理何言!南宋窩窩囊囊一百五十余載,砥柱中流功垂千秋者,魁首朱熹,何人可比?
春秋無義戰(zhàn),大道崩摧,孔子為此痛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他選定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一條路。面對南宋的淪落朽墮,朱熹則截然不同,他認(rèn)為自孟子歿后,道統(tǒng)久已不傳,如今天命有歸,理該當(dāng)仁不讓。
朱熹成功了,他用自身的剛健,傳承發(fā)展了儒學(xué)道統(tǒng)。理學(xué)的新生正是巾華民族成長壯大的象征啊。在朱熹構(gòu)筑的理學(xué)大廈之巾,人類社會的一切變化全是客觀進程的渺小瞬間。而這種瞬間,朱熹也作出了明證,它就是微小的堅持。義化天生的就是細(xì)致扎實、微小而無盡,從來都不是空言虛浮、媚俗而邀寵。朱熹在委屈巾生,在委屈巾長,在委屈巾成就理學(xué)的萬古不朽。文化文化,文化何物?如果非要切題,委屈、委屈,無非委屈二字。
我只知道,眼前一直行走著一個孤獨的身影,耳邊一直響著斷續(xù)的吟哦:
行行重行行……
唧唧復(fù)唧唧……
人皆集于莞,己獨集于枯……
雖九死而猶未悔,
吾將上下而求索……
兩天后,我們被暴風(fēng)雪堵在襄陽城內(nèi)。戊子年的大雪啊,曠古少有。
我猛然頓悟,一聲暗喝:“好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