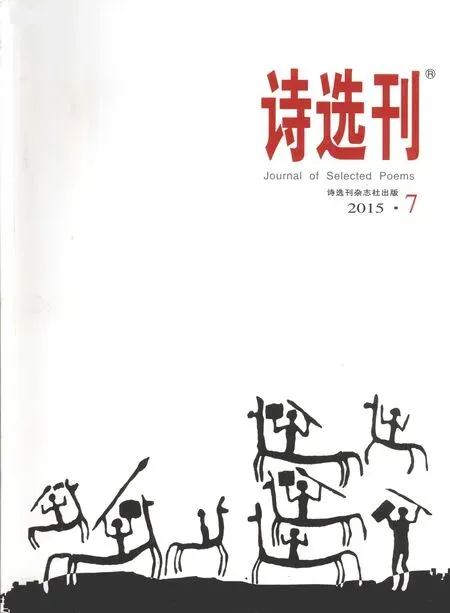記憶或記錄
谷地
x
手的意義
——致諾爾曼·白求恩
你在蒙特利爾
皇家維多利亞醫院
無影燈下主持
胸外科手術
這時聽到了來自東方的隆隆炮聲
聽到來自老人和孩子們內心的慘叫
你收起手術刀
毅然東行
“手術刀就是武器”
你要用手中這個武器
去抵御那場法西斯戰爭
中國延安
你脫去油黑锃亮的皮鞋
穿一雙露腳后跟腳趾頭的草鞋
你在墻上畫了一只高高舉起的手
一只火炬一樣燃燒的手
你說這手的意義叫:抗日!
謝絕毛澤東給你的
每月一百大洋的津貼
經常在一棟草屋的門邊
坐在小板凳上
認真地餐吃一碗小米粥和一小碟土豆
更多的時候
騎馬奔馳在戰場
用漢話大聲呼喊
快快快!傷員傷員!
在老鄉的炕頭
在村頭的小廟
在炮聲槍聲硝煙里
你鎮靜地為八路軍傷兵
取出一塊塊彈片
為他們包扎好傷口
為搶救一名重傷員
你的300cc鮮血
流進中國戰士的心臟
你說:我的血,O型
O型,萬能!
孫家莊小廟,1939年
10月28日,你和往常一樣
鎮靜地給傷員實施手術
突然 你的左手的中指
被手術刀劃破
不那是被殘酷的戰爭刺破
丹毒無情地滲進你的血液
你知道你就要被戰爭的毒菌摧毀
可作為一名世界著名的
外科專家
你說 我十分憂慮的是
前方流血的戰士
那是一個秋天的傍晚
夕陽照耀在草屋屋頂
你在屋門前
赤裸著脊梁坐在藤椅上
你的手反射出光芒
左手明顯突兀的血管
奔騰著力量
你把這近兩年
看作是生命最愉快最有意義的時日
你在彌留之際 想的是
以后千萬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帶
購買奎寧和針劑了
因為那里的價錢比滬港的貴兩倍
1939年11月8日清晨
你壯麗的生命
結束在太行山上
所有法西斯的刺刀
在你的手術刀面前
都黯然失去光亮
所有法西斯們的頭顱
在你高舉的左手面前
都要低沉彎曲下來
諾爾曼·白求恩
一個超越一切時間和空間的名字
冉莊,地下的路
要不是各家各戶的門口
標明“文物”的字樣
你真不敢相信
這就是當年威震敵膽的
地道戰村—冉莊
樹還是那棵樹
房還是那些房
院還是那些院
墻還是那堵墻
硝煙早已散盡
槍聲早已遠逝
當年的游擊隊員
如今白發蒼蒼
坐在臨街的石碾上
瞇眼吸煙
幸福的臉上灑滿陽光
而這個石碾下邊
就是地道口
碾礅四周
長滿了隱秘的槍眼
大槐樹已經干枯
卻依然挺立
銅鐘依舊掛在枝頭
只是再不需要把它敲響
那鐘聲尖銳得像一把利刃
響一聲會刺傷孩子們的胸膛
而如今那掛銅鐘下
一位年輕漂亮的媳婦
支起烤爐賣燒餅
剛出爐的熱火燒
夾足了驢肉
咬一口該有多香
十字街的西北角
關帝廟
—冉莊人民武裝委員會舊址
門楹上有一副新貼的對聯
“求財敬神誠為本
燒香奉佛求好運”
有位老婦救會會員
倚著門框
滿足的笑容掛在眉梢
她說 能活過來就是福氣
她會唱冉莊婦女自衛隊隊歌:
掩蓋水井柴草疏散了
糧食和用具都要理藏好
困死敵人餓死敵人
不用槍和刀
我見到的一切
牲口槽土炕柜臺
水井燒餅爐豬圈茅房
石頭堡高房……
由于戰爭
再不是農村風光
地道是一條長長的導火線
把它們聯結起來
干是參加到戰爭中去
成為戰爭的一部分
成為地雷或手榴彈
由于戰爭
人也像老鼠
四處打洞
八方抵擋
冉莊 才有了這神奇的
地下通路
紀念館的展櫥里
一頂日本兵的鋼盔
銹蝕斑駁
再也沒了囂張的氣焰
它讓我想到那個戰死的日本兵
魂靈能否涉過大海
如不能 如今他在哪里游蕩
鋼盔旁還有一封信
那是原駐黑風口據點日軍官
淺尾公平寫來的
關于地道戰的回憶
和
對那場戰爭的
反思與懺悔
蕩氣回腸
南京的傷疤
這是中華民族心頭
一塊最深重的傷疤
一塊時常作痛的傷疤
那33萬架白骨
始終沒有睡去
他們睜大眼睛
你沒看見他們深藍色的目光么
他們張開喉嚨
你沒聽到他們憤怒的吶喊么
1937年12月13日
南京的太陽被膏藥旗遮蔽了
黑暗降臨
這座古老文明的城市跌進深淵
老人們的矍鑠熄滅了
孩子們的雀躍靜止了
姑娘們的花朵凋零了
33萬個生命呵
那些手持刀槍的人
也是血肉之軀呀
而這33萬血肉軀體
就慘死在他們手中
那些手持刀槍的人也有父母啊
而和他們父母一樣年齡的老人
就仆倒在他們的刀槍下
那些手持刀槍的人
也有兄弟姐妹呵
而這么多鮮亮的年輕人
就像油燈一樣被他們吹滅
還有那些不懂事的孩子
瞪大迷惑不解的眼睛
猜不透這些手持刀槍的人
為什么像豺狼一樣兇殘
不懂事的孩子們呀
被一顆顆子彈炸裂了頭顱
那一刻 有的孩子
小嘴還噙著母親的奶頭
他們——手持刀槍的
哪里是人呢
他們不是人
不是人!
他們是一群畜牲
是畜牲都不如的一群
這座慘遭洗劫的城市
鮮血成河淚流成河
記住這個罪惡的屠殺吧
記住這個悲慘的日子吧
悲慘和罪惡
深深鏤刻在33萬架白骨之上
誰想逃避罪惡
只能是罪上加罪
讓陽光撫平傷痛
讓鴿哨慰藉魂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