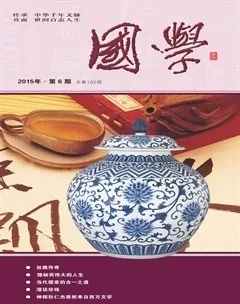白衣飄飄的年代
子不語
中國歷史上文人的幸福感哪家強?
有人會說是唐,李白寫個詩,龍巾拭吐,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這種待遇,幸不幸福?
有人會說是宋,柳永搞個讀者見面會,朝底下喊:大家都說說在什么地方能聽到我的詞呀?底下喊成一片:有井水的地方,就有柳詞。這種一呼百應,幸不幸福?
還有人會說是晉,大家見面就喝喝酒吹吹簫磕磕五石散,磕嗨了就赤身裸體地跑出去:這天地都是我的房子,這房子都是我的衣服,你們怎么都鉆我衣服里來了?這種自由奔放,幸不幸福?
幸福感是一種很玄的東西,不像經濟民生水平那樣可以找到具體量化的指標。況且文人團體又是個性特別強烈的一群人,要找到一個適用于大部分人的指標恐怕會眾口難調。當然,從文學史角度而言,一般認為,浪漫主義開始復蘇的魏晉南北朝,以及受其影響頗深的唐與宋,是中國歷史上文人最富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時代。但畢竟想象力和創造力決定的是文人的作品,而不是他們的幸福感。
始皇帝以法家治天下,秦亡后漢高祖尊黃老,文景兩朝繼之。但這畢竟都是短之又短的歷史時期。至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察舉制選拔官吏,開始以中央集權的力量駕馭文人的思想。從此文人的命運便與龐大的帝國捆綁在一起,每個文人都被努力吸納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而非獨立的個體。維持長達兩千年之久的文官制度,放眼世界都是一個奇跡。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文人創作中對于個性的表達,往往都是基于一種對抗的目的而非順應時代的大趨勢。所以當漢亡之后,集權統治出現暫時的松動,憤世嫉俗的竹林七賢就一下子可以把這種對抗推到極致。后來隋文帝的打壓沒有消滅這種對抗,唐高宗的自信又給予這種對抗一段繼續生長的空間,所以這種浪漫主義才得以延續下來。但這,一定不是統治階級需要的社會主流。
這就塑造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即使在中國文學史最璀璨的頁數上,那些最偉大的文學家統統混得很慘。最為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這些偉大的作品,在當時的視角下統統是非主流。
李白最為崇拜的二謝——謝眺與謝靈運,統統都不到中年就死于政爭;李白自己只被玄宗欣賞了一年就拋離京城,晚年更因為站錯隊伍被發配夜郎;杜甫干脆就一輩子都沒如意過,每天發著各種各樣的牢騷,不是“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就是“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司馬光若不是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貶到洛陽,不會有那么多閑工夫琢磨他的《資治通鑒》;蘇東坡若是能留在京城做官也不會跑到赤壁去念兩句“千古風流人物”;有井水的地方就有的柳詞,其中又唱出三變先生多少的辛酸與失意,“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
那有沒有文人真正能夠主宰思想潮流的時代?有,在先秦。
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完成過真正意義上的統一,松散的政治體制下文人為自己的理想而活著。那未必是一個文采飛揚的時代,卻是一個能產生如此多思想流派,并能自由爭鳴,由文人的意愿去主導政治主張的時代。
當我們回憶孔子在衛靈公面前的灑脫,回憶孟子在梁惠王面前的譏誚,回憶荀子講學于齊、仕宦于楚、議兵于趙、議政于燕、論風俗于秦的博學,哪怕回憶韓非子那句兩千多年來我們仍沒有做到的“君無為,法無不為”,我們都會深深地被那個時代的兼容并蓄所震撼。
這才應該是文人幸福感最強的時代。這也是一個奇跡——在一個沒有印刷術、沒有紙張的時代,靠笨重的木簡記載、傳播的文字,能取得如此大的影響力,并有如此大量的典籍流傳至今,足以證明那個時代的人,對于文字、思想的看重與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