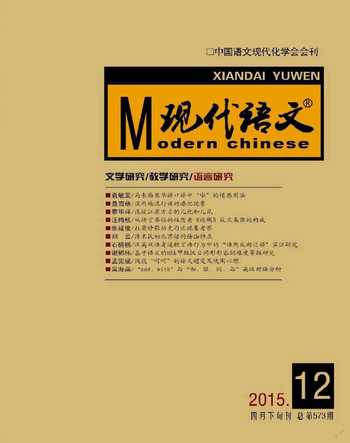基于福柯的微觀權力論看《牡丹亭》譯者對隱性情態意義的顯性重構
摘 要:基于微觀權力的非物化和去中心化等特征,本文對翻譯語篇(《牡丹亭》許淵沖、許明譯本)中的情態顯化翻譯行為進行人際權力距離角度的闡釋,以原文與譯文情態動詞類型分布、量值分布和使用頻率的數據對比為基礎,從譯者對情態動詞的選擇和添加分析情態的顯性重構對中國傳統家庭中“長幼輩分、男女性別和主仆階層”三方面的人際微觀權力關系的突顯。譯者對隱性情態意義的顯性重構體現了翻譯過程中以及中國傳統家庭作為微觀社會中權力與話語的互動。戲劇文學英譯過程中譯者對隱性情態的顯性重構行為揭示了中國傳統社會基層不同于西方社會的微觀權力關系,對提高跨文化可接受度并推動中國古典戲劇和中國傳統文化走向海外英語國家具有促進作用。
關鍵詞:微觀權力論 情態 《牡丹亭》 人際權力關系 顯性重構
一、引言
說到權力,傳統上的概念是以統治權力為核心的。福柯(Foucault,20世紀中晚期法國著名哲學家)基于后現代的理論立場,對這種宏觀權力學進行了批判性分析和解構,建立了去中心化的、非物化的、相對主義的微觀權力學思想。福柯微觀權力論的觀點之一是權力的去中心化,“權力是彌散性的,它彌散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劉樹奎、劉芳,2013:64)。在福柯看來,權力不只存在于統治權力為核心的行政場所,“它也普遍存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傳統習俗和閑談碎語等等之中”(張之滄,2005:45),權力在社會生活甚至家庭生活的每個角落都存在,呈現非中心化的彌散性分布而不是以政府權力為核心的中心化分布。微觀權力論的這種去中心化思想使權力研究者的目光從國家政府機構之類的宏觀權力中心轉向社會邊緣、社會底層或基層,比如福柯的研究對象包括瘋人院、監獄、修道院等邊緣實體內人際的微觀權力關系。福柯還把這種權力觀引入了話語分析,認為話語始終是與權力及權力運作交織在一起的,并指出一切事物都可以歸結為兩樣東西:權力和話語。(辛斌,2006:3)
本文考察情態英譯話語所反映出的人際微觀權力及其跨文化意義,以《牡丹亭》譯本(許淵沖、許明,2009:12~23、170~180)為話語語料分析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家庭生活對話語篇,揭示譯者對漢語隱形情態意義的顯性重構在展示中國傳統家庭這個微觀社會中人際權力關系的作用以及在提高跨文化可接受度方面的作用。之所以聚焦情態來展開權力與話語分析,是因為情態動詞具有表達人際意義和主觀態度的功能,是日常生活人際交談中“傳情達意和使人做事”必不可少的功能詞,能夠體現說話者的身份和權威。
《牡丹亭》這一經典劇目中,杜麗娘在“足不出戶”的封建禁令下囿于家中,連后花園都少有涉足,因此絕大多數劇目場景和對話都發生在家庭內部和家庭成員之間,對話中所反映的人際權力不是傳統概念上的中心化的國家核心權力,而是非中心化的社會邊緣或基層的微觀權力。選擇《牡丹亭》曲詞原文及其英譯本對情態表達進行漢英話語對比和微觀權力分析,可以揭示在完成情態意義跨語言轉換的過程中劇中角色人際權勢關系對譯者選詞決策行為的支配及譯者對家庭成員間人際權力關系的感知、重塑或再現,突顯翻譯過程中及微觀社會中權力與話語的支配和被支配關系。
隨著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國內外的巡演熱映,該舞臺劇曲詞的字幕英譯對海外觀眾理解該劇以及了解中國文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當時歷史背景下,劇中人物的人際權勢關系是傳統中國文化的關鍵組成部分,如何通過恰當的英譯選詞策略促進原文情態意義的跨文化傳遞對幫助海外觀眾理解該劇的矛盾沖突及該劇的社會意義相當重要。中國傳統家庭的成員之間那種微觀權力關系與西方家庭有著跨文化上的不同,譯者對情態措辭的選擇有助于海外觀眾了解中國傳統家庭作為微觀社會在成員互動中所展示的層級性權力關系,這對理解劇情沖突和情節發展有著重要的輔助意義。因此從微觀權力論角度對《牡丹亭》的情態英譯進行考察,對促進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具有實際作用。分析譯者對隱性情態意義的顯性重構既具有人際意義,也具有跨文化對外傳播意義。
本文對翻譯語篇(《牡丹亭》許淵沖、許明譯本)中的情態英譯話語進行微觀權力角度的考察,以原文與譯文情態動詞類型分布、量值分布和使用頻率的數據對比為基礎,從長幼輩分、男女性別、主仆階層三方面的人際權力關系,分析譯者對原文隱性情態意義的顯性化在反映劇中人際權力距離和向海外傳遞中國傳統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
二、微觀權力的特征及情態動詞的分類
微觀權力除了有去中心化的彌散性特征之外,還有非物化特征。對福柯來說,權力不是物而是“一種關系”(陳炳輝,2002:86)。權力關系是處于流動的循環過程中,具有相對性和不確定性。傳統的宏觀權力觀把權力看成物,依據權力在誰手里不在誰手里而區分權力的擁有者和權力的服從者。福柯的權力觀認為擁有權力與否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此情境中的權力擁有者可能是彼情境中的權力服從者,權力是流動的,依據情境中的人物關系而定,具有相對性。因此,本文依據《牡丹亭》劇中的當時情境,區分占權力上風者和占權力下風者,而不是區分權力擁有者與權力服從者,以體現微觀權力關系的相對性和非物化特征,體現權力是“流動性的場”這樣一個概念,在這一“場”中的角色是否占上風,取決于其交手的對象。本文考察的是基于《牡丹亭》臺詞的“話語的場”,通過劇中角色的會話及其英譯語篇考察話語與權力的互動,不是將權力當作自上而下的二元單向直線關系,而是當作多元交錯的網狀關系,因為“權力是通過一個像網絡一樣的組織來行使的”。(Foucault,1980: 98)
情態的主觀性特征決定了情態話語的運用可以顯示說話者的態度、地位和身份。情態形式的選擇不僅暗含說話雙方的人際距離,而且表明他們之間權力、身份和地位的差別 (Eggins,1997:98)。由于情態運用的對比可以顯示社會地位的對比,研究原文中說話人的情態選擇并對比譯文中譯者的情態選擇,可以體現譯者的選詞行為中基于跨文化傳播意識而對劇中人際權勢關系進行的突顯,以及權力因素對英譯情態措辭的制約。
關于情態的分類,基于情態專家Palmer (2001)的跨語言情態研究,可將之分為事件情態(Event Modality)和直陳情態(Propositional Modality):事件情態又分為能動型情態(Dynamic Modality,表能力和意愿,本文稱之為能愿型情態)和道義型情態(Deontic Modality,表責任與義務,本文稱之為責任型情態),直陳情態則包括認識型情態(Epistemic Modality)和實據型情態(Evidential Modality),都表示可能性判斷,但英語中只有認識型而無實據型情態(賴鵬,2005: 322~327)。因此下文將區分“能愿型情態、責任型情態和認識型情態”三種情態類型對《牡丹亭》原文及其譯文中的情態形式進行類型分布和使用頻率方面的統計和對比,基于情態量值的劃分探究情態形式的選擇和添加背后體現的社會地位意義和人際權勢關系。
本文選擇《牡丹亭》中《訓女》與《詰病》兩出中的曲詞對白,分別對原文和譯文所選用的情態動詞類型、頻率及情態量值進行統計。原文中沒有用到情態動詞卻傳達出的情態意義在本文中稱為隱性情態意義,對應的譯文中如果出現情態動詞則視為譯者對隱性情態意義的顯性重構。所選的兩出劇目是在未細讀全書各出劇目譯文的情況下隨機選擇,選取標準是包含杜父、杜母、杜麗娘和丫鬟春香幾個主要角色的對白的劇目。《訓女》中包含杜父、杜母與杜麗娘三人之間的對白,《詰病》中包含杜母與丫鬟及與杜父之間的對白,統計數據分別制成表1和表3。通過這些情態數據可以顯示中國傳統家庭這個微觀社會中長幼輩分之間、男女性別之間、主仆階層之間的人際權力距離。
三、譯者對情態的顯性重構及其體現的長幼輩分之間的微觀權力關系
福柯在《話語的秩序》中首次把權力理論引入話語分析。他認為話語從來不是自足的,權力以日益精致的程式形塑了話語(呂振合、吳彤,2007:137)。本節考察《牡丹亭》譯者對情態類型和情態量值的選擇如何體現杜父、杜母和杜麗娘三者在這個家庭微觀社會之中輩分權力上的等級差異。譯者對中國傳統家庭中權力等級關系的感知形塑了翻譯話語,權力以潛在形式影響了譯者對情態動詞的選擇、添加或者說重構。
表1:從原文和譯文中杜父、杜母和杜麗娘對三類情態動詞及其不同量值的使用頻率
看輩分間的微觀權力關系
情態
類型 能愿型情態
(表能力和意愿) 責任型情態
(表責任和義務) 認識型情態
(表推測和判斷)
情態
量值 高值 中值 低值 高值 中值 低值 高值 中值 低值
漢英
對比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杜
父
3
2
6
1
1
3
杜
母 1 1 2 1 2
杜
麗
娘 1 1 3 1
注:未填寫的空格表示統計數為0;本表情態數據統計自《牡丹亭》中《訓女》一出,不包括開場獨白和尾聲(集唐詩)。
從表1可以看出,在《牡丹亭》的《訓女》一出的原文中出現顯性情態動詞很少(三人加起來共4處用到情態動詞),譯文中出現的絕大多數顯性情態動詞是譯者添加的(譯文的三人對白中共出現25處)。原文中顯性情態動詞較少出現,可能是因為戲曲唱詞和漢語古文中慣有的省略。即便如此,國內讀者基于對中國當時社會文化和對漢語的熟知也能明顯體會到文字背后的隱性情態意義和人際權力距離。但譯者所面對的是不太了解中國文化背景的海外觀眾,為了使劇中角色之間的權力等級差異明晰化,譯者對自己感知到的隱性情態意義進行了顯性重構,添加使用了20余個情態動詞,這種顯性添加從跨文化角度來說能更有力地傳遞人際權力關系。
在原文中,杜父只有2處使用了情態動詞(都是表示中值責任型情態),但在譯文中杜父共在14處使用了情態動詞,其中10處用于表責任型情態(71%),4處用于表認識型推測(29%)。譯者為杜父表責任型情態的語言所添加的8處情態動詞中有3處是表高值情態(超過三分之一),4處表中值情態(達二分之一),表低值情態的只有1處。Martin(1992)指出,地位高者趨向于運用較高量值情態(陳其功、辛春雷,2005: 7)。譯者在杜父的言語中大量添加了與他的社會角色地位相符的高值和中值責任型情態詞,向海外觀眾凸顯了杜父在家中的權威,在權力關系中他屬于占上風者。譯者翻譯杜父表高值責任型情態的3處所添加選用的情態形式均為“how could she/you”(在原文中無顯性情態動詞與could對應),雖然could本身是低值情態動詞,但放在這個表質疑的反問句里卻是表高度否定的非疑問用法(怎么能……?=不能……),相當于轉變成了情態的否定形式。情態的否定形式都相當于高值情態(肖唐金,2011: 98-103)。例如,原文中“女孩兒閑眠,是何家教?”“你白日眠睡(不讀書),是何道理?”分別翻譯成“How could she sleep away her hours?”、“How could you sleep away your hours without reading books on your shelves ?”看似疑問句但不表疑問,而是通過反問表高度否定的語氣,相當于 “She/you shouldnt sleep away your hours”。Should表中值責任型情態,但其否定式shouldnt產生了情態量值上的變化,表示的是高值責任型情態。譯者為杜父添加的高值責任型情態形式體現了情態選擇與說話者身份的一致性,凸顯了杜父作為封建家長在權威方面的高高在上,訓斥女兒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顯示了人際關系的不平等和社會權力距離,為其后的情節沖突高潮(杜麗娘追求愛情自由反抗封建意識形態壓迫)奠定了基礎。雖然以上例句的原文未用情態動詞而譯文用了,看似在情態形式上不對應,但譯文采用了與原文一致的反問句式,反問句在原文中雖不含情態動詞但卻包含了較濃烈的隱性情態意義,譯文從跨語言角度將之與包含情態動詞的英語慣用反問句式相匹配,與原文在情態效果上達到了一致。情態意義的顯性化從跨文化角度向重視平等觀念的海外觀眾突顯了中國傳統社會中以上壓下的輩分差異。
再從女兒杜麗娘對以上反問的應答看這個家庭中父女之間的微觀權力關系。根據Halliday(2000)對言語交換的分析(見表2),杜父的反問雖是問句形式但并不是求取對方答案的真正問詢,而是“非疑用法”,實際表“陳述”(提供信息)。在此劇中杜父的反問實際是陳述了一種價值觀(白日不應眠睡而應讀書),女兒杜麗娘對此的回答是,“從今后茶余飯飽破功夫,玉境臺前插架書”。該句原文無情態動詞但包含隱性能愿情態,譯者添加了顯性情態動詞“will”將之譯為“From now on I will spend more time,to read more books in prose or rhyme”,表現了女兒遵從父親意志的意愿。根據表2,她的應答符合預期,屬于對父親陳述的價值觀的認同,有順應的意愿(“will”),這說明權力關系發生了作用,占權力下風者明白占權力上風者話語中所傳遞的對某一行為的觀點態度(白日不應眠睡,而應讀書),對占上風者所期待的“讀書”這一行為予以承諾(“will”)。這種認同和承諾顯示了杜麗娘小輩服從長輩的不平等權勢關系,在這一話語場中她占下風,屬于權力的服從者。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她可以對父親的反問(=陳述)不給予預期的回答而表示不認同或甚至對父親提倡的價值觀予以抵觸,見表2。但父女對白中的言語行為和話論控制顯示出了他們之間的人際社會關系,可見權力關系雙方(占上風者和占下風者)的言語行為受權力關系和會話準則支配,通常表現為符合預期應答模式,因權力的支配關系而較少出現與預期相左的應答。
表2:言語交換與應答模式
交換物 言語交換 發起談話 預期應答 與預期相左的、任意的、其它可能的應答
貨品或
服務 供(give) 主動提供(offer) 接受 拒絕接受
求(demand) 命令、要求(command) 承擔做某事 拒不做某事
信 息 供(give) 陳述 (statement) 認同 不認同或予以抵觸
求(demand) 問詢 (inquiry) 回答 不回答或否定性回答
(Halliday,2000:69)
在這一場的曲詞/對白的英譯中,父親使用責任型情態而非能愿型情態,女兒使用能愿型情態而非責任型情態。譯者在譯文中為了體現封建時代的父女關系而添加了原文中不曾出現的情態動詞,并且為劇中各人物添加情態動詞的類型、頻率和量值各有不同,以此顯示出人物間的人際不平等關系。這種對情態動詞的顯性添加和類型選擇傳遞的是社會權力距離,為觀看《牡丹亭》的外國觀眾了解中國當時的社會背景起了一定作用。如:譯文中杜麗娘作為女兒,使用到情態動詞的地方共5處(見表1),其中4處表示能愿型情態(高值和中值),1處表認識型推測,沒有用到任何表責任型情態的情態動詞,情態類型體現了其作為占權力下風者的身份。原文中杜麗娘只有1處用到情態動詞,譯文中的多處能愿型情態動詞為譯者所加,分別用于體現杜麗娘作為女兒因服從父母所作的承諾、為父母做事的意愿和報答父母的能力。這種情態類型的分布符合李杰(2005:49)所指出的,權勢較低者通常選擇能愿型情態模式,不平等地位關系中更加有權勢的發話人才選擇并使用責任型情態模式。譯者對所添加的顯性情態動詞的情態類型的選用源于權力與話語的互動,清晰地顯示了父女雙方的輩分差異和權力不平等關系。
四、譯者對情態的顯性重構及其體現的男女性別之間的微觀權力關系
譯文中杜父表責任型情態除使用情態動詞的反問句式表高度否定的語氣情態之外,譯者還多次添加使用了表責任的中值情態動詞(should),如“Fair maidens should be good in reading and writing”(原文為:看來古今賢淑,多曉詩書);a wife at home should do her best(原文為:有一日把家當戶);Your mom should tell you what to do(原文為:道的個為娘是女模),以對原文隱性責任型情態的顯性重構來突顯他作為父親對女兒的要求、作為丈夫對妻子的要求,向海外觀眾傳達了當年中國社會背景中父女在權力上的不平等關系和夫妻在性別上的不平等關系,從家庭微觀中的男女不平等折射了當時社會宏觀中的性別不平等。
根據表1中的數據以柱形圖統計譯文中各角色使用情態類型的分布和頻率,得圖1如下。
從圖1中可看出,譯文中杜母使用情態動詞的頻率遠低于杜父,表責任型情態僅3處(杜父的使用頻率為10),且多為中值責任型情態,均表現為對女兒的忠告,體現了當時女性比男性更卑微的身份,如“Seeing the front,you should know the rear,youd try to understand and feel what your father has to reveal(原文為:兒呵,爹三分說話你自心模)”,要女兒遵從父親的意志,體現了當時社會背景中的性別差異意識和子從父、妻從夫的權力不平等意識。使用責任型情態動詞的頻率對比可以體現對話雙方的權力關系,從圖1所統計的譯文中杜父與杜母對責任型情態動詞的使用頻率對比(10:3)、杜父和女兒對能愿型情態動詞的使用頻率對比(0:4)可以看出譯者的顯性化重構傳達了中國傳統社會中在權力關系上的性別不平等,這對于重平等的西方社會的觀眾來說,具有促進跨文化顯示度并幫助理解中國古典戲劇劇情發展的作用。
結合表1和圖1,可見在該劇目原文中未用到任何表認識型情態的顯性情態動詞,但譯文中杜父、杜母和杜麗娘分別使用了4、3、1次。這種表推測的情態動詞在該劇目譯文中的使用,多數是表達杜父和杜母對沒有兒子的遺憾、對將來是否會有兒子的推測和杜麗娘對父母將來會有兒子的祝愿。如,杜麗娘的祝酒詞中對父母說:Though I regret to have no brother, a later son would bring joy to father and mother (原文為:祝萱花椿樹【喻父母】,雖則是子生遲暮,守得見這蟠桃熟【蟠桃喻遲生的兒子】),原文無情態動詞,但譯文中添加了符合英語表達習慣的顯性情態動詞would。杜父因為沒有兒子因而對女兒寄予厚望,望其飽讀詩書光耀門楣,其在臺詞中的表達為:中郎學富單傳女,伯道官貧更少兒!這句臺詞顯示了對沒有兒子所感的遺憾,譯者轉譯為:A daughter may transmit my fame,since I have no son to tarnish my name. 該譯句中添加了表示可能性推測的低值情態動詞may,傳達了杜父對女兒傳承自己的確定性不高,以及對沒有兒子傳接衣缽的無奈心理。杜母則寄望于女兒嫁個好女婿,她對杜父說道:相公休焦,儻然招得好女婿,與兒子一般,“做門楣”(即“光耀門楣”)古語。譯文為:Dont worry,my lord,a worthy son-in-law is as good as a son.He will glorify the house,as ancients say.譯文中添加了表示肯定推斷的顯性情態動詞will,表達了杜母對未來女婿的樂觀心理。綜合來看,圍繞“沒有兒子”這個事實,家中三人有關“兒子”和“女婿”的言論,顯示了當時中國傳統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和性別權力不平等的觀念。在重男輕女這方面,東西方有著跨文化的差異,譯者通過添加顯性情態動詞向海外觀眾突顯了中國社會中男女之間的性別權力不平等,有助于英語國家的觀眾理解該劇的劇情和社會意義。
權力是貫穿福柯話語理論的核心要素,他從動態上考察話語出現的背后的權力運作機制以及權力對話語的約束機制(陳長利,2006:127~128)。杜父杜母和杜麗娘之間針對“兒子和女婿”的這類情態話語的出現,體現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權力運作機制。譯者在他們的話語中,對情態動詞的選擇和添加,向海外觀眾揭示了在中國傳統封建體制中男性被賦予比女性更多的權力和價值。
五、譯者對情態的顯性重構及其體現的主仆階層之間的微觀權力關系
如第二節所述,基于微觀權力論,權力不是物而是關系,具有相對性和流動性。這在表3所統計的情態類型及量值的漢英對比數據中也得到了清晰體現。雖然在表1的統計中基于性別差異,杜母相對于杜父是占權力的下風,使用的責任型情態動詞遠少于杜父,但在表3的統計中,杜母相對于丫鬟則是處于權力的上風,使用的責任型情態動詞多于丫鬟(丫鬟未使用責任型情態動詞),而且也通過高頻并高值使用認識型情態動詞的反問句式表示對丫鬟的詰問和責備,顯示了主人的高高在上和仆人的低勢地位。杜母在不同的話語場中其權力角色的轉變通過情態動詞的使用得以展示,印證了微觀權力論的一個重要視角,即,權力關系不是絕對的,話語與權力是互動的。具體分析如下。
表3:從原文和譯文中杜母與丫鬟對三類情態動詞及其不同量值的使用頻率
看主仆間的人際權勢關系
情態
類型 能愿型情態
(表能力和意愿) 責任型情態
(表責任和義務) 認識型情態
(表推測和判斷)
情態
量值 高值 中值 低值 高值 中值 低值 高值 中值 低值
漢英
對比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杜母 1 1 2 1 7
丫鬟 2 2 1
表3是對《詰病》一出中情態使用類型的統計,該出劇目包含杜母的獨白和杜母與丫鬟的對白。由于杜麗娘因情生病,臥床不起,杜母責問丫鬟并怪罪于她。從表3可看出,在原文中杜母和丫鬟都未使用任何顯性情態動詞,但在譯文中丫鬟則總共使用5次(但沒有一次是責任型情態動詞),其中4次是能愿型情態動詞,表示能力或愿意做某事的傾向(惠及對方即占權力上風者的動作),顯示出其在權勢上的低位姿態。而杜母的言語中譯者為其添加了表責任型情態的顯性操作詞(3次),體現了她作為母親和作為主人對女兒杜麗娘和丫鬟春香在責任上的要求。譯者也為杜母添加了能愿型情態動詞的使用(2次),但結合其句中所說欲行之事(“punish”=懲罰),不是惠及對方而是損及對方(權勢低者),因此能愿型動詞在這種情況下的使用非但不表示權位低,而是權位高的體現。如:“See how I shall punish your evil tongue”,原文為“打你這牢承,嘴骨棱的胡遮映”,并無情態動詞,但譯文中較高強度的能愿詞“shall”的添加,恰當地表現了原文中杜母生氣而欲責罰丫鬟的情態,體現了主仆之間階級權力不平等的人際關系。
譯者還為杜母言語添加了7處表高值認識型情態的操作詞(表可能性),使用的句式多數為“How could she”,如“How could she have fallen ill since your service?(原文為:才著你賤才服侍他,不上半年,偏是病害);How could she grow so slender(since your service)?(原文為:她一搦身形,瘦的龐兒沒了四星)”,該句式在譯文中為反問句式表詰問和否定,意為“她怎么可能你才伺候她半年就病倒了?她怎么可能變得這么瘦?”,即:“若不是你服侍得不好她不可能病倒或變瘦”,顯示了她作為主人對丫鬟的高度責備。表可能性推測的低值情態詞could在該反問句中的用法等于高度否定的語氣(couldnt = 不可能),否定句式中的低值情態詞實際轉化成了高值情態,表示對可能性的認識型高值判斷。譯者在杜母言語中添加的另一表認識型高值判斷的顯性情態動詞是must(肯定),如“It must be you who have induced her to become thus(原文為:都是[你這個]小奴才逗他)”,表示“肯定是你導致這一切”,同樣是體現對丫鬟的責備。可見,原文表示高度責備但未用情態動詞(屬于隱性情態意義),譯者添加了顯性情態動詞而使其更符合英語的情態表達習慣,便于海外觀眾清晰地判斷劇中角色人際間的社會權力關系,為理解之后的情節沖突做鋪墊。這是譯者出于跨語言和跨文化考慮而對感知到的隱性情態意義和權力關系進行的顯性重構。
譯者對杜母和丫鬟這兩個角色話語中情態動詞的添加和選擇,使杜母從之前夫妻對話話語場中權力的占下風者(服從者)轉換為主仆對話這一話語場中權力的占上風者(支配者)。這種權力角色轉換可以體現福柯的觀點:微觀權力不像傳統權力是二元的、單向度自上而下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而是多元的、多向度交錯互動的網,“權力以網絡的形式運作著,個人不僅流動著,而且總是既處于服從的地位又同時運用權力”(福柯,1999:28)。譯者對情態動詞的添加和對情態動詞類型的選用,既受到從原文中感知的權力因素的影響,又在譯文中體現了權力的流動,展示了話語與權力的互動。
六、結語
概而言之,不平等交際中反映出權力與義務的不對稱性(丁建新、廖益清,2001:305),這在《牡丹亭》劇中幾個人物角色對責任型情態動詞的使用頻率上得到了反映。福柯認為,權力總是通過話語去運作,話語建構社會(辛斌,2006:4)。從表1上下兩輩人話語中對情態類型和量值的使用頻率體現出當時中國社會中長幼輩份和男女尊卑在權力等級上的差異:父母多使用責任型情態(表示對方義務),女兒則多使用能愿型情態(表示服從對方權力);男性(杜父)使用責任型情態動詞的頻率遠遠高于女性(杜母)。從表3主仆二人話語中對情態類型和量值的使用頻率則體現出各自身份的差別和階級權力等級上的差異:杜母所用情態多強調丫鬟的義務。這些在原文中并不一定由顯性情態動詞體現,譯文中大量添加的顯性情態動詞是譯者基于從原文中感知的隱性情態意義及當時的權力等級狀況進行的顯性重構。情態動詞的選擇和使用頻率的高低因而不是任意的,而是權力地位差異的體現,彰顯語言的人際功能(季紅琴,2011:230)。從微觀權力論角度來分析翻譯語篇中的情態話語,權勢和地位在闡釋譯者對情態動詞的選擇和添加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原文劇中角色社會權力關系的不平等決定了譯者對情態動詞類型和量值的選擇,以添加不同類型的情態動詞(責任型、能愿型或認識型)反映出人物角色之間的權力不平等關系,從跨文化角度傳遞了文化背景含義和社會權力等級含義。另外,從跨語言差異角度來解釋譯者的情態添加行為,英語主要通過顯性情態動詞的使用來反映說話者與聽話者之間的人際權力關系和社會距離,而漢語古文唱詞中顯性情態動詞常被省略,因而常表現為隱性的情態意義,在譯文中有必要間接經由譯者的顯性重構向譯語觀眾傳遞劇中角色間的人際關系。譯者基于對本族社會文化中的權力感知進行情態重構,情態形式的恰當選用和添加可以突顯當時的社會權勢背景并有助于劇本的跨文化溝通。
微觀權力論關注社會的不平等和社會基層的權力關系。福柯指出,反抗與權力是共生的、共同存在的,只要存在著權力關系,就會存在反抗的可能性(岳進,2008:72)。譯者通過情態動詞的添加,凸顯了社會基層的中國傳統家庭中杜麗娘和丫鬟的弱勢地位,反襯杜父作為封建家長的強勢地位。這種權力不平等的反差為其后情節中杜麗娘追求愛情和自由、反抗封建意識形態的禁錮起了強有力的鋪墊作用,有助于不了解中國文化的海外觀眾理解情節的沖突高潮并更好地欣賞中國戲劇。
本文基于微觀權力論對情態英譯話語的考察,著眼點不是探究翻譯技巧,而是以翻譯語篇為語料分析話語與權力的互動。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揭示翻譯原則,也沒有探究該譯本在“信達雅”等翻譯原則上的表現,只著重考察情態話語方面譯者的選詞和重構所體現的權力因素和人際距離。
“毛細血管”狀分布是福柯權力觀點中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他認為眾多權力形式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橫斷面,社會的點點滴滴是權力的實質所在(陳長利,2006:128)。中國傳統家庭作為社會的基層體現了微觀權力的所在,因此對《牡丹亭》杜府家中日常生活的各場會話及譯者對會話重構后的情態話語進行分析,可以體現微觀權力的如下視角:權力是流動的關系而不是具體的物,是多元多向相互交錯的網狀關系而不是二元對立自上而下的單向直線關系,是毛細血管狀伸向社會各個角落及底層而不是僅存在于國家政府、法律機關等核心機構。這些都反映了微觀權力的非物化、去中心化、彌散性以及相對性特征。上至君主統治者,下至平民百姓,每個人都身處權力之網中,每個個體都是權力的實踐者,同時也是權力所操控、支配的對象(劉樹奎、劉芳,2013:64),即,在不同的權力交鋒的話語場中,每個個體都依據話語交鋒的對象而或處于權力的上風,或處于權力的下風。權力的流動以及話語與權力的互動不但體現于人物在各場景的會話中,也體現于譯者在重現各會話時的情態選詞決策之中。
參考文獻:
[1]Eggins,S & D.Slade.Analyzing Casual Conversation[M].
London:Cassel,1997.
[2]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ume I:An Introduction
[M].New York:Vintage,1980.
[3]Halliday,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Second
Edition)[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0.
[4]Palmer,F.R.Mood and Modality(Second Edition)[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5]陳炳輝.福柯的權力觀[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2,(4).
[6]陳長利.論福柯的三維話語理論[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2006,(3).
[7]陳其功,辛春雷.廣告英語語篇的人際意義及其體現的勸說功能
[J].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2005,(3).
[8]丁建新,廖益清.批評話語分析述評[J].當代語言學,2001,
(4).
[9]福柯.必須保衛社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0]季紅琴.圣經.語言情態的人際意義解讀[J].外語教學與研究,
2011,(2).
[11]賴鵬.情態的概念范圍和跨語言研究——語氣與情態評介[J].
現代外語,2005,(3).
[12]李杰.情態的表達與意識形態的體現[J].外語學刊,2005,(4).
[13]劉樹奎,劉芳.福柯的權力理論與權力哲學[J].前沿,2013,
(3).
[14]呂振合,關彤.福柯的微觀權力觀[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2007,(2).
[15]肖唐金.情態動詞的值的變化及意義[J].貴州民族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2).
[16]辛斌.福柯的權力論與批評性語篇分析[J].外語學刊,2006,
(2).
[17]許淵沖,許明(譯)牡丹亭(Dream in Peony Pavilion)[M].
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9.
[18]岳進.權力視野下的別樣人生[J].湖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08,(1).
[19]張之滄.福柯的微觀權力分析[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5,(5).
(賴鵬 廣東廣州 中山大學外語教學中心 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