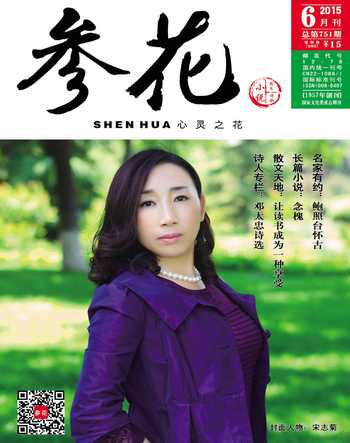下學(xué)而上達(dá)
——淺談“學(xué)而時(shí)習(xí)之”與論語(yǔ)的開(kāi)端
◎陳凱麗
下學(xué)而上達(dá)
——淺談“學(xué)而時(shí)習(xí)之”與論語(yǔ)的開(kāi)端
◎陳凱麗
《論語(yǔ)》以“學(xué)而時(shí)習(xí)之”作為開(kāi)篇首句,以《堯曰》的最后一句“不知命,無(wú)以為君子也”為全篇結(jié)句,這之間隱含著“學(xué)”、“習(xí)”、“命”、“君子”的一個(gè)內(nèi)在邏輯,是一個(gè)下學(xué)上達(dá)層層遞深的情理結(jié)構(gòu)。在某種意義上,《論語(yǔ)》彰顯的是一個(gè)“文化生命”的深度與高度,是作為一個(gè)民族的文化生命之肉身化表達(dá)。
一、學(xué)悟、時(shí)察、行知:主體性覺(jué)悟的統(tǒng)一
(一)“學(xué)-覺(jué)”的內(nèi)涵啟發(fā)
從孔子教學(xué)的內(nèi)容、方式上理解,“學(xué)”既有學(xué)習(xí)知識(shí)的意義,較多的是學(xué)習(xí)做事為人修身之學(xué);又側(cè)重于道德與修養(yǎng)的培養(yǎng),認(rèn)為好學(xué),首先在如何為人:即孝對(duì)父母,懷悌于兄, 忠誠(chéng)對(duì)君,信義于友;其次在如何修身:見(jiàn)賢思齊,不遷怒, 不貳過(guò), 不崇尚追求物質(zhì)生活的享受,而崇尚追求人性的完善、道德修養(yǎng)的提高。
(二)“時(shí)習(xí)-行知”的動(dòng)態(tài)延伸
“時(shí)”當(dāng)為“時(shí)時(shí)、每時(shí)”之意,是一種不間斷的切實(shí)之行,一種動(dòng)態(tài)延伸的無(wú)有間隙。學(xué)習(xí)的內(nèi)容無(wú)處不在,學(xué)習(xí)的方式豐富多樣,學(xué)習(xí)的時(shí)空隨時(shí)隨地。而“習(xí)”一般被認(rèn)為是“誦習(xí)、傳習(xí)”,《爾雅》曰:“貫, 習(xí)也。”轉(zhuǎn)注之習(xí),亦貫也。時(shí)習(xí)之習(xí), 即一貫之貫。貫主行事, 習(xí)亦行事。故時(shí)習(xí)者, 時(shí)誦之, 時(shí)行之也。
二、“說(shuō)”、“樂(lè)”、“君子”:內(nèi)在的邏輯結(jié)構(gòu)
(一) 由“說(shuō)”而“樂(lè)”進(jìn)而“子”之平和
“說(shuō)”是“習(xí)”的結(jié)果,而“習(xí)”有所“說(shuō)”,才能說(shuō)是學(xué)有所成。關(guān)于“有朋”的解釋?zhuān)械淖g者認(rèn)為其是“友朋”,包含著與孔子志同道合的人、朋友和孔子的弟子。但不管是哪種解釋?zhuān)瑥摹皩W(xué)而時(shí)習(xí)”到“有朋自遠(yuǎn)方來(lái)”、由“說(shuō)”而“樂(lè)”, 是一個(gè)遞進(jìn)并且不斷前行的過(guò)程。
或“說(shuō)”或“樂(lè)”或“君子”之平和
“人不知而不慍”是己與天關(guān)系的體現(xiàn),《禮記·中庸》有言, “正己而不求于人, 則無(wú)怨。上不怨天, 下不尤人。”《論語(yǔ)·憲問(wèn)》說(shuō)道,“子曰:‘不怨天, 不尤人, 下學(xué)而上達(dá)。知我者其天乎’”,兩者都是內(nèi)心平和的過(guò)程。此處與己、與人、與天的關(guān)系處理亦是并列之結(jié)構(gòu)。
(二)“說(shuō)”統(tǒng)“樂(lè)”與“君子”之平和
為學(xué)之“說(shuō)”不僅貫穿于“有朋自遠(yuǎn)方來(lái)”,而且包含于“人不知而不慍”的過(guò)程,一方面,“有朋來(lái)”是為學(xué)的積極取向,“說(shuō)”進(jìn)而“樂(lè)”;另一方面,“人不知”是為學(xué)的消極取向。在亂世之中,只有內(nèi)心“說(shuō)”,才能“不知不慍”,才能保持“君子”之平和。由此可觀,“說(shuō)”代表最高境界與為學(xué)過(guò)程的最佳狀態(tài)。
(三)“君子”之平和統(tǒng)“說(shuō)”與“樂(lè)”
“君子”之溫和平柔對(duì)現(xiàn)實(shí)具有理想指導(dǎo)意義,主要體現(xiàn)在“成己”、“成物”兩個(gè)方面。《禮記·中庸》云:“誠(chéng)者, 非自誠(chéng)己而已也, 所以成物也。”經(jīng)常的復(fù)習(xí),進(jìn)而可以得己,可以使朋來(lái)。得己之道,乃悅?cè)葜畱B(tài);成物之中,雜樂(lè)之悠。由此觀之,“學(xué)而時(shí)習(xí)之,不亦說(shuō)乎?”是理想向現(xiàn)實(shí)中的自我反應(yīng);“有朋自遠(yuǎn)方來(lái),不亦樂(lè)乎?”乃理想向現(xiàn)實(shí)的自我反應(yīng)。
(四)“樂(lè)”統(tǒng)“說(shuō)”與“君子”之平和
“君子”之平和是一種心態(tài)基礎(chǔ),有了平和之心,才有“學(xué)而時(shí)習(xí)”以及“有朋自遠(yuǎn)方來(lái)”的可能。“不慍”是“說(shuō)”的基礎(chǔ) 亦是“樂(lè)”得以實(shí)現(xiàn)的根基。這種解讀結(jié)構(gòu)以“樂(lè)”為最高境界,以“君子”之平和為底線,逐步實(shí)現(xiàn)由平和向“獨(dú)樂(lè)”與“眾樂(lè)”的提升。
三、下學(xué)而上達(dá):深邃的哲思
《論語(yǔ)》筆下的君子之道,是人之為人的仁說(shuō),也是為仁由己的概括,其心于自身,動(dòng)全身之固性而終仁,順天而仁,順己為仁,乃人中之人,就幸中之幸。因此《論語(yǔ)》以“學(xué)而時(shí)習(xí)”告示于我們,自由自律方可自成自得;修德修行盡可修己修身。“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是“學(xué)而時(shí)習(xí)”的深層次拓展延伸,當(dāng)然,這也是“有朋自遠(yuǎn)方來(lái)”之后的理想境界。人不知而己達(dá),人不論而己學(xué),是下學(xué)而上達(dá)的成就,《學(xué)而》將其放置在“學(xué)而時(shí)習(xí)之”與“有朋自遠(yuǎn)方來(lái)”之后,實(shí)際上是將前兩者視為它的基礎(chǔ)。學(xué)成則友至,人不知所以己?jiǎn)⒅恰?/p>
(作者系浙江師范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
(責(zé)任編輯 劉冬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