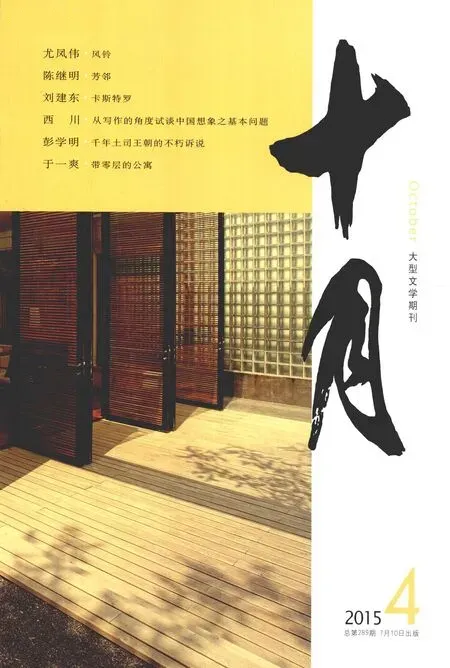女人是會變老的,應該有一個喜歡的事情一直做下去
于一爽
寫作的時間不長,但是年齡已經不小了,自發地創作狀態已經結束,也可以說是江郎才盡,如果曾經還對寫作有過一點點感覺的話,但是反而,現在的愿望更強烈了。年初的時候在南京,半坡酒吧,劉立桿說:女人是會變老的,所以應該有一個自己喜歡的事情一直做下去。他只是隨便一說,因為我們根本就是在喝酒、抽煙、聊天,誰會聊文學呢?文學也不應該充當生活最后的修飾。我并不知道寫作是不是自己喜歡的事情。我總是搞不清自己喜歡什么。但是應該寫下去。因為我正在變老。
像很多人一樣,讀過一些小說,這個世界上的小說太多了,這件事情本身讓人煩躁。雖然不用都看,比如我永遠不會看冰心的《小桔燈》,那么這就證明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書我不用看,但是另外的十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萬分之一,也依然叫人煩躁。我時常感覺,自己已經不會讀小說了。為什么有人寫的那么好,有人寫的連豬狗都不如,甚至連我都不如。我總是情不自禁地跳出閱讀的情感,變成一個躍躍欲試的人。這件事情比之前的煩躁又增加了一分。
出過一本小說集,叫《一切堅固的都煙消云散》,因為已經沒有了當時的心情,也就沒有了繼續談論的基礎。小說里面寫了一些我經歷的或者沒經歷的感情,但對世界的理解都是一樣的——失望。雖然這種失望很多時候并不屬于我。我已經開始對這本書不滿了,并不是出于徹底的謙虛。雖然我以后可能再也寫不出來這全部,以及那些沖動,甚至那種幼稚的失望。小說需要創意,在這本書結束之后我開始慢慢理解里面的樂趣,就像小時候做的數學題。小說的世界是嚴密的。
新書出版之后,我的好朋友昆鳥寫了一篇書評給我,他是批評我的,我有點難過,昆鳥說——我被流行寫作害了。我想他說的流行寫作就是從2000(?)年開始的那種對于生活的向下描寫,認為所有向上都是假的。于是向下成為了時髦、成為了主流,甚至變成了虛假本身。
其實我一直相信一點——雖然趨利避害是人性,但是舍生取義也是人性。就算我只是描寫了向下,但也從不認為向上是假的。只是缺少發現的愿望以及能力,為什么?我也不知道。可能我還不夠老。我還有的是時間對自己失望。
昆鳥說我生活中是一個認同主流價值的人,所以我的寫作是虛偽的。這點讓我十分難過。但也許這正是我希望在寫作中表達的一點:我不相信在我這一代人身上,還有主流價值和非主流價值的區別,甚至連主流非主流本身都在坍塌。人和人都是不一樣的,這也是孤獨找不到出口的原因。我的主流也許在于我太喜歡買包包了。
在我寫作的時候,我是不關心道德的。因為一切都是道德。而只有不準確的才是不道德的。但,這依然不妨礙昆鳥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所有的事情都并不妨礙另外的事情。甚至寫作也不妨礙人繼續變老,變得很沒有意思。
從南京回來之后,我寫了兩篇小說,較短的一篇叫《三人食》改自之前寫的一篇小說叫《熱天午后》,一個熱天的午后,兩個女人在院子里聊天,聊啊聊啊,一個女人告訴另外一個女人我懷孕了,這讓另外一個女人產生了極大的妒忌。接下來事情變得更糟糕,懷孕的女人懷了前夫的孩子,這讓沒懷孕的女人簡直不光是妒忌了。而是恨,不徹底的恨。恨自己連做錯事的機會都沒有。而其實懷孕的女人也恨,恨自身的軟弱之處,前夫一招手她就回來了。
我最開始是想寫一個女人之間妒忌的故事。寫這篇結尾的時候,我正坐在從南京回北京的高鐵上,有一段時間,我總是去南京出差,在高鐵上我就想,那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男人呢,于是在小說最后,我就讓這個男人出現了,接下來,他們三個人一起做了一件事,他們一起吃了一盤炒雞蛋。
寫完炒雞蛋之后我看著減速玻璃外面快速移動的大片中國的農村,我突然覺得這盤炒雞蛋是世界上、古今中外的,最溫柔的炒雞蛋。
較長的一篇叫《帶零層的公寓》講的是兩個男人有事沒事就談論著同一座公寓,甚至他們無法保證彼此談論的是不是這座公寓里的同一個女人。甚至女人死了,他們都還不清楚他們是否都認識她。因為這是一座帶零層的公寓。一個人嘴里的一層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嘴里的二層。但是一層可能就是二層。自始至終,他們誰也不想糾正對方的錯誤。小說源自生活中某些很平常的時刻,比如偶爾和老公走過一個地方,他會突然說——你知道嗎,我對這里曾經非常了解。
就是因為這樣一句話,會讓我十分不適。
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恐怖也已經免疫了。也可以說,喪失了好奇心。《帶零層的公寓》本來是想寫一個恐怖的故事,至少是有恐怖感覺到故事,這種恐怖來自于:一個人死了,但是你無法確認死去的人是誰。很多跡象表明死去的人與你無關,但是這,絲毫不能減輕幸存者的壓力。
就是這樣,我們聊啊聊啊,他們走后,我還收拾了房間,我把他們剩下的酒都喝光了,有時候,我想變成這樣一種人——只認酒,不認人。簡單粗暴。
甚至我想,在未來的某一天,我會寫出這樣一個徹底的人——他只相信一件事情。于是這件事情之外的所有事情都是一種障礙。